[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另一次座谈(这次是在一个讲演厅,开放给香港的大学生),我们三个各自讲“青春的伤疤”。我讲的是我高中时(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全国高中生都穿着日据时期留下的那种军训卡其服),我和一群互不认识的那学校的坏分子,每天傍晚会聚挤在一处黑暗楼梯间,隔着车潮汹涌的马路,偷看对面一幢大楼,某一户人家,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不知什么原因,都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在那小框格里移动,像水族箱里四尾美丽的回游的鱼……
马来西亚女作家则说起她的童年,她的父亲是个烂人,母亲则是这男人的小三,总之她的童年里,父亲极少出现,每次要来那小镇看她们,她母亲就说不出的开心,弄了满桌平时想都不用想的菜肴,空气中都是那种混乱的香气,母亲也会盛装打扮,一脸笑意,那时她和妹妹再怎么调皮,都不会受到责罚。但这样等待的光影记忆,十次有七次,父亲后来又来电说不过来了。母亲则像瞬间枯萎的花,整个奄了。那接下来整个礼拜,她们要把那桌菜,鸡啊鸭啊鱼啊猪肉啊,重覆热过,吃十几顿才吃掉,吃到都快吐了。有一年,她母亲跳机到台湾打工,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人住在那小镇的屋子里。她那时其实还只是小孩子,但要扮演好姐姐的角色。有一个晚上,她们将门窗都锁紧了,但妹妹突然叫她抬头看,上面窗外有个流浪汉,爬上屋前的一棵树上,脸贴着玻璃,目光炯炯盯着屋内看。她的眼神和对方相接时,他也完全不避开,好像知道这屋里没有任何大人。说不定待会他就会想办法撬开窗子进屋来了。她们姐妹俩,害怕到一直尖叫,往卧室跑,把卧室门锁起来。即使两人躲到床底下,还是不断尖叫。她也不记得后来,第二天天亮,她有没有去跟外婆或阿姨说,或是出门有没有瞥一下那树上还有没有那个男人的身影……
很意外的,轮到大陆女作家发言时,她竟然哽咽,甚至啜泣起来。她说她被我们之前的故事深深打动,觉得那真是说不出的忧郁和悲伤。她很简短的说了一些她少女时期的画面,大约是文革时期,他们一些男孩女孩,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离开家,进入一个全是同龄人的群体,那时懵懵懂懂,物质的贫乏和肉体的劳动好像因为躲在这个群体中,没多大感觉。直到有一天,好像是他们这边的年长些的,和另一区的另些青年发生了武斗,好像一个军卡车开回来,所有人脸上都是血污和惊惶的神色,那后车篷里头搬下来的,全是被刀砍断的、或枪械打残了的身躯,有几个好像已经死了……
总之,那次座谈之后,我们三个,好像感情更亲近,更像一个大姐、一个大弟、一个小妹,搁浅在那个那时仍感到强烈“华洋杂处”的前英殖民小岛。有一天,中餐时,马来西亚女作家告诉我们今天是她生日,当晚,这大陆女作家便招待我们,去一间极高极的云南馆子,那每一道菜(什么气锅鸡、过桥米线、牛肝菌、鸡油菌、珊瑚菌……)都好吃翻了,但都贵得不得了,这大姐像中了什么奖一样,乱点了满桌,吃到后来我都心慌了。而她平时看去颇节俭,不像个手头那么宽裕的人,她对马来西亚女作家说:“我是真的把妳当自己妹妹。妳这孩子吃那么多苦,却那么坚强。我们就是该吃好的,尽量吃。”那次那间高级餐馆的镶金筷子、青花瓷盘瓷碗、那啜饮起来舌蕾立即告诉你是极品的普洱茶,给我一个印象:这个大姐有个温暖宽润的灵魂,她是从共和国疯狂贫困的换日线那端走过来的,她对他者所曾经承受过的苦(也许故事化了的),如此易感、认真以对。那是二○○四年底,香港回归七年,台湾刚刚经历过“两颗子弹”阿扁连任的政局动荡。我觉得我们这三个年纪各一截差距的不同小说创作者,眼中各自展开完全不同的,《雾中风景》的公路电影。
另一个下午,我们在荷里活道一间,周遭全坐着老外,连侍者也用英语询问点餐的咖啡屋。当时好像只有这样的老外咖啡里可以抽烟(事实上我们里头也只有我吸烟)。那位香港大学的年轻女助理也一道(她的英文非常强,但普通话说得支离破碎),我记得她说了好几个她大学时女生宿舍里流传的鬼故事。好像还有“有个男子跟他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他的女友掉进河里了,那个男子就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他伤心的离开了这里。过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这时看到有个老人家在钓鱼,可那老人家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他就问那老人家为什?鱼身上没有沾到一点水草,那老人家说:『你不知道啊,这河从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子突然跳到水里,自杀了,为什么?”这一类的脑筋急转弯。但她说完后,大陆女作家深深叹息,说:“珍妮佛,我来香港这么多天,直到今天听妳说了这些鬼故事,才对这地方,真的有了感情了。我本来很不舒服,明明脸不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脸吗?为什么他们在很多场合刻意都要用英文,而且显摆着用英文是更高级这种气场。妳现在说了这些鬼魅啊、恐惧啊的,我才觉得,咱们潜意识是相通的。咱们以前女孩子聚在一起,也猛讲这些鬼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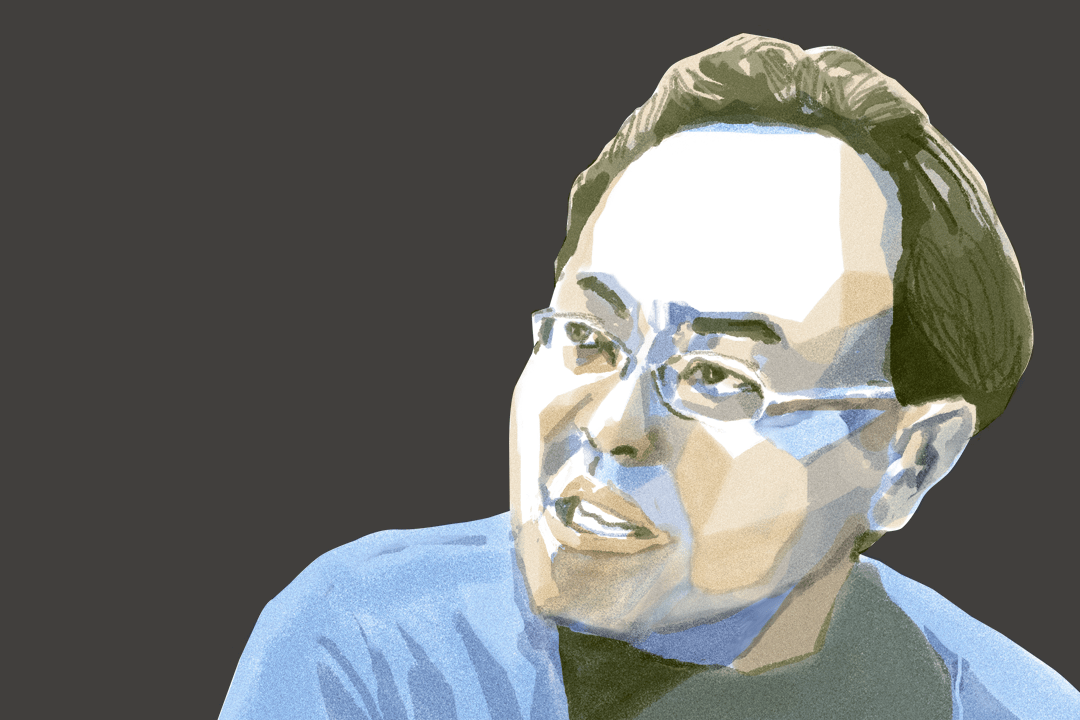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