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我小时候有人帮我算命,说这孩子命里犯水,很容易溺死在水边。这还真的,我大约六、七岁时,有一个冬天,和我们那区全部的小孩,都在结冰的湖面上玩滑冰,或是木箱上绑两铁条当雪橇车,让我哥拉着跑。总之,那个冰啊,结得也不是很均匀,靠岸这一大片,后的像大理石地板,怎么蹬啊跳啊都没事。但靠湖心处的,有些冰层下头结得并不扎实。但有些大孩子是真的玩花式滑水,他们滑行的范围特大,但好像总能不靠近那,像有条隐形的线画着的危险区。我那时啊,也不知怎么了,远远看着一只鸟,蛮大的鸟,头伸进冰层里死了,像个雕像。我就好奇,歪歪趄趄走过去,慢慢离人群。那些小孩的声音远了。就在手将要触到那鸟羽毛还栩栩如生的一刻,哗啦我脚下裂开一个窟窿,我整个掉进去。很难描述那个过程,我水性算好的,但那可是零下十度的冰水啊,在那十分钟或五分钟,我觉得我是在『死』的境界里。岸那端的同伴没有人发现我这儿出了事。我独自在那挣扎啊,张口吐出喝下去的水啊,浮着、手死命扒那裂洞的边沿,一滑下去,往下沉,就是一片静幽幽,周遭全黯只有我这有一道光束的水底世界,我心脏都被回收血液的低温冻得缩起来,发疼啊。我一直恐惧的自言自语:『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事实上,我们那小城,每年冬天,都一定会有几个小孩,在这样冰上玩儿的时候,掉下去,人就没了。”
“后来呢?”我问,但旋即后悔,听这种故事最傻逼的,就是问“后来”;如果那时她挂了,那线在是谁在跟我说这故事呢?
“后来我也不知是什么神奇力量,总之我竟然自己爬回那冰上。原本靠岸边那群小孩,我的玩伴,全不见了,没个人影。大约是有人发现我不见了,一害怕全跑回家了。我在那死而复生──感觉那湖下有个吃小孩的魔鬼,已经一口把我吞下了,味道太差又吐回来──的冰面跪着喘回了口气,走回岸上,又不敢这样回家,被大人打死了。我就这样全身湿漉漉的,一直发抖,在那小城的工厂旁啊,人家的门口啊,晃着。那个天气很怪,是有阳光的,但气温是零度上下。我就那样把衣服风干、晾干,才敢回家。回去后发烧躺了一个礼拜啊。”
“真好听。”我说。那时,我以为,我每回在中国大陆,遇上一个哥们,喝个两杯,都可以听到这么一段如梦似幻的故事。
“我们那小城啊,九○年那段时间,一些砖造的工厂,像刘慈欣写的〈乡村教师〉里的那样,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可能全城八成的妇女,全在那些砖造房里的工厂鞣皮啊,缝线啊。那时咱们城最高的建筑地标呢,是栋人民医院,它医院后方有个池塘。那池塘呢,可能医院里一些过期药剂啊、清洁剂啊什么的,全往那池里倒,臭不可闻。那个臭,是化工剂料强酸的臭,不是厨余鱼肉蛋白质腐蚀的臭。当时也不少妇女,可能年轻女孩被男人骗了,也可能是妓女没小心怀上了,跑去这唯一一间医院打胎。那是违法的。但那医院,或说那年代,也没个处置这些打掉的死婴的流程或有人来收什么的。他们就把它们倒进那池塘里,那些死婴会像皮球撑饱了气,浮在黑呼呼的水面上。好像也没人当回事。时间久了,被蛆吃了里头的内脏,可小骨架也塌了散了,就剩一坨小人形的深褐色的皮。我们小孩那时也不懂,找了根长竹竿,去池塘里捞啊戳啊,刺起一枚那样塌瘪的小死婴皮,就举在竹竿顶端,像举着旌旗那样大街上嘻笑追逐。现在想来,觉得真恶心。”
那让我恍惚,觉得此情此景,是我童年记忆里父亲那辈人的作派。
那算我从二○一一年左右,开始有机缘到北京的第一次还第二次吧?距这之前最后一次到北京(和新婚妻子的蜜月旅行),一九九六年,中间隔了十五年。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遇见大陆这边的“文化人”:出版社的、文化记者,或南边某间大学的老师,他们同时也都是作家,年纪约小我几岁,或小十几岁。我搞不太清楚状况,但感觉好像“出书”这一块,在中国,正兴兴轰轰,充满传奇和可能性。事实上他们做了许多事,翻译了许多对我来说不可能的国外哪个大名字作家的小说或哲学书,这在他们来说,好像也气定神闲。我被找去一家叫<湖广会馆>的餐厅包厢,他叫了一整桌油光潋艳的菜。他对我介绍这当初是李鸿章为照顾两湖两广读书人,进京赶考时,不须在车马颠簸后还忧烦人生地不熟,吃住皆有个照应;他拿着一瓶酒,说这正是李鸿章家乡的名酒;他介绍着那一道道有着古代感的名菜,它们各自的身世和讲究……那让我恍惚,觉得此情此景,是我童年记忆里父亲那辈人的作派。在台北,到我这辈,基本上极难得有这样的杯觥交错,圆桌攀叙一些老辈的风流逸事,或一桌人低声暗着脸,说起政局风向,一些可靠的消息,谁谁谁上了哪个位置,而他又是谁谁谁的人,嘁嘁窣窣,阴阳乾坤。同时挟菜,咀嚼,剔鱼骨,饮茶,敬酒。眼神整桌巡梭,适宜时说个与进行话题呼应之笑话。我们好像都习惯在咖啡屋或酒馆聚会像洋人那样在背景音乐中小方桌哈拉了。感觉在某个时光,就失去了这样的吃大圆桌应酬的教养了。或那辰光整个中国,都在一富起来的初启年代,生意实在太好,感觉各包厢都坐满了人,端菜的服务员女孩哪道重头戏的菜一直没上,主人非常焦虑的催了几次,最后还是没上,他们就非常认真的发火了。”怎么回事呢?不是,刚刚就是你这位姑娘,一个小时前了呗?这太离谱了嘛!”就连那样在餐馆被怠慢,被不尊重,那个怒气的撑起,必须亮一趟唱功台词,这都像我记忆里的父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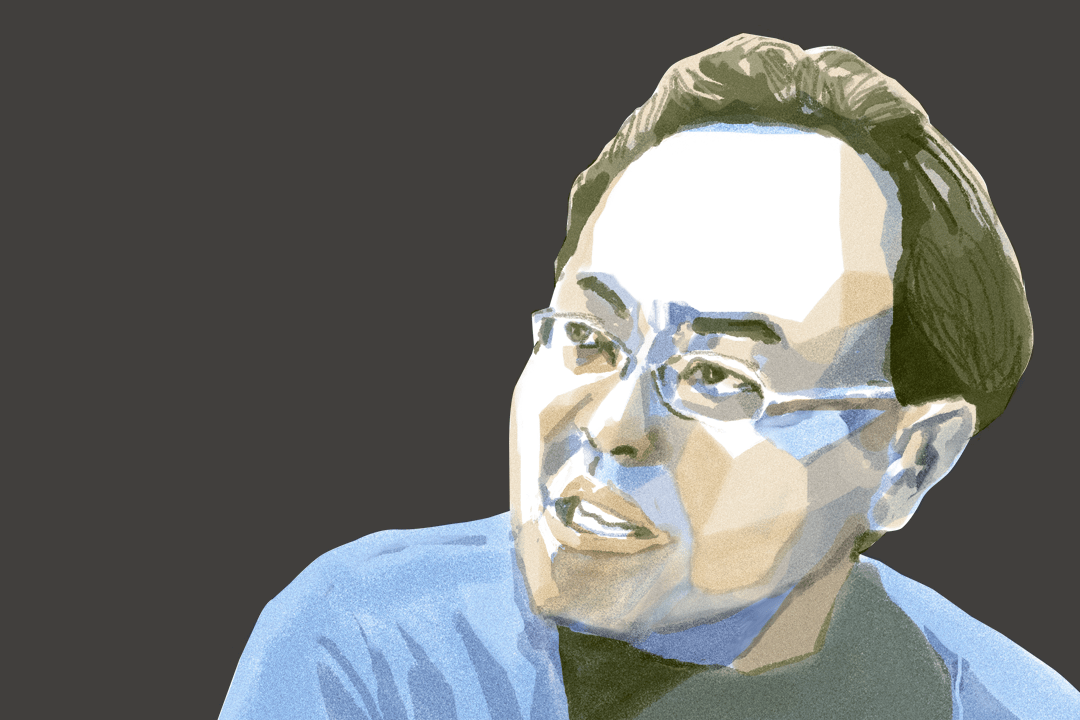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