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你是先有一個對家的想象,然後遇到了符合這個想象的人,於是跟ta在一起組建這個家。抑或是先遇到了一個人,然後因為這個人你才有了成家的慾望?」我舉著手機,問正在跟我視頻的伴侶。我們之間隔著14000多公里,正在經歷第二次異國。
手機那頭的他想了想,說「我覺得兩個都不是。從一開始我對家就沒有太多的想象,然後我遇到了你,我們在一起,我依然對家沒有太具體的概念。我覺得是兩個人在一起後再一起去創建、創造的吧。」
他給出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答案。這樣的對話在我們的相處中偶爾會出現,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在嘻嘻哈哈地過日子,但每當我因為現實生活的種種卡住的時候,每當我思考這些抽象性問題的時候,他大多數時候都能夠托住我,托不住的時候,他就會靜靜在一旁陪伴,等我自己慢慢overcome那些難關。我們就這樣嘻嘻哈哈又偶爾嚴肅地在一起了十年。
朋友問我,維持一段穩定親密關係的秘訣是什麼。我一時語塞,因為關係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把「穩定」設立成是經營這段關係的目標,我甚至沒有設定任何目標。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這個人好像蠻有趣的,那就在一起試試唄。一試,就是十年。在這十年裏,我經歷了几段疼痛的自我成長,也經歷了求學到求職的艱難轉變,他都一直陪伴支持。但關係也不是一直一帆風順的,在一起第三年的時候,我們經歷了一次「三年之癢」。

「三年之癢」
在一起的第三年,我「激情」出軌了。我在一次出差的途中,無法自拔地crush了一位男生,兩個人就像是火柴碰到了砂紙,一擦就點燃了。理智告訴我不應該這樣,但感性讓我蠢蠢欲動、躍躍欲試。我仿佛遇見了錯過了幾輩子的真愛,完全淪陷了,那一刻我知道我完了。
我也知道,我必須馬上向伴侶坦誠這一切。我跟伴侶說我喜歡了別人,我要分手。他很錯愕,但也只能接受。分手之後的我其實過得很拉扯,一方面跟「新歡」的磨合不順讓我從戀愛腦中漸漸清醒過來,另一方面,我不斷地自我攻擊。我覺得我傷害了一個對我很好的人。因為一己私欲而傷害別人,我並不喜歡這樣的自己。
這樣的拉扯快把我逼瘋了,於是我向心理咨詢師求助。我的咨詢師說,我是因為原有的關係裏沒有了激情,才會通過出軌來向死水一潭的關係裏扔了一顆大石頭,激起了萬丈水花,卻把自己給淹了。然後,我的咨詢師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的我看來非常匪夷所思的建議:同時維持兩段親密關係。他說,既然兩段關係都難捨難分、不分伯仲,那就都同時維繫一段時間看看,然後再決定。我出差結束之後,就跟伴侶提了這個建議,我說我想復合,但是我暫時沒辦法跟另外一段關係切割,我可能還需要時間去處理另外一段關係,我問他可以接受嗎?
伴侶同意了。於是,我從同居的房子搬了出來自己住。我需要拉開一些距離,才能看清自己。
我過了半年跟「新歡」異地,跟「舊愛」同城的探索期之後,我跟「新歡」徹底分手了。分手的原因之一是兩個人對親密需求的程度不一樣。「新歡」對親密關係的需求非常低,低到一個月見一次就可以了;而我對親密的需求是比他高的。因為他無法滿足我的需求,我在那一段關係裏很孤獨,也很痛苦。而且我發現,我跟他的關係無法落地。我們每天談論的都是形而上的話題,但一旦談到生活的瑣碎,他就變得很不耐煩,因為他對這些日常話題不感興趣。
原來,就算遇到了我以為的幾輩子才遇到的情人,也不代表兩個人適合在一起。原來,就算兩個人之間有愛有激情,也不足以維持一段親密關係。半年後的一天,我跟伴侶說,我跟另一邊的關係結束了。伴侶也沒多說什麼,生活就這麼繼續下去。他由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責備我的話,也沒有問過任何關於另一段關係的問題。我問過他會有受傷的感覺嗎?他說有一點點,但不多,因為我並沒有欺騙他,而是選擇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跟他坦誠。
他對「三年之癢」的處理方式是我沒有料到的,但這也是他讓我敬佩的地方。從此之後,我對伴侶的感情裏多了一份敬意,他比我想象中更加包容,也更靈活。如今再次拾回這段記憶,我還是有一絲自我責備跟羞愧的。這次出軌讓我學會了如何去應對crush。誰都無法保證在漫長的人生裏我會不會再遇到讓我crush的人,但我想我就算再遇到了,我也不會像之前那樣衝動了。我會選擇跟伴侶聊聊這份衝動,背後是怎樣的動力,是我們的關係裏有什麼無法滿足我,我才會向第三方尋求嗎?還是彼此的需求變了?
「三年之癢」之後,我變得更珍惜這段關係,因為我不想成為一個我自己都不喜歡的人,因為我深刻地意識到伴侶是一個很好的人,也是一個值得我敬重的人。

作為女性主義者的伴侶
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問過我的伴侶,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他的回答是,他支持性別平等,他也認同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因為性別的原因收到壓迫,他也不喜歡父權制下對女性、男性的壓迫,但他不會宣稱(claim)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對於女性主義究竟是什麼還不夠清楚。他對於自己要不要貼上「女性主義者」這個標籤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在他眼裏,我首先是一個具體的人,是他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伴侶,然後才是其他身份。
我也沒有很用力去「支教」。比起糾結他到底夠不夠女權,我似乎更享受跟志同道合的姐妹們一起玩耍,去做事情推動女性主義。當年在歐洲完成學業之後,我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到底是留在歐洲但可能事業發展會受阻,還是回亞洲拼事業但可能面臨異地。對於通過親密關係拿伴侶簽證留在歐洲,我一直是很猶豫的。一方面,我當時還是一個沒有受過時代跟社會毒打的人,心高氣傲的我還陷在「努力就能成功」的敘事中,覺得憑自己也有可能拿工簽留在歐洲,不需要靠伴侶。另一方面,我也擔心簽證會讓關係變了質。我會為了繼續留在歐洲而在關係裏不斷退讓、妥協嗎?如果我現在留下來了,我以後會後悔沒有在這個時間點為事業拼盡全力嗎?
當我把這些擔憂跟他說的時候,他既沒有承諾他會如何在關係裏保證關係不變質,也沒有跟我分析去留的弊端,而是說他會尊重我的決定。他說如果我需要一個簽證留在歐洲,那他就跟我一起準備材料遞簽;如果我決定回亞洲拼一把,他會配合支持,例如可以經常飛到亞洲來看我,也可以考慮到亞洲來工作。而後來因為疫情封關我在亞洲工作他在歐洲兩個人無法見面的時候,他也確實做到了他承諾的「配合支持」。他辭掉了歐洲的工作,在亞洲找到了一份工作,來到了我工作的城市。
我跟他說過,從結構性上來講,你是男性,你是歐洲人,你的所有學歷都是在歐洲拿的,你從事的行業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工作機會,我認為你在各方面都比我有更大的特權。如果兩個人之間有一個人需要妥協,那個人不應該是我。我們並不是因為對方的性別、學歷、國籍、從事的行業才決定在一起,可是當關係的發展受到了現實的挑戰,處在更優勢的一方如何應對會是很大的考驗。
當我回到亞洲,我跟新同事分享我的伴侶辭去了歐洲的工作而來到亞洲跟我一起生活時,ta們往往會稱讚他,說他是個好男人,說他為了愛情而作出犧牲。這樣的評論會讓我不舒服,因為這樣的評論不僅加深了對某一種浪漫愛套路的刻板印象,也矮化了他在關係裏的主體性。他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經過思考之後做出了他要來亞洲跟我生活的決定,他在亞洲從事著他喜歡的工作,他從他的工作中獲得了他的價值感跟體面的薪水,他也因為跟我一起生活而每天開心快樂,這裏面並不存在誰為誰犧牲了什麼。如果他當時辭掉歐洲工作來到亞洲是抱著這種「我為了你犧牲」的心態,我想我們的關係可能也會出現問題。
對於處於異性戀的女性主義者來說,如何在關係裏踐行自己的女性主義主張,這是一個非常私人但同時也非常有創造性的過程。我自己的感受是,女性主義也好,其他的意識形態的實踐也好,重要的不是對方是不是百分之一百跟你在各種光譜上吻合,而是雙方是否有這個靈活性跟開放性去調整和接納不同。如果人只是在尋找一個鏡像的自我去愛的話,在我看來那可能只是一種自戀。更重要的是越過標籤去看到真實的人本身,去建立超越各種主義之外的深度聯結,去擁抱複雜性,在複雜性中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輝,才不枉在這滾滾紅塵中瀟灑走一回啊。

結婚是一場冒險
我們在一起的第九年,要不要結婚成為了一個討論話題。我對婚姻制度本身並沒有太多浪漫的幻想,我不想結婚是因為覺得婚姻這個制度會限制我的自由。之前在歐洲,親密關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形式來維持,例如同居伴侶,婚姻並不是唯一選項。但當我們都身在亞洲時,同居伴侶關係並不是一個可選項,而疫情又使得國際旅行變得很困難,也讓人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變得更加難以耐受。
我開始想,如果結婚能夠讓我跟他都在疫情期間有更多身份上的保障,是不是可以利用結婚這個制度而為自己獲得一些利益呢?說實話,我為此糾結了很久。有朋友說,女性本身就已經承受了很多制度性的壓迫,如果在某些情況下婚姻這個制度可以為女性所利用而獲得好處,為什麼不呢?這樣的說法並不能完全說服我。這不是因為我把婚姻神聖化,而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我無法接受自己如此功利地對待親密關係。
當時的我在工作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為無法適應亞洲學術環境裏的高度功利化。在那樣的環境裏,每一個決定都必須導向一定的績效成果,接收到的每一次幫助都暗暗標好了回報的價格,我對這樣的學術氛圍深惡痛絕。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更加反感我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我的親密關係,給一個原本是我最安全最舒服的堡壘也標上價格。除此以外,我會質疑自己是不是為了一種自由而捨棄了另一種更根本的自由。我會有一絲絲覺得自己如果結婚了就背叛了女性主義的實踐,感覺自己在為異性戀婚姻制度添磚加瓦。
我的伴侶對於婚姻的看法跟我是不一樣的。雖然他並不會把婚姻神聖化,但他依然會覺得婚姻是親密關係的一種升華,是從法律上、家庭層面上把兩個人捆綁得更緊密了。他對於兩個人會因此被捆綁得更緊這件事是欣然接受的,但我則是有隱隱的恐懼,懼怕因為結婚失去很多自由。我讀過太多女性被婚姻困住了的故事,我也親眼見證過身邊的親友親歷婚姻帶給她們的束縛跟她們為婚姻所作的犧牲。當我把我的恐懼跟伴侶說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我知道那些女性被婚姻困住了的故事,但我跟你的關係並不是那樣的,我不是那些故事裏的男性,你也不是那些故事裏的女性。你的自由不是我賦予你的,而是你本身就擁有的。所以不管我跟你的關係怎麼變,你擁有的自由不會變啊。
我想,我的恐懼來源於對女性受到結構性壓迫的深深理解跟共情,但我也需要看到在個體層面,在我跟他的關係裏,其實兩個人一直都是平等且互相理解的,那些女性被親密關係吃乾抹淨的事情從來沒有在我跟他的關係裏發生過。最後,是好友的一番話,讓我鼓起了勇氣去冒這個險。她說,哪怕是在婚姻制度裏你也是有能動性的,你也依然可以發揮你的主體性去打破很多規範、規訓,不是嗎?她的話提醒了我,不管在婚姻這個制度裏還是之外,我都是可以去創造、經營一段符合我價值觀的親密關係,我的力量並不會因為進入了婚姻而自動削弱。相反,恰恰因為進入了婚姻制度,我可以去探索一種新的異性戀婚姻相處模式。
我當時對於工具化親密關係的糾結,也因為我最後沒有利用婚姻關係去申請歐洲的伴侶簽證而達成了某種自洽。可能這些糾結在某些人眼裏覺得很幼稚很可笑,但我知道對於當時那個階段的我來說,保持親密關係的純粹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不知道如果有一個歐洲簽證,對於我在歐洲找工作能有多大的助力;我也跟很多其他人一樣因為疫情的緣故一直處在惶恐跟無力之中,能潤出去也是一條出路。我都知道這些,但對於那個時候的我來說,我就是做不到。
現在回頭看,我很慶幸當時沒有逼自己變得「成熟而功利」,而是去探索一個能夠獲得自洽的平衡。小的時候,父母逼我練琴是為了考級,考試考好了才能出去玩。長大了進入了亞洲職場,發表、申請項目、教學,又是為了完成KPI。我那個時候的人生充滿了很多我不得不去服從的規訓,我才會那麼執著在我能夠決定的親密關係裏,堅持某一種純粹。這類似是一個對抗外部規訓的隱形反抗,哪怕它很微弱,但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種反抗是在告訴我自己,你可以繼續保持你的理想主義,你可以不那麼圓滑成熟,你可以繼續誠實地做你自己。
今年我們剛過了兩週年的結婚紀念日。我們相處的模式沒有變,我的自由也沒有因為一紙婚書而被變少。可能唯一變的就是我們跟彼此的家庭成員相處的時間變多了。我想進入婚姻對於我而言,它開啟了一些新的體驗,例如身邊的人會因為我身份的變化而改變他們跟我的相處方式。我爸會在我結婚之後說一些什麼「你成家了,要考慮把家安在哪裡」的話。我下意識會對這些「家庭敘事」有一些反感,大概我的婚姻在我跟我父母那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吧。

新型婆媳/岳婿關係
既然結婚了,婆媳/岳婿關係是繞不開了,畢竟伴侶有媽,我也有爸。說實話,從小到大我接觸到的中國式婆媳關係範本都是非常糟糕的。從狗血電視劇裏的婆媳矛盾,到現實生活裏我親歷的我媽跟我奶奶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都讓我對婆媳關係本身有一些恐懼。
伴侶的媽媽是很早就到歐洲打拼的華人,她身上既有亞洲女性的那份堅韌跟顧家,也有西方文化裏的開明。我一開始其實是不知道以怎樣的姿態去跟她相處的。一方面,我不想自己落入傳統亞洲婆媳關係的範本中,去扮演一個「好兒媳」。另一方面,如果拋開舊腳本,我又不知道新腳本是怎樣的。向歐洲模式那樣跟婆婆做朋友?拜託,我跟我媽都做不了朋友,讓我去跟一個跟我媽年紀差不多但卻很不熟的老太太做朋友?不要開玩笑了。
一開始幾次的接觸,彼此還是很客氣的。我能感受到她渴望了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的愛好是什麼,她也並沒有試圖用傳統那一套婆媳關係來規訓我。我仿佛是她的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每年拜訪(叨擾)一周左右。在這一周裏,我們都客客氣氣的,小心試探著對方的邊界並都努力不越界,保持尊重、微笑。我跟伴侶沒有壓力說聖誕節一定要回去歐洲「過節」,平時我跟她也沒有過多的接觸,我是在結婚一年之後才加了她的WhatsApp,但她最多也是過時過節發幾句節日問候。我偶爾會網購一些佳節食品給她以表心意,她也會在適當的時候「還禮」。
我對這樣輕盈的婆媳關係還是挺意外的。雖然在相處中肯定會有因為生活習慣、觀念而產生的小矛盾,但終究不是大的過節,距離拉開之後自然就消解了。反觀伴侶在跟我爸媽相處的過程中,他就少了很多在岳婿關係裏的糾結。因為他跟我爸媽語言不通,他在我爸媽眼裏就是一個在中國旅遊比我外甥女還要弱雞的外國人。因為他不會中文也沒有支付寶,在國內旅遊迷路的話可能就只能求助會講英文的中國人了。
有意思的是,我身上的中西混合成為了我更好去理解他家庭的一個因素,但他身上的中西混合卻因為他不會中文而使得他免於這些複雜中式姻親關係的糾結。我身上終究還是有成長過程中女性被規訓得要更好去照顧家人的影子,但有的時候,我也會猶豫我要不要有意識去調整,因為我就是喜歡對我在乎的人好啊。而當我在乎的人恰好是我伴侶的家人的時候,難道我要因為他們的身份而停止對他們好以示政治正確嗎?可那樣的話,最後我活成了一個正確的人,卻不是我自己了。
我們結婚之後,雙方父母從來沒有見過面,也沒有打過招呼。雖然這並不是我們故意而為的結果,但我跟伴侶確實也沒有積極促進雙方見面。我的想法很簡單,有機會見到就見,沒有機會也不用勉強。我不想因為我們結婚了,我爸媽就多了一重義務去跟伴侶的父母寒暄、建立某種姻親關係,更不要提四位老人之間可能出現的語言溝通障礙跟文化差異了。這般邊界清晰,看起來不太中式,但也不完全西式,大概這就是我這段親密關係的一個主題吧。
隨著年月的積累,兩個人一起經歷的事情越來越多,我和伴侶之間的感情從愛情升華到了一種共患難的人生伴侶之情。我們有因為長期一起生活而建立起來的默契,也有因為一起走過高山低谷積累下來的情誼,我對他有一分敬意,還有一份義氣。這份義氣是我感激他在我好幾次低谷的時候都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我身邊。人生可能還有好多可能性,但此生我不想辜負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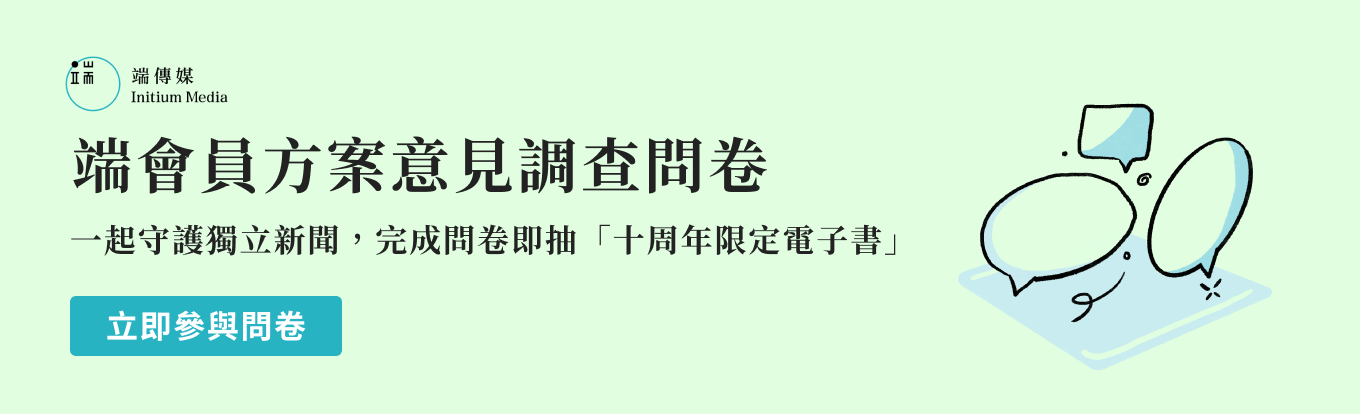



婚姻是什麼?
我對此問題作出追溯源頭的思考,結論是婚姻的作用是「遺產繼承」。
遠古「狩獵搜集」的族群社會,並未出現個人資產,大家狩獵或搜集得來的食物會共同分享。後來農耕社會發展,出現了「土地」私產繼承問題,如果證明「哪個人」是土地持有者的親屬便是問題了,婚姻及其儀式的作用乃告訴週遭所有人,夫或妻或其子女才有財產繼承權。
有点无聊的一篇,像是微信或小红书上面的网友人生自传
我覺得喜歡與愛上是一個人的事,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我覺得一段關係中的故事總是要結合各方角度的敘述才會顯得立體的。一段關係到底是如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外人也不好評價什麼,只是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個更立體的故事。
讲了半天,对方的形象非常模糊。在作者的讲述中,作者本人呈现出非常多人性的各种真实面相,但是对方没有,好像总是表现得那么合理、宽容,于是形象非常模糊。
我更加相信这样的亲密关系是存在的:彼此都能以“我”诚实地与对方联结。其中需要很多美好的品质,比如诚实、勇敢、对自私傲慢天性的克制、持之以恒,但再想想,更多时候可能也不过是关于机缘、时运的概率事件。祝福作者
最近刚好对“关系的形式”很是困惑,谢谢作者的实践和分享
很同意下面书友的评论:“在这篇文章里我看见了三个字‘我我我‘”。
作者的伴侣,离开几十年生活的地方,为了她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换了得心应手的工作,重新适应自然环境,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结果作者说这是对方主动做的,不是“牺牲”,也不是为了她。这种想法,也未免太过于新自由主义了。我是一个女人,如果现在我遇到一个人,因为我有优势就让我离开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到TA那里去,我是一定不会同意的。
恭喜噢,我和我的伴侣也四年了还未考虑结婚,没见过对方父母,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松弛了一些
在这篇文章里,我看见了三个字“我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