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与Indi Chan见面,,是去年在香港一间独立书店。当时在书店偶遇香港编剧庄梅岩,她介绍身边两位说日语的女士,一位是日本剧作家,另一位就是帮忙中日翻译、现居于日本的香港剧场人——インディー・チャン(Indi Chan)。
Indi在日本生活长达十年,最初留学东京,攻读舞台剧,如今已是著名演剧剧团“文学座”(文学座)的座员。第二次和她见面,已经在东京。她说,自己正要改编一套香港舞台剧,在日本公演,正是出自庄梅岩手笔的《野猪》。
但搬演香港作品,不为说好香港故事,她相信,两地有太多类似,而剧场能带来的共鸣,无分地域。戏如人生,对她来说,港日两地,同样如梦幽回。

小挨过来的入座岁月
“最难是,有时A前辈说的做法你照做,B前辈见到,会说这样不对,C前辈又说不是这样。但你就只能一直道歉,好像全部都是自己的错。”
来到信浓町的剧场“文学座アトリエ”,为文学座的排练和演出场地。这座旧式都铎建筑落成于1950年,陡坡屋顶下,刻上一句拉丁文,”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取自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意味世界即舞台。如此一栋朴实无华的木建筑内,上演无数出现代演剧,一代人谢幕,又一代人登场。
有别于娱乐性高的商业剧场,或以影视明星作招徕的制作,文学座属于日本小剧场类别。追溯至战前时期,日本开始翻译英、法等外国戏剧,称为“新剧”,与当时国内的歌舞伎、能乐等传统戏剧区分。昭和12年,即1937年,文学座由岸田国士、久保田万太郎、岩田豊雄三位作家创办,正是新剧最早期创立的剧团之一。剧团经典作包括森本薫的《女人的一生》(女の一生),担纲出演该剧的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风头堪称一时无两。
这天剧场公演后,演员与观众聚在正门前方,各自围着聊天。一身全黑装扮的Indi,正在后院来回干活。剧团分演技部与幕后部,前者为演出人员,后者则包括灯光、音响、舞台监督、美术设计、服装等,由剧团成员轮流分配每场公演的岗位。像这次,Indi则被派到服装部,负责在演出期间帮演员快速换装,缝补衣服,还有洗衣服。她捧着一篮又一篮戏服,到场外的洗衣场,间中有人经过,连忙点头互道一句辛苦了。
她说,剧场人手不够,幕后部流失率高, 一来辛苦,二来日本社会常见的“パワハラ”问题,即是权力霸凌,很多人抵受不了就离开;除非有一些很想做的作品,很想继续留低。

时间回拨,2015年,Indi在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来了日本读专门学校。她时常流连下北沢、新宿,池袋看小剧场,对日本演戏深感兴趣。直到第二年,研读舞台剧专攻,她自觉,做演员的话,无论语言和外型,也许未必够竞争力,于是打算朝剧场导演的方向发展。那时,多位老师和剧场前辈异口同声建议她,要是想学做导演,就到文学座去吧。
要“入座”成为文学座准座员,著实不容易。她首先进入剧团的附属演剧研究所,日间班由早上十点开始,周一至周六,每天上课四小时,学习演戏、音乐、动作武打,体操等,还有一些特别授课,“例如学习和服的穿衣礼仪,因为剧团有很多古代戏,穿和服时讲究细节。还要学递一杯茶时用怎样的手势,男人进房间时,女人要怎样背对,所有东西都有很多细节。”日间和夜间部合共差不多六十人,过了第一年,往往只有三分一的人能晋级。
到第二、三年,差不多全部时间都跟剧团公演,而最终能否成为座员,没有评核考试,正是由评审视乎所有公演表现,决定谁能留下来。2022年,Indi终于升格,成为座员。她谦称,感觉只要你挨得,多数都让你晋级,毕竟幕后人手长期都不够。
但能够挨过来,才是真正考验所在。Indi说,最初完全无法适应,“所有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做。最难是,有时A前辈说的做法,你照做,然后B前辈见到,会说这样不对,C前辈走过来,又说不是这样。但你不会说是谁教的,就只能一直道歉,好像全部都是自己的错,这些时候心理比较辛苦。”另一个要挨的,是半工读的过劳。Indi一边读书,一边兼职,做过拉面店、居酒屋,旅馆,还有24小时营业的连锁超市。她忆述,剧团日程很忙,几近捆绑起长时间,待日间授课结束后,就赶到超市打工,一般由下午三点直踩到夜晚十点;要是隔天放假,甚至返通宵更,由下午六点到凌晨五点,足足十一个钟。
在研究所时,她忙于做助导,直至去年开始,以导演身份活动,投身剧场工作。然而,因为她的在留资格是“兴行”签证,限制了演艺活动为收入来源,无法像过去兼职帮补生活费,她苦笑道,剧场收入甚至少过在超市兼职,“这也是人才流失的一个原因,人工说出来,你会问到底是怎么生存的状况。”

香港的野猪 日本的野良豚
剧中的记者经常说要追求真相,但自己又有隐瞒的秘密,“其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开始的。”
今年九月,Indi将会在文学座首次执导作品,剧本改编自香港编剧庄梅岩的《野猪》,日文版取名为《野良豚》。去年,她已多次翻译香港剧作,如钟卓桁的《知秋》和郑国伟《最后晚餐》,俨然串连港日演剧的桥梁。不过,其实她曾经对香港剧场一无所知。
她是来到日本后,才开始真正接触舞台剧,曾经被剧团的人问起,有哪一些香港剧作推介,她明明是香港出身,却几乎答不出来。于是,她有次回港,决定找一些剧本,买回来读。香港舞台剧作品无数,出版剧本则不多。其中,庄梅岩是相对有较完整个人剧本集出版的编剧。Indi 坦言:“那时候我都不算很熟悉庄小姐。但后来知道她的作品,还有当时自己很炽热的心态,对这个作家更加有兴趣。”
后来,她在日本看到《野猪》出版消息 ,惊讶于在2022年的香港仍出版探讨新闻自由的剧作,立即叫朋友帮忙寄书。“我看第一幕时,还不算是喜欢这个作品。但看第二幕的时候,感受到她(庄梅岩)很想传递给观众的讯息,更加拮入个心度(刺入心里)。”在紧接的下一年,剧团公开招募公演计划书,Indi决定申请改编这部作品。“当时日本社会闹出杰尼斯事务所丑闻,我觉得跟《野猪》剧本十分吻合。因为那是日本媒体经常被诟病的问题,虽然是民主国家,新闻自由度真的很低。这个作品在日本演出,应该很有共鸣,会带给日本观众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媒体是不是正确的,自己看到的、自己相信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她说,日本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像少子化,年金争议,但一般大众漠不关心。

她形容,《野猪》是一个很矛盾的故事,剧中的记者经常说要追求真相,但自己又有隐瞒的秘密,“其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开始的。这个剧本很有趣的是,它讲到一些社会大层面的事,又会写一些很细微的个人感情,内心矛盾。每一个角色都是很实在的个体,不是每一个剧本都做到,有些会流于表面。像日本有很多关于战争或者社会问题的作品,太专注在议题上,那些台词全部都是在讨论,就像在看星期日那些辩论,在维园那个。”她一时想不起时事论坛节目《城市论坛》的名字,而这个香港历史悠久的议政平台,早已在2021年停播。
这一次改编,Indi先翻译原作,经过多次围读,又访问了一些日本新闻记者,试图让剧本贴近日本脉络。“我想知道这些日本记者是怎样看业界,遇过什么困难,一些他们觉得日本存在的问题,写进日文版。例如,现在大家接收消息,不只是新闻、电视,还会用SNS(社交平台),很多记者说开始愈来愈少人读纸本报章,但网上新闻求快,有时候就出了一些错误报导。有些读者不会理对错,喜欢一些juicy的东西,而不是真实,就有一些网媒专门发布那些juicy新闻。这些还在做报社的人就会很困惑,那到底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仍被需要呢?”
这一连串新闻行业面对的困境,不只日本或香港,甚至在世界各地愈趋普遍。Indi指,《野猪》原著亦无写明是哪国何方,“我也觉得,故事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话,会有趣一点,我不是说要将剧本全部代入日本,也保留一些只在香港发生的东西,让观众有点抽离,听到对白时又有些感受。不过,看这个剧本,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到底知道真相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不是告诉你一个真相等于好的价值观,而是一个提问,令你自己去思考。”
“香港人关心社会多一点,但日本整体上社会关心程度很低。香港人说话是很直接,日本演员跟我说那些对白好像直接戳进心里,反而是日本较少的。”
她既认为港日两地有不少共通点,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她对于人们的反应,感觉不一样,“做这个作品,是想日本人再多一点警觉性。香港人警觉性较多,比较关心社会多一点,但是日本整体上对社会的关心程度很低。还有,香港人说话是很直接的,一些日本演员跟我说过,那些对白好像会直接戳进你的心里,反而是日本比较少有的。”

迟来的身份认同
今年是Indi旅居日本第十个年头。最初,她一直想融入日本,几乎所有生活习惯都跟日本人无异,一起上课和公演,不说日文以外的语言。当时她的心态上,甚至觉得能扮成日本人是有成功感。但有些时候,无论日语多流利,如何跟足工作指引,也会单纯因为兼职制服的名牌写上外国名字拼音的片假名,就遭受客人歧视,动辄刁难,“我也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当时有一种很不舒服的心情,算是有很大的推动力,令自己更加倍努力。”
与不少憧憬在日生活的外国人一样,Indi对日本的钟情源于日剧,动漫,还有日本流行曲,“但那只是某一面的日本。来到生活之后,看到日本人怎样对待外国人,有些比较排外,还有难接受新事物。有时候发觉,大家的价值观原来很不同。”就像她听到,日本人经常说:“这是常识吧。”她心里疑惑,即使说者无恶意,倘若是守旧的常识,是否必然跟从?“我有一段时期觉得没那么喜欢日本,但又好像当年的那种爱仍是留在这里,摆脱不到,好像喜欢过一个人,虽然发现了他有很多很多缺点,但你还是会想继续在他身边的那种感觉。”
“我有段时期觉得没那么喜欢日本,但又好像当年的爱仍摆脱不到,好像喜欢过一个人,虽发现他有很多缺点,但还是想继续在他身边的。”
至于香港,Indi也不是因为不爱才选择离开,只是因为向往日本生活。但是,多年来拼命融入日本生活,近几年的她,反而开始表现出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
“之前我不会在聊天时主动跟人说关于香港的东西。可能是这几年很多事情发生,新闻报道香港的事,大家都来问我。往后我也主动告诉别人,香港其实是怎样,”她笑说,就算很小事也好,“例如香港吃烧卖是不会和白饭一起吃的,因为我看到日本推出了烧卖便当。”疫情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受疫情影响,无法如过往一样,每年都会回港一、两次。由是物理距离,拉长了思乡情绪,她开始在东京特意找茶餐厅,食鸡蛋仔,歌单全都换上广东歌,天天追看MIRROR、《试当真》和《小薯茄》。
每当她想好好跟别人介绍香港的时候,总发现自己对香港认识不够多,所以重新读了很多 历史文化知识。“可能因为成长生活在一个地方,反而不会特别想到为什么,或者以前有过什么事。为什么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开埠的历史,小时候上历史课的知识,记忆很零碎,不算可以很流利地跟人解释,现在重新整理了一次。”

许多日本人不清楚两岸三地的关系,也不知香港人说广东话,她甚至偶尔被误会是台湾人,“以前的我是不会更正,觉得很累。现在,假如对方没异样的话,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甚至快速说明港台两地的简单历史。为什么香港人有自己的法律呢,跟中国政策制度的不同。”她说,开始习惯了随时拿出一张纸,一副正儿八经,画出中港台三地来辅助讲解。
如此转变,她说,是身份认同多了,想别人知道自己是由香港来的,不想大家分不清。在剧团网站,她的个人简介中,语言能力为“広东语”与“中国语”,分别补上“母语”与“北京语”的说明。不过,她也有无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只是自我满足力而已,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好像不说出来,心里会不舒服。其实做舞台剧的也是,不知道别人看完那出剧之后,会有什么带走,有些人可能礼拜六、日看剧,只为放松娱乐。未必会改变到世界,一定改变不到。但好像希望会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改变,而你不会确保到什么,所以算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已。”
“假如对方没异样的话,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甚至快速说明港台两地简单历史。为什么香港人有自己的法律呢,跟中国政策制度的不同。”
最初进剧团的时候,她单纯觉得舞台剧很有趣,好奇做导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直到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对香港的感情深厚了,又因为住在日本很久,知道这个社会的构造是怎样,虽然有很多缺点,都有很多值得喜欢、珍惜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都想为日本做一些事。不管是日本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我都希望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加好。生活的意思,不是物质上,是心理精神上,而舞台剧正正能够令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疫情的时候,很多舞台剧界的人都是说,舞台剧是不是被需要的呢?我觉得,其实它跟其他媒体很不同,即使你听不懂那个语言,有时你会感受到那个人的电波,感觉到人的感情,会受到影响。”
现实是,香港舞台剧界近几年不时传出演出场地被取消的新闻,舞台剧奖又被艺发局中止资助。身在日本的Indi也留意到这些新闻,她说,难处之一在于香港剧院大都是公营,限制重重,反观日本,有很多不同的小剧场,包容不同独立创作。她想,倘若有合适机会,也想在香港做演出,但始终目前正在日本发展,依然想留在这边。“其实会想留住一些记忆,而那些在香港有很多限制。我留在日本,可以做到的就是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随着九月上演《野良豚》,她也着手翻译出版庄梅岩的日文剧本集,“好像留下了一个纸本纪录,就算我们全部都死了,广东话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价值观和想法,都可以留给后世的人。好像北海道的爱努族(アイヌ),有一些描写他们的作品是留下来。这个是我觉得,隔在一个远的地方,希望做得到的事情。”

梦里身是客
“就算我们全部都死了,广东话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价值观和想法,都可以留给后世的人。”
每个异乡游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乡愁浓淡不一,自有熟悉与模糊,以及虚妄与实在。Indi记得,最初留学日本时,每当回港,总觉得好像发了一场异国梦;渐渐地,当她返回日本,又觉得在香港那匆匆数周,不过是另一场梦。走过的街道,路上交换语言,她生活周遭的所有都切换过来,竟如幻觉,好像在另一个空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时间向前走,转变原来在不知不觉间滋生。“这一两年回香港的时候,少了这种梦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可能是因为有些工作上的事要处理,又或者可能已经在日本十年了,感觉已经很实在。反而,我回到日本之后,觉得在香港那段时间,才是一场梦。”
双城往返,无论哪一个出发方向,Indi发现,同样是返程,唤作“回去”。唯独最近一次,她记得回到日本的时候,故意不用“帰る”,改口说了“戻る”。
她说:“回去的感觉,很有趣,也很复杂。我小时候住的屋企,已经没有了我的房间,回香港时都是住在妈妈那边,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屋企。回到日本,才住得最舒服。但我觉得我不是回家,只是回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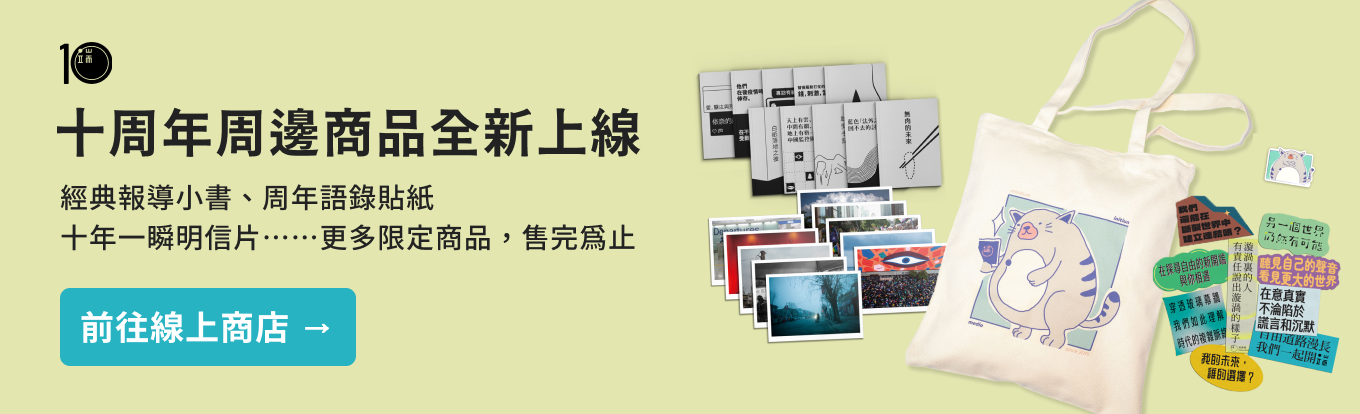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