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日,中国南方航空吉林基地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有着十年飞行经验的机长李煜众刺伤两名同事后从15楼跳下。被刺两人送医后脱离危险,李煜众不治身亡。
事发后第二天,李煜众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是航司领导故意“挑刺”将无任何问题的李煜众强行降级。南航与当地警方至今未对外公布案件细节与原因,也未回应公众质疑。真相缺席,航空圈自媒体及业内人士传,这起案件与各家航司正在“火热”进行的降本增效不无关系。
疫情后大陆航司连年亏损,民航扩张期增加的飞行(学)员开始“过剩”。各航司为求生“降本增效”,飞行员的晋升通道不再像往年那样畅通,内部考核与“作风问题”检查也更加冗繁严苛,曾经高门槛、高收入的光鲜行业在“寒冬”中褪色。

迟到的复苏
2014年高三的时候,航空公司招收飞行学员的宣讲组来到马成光的学校。马成光就读于中部某市一所重点中学,高考正常发挥的话可以考入一所普通一本高校。看到招飞宣讲后,马成光觉得这是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门。招飞的基本身体条件他都符合,再加上英语成绩还不错,他马上就动心了。
“当时心里想着,飞行员这个职业感觉特别‘高大上’,并且还写着培训期间有补贴,正式入职后年薪20-40万,就特别心动。”马成光的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两人年薪不到10万,看到这么好的条件,以及“飞行员”听着非常有面子的名头,也都支持他的决定。
成为大陆飞行员有两种最主要的培养模式,一是航空公司出资委托航校培养,这些学员被称为养成生(高中招飞)或大毕改学员(大学招飞);另一种是航校自主出资培养,然后将学员“卖”给航司。两种培养方式均需要4至6年时间。
马成光属于“养成生”。通过初筛选拔流程后,马成光开始了漫长的飞行学员生涯。先在航校完成理论知识、民航英语等课程培训,接着被航司送往美国培训。结束在美国的两年培训拿到了商用飞行证,马成光回国开始了“换证”考试(注:考取国内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五年后的2019年正式上机,成为某大航司的副机长。
“说出去有面子,实际上也就是个蓝领。”马成光如此描述飞行员这个职业。
正式上机飞行后,机组排班通常是飞三天休息一天,一个机组一天飞四个航段。如果遇到旺季或特殊情况,经常一天要飞五个航段。原本第四天的休息日也可能变为“备份”班,需要随时待命。虽然备份班可以申请不到岗,但马成光说,“这样做是在跟自己的前途作对。”
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民航局”)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规定,两人制机组单次值勤不得超过14小时,飞行时间不超过8小时。三人制机组在配备睡眠设施情况下,单次值勤期可延长至16小时,飞行时间不超过10小时。但2020年之前,民航仍处于发展期,大部分民航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卷起来”。
转折始于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后国际国内航空受防控政策影响遭遇重创,大陆民航业至今仍在承受疫情导致的亏损。
对马成光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无尽的“备份”班。马成光说,他们的底薪和普通工薪阶层并无太大区别,收入最主要来源要看累计的飞行时长。“那段时间别说年薪20万了,可能连我爸妈(的收入)都不如。”
当时马成光尚未升机长,收入如果想达到招飞宣传时承诺的最高40万,必须在职位上提升。然而,升为机长最重要的条件是“累计飞行时长”,疫情的到来大大拖慢了马成光飞行时长累计的速度。原本以为五年内能做到的事情,在疫情后变得遥遥无期。
在航空业内,从副机长升为机长通常而言需要5到8年时间,5年是较为理想的情况,“五年能当上机长也算好啦,现在有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当副机长咯。”马成光对自己在航司的前途并不乐观。

疫情后,由于航司收益没见好转,开始削减航线,一些已经达到累计飞行时长标准的副机长,转正申请一直被拖延。副机长停止了“流转”,仍在培训的准飞行员们也只能继续等待空缺的职位。
根据“小牛行研”对民航局数据的整理,2010年代,民航客机增速多保持在10%以上,并呈逐年递增趋势。2020年至2023年三年间,这一数字“腰斩”,无一年份超过5%,并且每年仍在减少。查阅各航司年报可看出,为数不多的新增客机多数来自疫情前的订单。
由于航班量骤减,民航学院的准飞行员们也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一样“毕业即失业”。据马成光了解,不少“学弟”在疫情期间被迫延长了培训时间,预期中的收入翻倍迟迟没能实现,继续靠在一二线城市算中低水平的培训补贴生活。
疫情封控结束已经第三年,各大航司的情况并未好转。虽然客流量有所回暖,但2025年上半年,三大航仍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南航、国航、东航2025年上半年预计共录得净亏损42.38亿元~55.56亿元,不过,三大航亏损幅度均有收窄。各大航司公告称,亏损主要因旅客结构变化、高铁冲击、国际环境等因素。
由于“养成生”与“大毕改”飞行员均为公费培养,由航空公司承担培训期间所有费用,通常为50万至100万元。这意味着,飞行员与准飞行员在规定的服役年限内不能随意跳槽,否则须赔偿航司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所以,即使民航业前景暗淡,这些等待升迁与就业的飞行员也不能转行去顺丰航空这类正处于扩张期的新兴货运航司。
马成光说,封控刚刚结束时,民航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都以为会快速复苏,吸纳了一批新飞行员入岗,但大家很快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中乐观。
持续的亏损逼迫各家航司“降本增效”,甚至转售飞机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航空业内最为著名的是南航转卖全部空客A380。A380客机是全球最大的宽体客机,主要执飞载客量高的中长途国际航线。《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南航先后共引入5台A380后,因为上座率不够,2022年底南航将5台A380全部退役。
期待中的复苏并未如期而至,航班、航线都在减少,各航司对飞行员的需求自然随之骤减。
马成光透露,一些2024、2025年本可以入岗的准飞行员现在只能继续等待。“他们拿培训工资的新人想赶紧进来,而我们这些已经在执行的飞行员才知道,进来之后才是最可怕的。”马成光感慨。

扩大的“作风问题”
“降本增效”对飞行员和空乘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航司对各种细小问题抓得越来越严。
如果事关飞行安全,马成光觉得无可厚非,但是衬衣扣子没扣好、未及时汇报休息时动向、备份要求到岗多长时间内未回复,最近几年都成了记录差错的扣分点,被一律称为“作风问题”。
甚至连飞行员谈恋爱这类私人问题也要向上汇报,汇报内容从对方家庭背景到个人情况事无巨细,不能有任何遗漏。这些“差错”累计多了,代价就是降级,最严重可能降回见习。降级不仅仅是工资变低,马成光说,更麻烦的是如果想再重回原岗位,需要重新累计训练和飞行时间。
“这跟李煜众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马成光透露,李煜众认为自己被挑了一些很“无聊”的刺,从机长直接被降级到见习(注:李被以“业务能力问题”降级为Z类机长,相当于见习飞行员),不仅收入减半,还要重新累计训练和飞行时长。“这些时间也不是自己想累计就能累计,要上级领导给你排,所以等于全部被领导拿捏住了,自己没有一点余地,想回来还得求他们赶紧给你排。”
当问及马成光能否证实这一说法时,他说,“圈内都这么传,航司也不出来表态,你看2022年东航事故都传成什么样子了,航司和官方出来表态了吗?”
生活在南方某一线城市的空乘刘慧丽,和马成光一样对航司严抓“作风问题”颇有怨言。她向记者讲述了三个月前在空乘圈广泛流传的一件事。
每次航段飞行任务结束后,航司会派人对空乘进行例行检查,主要检查空乘是否有夹带“公司财产”。在刘慧丽看来,这种检查以往都不过是形式化的“走过场”。然而,今年5月,一家大航司的两名空乘人员因被查出“私自夹带”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纸巾遭到开除,而且没有任何赔偿。

刘慧丽2023年通过航司官网的招聘进入空乘队伍。相比于飞行员,空乘的招聘流程相对简单。疫情结束后的2023年,经历过一轮人员流失、预计客流会迅速回暖的航司重启空乘招聘,以补齐人员不足的情况。
当时,毕业于高校空乘专业的刘慧丽已经在家待业大半年,这次机会下她迅速入职了某家国有航司的空乘。但2023年客流恢复不如预期,航司不得不再次取消部分航班,以避免“飞越多亏越多”。
对于刚入职不久的空乘而言,班次不密集意味着排班不多,而排班多少直接影响工资。刘慧丽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们私下聊起来时认为,可能是他们刚入职“关系不够”,总班次不多时排班不会特别“关照”他们,老员工才能拿到更多班次。
但在收入之外,刘慧丽更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苛的公司管理,“一些很无聊的严格”。刘慧丽介绍,现在每名客舱经理都有工作指标,盯着每一名乘务员的工作细节,遇到比较严格的客舱经理,空乘的大小“差错”都会被记录上报,轻则扣分扣绩效,重则停飞、重新培训甚至劝退。
这些“差错”时常是一些流程上的瑕疵,如某些动作、用语上的不规范,刘慧丽认为这些事情无伤大雅,也肯定不会对飞行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一名服役时间更长的“师姐”告诉刘慧丽,这些事情是从2023年开始变得越来越严格的。
航司严管空乘“作风”,却对乘客的“作风问题”视而不见。刘慧丽说,有时女空乘遇到高端会员旅客的言语不敬甚至骚扰,上级只会表示“他又没真的做什么,他说你就让他说呗”。针对高卡(高端会员卡)投诉,即便空乘占理,公司也只会息事宁人。
“今年以来一半以上针对空乘的投诉都来自高卡旅客。”刘慧丽透露,去年开始自家航司为了留住“核心用户”,降低了高端会员卡权益发放标准,越来越多乘客成为高等级会员。航司对高等级会员服务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从问候、饮料、书刊、毛毯等都要符合高卡会员喜好,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投诉。
“有时候想想还不如送外卖,送外卖不用整天飞来飞去还要小心翼翼伺候这么多人。”但在如今悲观的就业环境下,刘慧丽也迟迟下不了辞职的决心。

“变相裁员”
大陆航空业的艰难复苏,还同时遭遇了“恐飞症”和高铁的侵扰。
东方航空MU5735空难已过去三年,空难调查组至今仍未对外公布事故原因。由于遇难航班机型为波音飞机,再加上近三年波音频传飞行事故,航司的日常工作也不得不应对越来越多乘客对飞行安全的担忧。
在一家大型航司做客服的李妍青对“波音问题”烦透了。她说,每年总有一两则新闻说波音这里那里有问题,新闻出来后就会接到旅客电话,“称自己的航班是波音,现在不坐了,要求全额退款。”
李妍青并非不能理解旅客的担心,但她对“全额退款”的要求感到为难。“正常航班都无法全额退票,退票乘客自己承担退票手续费,怎么可能全额退款呢。”谈到最近几年的客服工作,李妍青略显生气,她觉得旅客来势汹汹而且有点胡搅蛮缠。
有来退票的旅客说,“抖音说波音已经全球禁飞了,凭什么你们还要我承担这个风险,你们航司凭什么飞波音?”李妍青很无奈,对于这种无稽之谈,她也只能压抑不满、机械般地运用客服话术拒绝,即使如此,航司的形象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民航空的另一重独特挑战是高铁。出于时间、价格、便利与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多中短途乘客从飞机流向高铁。
据澎湃新闻,高铁网络不断完善后,民航和高铁重合线路不断增加。尽管民航和高铁旅客量2024年都实现了高增长,但2024年多个黄金周与2019年相比,铁路旅客发送量增速都高于民航国内旅客运输量的增速。
高铁对民航的冲击中,最为典型的是京沪线。航班管家数据显示,2024年京沪航线发送旅客86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84%。但从总客流量来看,仍与京沪高铁5201.6万人次相距甚远。
对于高铁,马成光忿忿地说:“高铁这些年也是媒体在疯狂炒作,但是长距离出行无论在票价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民航更有优势,结果一边炒作高铁一边炒作飞机不安全,你们媒体就是有意针对民航。都是中国的骄傲,怎么这么区别对待。”

恶性循环下,各家航司断臂求生,更为急切的“降本增效”。今年3月,南航宣布将部分航班的座椅更换为更“节能环保”的轻薄座椅。这款新座椅被网友调侃为“刀片椅”,称南航简直是向“廉航”方向一路狂奔。
李妍青最贴身的感受是,所在航司正在极力压缩人力成本。李妍青说,自2024年以来,公司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大部分合同到期客服都被提前通知不再续约,这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变相裁员。2024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近百人离开岗位。“客服就这么些,补人也很少补,人工接入当然更难了啊。”
李妍青的合同明年到期,她有些犹豫现在是否该去寻找下家。“虽然我们当航司客服会一直骂OTA平台(注:提供酒店、机票、旅游产品等预订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如携程、飞猪、去哪儿等),但我们最后的出路大概也都是会去OTA平台。”
能从一线客服岗位熬出头,熬到“升职加薪”实属不易。在沿海一家航司工作的林淑瑜就是“熬出来”的客服之一。
2016年民航尚算得上“黄金时期”,林淑瑜入职担任一线客服,直到2023年才从一线转为后台工作人员,担任客诉处理专员,名义上是“客户经理”。林淑瑜说,客服比飞行员这种岗位更难有晋升空间。飞行员属于技术岗位,以前民航鼎盛时期,达到飞行年限、专业技能优秀,可能也要有一点“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有的情况下,最后转教员岗、领导岗是很容易的。
林淑瑜在公司近十年,周围同事换了又换,少说也跟五百多个同事共事过了。一线客服的上级岗位就像“萝卜坑”,想从一线熬到后台,是概率很低的事情。
根据自己多年经验,林淑瑜认为某种意义上公司确实更“喜欢”新客服。老员工工作熟练,处理速度越快接待量就越多,客服工资完全跟接待量挂钩,处理越多工资就越高。老员工工作熟练犯错也会更少,差错量是扣工资的一大指标。
新人处理速度慢接待量少,外加错得多,工资就不会太高。“对于公司来讲,错就错了,安排客诉处理人员跟旅客回电道歉解释一下就行,没什么大不了的。能多扣点钱是实实在在的,这不就降本成功了嘛。”

林淑瑜也表示,这些年明显可以看出公司正在全方位节流。至于这种节流是不是牺牲了服务质量,她认为这是必然的。至于不少中短途旅客从飞机转而优先选择高铁,林淑瑜觉得这是好事。“这样旅客少了,我们也没这么累了,都坐高铁去吧。”她说,即便旅客再少,有生之年也不会看到中国航司倒闭。
记者梳理疫情以来至2024年各航司财报发现,除全员亏损的2020年和2022年,其余年份均能保持盈利的只有廉航春秋航空。然而,与国有大航司相比,中小航司在寒冬中早已显现倒闭迹象。
据《界面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西安本土航空公司幸福航空宣布停航,成为疫情以来第一家停飞的航司。根据幸福航空内部人士消息,幸福航空还拖欠包括飞行员、空乘、地勤等各部门员工工资,最长欠薪达一年之久。不少员工为了自救,在航司停航之前就开始兼职跑外卖、做直播带货等。
马成光说,“放眼全球,除了中国,没有一家航司能连年亏几十亿还能继续,但在这里就是可以。”他对升机长不再抱有太高期望,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么混下去了,也没什么不好的。但也隐隐担心,再继续降本增效,自己还能混到退休吗?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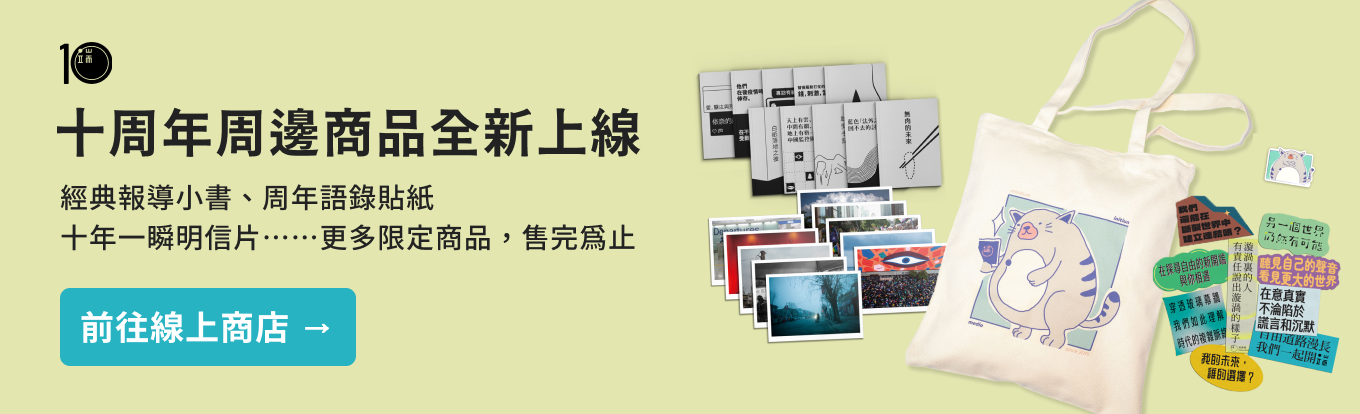



浮于表面的报道
來自介面新聞的報導:幸福航空的經營困境已存在多年,新舟60飛機利用率低、故障率較高,市場接受程度不高,因此幸福航空成本居高不下,收入提升比較困難。支線航空投資回報周期長,運營負擔也重,依賴市場補貼,但是民航支線補貼向大型航司傾斜,小型航司僅能分得少量資金。而且疫情後地方財政緊張,部分補貼未能兌現,加劇現金流壓力。
另外如果能找到地勤維修以及空管系統的人員訪問會讓這篇報導更完整,畢竟他們工作的質素與表現對於航空安全而言更為重要(且致命)
南航賣A380跟疫情後的航空市場沒有回暖的關係其實不大,主要牽涉到的是國內各大航空公司航權爭奪的問題。原本南航想把A380投入的航線最後沒有搶下來(好像是北京飛倫敦?)現有航線上座率又不夠。從買回來開始就一直在虧錢了。
延伸阅读:【从擦机尾事件看飞行员的两难处境?这背后隐藏了什么问题?-哔哩哔哩】 https://b23.tv/QnQUDK0
还真是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因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