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异乡的手艺人
“还是不太理想。”
在横滨的一家咖啡馆,杜杰在聊天间隙依然保持着关注国内院线票房的习惯。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电影摄影师之一,今年是他移居日本的第六个年头。
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到管虎、程耳,以及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来日本之前,杜杰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商业电影的蓬勃发展。在资本翻涌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银幕数和全年票房收入狂飙突进,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9年7月,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3》来到日本拍摄,浩浩荡荡的千人剧组,“惊呆日本人”的超大规模,加上横贯东亚历史的剧作编排,犹如这场盛世狂欢的缩影。
但身处其中的杜杰,已经隐隐有了危机感。这个市场虽然看起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除了头部的片子,大部分都赚不了什么钱。”积累了几次境外拍摄的经历之后,他决定尝试走出去看看。
借助《唐人街探案3》的工作机会,杜杰得以实地考察日本。此前的《唐探2》他也曾随剧组去过美国,但考虑到环境、成本和子女教育,他还是决定在日本留下来。这里只需要五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就能办理经营管理签证,获得在留资格。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他把留日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规划。

2024年,常年在幕后的杜杰初执导筒。他在日本拍摄的《椰树的高度》(The Height of the Coconut Trees)先后入围了釜山电影节和东京FILMeX。这部小成本的艺术电影讲述的是死亡、离去和由其引发的余波,有着纪录片一般的恬淡、静谧的风格,与杜杰此前以摄影师身份参与的商业制作大相径庭。
杜杰的选择并非个例。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统计,截止2024年6月,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两万人,比2019年增长了50%。关注中国中上层阶级赴日的《润日》一书亦成为今年日本出版界的热议话题,目前已达成第六次印刷。从一掷千金购买塔楼的中国富豪,到东京百花齐放的华人社群,后疫情时代的移民们被认为是显著有别于九十年代“新华侨”的群体。
杜杰坦言,拍电影是为了让自己的公司不至于沦为空壳,但日本独立电影的制作生态,也的确催生了他把自己想写的故事转化为长片的念头。十来人的剧组,没有美术,成本低廉。“日本中上规模的预算,在中国这些钱只能算一个小成本电影。”
《椰树的高度》的故事灵感,来自于杜杰在疫情期间对生死的思考。“疫情发生的时候,死亡离我们很近。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对死亡的看法都不一样,例如日本就会有三岛由纪夫的殉道式死亡、青木原树海的自杀森林。”杜杰尝试在电影中表达:我们当下的世界,其实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共同组成的。
现在,除了等待电影的上映计划,杜杰还在继续创作“人鬼神佛”系列的下一个剧本。不过来日本之后,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事业,如《独行月球》《唐探1900》的摄影工作。杜杰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客居异乡的手艺人,“我语言也不行,完全融入日本的规则也没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用外国人的视点去观察这里。”

喘息的空间
2019年,汪崎带着自己的长片《离秋》参加了First青年电影展。
这部讲述在日华人生活的电影几乎还原了他本人的亲身经历:父亲烟不离手,总想回国发展;母亲则努力打工,坚定在日本留下。“我记得小时候,我爸骂我不讲中文,他说你到底是哪里人,怎么搞得像日本人一样?看足球的时候,他会问我为什么给日本队加油,你是不是中国人?”
八十年代,汪崎的父母移居日本,他本人成长于九十年代的东京足立区。在很多日本人心中,当时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和青少年犯罪新闻,加深了对这里“不良少年多”、“治安差”的印象。临近小学毕业,父母终于意识到了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将汪崎送到英国。
谈及小时候的日本生活,汪崎将其类比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和行定勋的《GO!大暴走》。“我中学时特别喜欢《GO》。电影里有一个在日朝鲜人,喜欢上了一个日本女孩,他就假装自己是日本人,起了个日本名字。看完后我就感叹,哇,终于有人拍出来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我拍电影的话,很有可能会end up拍这种电影。就是我为了被认可,不得不很辛苦地去假装一个身份。”或许是这个故事打动了考官,汪崎最终进入伦敦艺术大学学习电影制作。
毕业后,汪崎回到国内发展。他并不讳言自己“才华平平”,只是一直幸运地有“贵人相助”。“如果不是在当时(10年代)国内那个环境,而是在英国、日本,我这样的人可能根本拍不成长片。”但同时,他也像一个外国人一样,在自己的母国面临着强烈的文化冲击。

“我去First的那一年。姜文导演是导师,我去听他的讲座,发现他跟其他人的交流我都听不懂。他的很多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就像在英国听Shakespeare一样。”
汪崎难以理解北方人的语言,也不了解国内剧组的相处习惯。由于常常被认为是不合群,他在国内屡屡碰壁。辗转多地的生活经历,让汪崎成了不同文化中的局外人。
疫情期间,汪崎一直住在上海,2022年冬天乌鲁木齐南路白纸运动之际,他离现场只有一个街区之隔。“我特地避开了这个。我一直很幸运,完全像一个外国人一样来到上海,做喜欢的事情。尽管也有不好的经历,但我觉得那些轮不到我来说。就像我关注日本的流浪汉,但也有很多事情没办法理解,我就保持这个距离,保持作为外国人的视角。”
2023年,汪崎时隔多年重回日本居住,继续从事着影视相关的工作。而他对流浪汉议题的关注,源自于刚刚完成的未命名新片。
这部电影围绕一位“无缘佛”(没有亲人或朋友的逝者)生前的日记,讲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性和一个从事支援活动的女性,借由探寻逝者身份的过程,思索被留下来的家人与友人该如何面对原因未知的分离。
本片的编剧之一是知名的华裔电影人王颖,他导演的《喜福会》等作品在日本也有相当的知名度。“王颖导演虽然是外国人,对日本文化了解不深,但他并不认为这会妨碍他在日本拍电影。他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同时继续推动创作,不拘泥于是否‘理解’某一文化细节。”
对汪崎而言,他的成长经历让他比很多外国人更熟悉日本社会的运转逻辑。“但有的时候我也偷懒,就利用这个外国人这个身份,在人际关系上留有喘息的空间。好在现在的日本,很多环境比以前变了,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日本人和我们的烦恼不一样⋯⋯”
在和张曜元导演聊他的新短片《祝日》时,他提到了与汪崎的童年经历类似的一幕。
剧组里有一位小演员,父母都是中国人,而他在日本出生长大,不太会讲中文,甚至有些抗拒开口。“副导问他,你为什么不讲呢?他就挺委屈的,感觉就要哭了。他妈妈过来跟我们说,他儿子小时候在学校里因为讲中文,有过不好的回忆,所以他不想去讲。我觉得至少还要再等一代人吧,也许三代以后就不会有身份认同的这个困惑了。”
《祝日》是张曜元近年的第三部短片,讲述一个在日华人家庭的足球少年从实训到落选的全过程。“是一个底层乱入了中产阶级,最后发现进不去,然后在门口张望了一下的故事”。
在此之前,他的两部短片分别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平遥国际影展获奖。这一系列作品除了均为华裔日籍演员阿部力主演,也都有强烈的直接电影风格,并和日华人相关的社会议题紧密相关:2023年的《中场休息》讲的是远赴日本打工的中国技能实习生;2024年的《相谈》则聚焦于日本残留孤儿的后裔,并且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取景,呼应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故土。
张曜元的这种电影趣味来自于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如《安阳婴儿》《小武》,也包括是枝裕和早期的电影《距离》《无人知晓》。因此,“我没办法像很多日本电影一样,天天喝着茶,吹着风扇,坐在窗边吃西瓜。我没办法对我身边的事情视而不见。虽然那些日本电影也是合理的,因为日本人跟我们的烦恼并不一样——至少不用为签证苦恼。他们跟我们看到的世界,那肯定就是两个世界。”

十年前,张曜元从大连来到日本求学,从本科一路读到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他注意到,疫情结束以后,大概是2023年左右,由于外国人犯罪不断增加,许多日本媒体也对相关事件大加渲染。“我老没事就逛日经新闻,下面评论区特别逗,说日本大米不够,涨价了,都是因为外国人吃的。这就是当下一些日本人对外情绪的缩影。”
今年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外国人议题达到了未曾有过的讨论热度,日本民间对“外国人日益增多”的恐惧也得以具象化。其中,日本新兴的极右翼政党,口号为“日本人First”的参政党以坚定的排外政策和日本中心主义立场,在年轻选民中博得了极高的人气,并且最终一举增加了14个议席,成为在野党中不容忽视的新势力。日本社会全面右转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对于在日外国人的遭遇,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我们在心态上是一样的无能为力。所以我想把这种情绪去展现出来。我们也想去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发现是徒劳。”
张曜元提到,《祝日》里小男孩被足球队拒绝时的说辞,来自于自己参加日本一个电影节的亲身经历。“被拒绝了以后,影展方面给了我一番话,我就直接挪过来用了。特别精彩,完美的台词,你没有办法去编出来。”
在那个电影节,张曜元原本志在必得的一个奖项却最终落空。“影展方面说,真的很喜欢你们的电影。但是,我们这个电影节选的是日本电影。你的电影里的演员是中国人吧?台词也有汉语,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你这个电影是不是日本电影,就没有把这个奖给你,实在抱歉。”
类似的本土保护主义还有很多。2006年,由日本文化厅委托、映像产业振兴机构运营的“年轻电影作家人才育成”项目启动。旨在面向年轻电影创作者,不仅通过工作坊和实际制作研修,传授打磨创作个性所需的知识与专业的影像制作技术,还将通过设立放映等作品发表的机会,为他们今后的创作活动提供助力与支持。近年崭露头角的山中瑶子、团塚唯我等导演也都入围过此项目。但其入围标准中明确要求日本国籍或日本永住资格持有者。
尽管张曜元还在准备自己的长片计划,但他已经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了许多。“我从来没想过要进入日本的这个体系里,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觉得能拍一两部,把自己想讲的讲完了就很好了,没必要在这里耗太久。毕竟,生活中有太多事比电影重要了。”

长片与短剧
东京艺术大学映像研究科的电影专攻于2005年开始招生,效仿法国的电影院校设立了导演、剧本、制片、摄影、声音设计、美术和剪辑等七大专业。在日本上世纪的制片厂年代,电影方面的人才通常由各个制片厂培养。随着制片厂体系的崩溃,日本电影工业的萎缩,人才育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向欧陆作家电影的风格。
近年来,赴日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增多,东艺大也涌现出了其他来自中国的毕业生。如张钰的《杀死紫罗兰》入围了2023年的平遥影展,杨礼平的《灰烬》被选入202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Nippon Cinema Now单元。这里有黑泽清、诹访敦彦、盐田明彦等导演任教,更因滨口龙介毕业于此而扬名。然而,受限于日本市场自身的规模,如果电影人追求更高规格预算的制作,也只能另谋出路。
在日本,电影业早在经济停滞之前就开始衰退,不再是深度内卷的艺术修罗场。不过,各个圈层依然保持着礼貌的界限,不会去轻易打破。有经验的留学生会根据各个电影节历年的入围状况,判断自己作为外国人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更多的人则面对这里的文化壁垒,选择离开日本或转投别的行业。近年掀起的短剧出海热潮,便成为一些电影方向留学生新的就业出口。

导演余园园也参与过日本短剧剧组的拍摄,在她看来,这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她先前合作过的一位日本演员原本只在独立电影界小有名气,“最近因为短剧爆火,接到了更多的工作,也能保证日常的生活”。
与此同时,她自己的电影《丈夫的房间》(夫の部屋)8月将在日本上映。
受滨口龙介《驾驶我的车》的启发,余园园写下了这个戏中戏嵌套的故事:一位舞台剧演员,心怀丈夫逝去的悲痛,同时还要准备《海鸥》的公演。在丈夫的房间里,她与另一位与丈夫生前有情感纠葛的女性展开对峙,契诃夫的文本由此与现实产生关联。
2020年,余园园进入立教大学。这里曾因九十年代的“立教新浪潮”而盛名在外,以黑泽清、青山真治等导演为代表的美学风格,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日本独立电影。
“那时候因为上网课,没办法接触,唯一可以对面上的课是Jareo老师的workshop,他的课上探讨如何与人不触碰到的接触,也会探讨物理以外的时间和空间。就比如带我们一起走路,如何和zoom里的人触碰。他让你用身体的感觉,去颠覆你对时间的认知,甚至忘记时间这个概念。”这种经验,也演化成了《丈夫的房间》成片里那种缓慢电影的风格。
为了完成毕业作品,余园园在立教上课之余,还报名了面向全社会招募学生的“映画美学校”,这是一所独立于传统高校体系的民间电影教学机构,涵盖创作、表演和各种技术部门。目前风头正盛的三宅唱便曾就读于此。
“进入大学院以后,我知道了一件特别惨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拍长片才能毕业。我那时候才来日本,语言都不太通,作为一个外国人,根本没有条件去拍长片。”而在映画美学校的剧情片课程(fiction course),不仅可以拉到人,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即每个班会选一到两个本子,由学校出资拍去一个40多分钟的中短片。余园园递交了《丈夫的房间》剧本雏形,但最终没能入选。
“我很不服气,我也不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我觉得按本子和我拍的东西来说,我不应该输。”于是,余园园在接下来的两年磨出了剧本,并独立拍成了长片。
在日本,像余园园这样一边打工存钱,一边实现自己电影梦想的人不在少数。“日本的独立电影历史深厚,自成一种文化。即使没钱、没有关系,也可以拍出一个片子来,作为一个创作者,哪怕三分钟你也想拍。滨口龙介导演也说过类似的话,慢慢地去积累拍摄经验,可能有一天你就会发生质变。”

由于电影中有许多戏中戏的部分,剧组就租用了市民文化馆的场地,四、五千日元一次,每次排练四五个小时。《丈夫的房间》的两位主演是她在美学校的同学,女主演还是一位上班族,所以她拍戏的时候,会利用中午休息的一小时和剧组进行视频会议。
不过,电影即使拍完,距离上映也还有很远的距离。在东京的一些独立院线门口,时不时能看到新人导演亲力亲为地为自己的电影做宣传。“如果跟电影院没有关系的话,你需要像无头苍蝇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给影院打电话。如果没有在PIA(ぴあ)之类的电影节获得曝光机会,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把它上到电影院,但这种真正能去到电影院的还是很少,大部分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了。”离开咖啡馆时,余园园也不忘记给老板发几张宣传单。在离这里不到两百米的一家独立院线,她为自己的电影争取到了两周的上映时间。
2018年,有过几年工作经历之后,余园园来到日本。对于想出国换换环境的人而言,这里是一个相对经济的选择。最初她读的是早稻田大学的日语项目,没有固定的同学朋友,于是写了一个滨口式的日本故事。但随着在日本的时间越来越久,她也想把对identity的思考融入到今后的创作中。
《丈夫的房间》是一部诞生于疫情期间的作品,用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2020年以来,余园园长时间滞留在日本,“我的外公还有好朋友去世了,但是我没法回去参加葬礼。很难受,也很后悔,连最终一面也见不到。”
去年,她回国上班了一段时间。相比于日本社会的平稳,国内的变化让她有些难以适应。“我一直觉得疫情没结束。特别是这次回国以后,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了,大家太依赖微信去交流,很难线下见到面。”

我所身处的世界
2022年5月,格桑梅朵从疫情尚未结束的中国来到日本学习电影。
她来自藏族自治州一个偏僻的小镇,成长轨迹遍及山村、汉藏杂居地带和大都会。童年时期奶奶和朋友所讲述的山灵鬼怪的故事,让她后来在拉美文学里找到共鸣。“在藏区也常会遇到有人像马孔多里的吉普赛人那样,挑着担子带来一些新奇的东西。”
中学时,由于在少数民族高中,身边都是少数民族,格桑梅朵并没有想过太多关于身份的问题。“但是来到日本之后真的截然不同。我很难想象一个康巴人走在日本的街上,我觉得可能会像是《幸福的拉扎罗》里的拉扎罗来到城市里面一样。”
在日本,万玛才旦是当代最知名的中国导演之一,不仅多次入围东京FILMeX,他的遗作《雪豹》还获得了2024年东京电影节的最高奖。
格桑梅朵记得,自己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从万玛才旦的《塔洛》开始。“那个时候在北京的高中念书,但已经有一些不适应了,我一直不知道这种裂缝是怎么样产生的。但是那次我看完他的《塔洛》之后,我就忽然明白了。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有太大的差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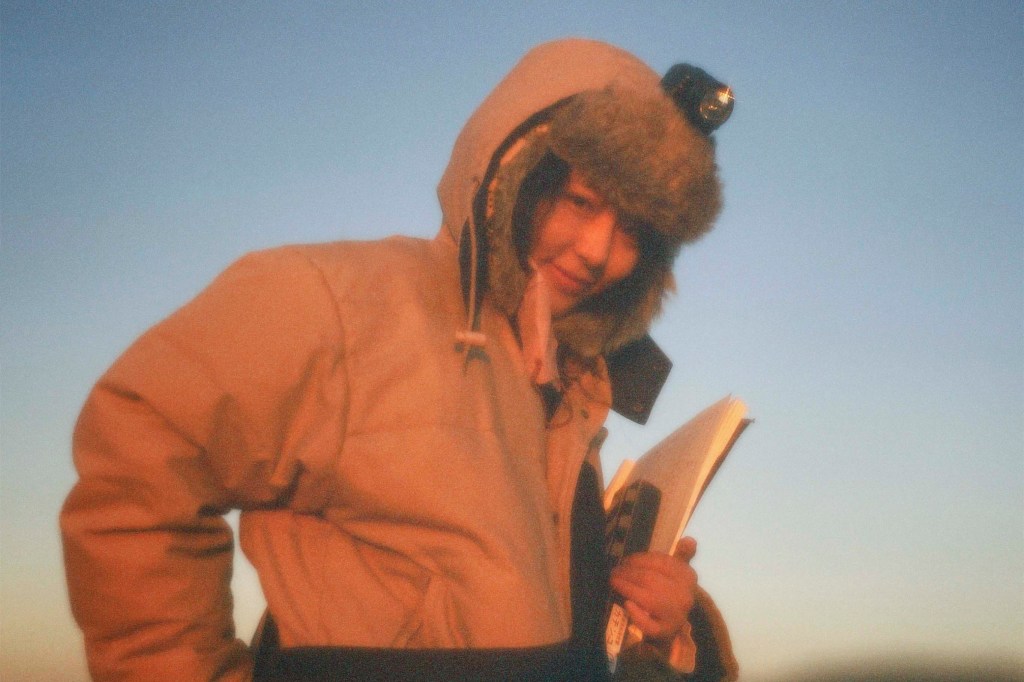
现在的格桑梅朵日常都会穿藏服,她觉得去到外面之后,就越会想起在藏地高原成长的前十二年:在传统藏式家庭学会说藏语,喜好古朴的藏式食物,在藏居小楼里受到庇佑。
对于她而言,日本的文化吸引力除了来自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更多也来自黑泽明的电影,尤其是《乱》《蜘蛛巢城》这样,将西方文本本土化之后依然极具魅力的作品。“我是藏族人,肯定想拍一个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比如藏戏。我觉得日本在发扬传统美学方面做得非常好,如果也能够在电影里面去用到的话,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对象。”
这个七月,格桑梅朵回国参加了电影节的训练营。她给我看了最近在写的短篇小说,这是一个有着马尔克斯风格,融合了AI、梦境、高原和大海的藏地故事。
“今年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拍这个。”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