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十岁了,过去十年,谢谢你一路相伴,让端得以成为你信任的媒体。我们即将推出十周年页面,回顾这些年来,世界的变与未变。同时,十周年的一系列周边纪念品,包括精选文章的小册子、明信片及实体贴纸快将准备就绪。在等待的路上,欢迎你参与将会推出可视化报告的年度用户调研,以及预览全新上线的会员限定新闻信“走进编辑室”。现在加入会员,首年限时75折,立即解锁更多会员专属内容。
亲爱的读者,
今天,端传媒十岁了。
近代许多人纪录的十年,是社会运动与进步思潮沸沸扬扬的1960年代。学运领袖Todd Gitlin 写了一本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一方面写那个年代改变世界的理想,一方面也写失控与崩坏的痛。作家Joan Didion写过一句关于60年代的名言:“60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那天曼森(Charles Manson)指使他的追随者闯入荷里活山上的豪宅,杀死了导演波兰斯基年轻美丽的妻子,当时怀孕八个月的演员Sharon Tate以及她的几位朋友。
这场谋杀血腥、荒谬,毫无政治逻辑,也没有明确目的,却发生在所有人以为“爱与和平”正在胜利的年代尾声。
“60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是因为那些在反战、性解放、反主流文化运动里活得最起劲的人,突然被提醒:暴力不是体制的专利,迷信、狂热与邪教也可以披著“自由”的外衣;曼森不是嬉皮士运动的产物,但他是运动的阴影。人类社会经历的,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就像爱尔兰诗人叶慈在一战后写的:The center will not hold. Things fall apart--混乱总是像风暴般卷来,中枢崩解,事物纷纷瓦解。
世界似乎一直如此荒谬,语言无用共识崩解,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不是例外。那么,端作为在这样的环境生长了十年的“树木”,到底有甚么意义?
对比《纽时》的173年,《卫报》的203年,甚或香港媒体如《明报》的66年,端的十年好像算不上甚么。又或者,对比宇宙的138亿年,不管我们做了甚么,没做甚么,有过或没有甚么热情或理想,人生有多少痛苦与挣扎,人类的上帝掷不掷骰子,宇宙太初毫不知晓,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太阳在60亿年后仍会膨胀成为红巨星,地球依旧会被膨胀的太阳吞噬。十年,连给宇宙做一场梦的时间都不够。
但在森林里,一棵长了十年的树上可能栖息著上百种鸟、昆虫、真菌、微生物,牠们以它为家、为食物来源、为繁殖场所。而且,真菌菌丝与树根交织,树木会透过这系统彼此传递水分、糖分、甚至“压力讯号”:有虫害来袭时,这棵树会“通知”其他树提早释放防御性化学物质。在这风雨飘摇,充满许多不能再讲﹑不堪再讲的记忆的十年,端找到了一个发芽成长的空间和许多读者,最重要的还是,它在重重限制中生了不浅的根。
如此十年,我们或许还没长成参天巨木,但够让我们和身边的林木彼此缠绕,抵挡烈风。
有许多读者在正在进行的年度读者调研里跟我们说,看端是为了理解世界如何运作,了解人如何生活。所以我们还在问,在这个纷乱的,“things fall apart”的年代,人如何书写自己的故事。十周年企划中,我们的代孕专题带读者去到高加索的格鲁吉亚,看人类最基本的,对繁衍后代的渴望,如何带动了世界另一端的灰色产业,也问及代孕和生殖科技带来的道德难题。我们的台海专题书写人如何面对可能逼在眉睫的战争冲突,而大陆的虐猫群体专题,写的不止是晦暗的大环境如何滋生出“恶”,也探讨人类社会中“恶”的本质。
而思想专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探讨我们心底里都在问,但却不知从何说起的问题:现在到处都是战争、玻璃心、仇恨、恐惧,人类怎么团结?这个时代讲团结,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是什么?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空泛的政治语言,那知识份子说的“地球村”不也是个谎言吗?加沙的人道灾难无日无之,共同体的建立是不是只能靠暴力?气候危机没有共同体如何解决?而我贡献的一篇,将探讨人类作为动物,我们的本质是暴力的吗?是推翻了这个共同体幻想,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希望?
说起希望。十年,也是贝多芬最后一首交响乐,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第九交响曲”(贝九)首演,和他上一首交响乐作品“贝八”首演相隔的时间。那十年间,贝多芬完全失去听力,只能以纸笔和人沟通;他也愈来愈孤僻,说过自己“急不及待想面对死亡”,甚至写过遗书给弟弟,表示活下来只是为了继续写音乐。
1824年5月7日,“贝九”于维也纳的剧院公演,最后的乐章既终,全聋的贝多芬却浑然不知剧院掌声雷动,要人提醒才从指挥台上转身面向观众。整首交响曲的开头,像是一场从虚无中爆发出来的地震,乐音模糊不清,调性未明,像一种无法命名的痛苦,一种在世界崩坏时试图抓住甚么的挣扎。动人的第三乐章缓慢而抒情,是贝九里最私密、最脆弱的片段。它像是苦难中的喘息,是对温柔的渴望,也是对世界的深层凝视。
最后一个乐章,是我们在幼儿园就学会的“欢乐颂”。一开始,贝多芬把前三章的主题全都拉回来,但之后一把高亢坚定的人声加入:“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朋友们,我们不要再重复这些声音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不是因为痛苦消减,不是因为前方有乌托邦,是因为即使走过苦难、混乱与无数怀疑,人仍可以选择希望——不是因为它轻而易举,也不是因为它显然正确,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事实上,贝多芬在“贝九”的成功后依旧贫病孤苦,但那个超然的﹑跨越的希望,对实现自由的追求,至少和痛苦一样真实。
最近看了揭发台师大女足抽血案的台湾女生简奇升的访问。她说起自己为甚么成为了吹哨人:“为甚么我好像能比别人关心多其他人一点,我觉得,是因为我被好好的爱过。”被问及如何处理巨大的媒体和社会压力,她说,“喝酒啊,”但后面又补了一句,“文字啊,我觉得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大。”
这个二十三岁女生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人生处处都是枷锁,我们没能选择是否出生,在哪里出生,没法选择父母﹑家人,也没法选择自己的身体和身处的社会,但我们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端十年了,这不是很多人说的,是一个“奇迹”,那是很多人日复一日作出的选择:选择留在这里,继续写生而为人的故事,让人在这个“不得不如此”的世界中找到归属。
这十年世界翻天覆地。有时我也丧气地说:“没希望了啊”,或者用我的母语广东话说:“算罢啦。”但爱就是一天天的,克难地,屡败屡试地,重重复覆地,沉闷地无聊地,作出一样的选择:即便世界如此,或者正因世界如此,我们才选择对晦暗的年代说,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
这就是端在这里的最大理由。平凡而深沉。
端传媒总编辑
陈婉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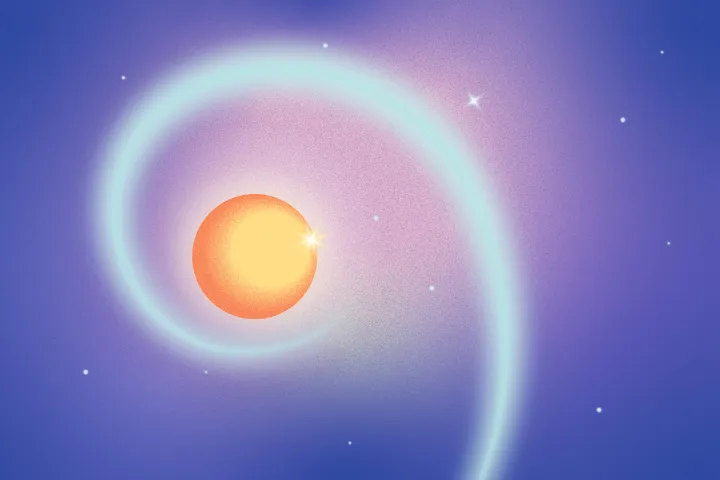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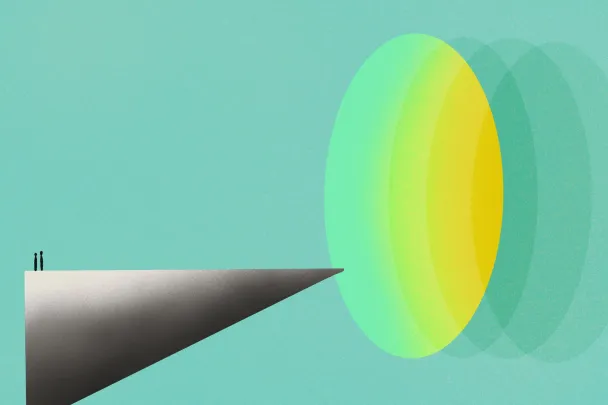
感谢端传媒这十年以来的努力与付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看清了当下的现实。
感谢坚持!同离散,同共勉。
小端生日快乐
祝贺端十周年快乐!感谢你们带来的全面深入多角度的华人世界报道,让不管身在何地,感觉和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连接,也深以华人身份为自豪。
陳婉容是端的best mind,期待她能帶端走出新方向。恭喜十年!
感謝 端陪我走過香港動盪的十年。
上星期參觀展覽「Pictograms」,其中一塊展板展示古埃及聖書體和中國商代甲骨文。古代人相信文字有神力,可以保佑健康,獲取財富,阻擋惡運。現代人已不相信文字的「法力」。即使如此,當我閱讀 陳婉容的報導,仍然感受到文字「力量」的巨大。
恭喜你
祝 編安。
久违地收到端的邮件,在地铁上读完了这封十周年的信,跟端相识于「尚未付费时」
恭喜端的十岁生日!!!
恭喜十年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