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分上下篇,上篇为《于渊:“自古以来的中国”,真的存在吗?》。
在晚清到中华民国之间,民国虽然继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国疆域,但是无论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何,疆域的性质已经完全变化了──“领土属性”的转型,才是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的本质转型,这一时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所提出的“五族共和”,代替了此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的就是防止疆土的分崩离析。
回望辛亥:为什么五族共和?
这是孙中山提出的著名命题──但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命题。他的最终理想,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汉族主导的民族国家,而“五族共和”,实则是“同化”其他民族。
辛亥之前,革命还是改良一度成为社会争论焦点。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 》中,历史学家张灏追溯了四个分属两派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意见,核心的是,革命派关注汉人的主权问题,立宪派则关注汉人的权利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产生了纷争。立宪党人主张整合国内各民族,而革命党人则认为,必须以站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
如前文所说,在晚清,中国已经朝向民族国家开始转型,但那时候的中国领土,不是“雄鸡状”,而是海棠叶形状──
“勾勒这片秋海棠叶的国际边界线不再是中国与个别邻邦之间的私相承诺,而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公开约定;不再是天朝帝王意志的体现,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实践;不再是模糊、游移的边疆地带,而是相对固定的国家分界。”
过去的边疆政策,其实质是隔离中国本部与疆部,而现在,则开始使用改土归流、移民实边、蒙藏建省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交通建设等手段,对帝国疆域内满、汉蒙、回藏五大区域进行整合。
中国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是一项复杂、持久、庞大的国际工程。首当其冲的一个间题是,何为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还是多民族的中国?
这一点,在20世纪初争议极大,孙中山自身也摇摆不定,并且更倾向于汉人为主的观念;在其实践中,五族共和也从未真正实现。
章炳麟则更加极端,他不赞同继承异族王朝的疆域,而要恢复到汉、明时期的疆域,那才是汉族正统。于是在章炳麟眼中,在清朝与中国形同异国的缅、朝、越,变成中华民国“必当恢复”的领土;而在清代内附且至清末已明白划在中国近代国际疆界之内的蒙、回、藏部,反而成了可以“任其去来”的“荒服”。
这种异想天开,其实是基于章炳麟对汉人民族建国的构想,因此,他在民族构建与疆域规划问题上,“舍近(清)求远(汉、明),为中华民国设计了一条穿越时空之路。”
这种大辩论之下的革命实践,在辛亥革命之后告一段落,民国仍然继承的是大清的疆域,而非汉明的疆土。
“五族共和”的公式,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各方妥协下,成为清朝“五大子民”的进化体──但从此后中华民国的发展看,刘晓原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不真实的命题之一”。
首先,中国国内民族的数量远远多于五族;其次,五族共和是汉、满精英的妥协,并不是五族之间达成的。五族共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将清帝国五域维系在民国之内,而中国实际上却进入了以分离为开端的大分裂时期──外蒙直接独立,最终成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书,彼时他表达了强烈的国家整合意识,强调民族、领土、军政、内治的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然而,这些目标在民国时代,一样都未能实现。因此,回望辛亥,刘晓原认为,辛亥的成就在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正名和恢复主政地位,并使中国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进入现代国家之列。”而其失败之处,则是民国“未能有效地继续晩清开始的国家整合,顺利地完成从帝国到民国的在疆域、人民方面的继承。”
康有为曾预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但不同于责骂革命派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的杨度,康有为承认,“蒙、藏之自立于革命之前,则不能尽责于今政府矣”。或许,没有人能够回答,倘若没有辛亥革命,而是立宪成功,蒙、藏将会是何种情形?
在共和与立宪的争论中,也出现过一种折中的“帝国共和主义”,主张留皇帝虚名,行共和之实──但这种方式,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辛亥革命的实现,迅速导致了蒙藏的解脱,并且按照王柯所言,以“勤王”满清的借口,脱离了民国。
在王柯那里,革命者的民族建国论应该负首要责任,而刘晓原则认为:“边疆动荡或许是中国在新的政治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所必须出的代价,历史研究不应因此而苛责1911年致力于缔造新国家的革命者。”
其实,对于1902年的孙中山而言,他和章炳麟没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清帝国的疆域,他主张是“因其势顺其情”,而非一定要继承清帝国的疆域。因为在孙中山眼中,“无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而“无可分割”的则是在过去五六百年间“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
而10年以后,孙中山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言论,就受到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他在这时候又认可了这一方案,从而主张继承满清的海棠叶疆域──到这时候,便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形容的,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疆域,实质上是“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因此,这种中国大一统观念在20世纪的延续,刘晓原认为,“更应归功于在世纪之交寻求稳定的满清政府和立宪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党。”
“五族共和”实现了吗?
但在民国以后,孙中山逐渐显示出对五族共和的摒弃,他主张的是“五域整合”。他认为蒙藏地区的人,并不懂什么是共和,所以才屡屡发生背谬民国的事情。这和立宪派的观点类似,辛亥以前,立宪派的观点认为,满、蒙、回、藏尚未进入“国民社会”,因此中国不可骤行共和制度。
不过,孙中山放弃“五族共和”的最重要原因,并非因为边疆地区的落后,而是深感“中国本部政治局势的糜烂和汉族自身国民程度的久缺。”刘晓原认为,使孙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鞑虏”之驱逐和“中华”之恢复,带来的却是五族离散,中原板荡。他不得不在失去满清这个对立面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民族主义,以为继续进行革命的主导思想。
而孙中山的改造结果便是,“将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从中国之内转向中国之外,并使民族主义的主旨摆脱五族多元观念的干扰,重归华夏一元的正统。”因此,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手稿中,孙中山指斥,“五族共和”为辛亥之际“无知妄作者”所创,为官僚旧党所附和,荒唐之极。
从此以后,孙中反对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强调必须大讲汉族的民族主义,使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大民族国家。刘晓原发现,孙中山在1919年以后的讲话和文件中,以及在后来广为流传的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将汉族民族主义提升到“国族主义”。
孙中山从此变成了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者,他认为,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都是一个民族组成,在演讲中,他愤然汉族以四万万之众,却未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
而对于其余四族,在孙中山眼中,就成为了掺杂在汉人当中的极小部分人口,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此时还在列强控制之下,将来只有在汉族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拯救。同化为汉族,成为了孙中山此后的核心思想。
而共产主义在一战之后的到来,则又让中国的民族思潮经历了新的碰撞。
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苏俄谋华等等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以后,“民族自决”开始进入中国政治。但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面向边疆地带使用“自决权”和“自由联合”时,都是为了取得莫斯科对中国革命政党的信任──共产党自不必说,国民党在改组后,也变成一个半列宁主义政党。
刘晓原认为,“在两党以后的历史中,这些语句从未超出宣传上的意义,在实践中带来的只有尴尬。”这是因为,两个新型政党以这种列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国早已大分裂。而至此以后,刘晓原认为,独立思想者的大辩论时代也成为过去,民族将被党族所代替。
在这一对“五族共和”的理解、扬弃的发展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国共,其出发点,都以汉族为中心。而孙中山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缔造者,在其后,虽然显示出从孤立的汉族立场,转向包容他族的国族立场,但其族群政治的出发点,基本延续了辛亥前革命党的一元立场,因此同化政策才是孙中山后期的核心。这种坚持,到了苏俄影响传入中国,并对国民党造成深远影响后,也没有改变。
孙中山唯独在国家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上,全盘接受了曾经的论敌立宪派的观点,在事实上继承了清王朝帝国。但这种继承并非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结构,而只剩下疆域的继承,如刘晓原声称的,“辛亥妥协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汉族为中心的五域统合理念所取代。”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族共和”在事实上,确立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族。在此后抗日战争中,无论国共,都以民族主义为大旗,而建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更加强了汉族主体政治的意识。很多年以后,人们也就淡忘了,1911年以后的“五族共和”,只是东部中国政治精英的短暂共识,“蒙藏回部不仅未参与,甚至用勤王分裂等行动,表达了反对。”
刘晓原看到,尽管“五族共和”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也没有得到蒙藏回部的认同,但其仍然承认了各族“心理”诉求的合理性,而这种承认,在以后中国政党的纲领中不复存在──国共在野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边疆民族的分离心态和自治要求给予肯定,但在自己主政以后,都调转枪头,不再提及民族自决。
而理想的“五族共和”,直到现在,也终归没有真正的实现。
中国边疆变化至今未最终结束
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族共和”变成了民族区域自治,但从根本上,中国仍未走出“边疆中国”。
在刘晓原看来,无论中外,中国现代史都长期缺乏对“边疆”主题的研究,中国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如何被帝国主义破坏,如何丧失土地,是一种“失地学派”。而西方学者则把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从帝国角度研究民族冲突,是一种“帝国学派”。
但这些学术作品,并未对中国边疆的地位、属性,以及作为边疆国家的中国有更多思考。
在历史上,中国一直具有“边疆国家”特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概括道,中国历史的边疆特征,要么是边疆及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要么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取得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
所以中国从来不存在“自古以来”,相反,自古以来,中国的边疆都处于变化的过程,并且成为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往或隔离、同化或抵抗、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1890年宣布终结“开拓者边疆”,距离美国建国100年以后。而中国的边疆变化,则到如今仍未最终结束。
中国到目前为止,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切实的多民族共同体,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被国族化的汉族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族群政治并未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从民国到如今,继续延续着。
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按照意识形态,他们本不应成为民族主义者,而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开展阶级斗争,超越国境,超越民族。在其创始之初,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是苏俄谋华的一步棋子。刘晓原分析,在那时候,“共产主义者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边疆人民的民族自决。”而这也被认为是针砭中国顽疾、回生中华民族的良方。
是毛泽东的革命策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自然而然引领了中共的本土化。到抗日战争时期时,民族主义不再是共产党人批判的资产阶级陷阱,而是要与国民党竞争取得民心的旗帜。也因此,毛泽东在1935年曾公开对内蒙古宣称,“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的组织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到了1938年,毛泽东则在《论新阶级》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各民族面已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新的表述里,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这一政策主张延续下去,至此以后,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与中国国家的民族化,仍在进程之中,并且比之于积贫积弱、处于动荡世界中的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境遇好得太多。
在1949年后的两年中,无论是政治还是领土,中华民族都实现了对中国东、南各省以及西、北边疆的全面覆盖。刘晓原评论道,“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了国民党所未能做到的使中国从政党观念,向民族实体的扩展,由此继国民党打造党国之后,完成了党族的构建。”
内蒙的自治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成功经验,亦即“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实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政治同质化的重大进展。”于是,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中产生的《共同纲领》“代宪法”,宣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引入,也导致了中央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确认,最终确定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在直接的政治结果中,55个少数民族的确认,“有助于淡化诸如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区域的特殊性”。
苏联领导人后来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基本是不错的。中共领袖和其敌对的国民党前任,在边疆问题上没有更大的差别,而是同样决心继承清王朝的遗产。
民族区域自治是逐步实施的──在1949年以后的五年里,内蒙古是一个自治区,新疆是一个省,西藏是一个“地方”。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
但这一制度并未更长久的坚持,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回避的宏伟目标。而这也导致边疆中国的实质,并未得到改善。
刘晓原分析道,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仍然存在三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边疆民族其实大大迥异于内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因为它们都被称为“少数民族”而消灭。而区域自治取代民族自决,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对于边疆分离主义的克服,但是否能取得各方的认可,则是未解的难题。最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目标,使得边疆与内地都最终实现政治同质化,这注定导致原本边疆与内地合作的气氛变得紧张剧烈。
文革期间,这种冲突变得更加剧烈。而拉铁摩尔对于中国是“边疆中国”的论断,则仍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边疆政治的争执以新的方式延续。迄今为止,民族边疆与中国内地被一种超民族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但反应的主要是中国内地汉族的政治意志。
也因此,尽管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自己的国际边界,“然而,在过了一个甲子之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边疆状态依然在延续。”
刘晓原在本书终结处,并未给出如何走出边疆中国的方式和时间,而只是给出了美国的经验:美国用了近120年才结束自己的边疆状态,变成一个整合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的两倍时长。
至少现在看上去,边疆中国,仍然走不出这幅员辽阔的边疆。
《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
作者:刘晓原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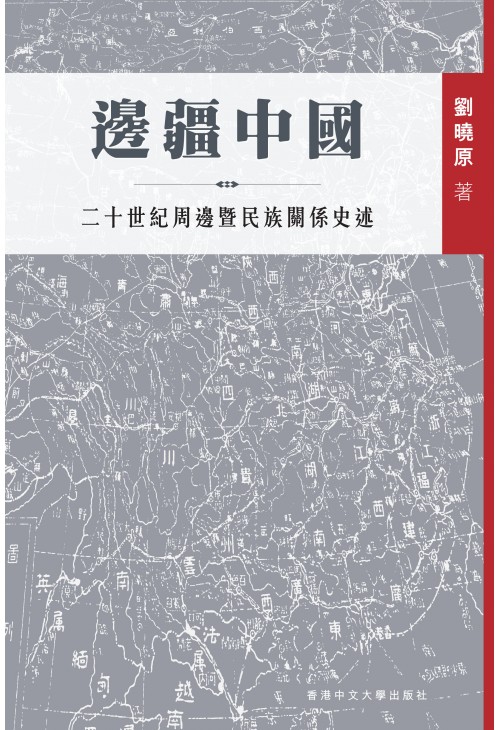
(于渊,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

我也感觉写的有点乱,试着就两篇文章解说一下:
近代以前的清政府对于边疆的认知大概是这样的:一圈卫星国(藩属)形成“众星拱月”。有敢对抗的,灭掉,扶植傀儡政权;还敢对抗的,灭种,然后实施军管(如准格尔汗),核心区域(汉本部十八省)实行中央集权。注意清政府此时没有明晰的边疆概念,军事管理不等于建立行政区划,因为满清的政治理念很落后的,尚停留在部落(八旗),东北到清末才设省。上述构成了所谓“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边疆和领土概念模糊。
而到了近代,外藩外国化,就是卫星国被视为万国之一,平等的民族国家,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内藩内政化,指清朝对于距离近的,效仿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范式,“确立近代绝对主权”,这样就构成了海棠叶的领土版图。不过,后一个不能算完成,清朝就拜拜了。
上文表述的是大清疆土的形成和治理,满清用的是分而治之的方式,制造了一种边疆和民族隔阂,从而为后来整合边疆、民族的困境埋设伏笔:中国至今更像是一个民族的马赛克,而非民族的熔炉。在中国转换为民族国家的过程时,矛盾加剧了。
进入民国,民族主义兴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单一的“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帝国,这就是“五族共和”,把五族都合并成一个,走这条捷径解决民族整合和疆域继承问题。不过这个帝国实质上是汉族人占统治地位的翻版大清,所以蒙藏作为满族盟友,并不买账。结果孙中山到了后来,已经有点中国法西斯的味道了。
至于中共建政,基本一脉相承,只是采用苏联的民族自治区,给边疆民族一点特权,放长线钓大鱼,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百年以来,上台的执政者都在想怎么保持领土完整与权力集中。边疆既然不属于边疆的民族,这些民族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了。
寫得有點亂,看得費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