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harlie Kirk遇刺身亡几个小时之后,一个问题立刻引发激烈争辩:他是一个落实民主精神的对话者吗?一方面,不只右翼的评论人经常主张Kirk用辩论说服人,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就连知名的自由派评论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Erza Klein也表态,认为Kirk在这个时代的定位是“以正确的方式实践政治”,主动与意见不同的自由派对话。另一方面,不少泛自由派、进步派的评论人则无法接受这样的定位方式;他们强调Kirk的立场对许多弱势群体充满敌意,对自由派而言,他所谓的对话充其量只是挑衅,甚至经常已经构成威胁。
然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立场其实共享同样的前提:不论是哪一种定位方式,人们经常都把目光放在Kirk与自由派的互动之上,争论的只是该将之理解为有建设性的对话,还是无建设性、甚至具危险性的对抗。
但是,著眼于他和自由派的互动,是理解Kirk最恰当的方式吗?他所留下的主要“遗产”,真的是他和自由派对话/对抗的尝试吗?实际上,Kirk创造的事业与其说是在和自由派对战,更重要的特质其实是取代了既有保守派组织在青年之间的影响力,协助特朗普在近十年之间垄断共和党。是Kirk这样的人和特朗普合作,共同定义了当代身为美国保守派、特别是保守派青年的具体意涵。
具体而言,当Kirk在大学校园内发展学生组织时,直接被挑战的并不是泛进步派的学生团体,而是各校共和党社团等其他既有组织。再举例来说,当Kirk率先邀请凡斯(JD Vance)担任节目来宾时,他并不是要协助凡斯向自由派宣扬关于婚育、家庭的信念,而是要提高凡斯在MAGA派的声望,终于协助凡斯成为特朗普所指定的副总统人选。几周前,当Kirk以谈笑风生的风格运用基督教的语汇,在节目上呼吁泰勒丝(Taylor Swift)婚后必须“顺服你的丈夫”,并且要她“抛下女性主义”、去生个孩子时,他也显然不是在和泰勒丝传教,而是在向自己的听众重申两个阵营的价值观差异,并且用“想想对面的人听到这种话会有多生气”来让自己人感到痛快。
对自由派而言,Kirk只是另一个张牙舞爪的MAGA代言人,只不过特别有名而已,角色用任何立场近似的网红都很容易取代。论者究竟要将其所作所为定位为对话或是对抗,其实只是标签问题──假使换成任何一位极右翼网红在那天被枪杀,来自自由派的评论都不会差异太大。相反地,他在保守派内部承担的角色,才是真正无可替代:在每个世代,美国右翼都有这样近乎教父般的角色,虽然自己从未担任民选政治人物或体制内幕僚,却能够左右共和党籍总统的决策,并且在体制之外透过在那个时代的媒体和组织工具上有所创新,定义身为保守派的内核何在。
而Kirk就是这样一位新世代的教父接班人,直到他被枪杀的那一刻为止。

“夺回整座大学校园”下的“绩效指标”
在近十年,Kirk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庞大事业,成为右翼校园组织的第一把手,也成为特朗普信赖的外部策士,是在MAGA圈内重要的话事人,足以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布局和选战策略。而即使只用最狭义的方式理解这位“创业家”,Kirk也都是成功的。从2022年起,他所创办的“转捩点”(Turning Point USA)年度营收就已突破8千万美金──相较之下,在特朗普当选的2017年,该组织的年度营收“仅仅”有8百万,等于在短短五年内,年度营收就已经来到原先的十倍之多,而这还不包含其所衍生的竞选志工动员组织,以及专职募款和政治捐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不过,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倒是维持一致:除了一年以外,组织都有超过98%来自捐献,金主每张的支票金额经常都是五位数甚至六位数;若以今年年初特朗普就任那场晚宴,地点定在离首都不远、由特朗普拥有的维吉尼亚州高尔夫球场上,光是入场门票定价就在5,000至15,000美金之间,才得以和凡斯、特朗普的儿子Don Jr.同场,而特别的VIP更是在进场前就已支付更高的金额。
而从一开始,他对金主最大的号召就是他在大学校园上的战功,是他怎样在上千座校园上建立分会,打造保守派青年的网络,可以在校园上让右翼的声音不容忽视。比如,他们在2016年年底推出的知名企画是“教授监察名单”(Professor Watchlist),一上线就列出全国约两百位教授的姓名,“揭露”这些教授“散布左翼宣传”的言行。列名于第一批名单的当然有谈论“白人特权”之类概念的“进步派”教授,但举例而言,也包含一名在德州大学任教的历史系教授,她的罪状是在校园内发起连署,呼吁禁止“隐蔽持枪”(concealed carry,随身携带枪械,且并未露出)的学生进入教室。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根本不是他的目标观众,他的重点显然不是针对这些问题一一和这些教授辩论;甚至,他们也不是要和自由派斗争,向校方争取聘雇更多保守派的教授,或是限制教授们可以在校园内从事怎样的政治行动。可想而知,这个网站确实导致一些名单上的教授遭受骚扰或者威胁,比如在2023年就有一名亚利桑那州的同志讲师在登上名单后被人刻意推倒在地;但整体而言,该组织并未投入资源动员支持者“一人一信”或是向这些教授近身抗议。在这样的行动中,Kirk所追求的并不是任何与自由派的互动──不论要说是对话还是对抗──而是要让右翼的金主和基层感到兴奋,感受到这群年轻人正在反制这个已经“左倾”的校园乃至社会。
又比如,任何提及转捩点历史的报导都会提到,他们最早向保守派金主宣扬的战功,就是帮助保守派学生参选大学校园自治中的各种重要职位,不让自由派、进步派学生独占这些位置。早在2017年,专门关注高等教育议题的媒体《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就发布调查报导,指出转捩点不只赞助金钱,还会提供专业竞选团队,制作文宣、负责社群经营,协助保守派学生击败通常没有太多金钱资源的业余对手。“你们会觉得很惊讶,但只要在一场选举上花费5,000美金左右,你就能够赢,就能够夺回整座大学校园”,Kirk向潜在金主报告时这么说。俄亥俄州大学的一位拟参选人和转捩点干部对话,该位拟参选人后来将电话录音提供给记者,录音也显示,组织愿意在这些校园选举中支付竞选团队成员“每日20至50美金”的日薪。而一位主要金主Doug Deason也向政治专业媒体Politico的记者表示,在这些校园选举中赢得的席次对组织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绩效指标”。数十年来,几个世代的保守派人士向来都认为自己在大学校园中失势。在此背景之下,提升右翼在校园内的声量、“夺回整座大学校园”,显然才是这个组织面对金主和潜在支持者时的重要号召。

用同样的角度,该组织其他指标性的活动也就更容易理解:比如在校园内发放“社会主义烂透了”(socialism sucks)的贴纸,同样带有这种表态、这种彰显右翼存在感的意图。在另一张贴纸上,他们则改造了一个对很多进步派青年来说都会相当陌生的符码:在2000年前后,有主张各宗教宽容共存的倡议者设计了一个标语,是用各大宗教的象征组合,拼出“coexist”(共存)的字样;这个标语在当代自由派内部称不上流行,但转捩点另一个指标性的贴纸是将之改编,改用子弹、枪靶和乌兹冲锋枪拼出同样的字样。比起与自由派互动,这同样更强调某种自我表达,建立一种“谁要跟他们共存”的兴奋感。
另一项指标性的活动,则是为了讽刺入学时将种族纳入考量(即所谓的“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论许久的敏感话题),所以在各大学校园内举办义卖饼干募款的活动,并标示出白人买饼干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不是在和自由派辩论──尤其考虑到,美国法院过去几次宣判“平权政策”合法的判决中,主要的论点是主张校方有权认为“创造多元的校园学习环境”是其想要追求的重要利益,所谓“白人买饼干更贵”的讽刺行动并未回应到此一论点。但是,若要说是刻意挑衅或威胁自由派,恐怕也太过只从自由派的角度看世界,忽略了对Kirk本人而言最大的行动重点:让保守派的青年学生和中老年金主展现自己的力量,能够展现自己的声音,看见可以这样表达自己对自由派的不屑与轻视,能够非常具有“存在感”──在一座又一座长期被保守派认为“已经被左翼控制”的大学校园之上。
理解这个背景,也才更能够准确定位Kirk所谓的“校园巡回辩论”,也就是最近再度获得许多人关注的“prove me wrong”系列。类似形式的影片从他崛起以来一直是他社群媒体上的重点:在枪枝、移民、堕胎等等议题上,他气定神闲地“destroy”(直译为“摧毁”,台湾读者更熟悉的说法则可能是“打脸”)自由派、进步派大学生。有没有自由派的大学生真的被他说服,或者至少表示更理解保守派的论点?甚至,有多少旁观者听完“辩论”之后觉得更明白双方的歧见所见,甚至因此认同保守派?这通常都不是这些影片呈现的重点,这些活动在设计上并未尝试去追问这些事情。他的态度有时嘻笑怒骂,有时气定神闲,甚至不时语气和缓,请对方先讲出立场,但这和点名左倾教授、发放“社会主义烂透了”贴纸、赞助保守派学生竞选等等活动一样,能够在大学校园里、进而在年轻人的社群媒体上展现保守派的力量,这就是Kirk在右翼圈内累积战功的方式。

取代旧的校园组织,建立新的右翼政治风格
一位转捩点的长期金主对这个组织的称赞,更能够清楚说明这点。在七年前,Politico的记者针对转捩点做了专题报导,过程中采访了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地产商人,是该地转捩点分会的赞助者之一。他这样说明他为什么愿意捐款:“转捩点这个团体的重点是,他们让保守派在千禧世代的年轻人眼中变‘酷’(cool)了”。
这位高龄的金主当时可能不知道,严格说来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通常已经不被当作千禧世代(millennials)的一员,而已经属于更新的Gen Z。但不论如何,他的核心论题依然成立:特别是在一般认为以自由派、进步派居多的大学校园内,保守派需要让支持者感到兴奋,乃至让潜在支持者感觉到这种声音并非少数人的无聊观点,而是在校园内风风火火的一支部队。他们需要让右翼青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是在参与一个更大、更有意义的运动,并且显得很“酷”。在七年之后,多次采访Kirk的纽约时报记者,在报导中用一个段落统整Kirk向他表达的策略眼光:
“组织的活动要有趣,参与者要有吸引力。民主党的‘王室成员’──甘迺迪兄弟、奥巴马──够‘酷’,Kirk想要让保守派也能像这样。”两篇报导时隔七年,采访了不同的受访者,但“酷”依然同样是关键字。
在这个过程里,Kirk在各校校园里并不是和自由派组织争抢学生,而是在各家保守派组织中成为最“酷”的那个,最能吸引学生加入,也最能吸取金主资源,改变了各座校园内的保守派组织生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会系教授Amy Binder曾发表专书和多篇论文,研究校园上不同的学生政治组织;而在Kirk死后,Binder受访时分析,Kirk的成就在于“把学生从共和党学生组织(College Republicans)那边拉走。共和党学生社团的形象太过建制派,也太过在乎让传统路线的共和党人当选……他让共和党学生社团的校园分会大幅流失财务和人力资源,几乎让他们集倒闭体关门。”
数十年来,共和党学生社团最能提供保守派学生各种人脉,尤其是到共和党政治人物办公室实习的机会,因此能够吸引有志于政治、媒体、法律等工作的保守派学生。但转捩点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行事模式,另一种更“酷”的风格。
在Binder和同僚Jeffrey L. Kidder共同合作的研究中,他们将这种模式与风格描述为一种有别于共和党学生社团等组织的“微型文化”。这份研究的时机是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两位研究者访问了某校转捩点分会的创办人,他就自陈,自己创会的契机是不满校园内的共和党组织没有“煽起(rile up)人们的激情”,并未热情帮特朗普造势,实在太不愿意“引起争议”,他才决定另起炉灶。
另一位受访者成员的故事更能够描述此一社团的微型文化:他因为支持特朗普而“被一位自由派的好友绝交”,在这个刺激下,他决定加入转捩点,而在组织成员的激励之下,他也决定在自己的脸书上刻意发文冒犯立场不同的“朋友”,包含自由派和传统保守派,刺激这些人与他解除朋友关系,这被他形容为“清理门户”(“clean house”,意涵接近于部分华语社群中所谓的“提纯”)。同时,他是这样理解自己身为“保守派”的使命:在自己的校园里,“把保守派的地下文化带到地面之上”,让所有人都不容忽视。

与转捩点相反,共和党学生组织的成员认为自己采取的是“严肃”的取径,并以广纳各种不同的保守派论点为荣;一位受访学生说明,他原先只是模模糊糊地支持保守派,是加入共和党学生社团后才听到保守派内部各种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特朗普的不同立场,“这给了我一个新的规范,告诉我可以身为共和党人却对特朗普有所批判”。在全美国,包含哈佛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共和党学生组织甚至曾拒绝支持特朗普,只为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候选人等助选。
而在特朗普崛起之初,很多共和党学生社团成员也以自己“不是”转捩点为荣:“我们不是来争吵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要争吵的话,你该去其他地方,转捩点就在那里。”另一位受访者也说,每次看到转捩点的成员,他们心里都会嘀咕:“你们可以不要站在我们旁边吗?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活动。”在共和党学生社团之外,校园上属于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派的小众社团也同样以严肃且深刻的辩论为荣,并且当时几乎全数反对特朗普,一位受访成员就承认自己很讨厌转捩点的成员报名参与他们举办的活动,因为“我们是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论点是否有瑕疵”,但转捩点成员都只是都只是“来吼叫”、来自说自话。
更广泛来说,自从90年代起,转捩点的这种政治风格就是美国右翼文化的一部分,经常被称为owning the libs(owning一词来自游戏社群,类似于藉著大获全胜以羞辱对手,或可翻译为“电爆那些自由仔”)。虽然owning一词来自在游戏中胜利,但现实上,这种对政治的取径更强调的是让对方(或者至少想像能让对方)气急败坏。知名新右翼刊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资深编辑向记者解释,这种风格背后的逻辑是要“宣示自己的尊严”,是认为自由派总是对一般美国人颐指气使,所以要能够反唇相讥,要站得比他们更高。
一个知名的代表是右翼广播巨擘Rush Limbaugh,就是新右翼眼中的“快乐战士”,以嘻笑怒骂的方式,对著右翼听众“电爆”自由派──比如,Limbaugh常说女性主义者是“女权纳粹”(feminazis),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丑女人有办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对他们口中的“Rush”,新右翼支持者的一大称赞就是这位主持人总能让他们大笑,非常具有“娱乐性”。同时,Limbaugh也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先驱:当时,他所擅长的是call-in式的政论广播节目,而他的崛起甚至早于在娱乐业采取类似风格、不时刻意发表惊骇言论的知名主持人Howard Stern。当时的政论call-in广播节目,就像是今日的podcast和短影音──都是最新、最能触及“大众”的媒体,而且不令人意外地,在这两种形式中,最吃香的也都是某种“做自己”、品牌色彩鲜明的主持人。
而在采访中,Kirk也多次自陈,他高中时的政治启蒙,也就是这位“Rush”。只不过,Kirk还比Rush更擅长经营自己的组织,同时,他的态度经常更为气定神闲,且更常选择和“无知大学生”直接面对面。但根本上,这种owning the libs的风格不但不是Kirk的独创,也不像一些论者以为的只是社群媒体时代的独特产物,而是新右翼之内长期存在的其中一支政治行动逻辑。
而此刻,这支政治行动逻辑蔚为主流;而在青年之间、特别是在大学校园,Kirk的遗产就是教导了许许多多的右翼青年:这就是当一个保守派的方式,让人们在owning the libs的过程中感受到骄傲,感受到胜利的光荣。无怪保守派的政治学者Jon Shields会在受访时表达他的忧虑:保守派青年的养成并非研读Burke甚或Friedman这些人的思想,而是从Kirk这些人身上学习如何当一个保守派,他们的保守主义内核因此并非任何对传统体制或自由市场的思想,而是以owning the libs为核心。这位保守派学者感叹,Kirk所提供的,是一种“很低劣的养成教育”。

特朗普夺下共和党,Kirk则为他建立“制度性鹰架”
就此而言,这种风格崛起的时间,正好也是特朗普爆冷门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权、共和党内部分裂的时候,这使得Binder团队访问的保守派学生也开始以特朗普为标准区分你我。这个时机点是重要的:那时,这些彼此对立的保守派学生多半还不知道,但在短短几年之间,特朗普路线将成为共和党内几乎唯一的路线,反MAGA的共和党人将近乎绝迹。
而Kirk所创造的事业也参与了这样的潮流:他是最早期就带枪投靠的组织者,一方面像是佣兵团的领导人,但另一方面却也因此成为特朗普家族的入幕之宾。
他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是受到茶党运动的启发而投入草根组织,最早也属于小政府自由放任派,最早支持的候选人是茶党运动的宠儿、威斯康辛州长Scott Walker。但他看到特朗普的潜力,透过组织金主的人脉和特朗普之子Don Jr.搭上线,而Kirk的青年校园组织经验正好符合Don Jr.在选战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于是成为Don Jr.在选战最后数月的贴身幕僚,既负责行程安排,也负责社群媒体管理。
选后,他回到转捩点继续经营组织,然而,选战经验和人脉让他获得总统一家的肯定,在Don Jr.选后的生日派对中,他终于有机会和特朗普本人促膝长谈,从此成为最被信赖的外部策士之一。特朗普经常直接用手机打电话咨询Kirk,Kirk也成为椭圆办公室的常客。根据Don Jr.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赢得信任,是因为他稳定而且忠诚,能做出有水准的评论,而且建立了惊人的网络。”同时,在内斗频仍的特朗普白宫中,他又因为被视为专注于“青年工作”而并未成为派系内斗的标靶,他的外部身分让他可以远离这些刀刀见骨的斗争。
这也抬高了他的身分地位,所以让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够常态成为福斯新闻网(Fox News)的来宾,建立他在右翼论述中的领导地位──当时,传统媒体的地位还更为重要,而新的右翼媒体也尚未兴起,福斯新闻网依然是最重要的平台,而Kirk是在这个时候取得了在新右翼、特别是新右翼青年之间的优势,能够抢占此一滩头堡。以此为基础,他的社群媒体事业愈趋强大,主持的podcast来到百万下载数等级,并且成功经营TikTok在内的各种短影音平台,成为青年右翼之间的第一流品牌。

而他并未忘本,也持续经营与特朗普的关系。他的忠诚更反映在2021年国会山庄暴动事件之后,在一片不确定当中,当时眼看主流共和党人有可能与特朗普决裂、新的野心家甚至已经准备征服党机器,Kirk依然选择对特朗普不离不弃,在特朗普的“流放期”依然持续担任特朗普的策士。根据内幕报导,包含如何面对期中选举、何时宣布再度参选,Kirk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也因为他累积了这样的资本,才让他对特朗普的人事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包含凡斯中选副总统,根据媒体普遍报导,也是Don Jr.和Kirk为首力荐的结果,是他们认可凡斯,特别是向特朗普保证凡斯已然是“自己人”,早已丢弃过去批判特朗普的立场。
这是一个以资本累积资本的故事:组织实力和经验让Kirk对特朗普家族有用,而特朗普的信任又让他个人更具影响力,不论是在“宫廷政治”还是在文化论述上皆是如此,而这些影响力又进一步让特朗普团队对他更为倚重。
当时的特朗普也真的需要这样带枪投靠的组织工作者,以及这样能号召一大群青年的意见领袖。政治媒体Politico的资深政治记者Ian Ward分析,在特朗普拆毁并重塑共和党的过程中,Kirk提供了替代性的支持机制,取代了原先党机器应该承担的功能:转捩点成为替特朗普服务的青年草根组织,而Turning Point Action这个由转捩点所衍生的募款与选战志工组织,也成为其中一支承继既有组织功能、挨家挨户敲门拜票的陆战团队,他的社群媒体和podcast也成为取代党文宣机器的其中一支佣兵部队,帮助MAGA派的论述与宣传。在既有党组织逐渐“空洞化”的过程之中,Kirk既是推动者也是获益者,负责填补此一空缺。
至今,Kirk依然持续履行这样的任务。举例而言,去年年底,特朗普预告提名的官员、特别是国防部长Pete Hagseth面临重大争议,当时,中校退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参议员Joni Ernst 等人尚在犹豫,不确定是否愿意支持。当时,Kirk直接公开威胁将动用转捩点的力量,投入初选拉下Ernst。要是不愿意支持特朗普指定的国防部长人选,“Ernst你哪天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在初选中被挑战,你就不要还感觉讶异”。
“旧的RNC(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旧有的党机器)做事情的方式已经死了,懂吗?你以为我们转捩点行动、转捩点政治行动委员会满足于现在这样而已吗?不,不,不,不!”这是Kirk去年12月的发言,平台当然就是他个人的podcast。后来,Ernst等人也都乖乖支持了Hagseth的提名,她本人也在这个月初宣布退休,不再争取连任,尽管她只有55岁。
Kirk崛起的背景,与其说是左右派之间怎样激烈的斗争,不如说是组织空洞化的共和党,以及强势“并购”共和党的特朗普。如同资深政治记者Ian Ward所分析的:“共和党逐渐成为一个空壳,以特朗普、而且只以特朗普为核心;在此之际,Kirk则是创造了新的制度性鹰架,让摇摇晃晃的结构可以不致分崩离析,能够环绕在领袖身边。”
所谓的与自由派对抗或者对话,其实都只是噱头,都是幌子。Kirk的核心不只是一个冲撞者,而是一个建立者,是建立并维系“特朗普秩序”的要角。就此而言,他以仅仅31岁的年龄,却已经成为新一代共和党中教父般的存在。

政党组织疲软下,一代又一代的右翼教父
不过,共和党之所以体质虚弱,能够由特朗普在Kirk等人的辅佐下取而代之,并非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是共和党在党组织和意识型态上长期的现象。在Kirk之前,美国保守派早已有数位这样的教父级人物。
政治学者Sam Rosenfeld和Daniel Schlozman 主张,美国两党的组织疲软、特别是共和党易于被外部人士左右,是美国当代政党体系的特色。从战后、特别是从70年代开始,许多利益团体兴起,对政党本身并无忠诚,只是工具性地利用政党达成其目的,会动用金钱和基层组织的力量强势要求政党、候选人遵照他们的立场。这些单一议题组织在广义的右翼尤其常见,包含福音派教会资助的反堕胎、支持“基督教价值”的团体,也包含诉求大幅减税的资本家。加上,美国政党的选举提名逐渐改采初选制,而在初选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动员少数最热情的选民,所以在核心支持者内部的组织和论述实力才是夺胜关键。加上后来的选举法规改革,更让这些团体有许多方式投入大笔金额,在初选和大选期间绕过政党,直接支持他们所属意的候选人。政党在组织和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因此逐渐下降,候选人可以在利益团体的支持下单骑突围,甚至骑劫整个政党。
其实,早在50年代的尾声,几位在当时属于极右翼的“反共”富豪就可以联手成立知名的草根组织John Birch Society,延续麦卡锡主义的论调,在各地寄发文宣、创办报章杂志,投入校区委员等基层选举,由下而上建立基层实力──就如同Kirk在大学校园建立组织,并且利用媒体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他们痛批包含共和党籍总统艾森豪在内、整个政府都充满共产党同路人,必须予以肃清。这个路线吸引了许多对冷战感到焦虑、对新的种族秩序感到愤怒、对艾森豪居然接受罗斯福新政体制不满的保守党基层选民。
当时,就连在党内已经属于反共右翼领袖人物、被政坛普遍认为属于激进派的Barry Goldwater都私下表示John Birch Society的阴谋论太过火,居然连艾森豪都被他们指控。然而,他还是接受该组织的大笔捐输和基层动员协助,连任参议员之后,又在他们的支持下爆冷门直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理所当然地,Goldwater拒绝谴责该组织,而当保守派友人劝告他必须与该组织划清界线时,他更留下了一个经典名句,为他不能这么做提供了夸示的借口:“凤凰城(亚利桑那首府)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John Birch Society组织的成员,我不是在说那种被共产党人吓坏了的苹果农夫,或是喝仙人掌酒的醉汉,我是在说社会上最有地位的那个层级。”而靠著这个层级的人所挟有的组织和宣传实力,靠著他们所教育出的基层群众(那些苹果农夫和仙人掌酒醉和),就足以左右党提名人的立场,决定一整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走向。
后来,包含Goldwater大选惨败后,也有新的“创业家”不甘心党内菁英背叛他们,在反工会、反对枪枝管制、反共、支持基督价值等的金主支持之下,开始使用当时新崛起的宣传技术,也就是透过类似邮购的方式直接邮寄文宣广告。像是Richard A. Viguerie以Goldwater支持者的名单为基础,开始广泛邮寄文宣(“自由派正在掌控学校,在教导你的小孩食人族和换妻都是可以接受的行为!”),成为此一传播模式的先驱者。有趣的是,Viguerie也投入大学校园内的组织,是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YAF)此一团体的第一代领导人──而在半世纪以后,YAF也和各校共和党组织一样,逐渐被Kirk的“转捩点”取代。
他也利用自己对选举管制法规的熟悉找到漏洞,成为第一代花费几乎可以无上限的助选组织,遂成为右翼新一代重要的话事人,并和另一位教父等级的人物Paul Weyrich合作,建立了基督教右翼的基层实力,将他们的诉求带到共和党的主流,进而成为列根在党内窜起、进而当选总统的重要功臣。相对于Viguerie,Weyrich的功能则是建立组织,到各地招募并训练符合基督教右翼价值的候选人,同时也成立智库,提供共和党候选人政策蓝图,加上还深入教会网络,鼓励更多牧师投入右翼政治。

就此而言,Kirk也可以说是Viguerie和Weyrich等的传人。在各自的时代,他们都是创新者,能够充分掌握新时代的文宣、组织和金钱的金钱力量,并以其与右翼的特定新兴候选人的早期结盟,让他们能够成为重要的掌权者,进而跃升为当时的右翼教父。他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在于他们的凭借不同:在组织和论述上,他们的实力基础可能来自报章杂志,来自教会网络,来自大量邮寄文宣,或者来自校园串联和社群媒体——但不论在哪个年代,也都必须来自金钱。至于后来以反女性主义草根组织闻名、也长期经营反“全球主义菁英”新闻信的Phyllis Schlafly,乃至90年代重要的福音派电台网络钜子、也同样透过教会网络散播动员文宣的基督右翼意见领袖如Pat Robertson等等,他们崛起的路径、展现的功能也都相当类似。
从John Birch Society到“转捩点”,从Viguerie、Weyrich到Schlafly、Robertson,再到今日的Kirk,他们的崛起轨迹和政治遗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比起和自由派有任何的互动或交锋,他们生涯的重点是利用美国政党体系、特别是共和党的弱点,经营起自己的组织和论述实力,并与特定政治人物合作,互相利用,成为新一代的右翼教父。尤其在Kirk的案例中,他所采取的政治风格同时又服膺owning the libs的指导原则,自由派的真实反应因此更根本不曾是他的主要关切,重点在于宣示右翼的尊严、展现保守派的存在感。面对像是这样的个案,如果在理解他时著重于他和自由派的对话/对抗,将很像是在理解电影《教父》时竟把重点放在主角和纽约警方的互动,反而忽略了他在纽约黑手党世界内的布局和影响。要定位他们的政治遗产,依然必须从右翼内部、从共和党党内权力运作的角度出发。
特朗普掌控的共和党,特朗普定义的保守派,特朗普统治的美国——这才是Kirk所投入的事业,他留下的真正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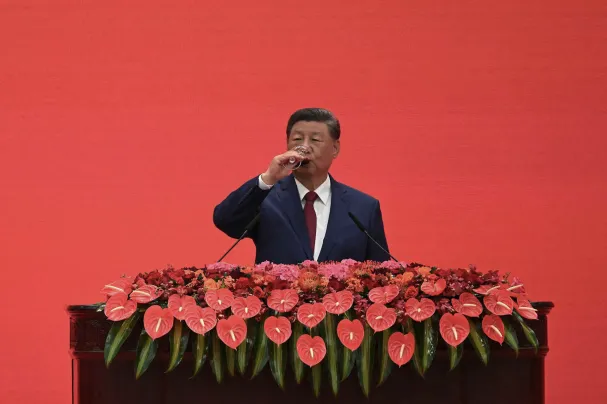

整編文章缺乏了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KIRK的信仰命召。作者只在政治上分析,完全觸及不到最核心的價值觀及信念,可惜。
@blm 認同你的看法 我自已也常會有這個問題。畢竟這種種標籤,很容易區分敵我,「撇清」我和我們的責任。但Trump自身也在運用其權力推進這個浪潮,我倒不覺得他是單純的產物。
仙人掌酒醉漢,not 醉和
而個人覺得Charlie Kirk的意義,反而是鏡像進步派的鏡子,讓你有更大維度去反思當下的意識形態,只要腦袋願意思考,努力把判斷是非的標準控制在同一把尺上,會發現相信那邊的主要論述也會顯得自己更愚蠢。
當下美國政治兩極化,仇恨值如此高漲,Charlie Kirk、白人精英、進步派、主流媒體、社交平台都是共業者,Donald trump只是這一切的產物,與其如此透徹分析Charlie Kirk就是邪惡機器的幕後推手,不如反思一下自己的標準,無論是那一個立場,至少學習語言運用精準一點,不要一味極右、極左、納粹法西斯,只要去過柏林猶太博物館、吐斯廉屠殺博物館,這些名詞我真不敢亂說
“自由派的真實反應因此更根本不曾是他的主要關切,重點在於宣示右翼的尊嚴、展現保守派的存在感。”
我非常認同本文論點。Kirk的成就在於讓讓保守派支持者們覺得自己贏了,從而更願意加入相關的政治議程並為此付出。就好像電影讓子彈飛里的張麻子,跟兄弟在黃四郎的碉樓前狠狠地向鋼門開火。這些子彈不能傷害黃四郎以及他所在碉樓的分毫。卻讓原本不滿但逃避冷漠的那群人覺得跟著他能贏,從而加入這場運動,成就勝利的自我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