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12月号(总第176期)所刊登文章。端传媒与《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经杂志与作者授权转载。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版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性质:学术双月刊
当期杂志:2019年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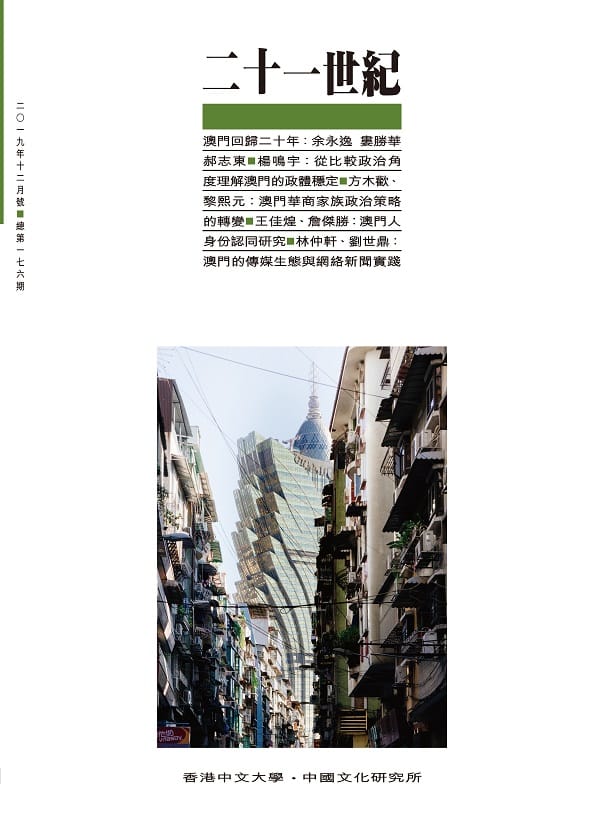
澳门回归后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亲北京力量主导的政治体制,澳门政府的“分赃”政策,政府主要官员的内地背景。

【编者按】: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12月号(总第176期)所刊登文章。端传媒与《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经杂志与作者授权转载。
版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性质:学术双月刊
当期杂志:2019年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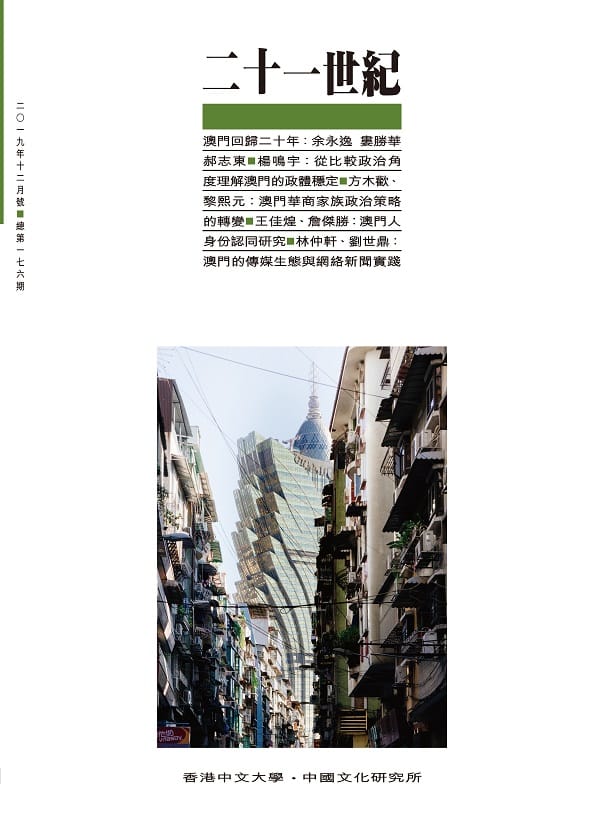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 端传媒编辑部 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