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半个世纪前,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们做过一番分析解读。他所著的《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自1968年英文版问世以来,便在海外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书中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深入揭示左翼文学运动的两难境地。夏济安独特的角度,呈现了这些革命斗士文人的另一面貌: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瞿秋白,名为左联文学领袖,实则在内部四面受敌的鲁迅......
夏济安(1916 –1965)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小说作家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9年赴美国后,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黑暗的闸门》就是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精彩呈现。夏济安与弟弟夏志清是20世纪中国文坛罕见的双子星。夏氏兄弟都拥有广博的文学见识与写作才华,作为文学研究者,两人眼光也都很犀利。夏志清肯定了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地位,而夏济安则被认为在小说创作上天赋异禀。
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黑暗的闸门》英文版全书重新翻译,增录夏济安另一篇相关的重要论文,并邀请翻译学研究专家王宏志教授对译稿全文审订,首次推出这本经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
如王宏志所说,夏济安研究左翼文学,摸索“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下、党争当中,文学作家能否团结一致?这些左翼文人如何在讲求集体意识、要求绝对服从的党领导下生存?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如何调和融合?在政治势力前,文艺和作家能保留多少独特性?”令人叹息的结论是:“政治和文学的角力中,文学始终是失败的。”“原来,一直以来,根本没有什么巨人能够肩住黑暗的闸门,把作家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一章,获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出。

共产党对整风运动所投注的重视恰恰说明,党内的的确确存在纷争,有隐秘的,也有公开的纷争。那些持异议的人士有的另立派系,对共同的信仰提出别样的见解;而有的则是对这一信仰的根基产生怀疑。
他们是怀疑者、幻灭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发觉,新的秩序并没有比旧的好多少。人们为了获取参加革命的权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有部分人开始对这惨重的代价怨恨不已。
我们对“硬心肠”共产主义者的内心生活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应对党所制定的教条与纪律。他们有的甚至就是这些教条与纪律的制定者。他们成功地重塑了自身的人格,是近乎完美的自我调适者。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名“软心肠”共产主义者是十分悲惨的。尽管他故作强硬,但始终是太软弱,没发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企图全身而退又会招致许多现实的困难,而且,他们对党可能多少还有些留恋。
但是在党内继续呆下去则意味着要忍受一切挫败、侮辱与伪善。他那依旧活着的良心,没法使他摆脱这样的两难困境;对自身的悲剧性错误以至整个党的错误,他一直都心知肚明,同时也饱受孤独的侵扰。
相互猜疑的氛围笼罩他的生活,他无法与同志们分享自己真实的感受,但他已跟往昔的非共产主义的世界隔绝。作为一个个体,在实力上,他绝对没法与整个党组织匹敌,而且他或许也无法提供一套可以替代共产主义制度的方案。
然而,这种种的软弱使得他维持住一小片个人主义的岛屿,这个岛屿拒绝被周遭黑暗、汹涌的海洋所吞没。作为一个怀疑者、一个忧虑者、一个沉默而内省的反抗者,他比那些强硬的同僚要有意思得多。
正是这些孤立无援、饱受困扰的灵魂的存在,让他对极权主义运动发出了静默的抗议。他可怕的经历可谓是最值得纪念的人间戏剧,他个人的命运连同人类的命运都在接受审判。
《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作者:夏济安
译者:万芷均 / 陈琦 / 裴凡慧 / 陶磊 / 李俐 等合译 / 王宏志 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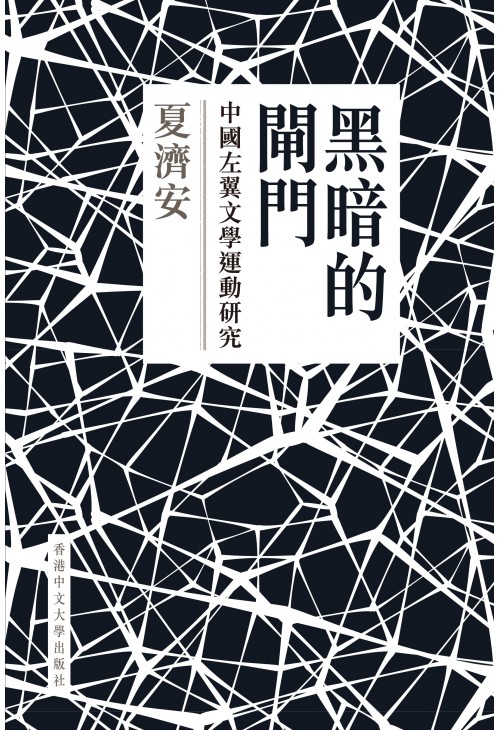
……
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把瞿秋白(1899﹣1935)归为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对象,因为他是个文人,而且详细地记述了个人心声。在1923年至1934年期间,瞿秋白写了大量作品,虽然字里行间有时也流露出他对所写内容的个人信念,但内容全都与党有关。
然而,他在首次赴苏联(1920﹣1922)时所写的两本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却是以惊人的坦诚而著称。这两部作品并不是一般的见闻游记或者宣传材料,它们包含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瞿秋白那会儿身处的俄罗斯穷困潦倒,民不聊生,而那几年对他而言非常关键,正是那时那地,他从一个非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在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之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的监狱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创作一些诗词,还写下自己的遗书,即《多余的话》。他这最后一部作品,就我们现有的版本来看,最为忠实和细腻地记录了一名共产主义者的灵魂。
……
瞿秋白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文人,毫无疑问,他勇敢而勤奋地用笔杆为党做出了贡献。他的名字与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密不可分。他很清楚知道怎样用简练易懂的汉语表述自己的想法,娴熟的俄语使他在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人中显得格外出挑。
除阐释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文艺方面的,他还致力于斟酌文字,使之成为鼓励和宣传的利器。他想要为更多的读者书写,于是他提倡“群众的语言”,以此来区别于五四以来的白话。在瞿秋白看来,白话并没有比“鬼话”文言显得更有生机,白话没能真正地把文言驱逐到鬼门关里面去。……
瞿秋白所做的这些有益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认可。纵然并非他所有的批评意见如今都为党所接受,但随着他的文艺著作(并非政治理论)以厚厚的四卷本形式出版,他已经成为一位公认的不朽文人。
他实际是一个真挚可亲、多愁善感、喜爱沉思的人,有一点理想主义,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内向到顾影自怜的地步,同时又常常被一种孤独感紧紧萦绕。
……然而,在瞿秋白被冠以永垂不朽的光环之前,他在早期的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自己是截然不同的形象,全然不是向蜂拥而至的人潮挥舞战笔的英雄形象。总体而言,他的性格要复杂和孤僻得多。
对于革命,他确实有满腔的热情,但那只是他复杂性格中的一个面向。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他实际是一个真挚可亲、多愁善感、喜爱沉思的人,有一点理想主义,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内向到顾影自怜的地步,同时又常常被一种孤独感紧紧萦绕。
这些性格特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的中国诗人,而很难与一位革命家挂钩。不过,瞿秋白的革命生涯那时才刚刚起步,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克服自己的弱点,把那多愁善感并且染上严重肺病的脆弱身躯淬炼成第一流的斗士。
一位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心猿意马,三心二意而已,所以往往也是蹩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性格转变有多么成功和彻底呢?”很难想像这个在文字中表现出对父母、表亲、友人以及野花和月夜浓浓爱意的年轻文人,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位让人联想到恐怖主义、盲目狂暴以及冷酷无情的革命家,尤其在他领导和发动那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武装暴动之后。
为了这脱胎换骨的转变,他一定把自己软心肠的一面完全抹煞了,因为性格中的这两面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这里就涉及一个耐人寻味的心理问题:一个人真的可以和自己的过去彻底一刀两断吗?能否把早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连同过往的记忆一道清空,脱胎换骨般重新塑造自己的心理习性?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量,他或许能够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他真的可以控制自己的潜意识吗?繁重的工作对此也许有所帮助。为了防止危险思想滋生,一个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迫使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
瞿秋白的绝大多数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可是,他偶尔也要无奈地面对闲暇,因为肺病时不时会复发,就需要他停下工作、休养治疗。在病床上度过的日子或许让他的内心无法平静下来。后来,他被捕入狱,被迫再度面对闲散,更要应付很多情况,比如国民党官员的审问。
就这样,他渐渐放松了对旧时光的防备。他丧失了人身自由,但心灵却获得了解放,这也是挺吊诡的。随著思绪的奔腾蔓延,他又找回表达自我的冲动。入狱期间他所写的那几首诗词本质上都是怀旧的,在《多余的话》中,他承认自身有著“两元化的人格”,他终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了。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瞿秋白呢?是那个革命斗士还是那个不断沉思的多愁善感者呢?或许两者皆是吧,只要我们相信,就算是共产主义者也有可能存在分裂的人格。
……
从他的陈述可以发现,他有很多的向往,但这些都是一个革命者绝对不该有的。甚至当他喋喋不休地述说著光明的未来,“红光”笼罩边宇宙,“遍地的红花染著战血”,他发觉,自己与“黑甜乡”这个家庭关系和审美理想都错综复杂的旧中国,很难斩断联系。
对那些自小就很珍视的人、事与地方,感怀之情油然而生,但他必须强行抑制。像这样的人性弱点必定是他“内在需求”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弱点对他想要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动”造成了多么大的阻碍啊!
当“饿乡”(编者注:苏联)的生存状况变得不堪忍受时,重回“黑甜乡”(编者注:暮气沉沉、贪图安逸的中国)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饿乡”和“黑甜乡”,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套不同的价值观,这两个词把瞿秋白夹在中间,进退维谷。这种矛盾折磨了他一辈子,永远没有得到解决。
“饿乡”和“黑甜乡”,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套不同的价值观,这两个词把瞿秋白夹在中间,进退维谷。这种矛盾折磨了他一辈子,永远没有得到解决。
……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个人“心波”的纪录,书中的语句大量借鉴他之前颇有研究的诗词和佛经。他的这两本书不是写给无产阶级和略微识得几个字的人的,而是写给他所属的这个阶级,即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读者,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而今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重新调整自身。这些读者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由“五四”运动所促生的新文学的风格与内容。
……
在俄国,病痛、寂寞,以及人生的阴郁和自然段惨淡给瞿秋白平添不少忧愁。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困境。他的忧愁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敏感而思乡的年轻人,病弱的肺让他时有怨言,而且身处一个令人不快的异乡。
他的忧愁体现在他的理想上。他可以离开这讨人厌的地方,但不愿轻易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依旧处于试验阶段,暂时还没有什么让人欢欣和安慰的结实成就,而公众的不满和冷漠反而十分显著。他需要在写作中为之辩护,以此说服自己以及中国的读者,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且美好的。
他需要在写作中为之辩护,以此说服自己以及中国的读者,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且美好的。
这给瞿秋白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自从进入西伯利亚之后,他就不得不关注革命沉重的事实。这些事实无疑给这个“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浇了一盆冷水。自然之和谐曾是他早年研究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信条,但在此时此地却无处找寻。
他的这两种人格都需要专一的忠诚,但是对之投入相同的精力是不可能的。一种冲动是要追随自己天性,满足自己对温和、柔情、美丽的物件和舒适的氛围的渴望。而另一种冲动则是追随理性,做理智认为正确的事情,毫不迟疑地从整体上来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随的严酷、丑恶和变态。
如果不能做出妥协,那么他必定要做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也正是他体力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当时他需要的应该是更多的休息,而不是更多的战斗。不过,对他来说,只有内心获得了安宁,才算真正的休息。
通过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进入一种新的人生。他曾经病弱且孤独,但现在有了党组织力量做后盾。他曾经有两个分裂的人格,但现在革命者的人格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在入党之前关键的几个月内,他饱受失眠的痛苦,这也是他内心挣扎的一种症候。
……
事实证明,在《多余的话》这部私密的自传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瞿秋白,而是剖析自我的瞿秋白。不过,我们不能妄下定论说,他最终感到了幻灭。或许他到死都还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微词,但终究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用毫不含糊的说法坦承自己是个“二元人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郁症患者;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唯美主义者;一个憎恶旧社会的多愁善感者;一个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菩萨行”人生观的实践者;一位追寻“饿乡”却又受不了黑面包的朝圣者。
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烈火并不能把革命者淬炼成钢铁那样的金属,而人的天性,无论人们对之如何定义,它即使在最彻底的思想改造之下也不可能全然改变。
《多余的话》并没有记录他性格上新的发展,只是再度确认了他早期的两本书留给我们有关他的印象。不过,对瞿秋白以及其他面临相似困境的共产党员,这部自传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那就是:革命的烈火并不能把革命者淬炼成钢铁那样的金属,而人的天性,无论人们对之如何定义,它即使在最彻底的思想改造之下也不可能全然改变。
无论是作为共产党的书记、理论家、左翼作家中的领军人物,或是国民党的阶下囚,他依旧还是那位年轻的秋白,对莫斯科那被云影遮住的月亮,慨叹不已;对那神秘而可怕的俄雪,发出绝望的哀嚎。
……
《多余的话》供认了瞿秋白不适宜从事政治工作,这一点在李克长(编者注:瞿秋白在狱中唯一接受过访问的记者)的访问记中得到了证实。除此之外,犀利的自我剖析在《多余的话》中也占了很大篇幅,这恐怕只有瞿秋白本人写得出来,假使真的有伪造者的话,那这个伪造者在直觉和想象力方面肯定是天赋异禀。
我们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虚度了一生的人的挽歌;它也是对自身懦弱、怠惰和虚伪等弱点的招供,即使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弱点,但还是因之犯下了一堆错误;同时,它又是对可笑命运的抗议(尽管这抗议略显无力),命运之神将最艰巨的任务降于他肩头,然后又嘲笑他赤裸裸的无能为力。
尽管这部作品包含大量的材料可以用进瞿秋白政治传记中(我有和中共“官方”传记作者同样的顾虑,所以也没有用),《多余的话》没有怎么涉及政治。在它的作者看来,政治代表了世间一切丑恶: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灵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恒的谎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毁灭。
作为一个软弱且疲倦的自我的悲哀陈词,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阶级斗争,超越了任何的意识形态。


正文第十段提到的瞿秋白去“苏联”的1920-1922年,那时候还没有苏联,当时的国名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苏联是1922年年底(12月30号)才成立的。准确的说,这个写法应该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