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卡伦 · 霍妮(Karen Horney)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两位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分别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做出批判修正,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做出精准剖析。两人也曾有过一段亲密关系。
《逃避自由》是弗洛姆的代表作,这本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切入点剖析极权主义和批判现代社会的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称为反极权主义三大经典著作。
弗洛姆说现代人在“逃避自由”,个体日益加深的孤独和无力,让人产生了臣服于某个权威或高于自己的存在的冲动,通过新的纽带来重获归属感,这就是“逃避自由”,也是现代极权主义和人性异化产生的渊薮。
弗洛姆一语道破了现代人满足外表下空虚的心灵,濒临消灭的自我和苦苦挣扎的灵魂,揭穿了乐观主义表面下掩藏的深深痛苦与不幸。我们号称自己是自由的,可却放弃了自由思考的权利,而是只知听从权威的言语。
这种“权威”有很多:道德舆论、心理分析、科学常识、广告标语……于是伪思想代替了真思想,伪自我代替了真自我。只有自发性的创造与爱才能将“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带离所处的精神困境。
而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则指出了现代人的焦虑,正表现为神经症人格倾向,盲目地需要爱和赞美与社会认可、对他人不必要的敌意与攻击、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价值......
所谓“正常”“正确”的人生,只是时代、文化等等外部环境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一套行为标准、生活方式。其中困住了多少鲜活不安的灵魂,他们在自我和世界的夹缝中,看不到出路,深深陷入对自己难以认可的沮丧感。如果我们了解自己和身处的时代多一点,会不会能活得更坦然?
弗洛姆《逃避自由》(节选)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出版时间:2015年4月
出版社:木马文化
作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译者:刘宗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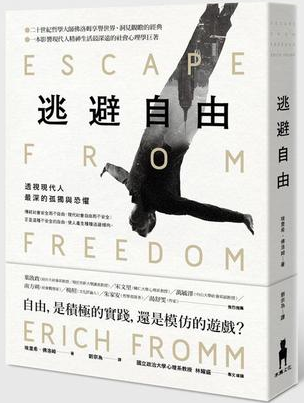
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经常是消除自发性,用加添的感觉、思想、和希望,来代替原有的心理行为。比如说,最早要压抑的感觉之一是敌意与厌恶,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儿童对外界的敌意反应。
使用的方法是很多种,有的是采取威吓与惩罚,有的是使用贿赂或“解释”。起先,儿童是不再表示出他们的感觉,最后,他根本就放弃了这种感觉,此外,人们还教导儿童压抑自己,不要注意别人的敌意与不诚实。
有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儿童有种本能,可以注意到别人的这种敌意,而是像成人那样容易受“文字语言”的欺骗。他们会“没有理由”地不喜欢一个人——他们会直觉地感觉到从那个人所发出来的敌意而不诚实。这种反应很快地便受到打击;儿童很快便达成一般成人的“成熟”,失去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感觉。
在另外一方面,成人在开始教育儿童时,便教育儿童种种根本不属于“他的”感觉;例如教儿童要喜欢人,对人们要友善,要微笑。教育未完成的工作,在以后,社会的压力通常会继续完成之。如果你不微笑,人们便会认为你没有“悦人的人格”——如果你想事业成功——无论你是侍应生,是推销员,还是医生——你必须具有“悦人的人格”。
惟有那些位于社会阶层最底一层的人——靠苦力维生的人——和最高高在上的人,不需要有“悦人的人格”。友谊、欢欣,以及微笑可以表达出来的任何事情,变成自动的反应,好像电灯开关一样,只要一开,便可以表现出来。
当然,在许多情形中,人们是会发觉到,这不过是做作而已;可是,在多数的情形中,人们未能发觉到这种情形,因此,便失去辨识虚伪感觉,和自发的友谊之间区别。
人们装腔作势,抑制敌意,挽救友谊。不仅如此,很多自发的情感也遭抑制,而代之以虚伪的感情。
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靠着和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就把对自己身分的怀疑压制下去,同时,得到了一种安全感。然而,他所付的代价也是很高的。放弃自发能力与个人的特性,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
就心理的意义而言,生理的机械作用仍然活跃着,而情绪及心智的机械作用则息止了。固然,一个人仍旧生龙活虎地生活,但是,他的生命则像砂子一样地从他的手上溜走。
现代人表面看起来是满足和乐观的,在这表面的背后,他是万分的不愉快;事实上,他濒临绝望的边缘。他拼命地依附着个人须有个性的观念,他想要“有所不同”他极欲“标新立异”。
人们把他的名字缩写,印在手提袋、扑克牌、及手提无线电上,使这些东西“人格化”所有这一切行为无非表示人们渴望“有所不同”;然而,这些几乎是留下来的个人个性的最后遗迹了。但是,由于人成了机器,不能自发地经验生活,他像是代表别人来追求兴奋与刺激。
如果人能借着自发性活动,来实现他自己,并使自己与世界,建立关系,他便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微尘了。他与世界化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一部分;他有其适当的地位,因而,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一扫而空。
如果人能借着自发性活动,来实现他自己,并使自己与世界,建立关系,他便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微尘了。他与世界化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一部分;他有其适当的地位,因而,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一扫而空。他发现自己是活泼而有创造性个人,也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
如果个人克服了对于自己及对于他在生命中之地位的怀疑,如果他在自发的生活过程中与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他便获得了力量与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感与个人未获得自由前的那种安全感不同。这种新的安全感不是依靠个人从外界较高权力所得之保护;也不是除去生命中悲剧成份的那种安全。
这种新的安全感是动态的;它不是依靠保护,而是以人的自发活动为根本。这种安全感是人从事自发活动而得到的这种安全惟有自由才能给予,这种自由不需要幻觉,因为它消除了需要幻觉的那些条件。
就实现自我而言,这种积极性的自由意味着,充分地肯定个人的独有特点。人虽然是生而平等,但却也是生而有所不同的。此种差异的本质就是人生而具有的,在心理及智力的本能,他们依赖着这种本能来开始生活,以后他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特殊环境及经验,还会影响到这种本能。每个人的人格的本质就如同两件东西,是绝少相同的。
自我的真正发展,永远是依照此一将有的本质而发展的;这是一种有机的成长,是因人而殊的核心的展开。相反地,机械行为的发展则不是一种有机的成长。个人的本质的成长受到了阻碍,硬把虚伪的自我加到自我的上面——换言之,就是接受外在思考及感觉模式。
惟有在极端尊重他人及我们自己的特性的情况下,有机的成长才是可能的。这种对自我的独有特性的尊敬与培养,乃是人类文化的最有价值的成就,而现在,就是这种成就处于危险之中。
惟有在极端尊重他人及我们自己的特性的情况下,有机的成长才是可能的。这种对自我的独有特性的尊敬与培养,乃是人类文化的最有价值的成就,而现在,就是这种成就处于危险之中。
卡伦 · 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节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出版时间:2011年5月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卡伦 · 霍妮
译者:冯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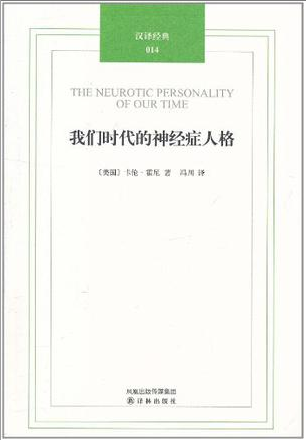
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权力、名望和财富必须通过个人自己的努力去获得,那么个人就不得不进入与他人的竞争。
这种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所有一切活动之中,并渗透到爱情、社会关系和游戏之中。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竞争无疑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无怪乎我们发现它在神经症病人内心的冲突中始终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
在我们的文化中,病态的竞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正常的竞争。首先,神经症病人老是不停地拿自己与他人衡量,甚至即使在不需要作这种衡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努力超过他人乃是一切竞争的本质,神经症病人却过分喜欢拿自己与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的人,与那些和自己没有共同竞争目标的人衡量并比较。
他会不加分辨地把诸如谁最聪明,谁最有吸引力,谁最受公众观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去。他对于人生的感受,可以与一个骑手在赛马中对生活的感受相比较。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这就是能否超过其他人。
这种态度必然会使得他对任何事业都丧失真正的兴趣。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他所做的事情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件事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成功和名望。神经症病人可能意识到自己爱与他人比较的态度,也可能只是机械地这样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他很难充分意识到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二点不同是:神经症病人的野心不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与此同时,他可能认为自己的目标比较起来总是最高的目标。他可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正被这种无情的野心所驱使,但也往往不是完全压抑了这种野心,就是部分地掩盖了这一野心。
在后一种情形下,他可能相信,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在从事的事业;他也可能相信,他并不想在舞台的中央接受观众的喝彩,而只想在幕后做些打杂的工作。他也可能承认他过去的确一度很有野心,但那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一个时期。
那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小男孩,却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基督或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幻想把整个世界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或者,她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却希望有朝一日嫁给威尔士亲王。
但神经症病人会宣布说,自从那时候以后,他的野心就完全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可能抱怨说他现在是这样地缺乏野心,以致他简直希望能够再有一点过去的野心。
而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野心,他就很可能坚信,他本人与野心完全无缘。只有当某些保护性的岩层在心理分析医生的发掘下发生松动以后,他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一些宏伟夸张的幻想,或者有过一些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
例如,希望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最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特别漂亮,或者因为自己身边的某个女人居然会爱上别的人男人而感到十分惊奇,甚至回想起来还十分气愤并怀恨在心等。
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意识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应中具有如此强有力的作用,他都并不认为这些幻想和念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有时候,这种野心会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目标上,例如才华、魅力或某些成就、某种德性。但也有一些时候,这种野心并不集中在某一明确的目标上,而是扩散到一个人的所有活动中。他务必要在他所满足的一切领域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他可能同时希望自己既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又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医生,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如果她是一个女人,她可能不仅希望自己在自己特定的工作领域中名列前茅,同时还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和最善于打扮、穿戴入时的女人。
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发现自己很难选择自己的职业或投身于任何一种生涯,因为选择一种即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或至少是部分地放弃自己最喜爱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同时精通建筑、外科手术和小提琴演奏的确可谓困难重重。
这些青少年也可能抱着许多过分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希望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希望自己绘画象伦勃朗一样好,写剧本象莎士比亚一样好。如果刚开始在实验室工作,他们就希望能准确无误地计算血球数目。
由于他们过分庞大的野心使他们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很容易心灰意冷,很快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努力而开始另起炉灶。许多天赋极好的人就这样分散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他们的确有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某种成就的巨大潜能,但由于兴趣太广野心太大,所以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都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一个目标。到头来他们一事无成,白白地浪费了自己很好的才能。
无论能否意识到自己的野心,他们对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却总是十分敏感。如果不能满足自己很高的希望,那么即使是成功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例如,一篇科学论文或专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鸣惊人,引起轰动,而仅仅产生了一点有限的影响,就仍然会使他感到失望。
这种类型的人在通过了一场困难的考试后,可能因为他人也同样通过了这一考试而认为这算不上什么成功。这种总是倾向于失望的态度,是这种类型的人为什么不能享受成功欢乐的原因之一。至于其它的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也都极其敏感。
许多这样的人在写了第一本书或画了第一幅画以后,就再也写不出书,或再也画不出画来了,因为即使是温和的批评也已经足以使他们心灰意懒,深感失望。
许多潜在的神经症病人,都是在遭到上司的批评或遭致失败的时候,显示出最初的症状来的,尽管这些批评或失败本身算不了什么,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精神障碍。
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三点不同,是神经症病人这些野心中隐藏的敌意,即他那种“只有我才应该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的态度。当然,在任何一种紧张的竞争中,都必然包含着敌意,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即意味着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
事实上,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存在着这样多具有破坏性的竞争,以致作为一种孤立的特征,我们甚至不敢说它具有病态性质。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模式。
但是,在神经症病人身上,竞争的破坏性方面总是比建设性方面更强大;对他来说,看见他人失败比自己获得成功要更加重要。更确切地说,具有病态野心的人的所作所为,就好象对他说来,击败别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重要。
虽然实际上,他自己的成功对他说来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于他对成功有强烈的抑制倾向──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所以唯一向他开放的路径乃是成为优胜者,或至少感觉到比他人优越。而这就意味着挤垮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干脆踩在自己脚下。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竞争中,损人利己,打垮竞争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荣誉,或设法扼制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切往往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神经症患者却受一种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和不区分对象的冲动所驱使,拼命地去诋毁他人。
他甚至可能明知他人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实际伤害,他人的失败甚至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仍然拼命地诋毁他人。他的这种感情可以清晰地描述为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而这不过是“只有我才应该取得成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在他的这些破坏性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着大量紧张的情绪。例如,一个正在写剧本的人,当听到他的一个朋友也正在写剧本时,竟突然陷入到一种盲目的愤怒中去。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