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英国作家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出版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蓝诗玲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作家、译者,现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任讲师,教授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曾翻译鲁迅、张爱玲、韩少功、阎连科的作品。
这本书在2011年的香港书展推出时,引发一时热议。蓝诗玲曾在书展演讲上,提到自己1997年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时,惊讶于自己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也第一次为身为英国人感到羞耻。这段发言,在2015年简体中文版推出后,被许多大陆书评引用。“英国课本对鸦片战争只字不提”“英国人为何对鸦片战争避而不谈”“这场战争被大多数英国人遗忘”.....成了讨论重点。而蓝诗玲成了英国年轻学者的良心代表。
但读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原著中第十八章Communist Conspiracies(共产党的阴谋),在简体版中被改为“20世纪历史中的鸦片战争”,第十九章Conclusion(结论)也被删去。其中探讨的,中国不同政治势力,如何让鸦片战争一步步成为中国百年国耻的序幕;这道“耻辱疤痕”对今天中国的影响,都是这本书的重点。
今年这本书推出繁体中文版,在台北书展上被重点介绍。端传媒获八旗出版社授权刊载,蓝诗玲对华文读者的话,以及简体中文版删减章节的节选。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出版时间:2011年
出版社:Picador
作者:Julia Lov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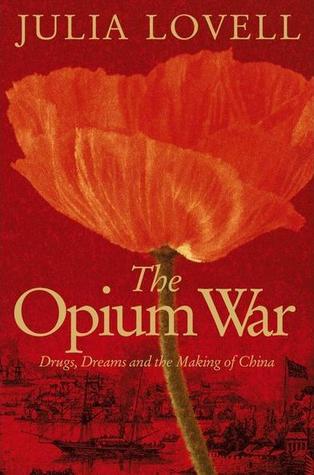
蓝诗玲对华文读者的话
无论是在中国和西方,鸦片战争都被视为孤立的中华帝国在十九世纪对外“开放”的象征。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书写中,鸦片战争被塑造成中国与西方阴谋斗争之开端。自此开始对抗西方用鸦片和炮舰外交摧毁中国的阴谋。
这本书旨在描述更复杂的近现代史图景,探索中国与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许多关系,并揭开在建立国家神话的过程中,所掩盖的令人吃惊和矛盾的历史现实。
本书采用大量中文一手资料(包括纪录片和文学作品),这些资料在之前西方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中几乎没有被用到。我尝试探讨十九世纪中华帝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它绝对不是一个团结起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国家;晚清中国在许多方面,同时与自己和与英国作战。
《鸦片战争》一书通过检视迄今以来关于此战争冲突的历史著作,分析它在中国和西方获得重大象征意义的过程,并审视鸦片战争在当代中国的持续影响力。在中国讨论鸦片战争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民族议题。
《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出版时间:2016年2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社
作者: 蓝诗玲(Julia Lovell)
译者:潘勋

(节选)第十八章
1928年,来自鸦片的岁收让中国的军队屹立不倒(总数有220万人,全球规模最大,一年耗费8亿元)。1931年,一则标题是<上海生意>的漫画勾勒出三个人:左右两边是名为“工业”的侏儒,抬头仰望中间耸立的巨人“鸦片”。
1933年,中国的鸦片贸易规模估计达到一年20亿元(占国内生产毛额的5.2%)。在很多地区及情况下,鸦片就算没更好用,也跟钱一样好用,而且是经商、社交的润滑剂——“点上烟灯”是“我们谈生意了”的标准中式说法;婚礼上,送上烟枪就如敬酒一样平常。熬鸦片的大锅大摇大摆地放在城镇街道两旁,全中国到处都是这玩意儿的气味。
到了1930年代,中国鸦片烟民可能多达5000万人(约总人口的9%)。
1920年代,忧心的公民自发组成“中华国民拒毒会”,发起“拒毒日”、“拒毒周”,发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强健的中国人痛殴焦黑的怪兽——鸦片。(单是在1924年,拒毒会的请愿书便有450万人签名。)
1927年,拒毒会不禁问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军阀的走狗,和国民的蟊贼……都是一般奸商,只顾贪利不顾公德,上而取媚帝国主义与军阀,下而诱引男女同胞吸用的恶结果。”与其同时,国民政府则把征收鸦片税的机构命名为“禁烟局”,而鸦片商联合会则委婉地称为“药商联谊会”。
国际反鸦片协会于1928年评论说:“几百万人已经戒烟,国民政府的专卖单位垄断各大城市的鸦片,组织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额税收。虽然在每次国民党演讲及无产阶级示威之中,都会提到所谓『鸦片战争』的邪恶,但是国民政府绝不放过鸦片种植和吸食税的每一分钱。”广东人有句谚语可不是无的放矢:“鸦片瘾易戒,鸦片税瘾难戒。”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出版时间:2006年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Julia Lov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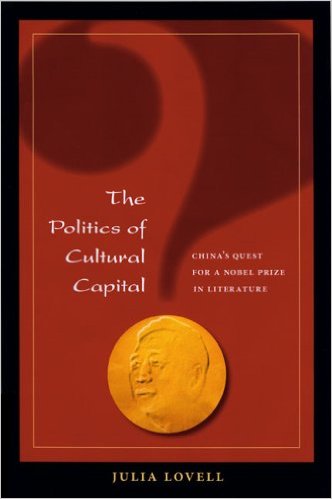
禁烟人士指责国民政府使用鸦片税收在有益的建国上面。“环顾境内,遍地烟毒,讵不痛哉!讵不痛哉!深望当局诸公……切实禁烟,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国誉,而永奠巩固之国基。”
国民政府向大众保证,它“绝对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种嫌疑……我们就认为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它。”
蒋介石又说:“要救中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禁绝烟祸,救国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孙,胥于是赖。”
他在另一个场合解释:“外侮是外来的侵略和压迫,鸦片是本身的堕落与自杀,所以从事态的性质上讲,鸦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险若干倍;而且外侮之来,本由于我们本身的纷乱腐败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尽所能地让碍手碍脚的反对者噤声,或是恐吓他们的赞助者,指控他们走私毒品以抹黑他们,或是发出死亡威胁,不然干脆在他们家中安放炸弹。
1931年,国民政府遇到掌权以来最大一件毒品丑闻之一: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忙着从船上卸下鸦片,却被一群上海警探拦截。那些执法者突然被抓起来坐牢,直到价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帮的目的地。
《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 蓝诗玲(Julia Lovell)
译者:刘悦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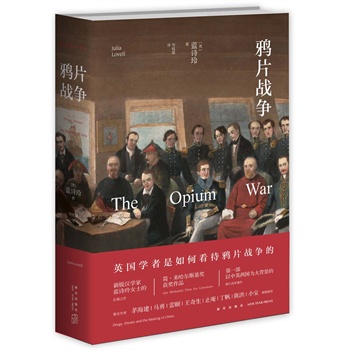
......
尽管中国国共两党是政治上的对手,但它们对中国该怎么成为有效率的民族国家,看法则非常一致: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的训练及国家统一。
诚如宣传部毛部长在1925年说:“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动者……都被我们视为敌人。”
尽管有左右之争,它们基本上都对中华民族抱持类似的贬抑看法,还有人民必须接受一党制民族主义。国民党第一任宣传部长1925年认为,中国是“一张白纸。上绿色,它就是绿的;涂黄色,它就是黄的。”
他的继任人毛泽东同意其意见;毛相信,中国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虽然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花了很大力气在指责老敌人国民党的“反动理想主义、机械物质主义、封建、买办、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是,两党对中国现代史抱持的看法几乎一模一样。妖魔化鸦片战争是由共产党完成的,但基础则是由先前的国民党官方历史学者所打造的。
共产党剽窃很多国民党范本的元素,把那场战争描绘成外国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终极和最凶恶的敌人”)阴谋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让他们“挨饿受冻”。
可是,一等毛完成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鸦片战争不再只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变成起始事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课”,还是一个世纪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起点。
自此之后,中国现代史变得相当简单,是“中国人民不屈的奋斗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暧昧的通敌和内战的历史,鸦片战争成为“人民不懈英勇的斗争”、“全国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1951年,历史书重新采用毛的观点:“整整一百年,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人践踏在脚底下。1842年后,中国沦落到奴役的可悲状态,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是这一百年最光荣的成就;我们的意志是痛苦的伤口形塑的。”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出版时间:2016年
出版社:Grove/Atlantic Inc
作者:Julia Lov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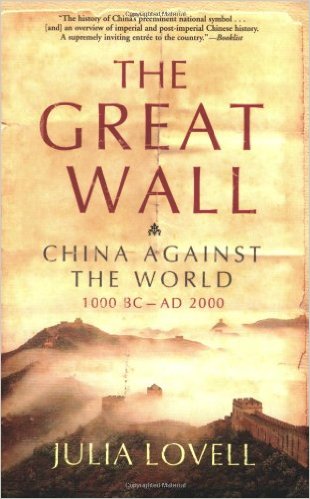
铭记过往伤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现今共产党带来的甜美——即使政府引起人为的饥荒、肃清反革命分子,还有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内战,让几千万人丧生。1950年的教科书在鸦片战争章节的前言解释:
“新中国的青年必须对近现代史有基本了解……还有革命的特殊原则……我们必须了解,先烈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受过多大的苦,如此我们会更爱祖国,愿意贡献我们所有的一切给祖国未来……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胜利的道路。”
借着坚称中国的外敌很邪恶,毛的共产党就可以就名正言顺地使用暴力,对抗帝国主义者及其所谓的中国同路人(国民党、资本家、地主,还有任何同情他们的人)。毛断言说: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就发生了……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
但是,尽管在形式上自1939年起,他便禁止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产制鸦片,声称它“让国家生病,伤害人民”,毛还是跟别的军阀一样,想由鸦片获利。他们自1935年落脚西北的陕西以来,因为毛想扩展武力到全省,共产党的财政很吃紧;
但是在禁烟的两年前,即1937年,曾短暂稳定下来。那一年,蒋介石提出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是为了对付日本。接下来四年,共产党的经济是靠着国民党与苏联每年给钱、给东西,而支撑下来。
然而,1941年以后,两党的关系又恶化到实质上内战的状态,国民党便切断金援,封锁与苏区交界地带,阻止重要的进口物资进入当地。那一年年底,苏区的财政赤字依法币算来是1500万元。
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宣传他们是借着刻苦及民主受到欢迎(实施减租、农业合作化),并渡过危机的。直到1980年代末期,历史学者陈永发注意到,当时的帐册多处提到有种“特产”拯救了共产党,让他们由1940年代初期的贸易赤字脱身,而且靠着它,该政权在1945年的收入比预算多出40%以上。
再深入一点,就发现“特产”就是鸦片。鸦片经“特殊工厂”处理后,运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创造出共产党军队的收入。(1941年,一篇共产党社论说,“自从鸦片进入中国,已变成伤害中国人民最大的来源,与帝国主义侵略密不可分,让中国变成次殖民地。帝国主义者用鸦片奴役、压迫中国人民。随着中国人民愈来愈弱愈穷,鸦片扮演最可恶、恶毒的角色。”)
但是在1945年,一支美国特使团观看毛的王国,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田野里全是高粱及大麦。罂粟已被及时铲除,以维持(至少接下来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战时纯洁正直的形像。
(节选)第十九章
170年以来,鸦片战争及其后续影响,在中西关系投下阴影。十九世纪,影响力大的英国人努力地掩饰贸易赤字是根本的问题,反而将开战理由变成是文明的冲突,起因是中国人“不自然地”不跟人来往。
二十世纪中国国族建构者加入这场归罪游戏,顺势把鸦片战争变成自己国家一切麻烦的起因,是帝国主义者阴谋计算,想奴役一个团结、英勇抵抗强敌的中国。
相形下,战争的实情阐明了英国人极其伪善,还有多族裔的清帝国断层线既多又深;中国统治者煞费苦心,纠合其官员、士兵及臣民对抗外国敌人,却告失败。
西方替战争找借口的公开立场,还掺杂着道德的罪恶感,进一步煽动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恐惧、紧张。鸦片变成西方违法乱纪的象征,又是邪恶中国污染的象征,引起不理性的黄祸疑云,或许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媒体的报导。
与此同时,鸦片、战败及帝国主义制造出愤怒、自弃及务实地崇拜西方,一直不安服地并存于中国爱国人士身上。


换个视角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