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出版社:香港大学出版社
作者:Adelyn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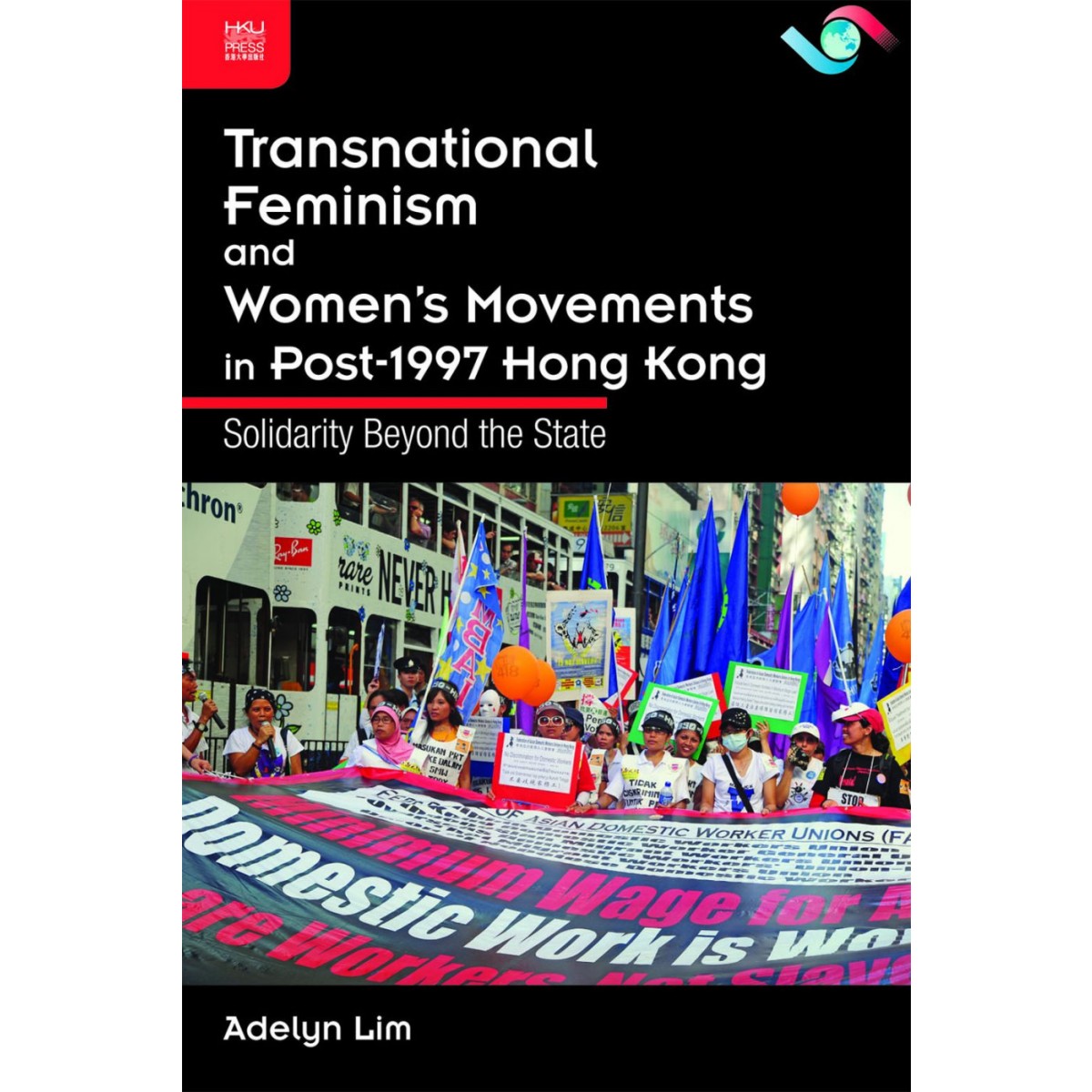
2015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向读者展开了香港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作者Adelyn Lim是人类学出身。她结合后殖民主义差异政治和团结政治理论,把女权主义,发展成社会运动的“框架”。
第一章,从“妹仔”(婢女和性工作者)问题开始,梳理了1843到1997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妇女运动的主要人物、机构、抗争事件和策略。九七之后的情况则分开四章,涉及贫困女性化、家庭暴力、卖淫和性工作者、家务佣人工人议题。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如何被组织起来,使用的宣传辞令、行动策略是什么。“阿姐”(性工作者)这个说法,就是“紫藤”(1996年成立的性工作者团体)提出的。
“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可以被完全划等号吗?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混用。“妇女运动”,更关心妇女切身利益的提升。共同利益把运动者们联结在一起。她们要挑战的,并不一定是男性主导的性别等级制度,和既有政治制度、权力秩序。
而“女权运动”则不同。它要从根本上瓦解这一套权力结构,使女性不再处于从属地位。更有女权主义群体进一步发展,在男女二元性别关系之外继续拓展,寻求更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压倒性的控制。

“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的分野在香港尤为明显。Lim描述,在传统妇女议题上(如贫困、教育、家庭暴力),香港本土妇女权益团体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亲中妇女团体,另一是权利导向的草根女权组织。
亲中妇女团体与政府关系密切,资源丰富。在中国政策框架下、男性主导的政治力量影响下(不少机构的负责人是政府高官的妻子),选择性地回应妇女议题,推进妇女福利服务工作。这种妇女团体更像一种社会进步的装饰。
而权利导向的草根女权组织,缺乏参与体制的机会。更多通过街头抗议、倡导、教育活动,推进妇女权益。这些团体也会批评男性意识主导的民主派,对女权运动被纳入民主运动框架,成为附属工具非常警惕。
2007年,林蔚文和 Irene L. K. Tong的一篇研究也指出,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后,强调统一(unity)和稳定(stability)的民族主义论述、限制公民社会参与,及选择性回应社会需求的政治框架,是两地妇女运动发展的主要障碍。
Lim的研究强调,香港妇女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跨国性”。由于港英政府对本地社会文化的不干预原则,“妹仔”被奴役、性虐等问题,直到1970年代才正式受到挑战。香港社会对“妹仔”的大量需求,导致人贩集团活动猖獗。他们从广东绑架女孩,贩运到香港卖掉。当时的首席大法官John Smale判处了几桩拐卖女童大案。但港英政府很快向本地团体的请愿妥协。商人需要保留“妹仔”,女孩家人也把这种买卖当做一种对抗贫苦的“风俗”。因此进一步解救“妹仔”、改变她们命运的社会运动,反而首先在英国发起。1919年,随夫来港的Clara Haslewood,就是废除“妹仔”运动的领军人。她也促进了1921年本土团体“反对蓄婢会”的成立。
回到今天,港人口中的“菲律宾女佣”,已经为自己争得“工人”的称谓。Lim从国际家务工人运动的背景出发,讲述香港本土的和跨国家务工人组织,如何团结动员,求同存异,提升自身权利。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其他跨国流动的、本土的性工作者的机构“紫藤”,则将组织工作延伸拓展到中国大陆多个地区。
这本书并不晦涩难懂。不过,“跨国性”和“边缘声音”作为核心主题的此书,所关注的“边缘人群”和“边缘话题”,取样上依旧是传统意义上相对主流的对“边缘”定义的范畴。性工作者议题也是从“卖淫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是工作女性”的角度来谈性工作者组织的认同和再现策略。这反映了作者在研究设计中的概念区分,未将基于女性的性(sexuality)及其主体性(subjectivity)建构的组织样本纳入女权团体研究范畴。
因而,女同性恋及多元性别社群组织,新媒体时代的女权文化运动群体和个体,就人口贩卖、国际难民议题工作的机构,都没有纳入本书讨论范畴。这与作者“填补没有全面研究香港妇女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写作目标仍有差距。
(曾金燕,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发起人)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