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兴是香港媒体人,创作人,自言喜欢站在时代风口上记录。过去多年旅居北京,上海,锐意观察大陆开放的新景象,他指自己的写作研究,从来都以香港为座标参照比较。直到疫情期间,经历上海封城,他回到香港,发现原来的座标,消失殆尽。
如今他在东京找到自己要站的位置,形容自己目前是散居状态,一边通过陌生化的距离来书写香港,另一边开展日本研究——不但继续关注他热衷的城市更新规划,也贴身观测当下日本社会酝酿的巨变。眼睁睁看过城市浮华万象的兴起与破碎,他仍孜孜不倦地把自己抛掷进另一个城市,观察时代转折,写下纪录。
城市之于李照兴,是一种“24小时不打烊的自由”,而且,抵达一个城市,只要带来新的观看方式,对他来说,就是新的自由。我们约他在东京街头来一场散策式访谈,边走边聊,而他就选定了高円寺一带
李照兴,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个人或合编作品包括《香港101》 、《潮爆中国》、《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新作《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与身分认同史备忘》。过去二十多年于香港、北京、上海从事媒体及城市记录创作。近年穿梭东京、台北、香港开展跨域华人文化及生活圈的记录与研究。
座・高円寺:语言以外的经验
“暂时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统,即是什么令到日本这么文明,或者日本美学如何领先。这些其实是通过你的个人体验。”
李照兴传媒经验丰富,涉猎文化写作研究,对采访习以为常。访问这天,早上新闻推送,传来东京热中症警告。日本的七夕,香港的小暑。
他的成长时期,正值日本文化大量输入香港,日剧入屋,也看《幪面超人》,听的广东歌不少改编自日语流行曲;彼时走出香港街上,日资百货公司进驻,在铜锣湾抬头一看,崇光、大丸,松坂屋⋯⋯难怪他常说,像他这一代香港人,早已很熟悉日本,令他现在的日子,也远远离开了与日本的蜜月期,完全不是来旅游观光的心态。
高円寺,位于东京杉并区,以古著店林立与独立音乐氛围闻名,对不少次文化爱好者来说,绝不陌生。李照兴传来的集合点,在艺术会馆“座・高円寺”,他时常来这里看剧场演出。这座综合文化设施由建筑师伊东豊雄设计,早于2008年落成,墙上遍布透光小圆窗,串连起小剧场、社区会堂和阿波舞厅各个楼层。

见面不久,李照兴如导赏上身,侃侃谈起东京小剧场文化和建筑特色,“这是中型剧场,从设计可以看到日本民间建筑的自由度大很多。当然要合乎规格,公共建筑也要配合政策投标等事项,但我说的是设计独立性和可变性已然是很高的。而且在东京,不同社区都不乏这类偏离主流、非常有视觉特色的建筑,这是在东京生活,视觉上有趣的地方之一。”
散步在东京,他喜欢留意街头巷尾的视觉设计审美,而视觉元素对他来说之所以是重要的,其一原因是自己日语能力所限,他形容自己日文程度“直头唔好(根本不好)”。譬如说,他向来写影评,但日本电影院一般不提供字幕,他每次去看戏,得先了解故事大纲,否则近乎没戏可看。另一边厢,他来看小剧场演出的时候,也主要是看舞踏,抹去文字语言,从诡谲的肢体动作与白妆,直视内心情欲。
他认为,今时今日在日本生活,其实语言也不成问题,但在专业方面定必有影响。“你也知道的,我们喜欢八卦,走进一间居酒屋,都会想同人嗲吓(聊两句),或者和司机搭讪。但这件事是消失的,导致我在做的,不是人和人、面对面采访的事。”
研究一座城市,却缺少了实实在在生活于当地的人的声音,李照兴承认,这点是自己目前的缺陷。“但在这一刻是无法克服的,不可以一下子很畅顺地同被访者或交流者交流,只能通过另外的方法,包括读文献、读记录,自己亲身观察经历,用自己的经历来做主体,而不是一个采访式的主体。现在的翻译技术高,文献都翻译得很好的,我现在几本很重要的日本读物都只有日文版。”
目前,他一边整理香港文化历史考古,一边认识了一批在日本研究香港的“香港迷”,他们收藏了大量香港研究资料,甚至有些连他也不知道的八、九十年代粤语流行曲。与此同时,他的在日写作计划,也都是城市街区研究,他强调:“暂时不是研究日本的人,是研究日本的系统,即是什么令到日本这么文明,或者日本美学如何领先。这些其实是通过你的个人体验,举例说,交通出行,就专门留意指示牌,是否正确,是否漂亮,或者会不会加了动漫元素的创意。就资料上来讲,文献已经很多,所以暂时对现在为止,语言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商店街:路上观察的方式
“你观察的东西一定要够无聊。无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于它是没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现在追求实用性的那个矛盾。”
“我们这些本雅明式的城市浪漫游人,一定要行街,要贴地。”李照兴说,研究资料虽然重要,但还是要靠亲身经验,路上蹓跶,好好观察。正如他说,座・高円寺称得上东京小剧场的地标之一,但更加重要的是,走回车站的路上,周边还有很多小剧场和Live House,形成不同层次的地下生态。
钟情行街,像他过往时常流连尖沙咀的文青岁月。到香港老牌英文书店辰冲买书,去海运戏院或港威戏院看电影首映,又是香港文化中心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再挤进HMV听歌,在My coffee坐下来,呷一口咖啡,谈文说艺。那年头,未有“文青”叫法,他说,这种四出寻乐,香港叫“蒲”。只是他过去的这些“蒲点”,不少已走入历史,留在那一代人的回忆中。
周一午后的高円寺,不算喧闹。往车站方向走,几乎不见外国观光客,擦身而过,似是悠闲邻里,吃食消遣,单车行人交错而和谐。从剧场沿直路,不出五分钟,到了车站南口右侧的PAL商店街。像惯常爬梳资料写作般,李照兴站在商店街入口,由历史起源说起,从19世纪巴黎的拱门街设计概念,谈到日本商店街与社区的连结,说话间往往夹杂“你都知道”,似乎都认定这些是一些基本日常事。

从前他来高円寺看剧场,知道这一带在文艺圈子深受欢迎,顺道也在附近蹓跶,“不一定是依书直读,一定是去到某处亲身体验之后,有些什么再click到你,然后你再好奇一下,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其中吸引他的,是这里的阿波舞传统,作为日本德岛县的传统盆舞阿波舞传入东京的起点,这里已然是德岛以外的重要据点。他不但对这类以传统祭典来振兴社区的课题深感兴趣,也热衷研究商店街出钱出力,集体推广街区,促进社区融合的实践。漫游街上,他的视线也会散落在经过的牌匾,顶上一列灯柱,还有吉祥物,慢慢发现不同街区都各有特色。就像过几条马路,来到北口,是高円寺另一条知名商店街“纯情商店街”。门牌上冒出一只青绿色公仔,李照兴说是这里的毛毛虫吉祥物,原来其名字叫“なみすけ”(NAMISUKE),为一只以杉树为灵感的妖精。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路上观察”风潮,主张观察一些偏离主旨、无实用价值的事物。李照兴说:“你观察的东西一定要够无聊。无聊的意思是非功能化,由于它是没用的,反而好奇它出现在追求实用性的那个矛盾。”多年来,他的写作专注于城市更新,规划政策,“你看,涩谷那边的工程这么多年,政府与房地产商一直在开发,就像北京那样,通过铲除所有你冇眼睇的东西,兴建天桥连接商场。当年那批发起路上观察学的人,也是对日本那些工整规划的东西做出很大的反讽,去非功能化。”
用广东话说出“纯情商店街”五个字,与不少华语使用者一样,李照兴也开起玩笑,其实有几(多么)“纯情”。即使语言不通,但他在日常接触和制汉字时,也找到乐趣,“与平日的中文有不同理解,这个陌生化令我突然有很多新认识。当然你看到中文字,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演绎,用一些新角度去理解很多熟悉的语言。”
这种新的观看方式,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自由。“比如说街区,定位某一个地点,在香港是用门牌,像英皇道几多号;在上海则是用两条路的交界;北京却是说朝阳门往北300米右侧。而日本,就是用三组数字,丁目、番地,号。这是地理上最大的理解分别。当你游走时,突然间觉得属于某一个区域的概念强了很多,即是你属于某一格里面。我经常用地图的鸟瞰方式来看事物,包括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新方式去看自己和城市的关系,或者看周边社会的角度,只要足够新鲜,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自由。”

小杉汤:钱汤复兴,城市更新实践
“将古老的东西潮流化,也是关乎审美,生活美学,你看那些新标志设计,是高于水准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
穿过纯情商店街,拉面烧肉立食,也有杂货古著店,街道切割区域,横侧直走,离开主要商店街,很快便钻进人迹稀落的民居一带。远远看到“小杉汤”招牌,直至转到正门,才看到整个钱汤建筑全貌。烈日下的散策,李照兴轻提小布袋,单手摇着纸扇,像个说书人,娓娓道来钱汤复兴运动的故事,远处看去,又似一个刚好从隔壁过来的居民,悠悠然,准备来钱汤浸浴。
“这个小杉汤是近年的钱汤复兴活动一个代表,改造一九三三年老舖,升级整个设备。以前的钱汤很破落,九十年代,我们来日本的时候,像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现在复兴,不单是给本地人,也吸引很多外国游客。我看日本杂志大,那些《Casa BRUTUS》、《pen》等等,全部都在讨论这个钱汤改造潮流。”
小杉汤的旁边是“小杉汤となり”,利落简洁的共用空间,平日采用会员制,周末为公众开放。“人们来工作、用餐,甚至像托儿所,带孩子来休憩。这是通过结合新空间和业态去改变老品牌,凝聚整个社区的尝试。作为城市更新或社区活化的实践和保育,把几个我留意的议题都混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案例。”
这位说书人乐此不疲,顺道提起,在另一边墨田区的“黄金汤”,邻近也开办手工啤酒店,他欣赏接手的第三代经营者有很多想法,“将古老的东西潮流化,也是关乎审美,生活美学,你看那些新标志设计,是高于水准之上,跟香港或其他城市差很多。我基本上观察的或者写的东西,都是从表面的美感出发,再关注实际内里背后的运作系统,政府怎样牵涉进来,产业面对什么困难。这些不是表面上看见的那么简单,背后必有一套运作逻辑。”

飞地书店:站在改变风口
“我最喜欢的是站在这时代风口上记录,这就是我应该站的位置。城市变化最大的时候,往往我就在场。Better or worse,无论是好或不好的变化,总之大变化就是动因。”
李照兴正在观察的,还有更庞大的一波社区变动,那是近年华人社区在日本的壮大,如何逐步冲击日本。近十年,中国人大举赴日投资或移居,年轻一代“躺平”,“润”到国外,日本是热门首选。目前在日的外国人留学生,中国人就占去四成。此行的下一站,李照兴选择了今年三月才开办的华语书店空间“飞地·离岛书店”,卖书办讲座,凝聚起一班东京华人,按他形容,正是这波华人社区趋势最新发展的象征之一。
“这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不单止华人,全世界都是这样,有移民、难民,又有人要‘润走’。在东京,特别是疫情之后,出现了专门针对华人的生活经济圈,餐厅不在话下,现在有这么多麻辣烫,茶餐厅,还有华人书店成立。从饮食到精神文化物质,在东京的华人社区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日本社会民间的冲击其实很大,移民数字到游客数字,抢米新闻,诸如此类,是不断冲击,你看到现在很多(华人)负面新闻。”他续说,无论日常所见,抑或统计数据上,大量外来人口,无论是华人,欧美人,南亚人,将彻底改变整个日本,他扬言可称之为“二度黑船来航”。
李照兴扬言,现今自己身处东京,正是记录日本另一个转折的大时代,“我经常说,我最喜欢的是站在这时代风口上记录,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站的位置。作为媒体人也好,创作人也好,在城市变化最大的时候,往往我就在场。Better or worse,无论是好或不好的变化,总之大变化就是动因。”
香港九七回归后,焦虑退烧,一波北上潮兴起,人们争风逐浪,要赶上好时机,开眼界,创潮流,见证时代新章。李照兴自然没有错过在场的机会,2004年跑到北京,四年间贴身观测他所经验的“潮爆中国”。回顾彼时北上,他直言与今时今日去大湾区的思维和想像完全是两个极端。“那时整个民主回归,前提是中国大陆不断开放,无论媒体、社会,还是文化的提升。起码我这一代人是这样想,假设将来香港和大陆城市都一样,意思是大陆城市变成香港这样。不是现在反过来,香港变成大陆城市。当时那个朝气和期盼是完全不一样的。回看2004年到2008年,是中国社会文化改造的黄金时期,我当时报道城市发展,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新建筑,天花龙凤的,又有地下音乐,所有都是气象一新,觉得好正。因为你会发现,哗,个未来嚟紧(未来正在来)呀!整个规模和可塑性真的很厉害,这就是未来。”时隔差不多廿年,听他忆述往事光景,依然感受到那股壮志振奋。
然而,这份对未来的期盼无以为继。李照兴看到北京的大规模汰旧换新,取缔旧店舖商场,铲除低端人口,“整个城市的组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对于文化的管制深入了很多,除了资本和政治之外,文化上已经不会领先。”所以,他离开了北京,把向往和关注转移到另一个大都会——上海。

“当时经济和整个社区发展,上海都走在中国的前面。上海世博之后的那十年,是其中一个发展最好的日子。疫情改变了所有事,上海封城,不单只是对我,很多曾经相信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先进的城市的幻象,是破灭了。不只是上海人,是广义上住在上海的人,造成身体和心灵精神方面的冲击。(疫症)最严峻的时期,人心惶惶,同一栋大厦如果有A户发现阳性,全栋住户都要迁去方舱,你觉得很荒谬。那个城市进展或者文明进展的假象,到此为止,终结了。”他再一次经历幻象破灭,意兴阑珊离场。
不消十分钟,来到早稻田通り,实际上已属于中野区范围。书店藏身在大路旁一栋偌大的浅灰色钢筋混凝土公寓大楼内,不过这天没营业,只见门口放有一块香港小巴车牌,以经典红蓝配色写上书店名。接着,李照兴提议最后去一间酒吧,顺便分享自己手头上针对IPA(India pale ale,印度淡色艾尔啤酒)的研究写作,于是重新往高円寺车站方向走。住宅区内,四周是重复排列的街道与平房,寻常相似,藏匿着低调的杂货小店。
告别上海之后,李照兴曾重新考虑回去香港,“但2020年之后,香港又不是那回事了。开始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base,还有身份的问题。以前都是以香港人身份做座标,我写城市观察,潜文本都是对比另一个城市,和香港作为参照,很老套的双城记比较。怎样看城市,其实座标就在香港。”走着说着,发觉竟绕了一圈,回到同一个路口。他停下步,打开了手机的地图程式,看着蓝点,指尖左右滑动。“但是发现,2019年后,个座标冇咗。就好像我现在,要不断看Google map,重新找到不同的座标。”他苦笑道。

消失的座标:昨日香港
“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整个新常态下,暂时对我来说,香港是突然间消失了,变成没有一个参照的base。我亦没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处于一个散居的状态。”
酒吧傍晚才开始营业,于是只好随便走进刚才经过的咖啡店,暂借一处能对话的空间。李照兴用简易日语向店员落单,大热天,他点的还是热咖啡。坐在咖啡店内,继续回到关于香港作为一个座标的话题。他解释:“座标的意思是,可以通过论述也好,观察也好,参考其他社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并带回香港。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整个新常态下,暂时对我来说,香港是突然间消失了,变成没有一个参照的base。我亦没有其他新的base,所以我处于一个散居的状态。”
按李照兴所说,自己作为传媒或写作人,无论是好或坏的变化,在场都很重要。那么,为何如今没有选择于香港在场?“我想经历了运动的人,好难即时处理那件事。现在都只称作为‘那件事’。某程度上,我现在心理上是在疗伤,我还未能面对。有几套重要的纪录片出了,我还未敢看完。”原以为,他早已见惯时代风浪起宕,原来仍有一处归途,苦无出路。
他续道:“简单来说,我们那一代相信了几十年的东西,突然间烟消云散,一夜之间是没有了。不单单是讲民主回归进入中国,相信中国城市会成为香港那个信念,突然没有了。以前北上,仍有一班人很抗拒大陆的事物,但确实是有一些大胆的想法,或者对于文化深入的思考,接触到很多大陆学者,确实很厉害,但是当时香港人不会认同。我做的事情,老套一点说,是做桥梁,说极致一点,就是在做‘无间道’,把这些东西反向传回来香港,开拓大家视野,将新消息回遣香港。”他形容,过去像探子回报,但现在回报的本营都不存在了。如今能做的,只是研究以往的香港,或者他所经历过的香港。

今年,李照兴出版新书《等到下一代》,副题明言“流行文化与香港身分认同史备忘”,正是疫情下散居日本时所写,论述香港流行文化演变,以及通过流行建构身份认同。人在异地,他认为可以通过陌生化,更加纯粹去做一些记忆的书写。他写书时,忆记起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二战后作者离开了欧洲,在手边没有任何文献之下,单从脑袋的回忆,来记忆他旧欧洲的生活。对我来讲,那段时间是在日香港人,当不可以面对从2019年到2020年发生的事的时候,只能先处理以前的事,以往五十年的香港文化为何这么兴旺,我当年的文艺青年成长经验,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经历过。”结合个人经验与流行美学梳理,他写港产片与Cantopop,电视捞饭,流行电台,也写街道文化与饮食,其中一篇针对电子音乐,说当年达明一派的声音回应时代焦虑急迫。殊不知,时代换过模样,人们仍旧凭歌寄意,慨叹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李照兴六月也去了黄耀明在东京举行的演唱会。他说,明哥唱了李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同一道问题,李照兴答得直接:“当然不会好。我本身是很悲观的,面对过这么多的变化,对全世界人类悲观。我们这一代九十年代读大学的人,相信多元文化,相信‘历史的终结’,全世界民主自由化。但现在全球转右,封闭主义,难民和移民是新常态,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最新的冲击。”
“我不是浪漫化、哈日的人,不是认为日本什么都好。”紧接这句话,是李照兴的一个强烈主张:“这是一个很个人的理解,这么多年游走全世界不同城市的经验,在整个社会礼仪到文明程度,从最基本的干净程度,到待人接物,礼貌守则,日本已经去到这么多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不会比现在或者之前的日本更加好。所以我记录的不单止是城市,还是人类文明的下跌,从2020年开始,人类文明不会再进步,这就是我的结论。所以我一直处身在这个极端的,本来相对来说是好的基础上,我在进行这个新的观测。”
他时常提到的一个樱花比喻问题,“每年日本以个位百分比下跌人口,纯属数学层面计算,以后人口减少,那日本会消失。我问日本人,你宁愿像樱花一样,灿烂然后凋谢,还是为了苟延残喘,输入一些外劳或者外人,令到这里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但已经不是以前那回事了?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正面回答,但我觉得这个比喻是valid的。”

散居者与城市的距离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现在面向的写作市场和目标,都是全球自由华人社会。”
流连不同城市,幻海万象,有过期盼张狂,屡屡扑空退场,李照兴对城市人间,始终抱持惊人的执迷。他清楚自己完全属于大城市,追求一种“24小时不打烊的自由”,“很沉迷随时可以选择任何东西,就是说你随时随刻,突然间想去吃一碗面,或者看一个show,见到一个人,到你想安静,就关上门,留在家里。大城市的五光十色,happenings,仍是我的追求,或者是生存的重要条件。追求一种知识,或者追求一种寻根问底,而那些都很物质化的。”这番说话,是否与他那一代人,亲身经历过所谓香港黄金时代的鼎盛有关?他不否认有这样的背景,却无法就此断言,“当时确实是这么物欲横流,声色犬马,可能是背景价值,也不排除。但我觉得有种根本,是个人的,不知道是否是一种inborn,还是后天,但对我来说是这种身体或者是物质更加有兴趣,而不是一种灵性或自然。”
这样一场高円寺午后漫步,言谈间,大议题如城市规划、社区更新,到钱汤与舞踏,专精如IPA,小津安二郎等,李照兴一直侃侃而谈;但偶然谈到正进行大型世界巡演的当红日本歌手,他不但不认识,更大方承认,对于时下日本流行音乐知之甚少。诚然,城市色相纷陈,层层复杂组成,认识一座城市,往往受经验与资讯所限。说到底,怎样才算得上熟悉一个城市?
“真的不能单凭问所谓熟悉的知识,像我讲某样东西,你有没有听过?你会发现,很多日本人对你讲某些东西,反而不知道。难道我比他更熟悉日本?当然不会这样。所以对于地理或者历史文化的知识,不能作为评判熟悉的标准。那是很狭窄。我觉得,反而那个属性是反向来理解,对于这个城市还有多少好奇,多少热爱。熟悉是温度,一种热能来的,所以,我理解的那种熟悉,就是在于你对于那个城市的热情,不停发掘,不断去煲个温度,而不是冷却了。”这种说法乍听之下其吊诡之处,因为假如对事物了如指掌,理应不再感到新鲜好奇。李照兴解释:“我觉得因为这个城市变化很快,你要紧贴城市新的模式、新的规则,反而需要刚才说的好奇和刺激,才会维持整个趋势。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像刚才所说,只要愈是包含著好奇,发掘新的东西,保持更新,才会更加熟悉。”

那么再次回过头来,又是否对现在的香港已经不熟悉了?李照兴闻言,答得斩钉截铁:“我绝对不熟悉。”
“说真的,我十多年前开始已经不熟悉了。早在2004年,我大部份时间不是在香港。当然我说,以香港作为座标,意思是建基于我的写作生命和写作方向,或者读者群众在香港。所以,正如我在新书所讲,我只能够写到2012年。”书中也有论及近年香港电影现象,他坦言只是藉新气象来展现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消失的座标,身份成了另一个课题。李照兴在新书首章,第一句就写:“当身分出现之时,它却首先是以正陷于消失的形式呈现。”如今,他定义自己是散居日本的香港人,萍水相逢,偶然被问到是哪里人,他认为,能避则避。“我避免说是什么人,我只会说我来自香港,I am from Hong Kong。因为避免解释Chinese这么复杂的词。又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又可以是overseas Chinese,华裔,华侨,也可以指你正在用的语言是中文。说真的,你行走江湖这么久,你知道跟这个人是不是会深入交流,以后做朋友,如果只不过是打招呼的过客,就无谓交流那么多。”

他没有否认身份的重要性,深信香港人的身份建构很大程度上来自香港的流行文化。“没有流行文化的话,向外人是无法解释的。 没有香港文化,或Bruce Lee那一代开始,香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Beyond唱的《海阔天空》,没有粤语歌在八、九十年代风行全中国,就不会令人知道香港。来自香港,不单止身份认同,甚至有身份自豪。好了,今天对于我来说,香港被摧毁了。整件事怎么重新建立你的身份呢?你identify的是哪个香港?对于我们这些英殖时期的人,当然是1997年时的香港,在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又不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都是模糊其词去说这件事。”
过往在北京和上海旅居,李照兴以说得一口北京腔或上海话为乐,试着融入社区,变成当地人;但到了日本,要试图成为日本人或东京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如果长居(日本)的话,都是一个城市的陌生人。从语言到整个文化,我说我fit in在这里,是因为我不会引起麻烦,就像那些‘すみません’文化,只求没造成麻烦。所以,反而我再stick to自己,就是一个来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我现在面向的写作市场和目标,都是全球自由华人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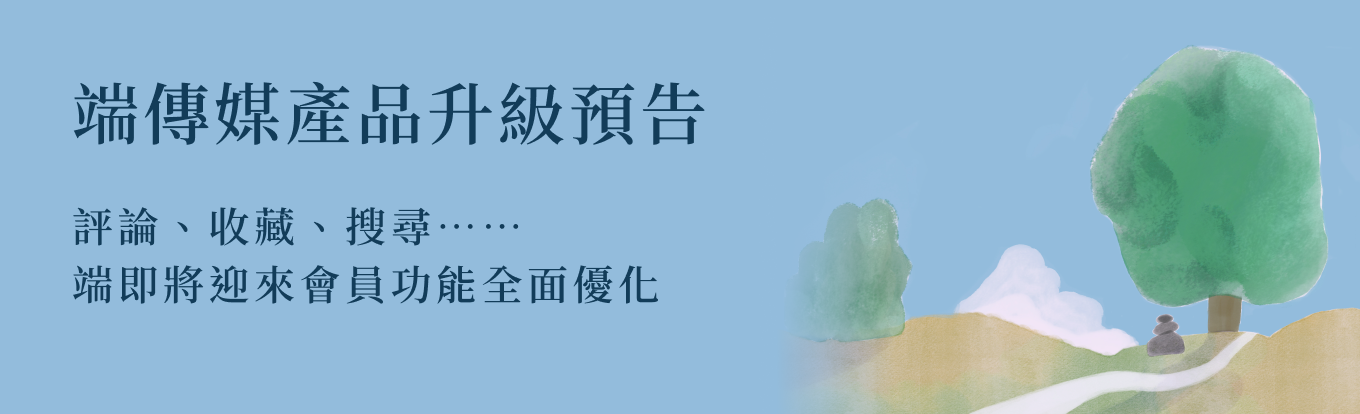



「一個來自香港,散居全球的人,面向全球自由華人社會的寫作者」這個定義非常有意思。相當期待。
有日本人問過我一個問題,大陸和香港台灣的教育發展水平非常不同,一同在日本,能有什麼樣的交流?
讀文章初段,覺散亂摸不著重點,中段以後轉入受訪者的遊歷(北京、上海),最後踏入李照興的起源地~香港,哪個消失了的「舊香港」。
多麼優秀的文章佈局呢。
「從2020年開始,人類文明不會再進步」這句話滿震撼到我,世界在極速變化是真的,但進步與否卻是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