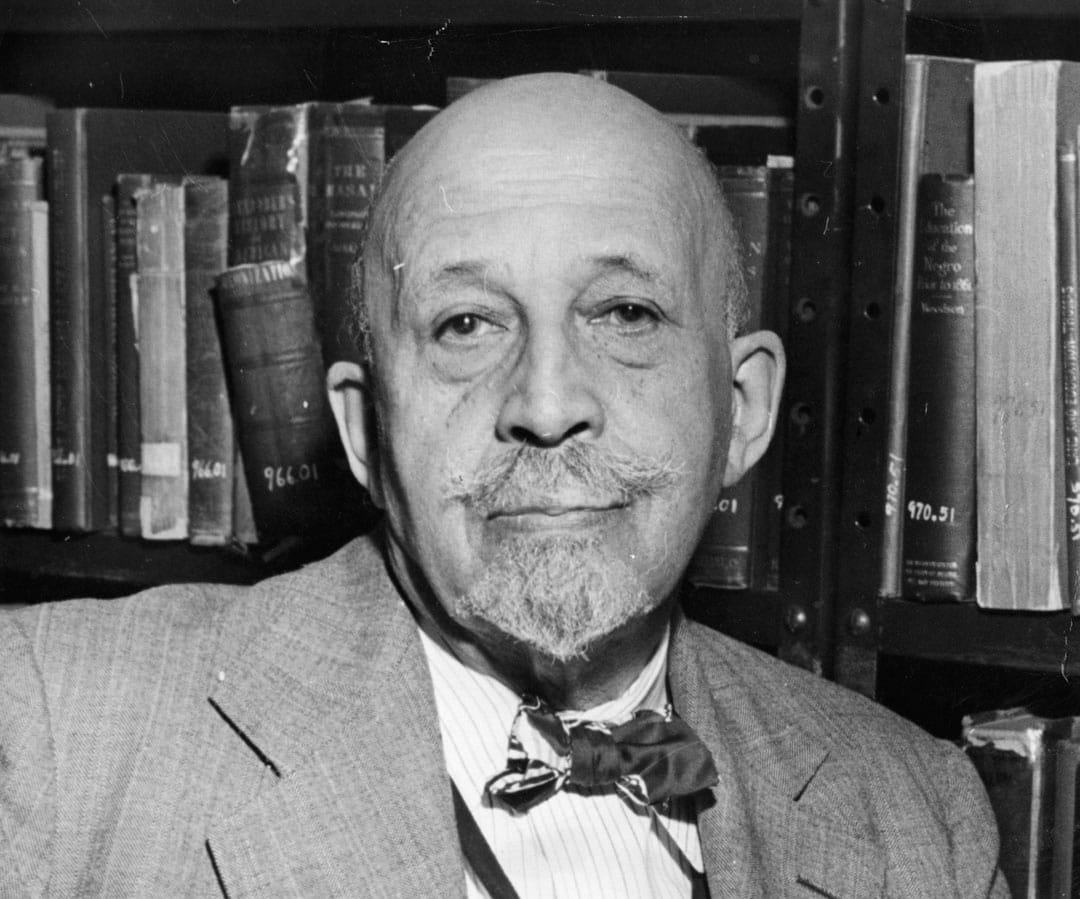几年前,在美国一个“非洲社会主义”读书会上,我曾听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闲聊到说自己每周末都要开车去附近的乡镇,参与本州的社会主义政党活动,周周如此、雷打不动。最近,这位年近八十的非裔教授再次出现在乔治·佛洛依德之死所激发的抗议活动前线,还在媒体采访时强调,这是“我们必须走上街头”的时刻。他的一篇短评更是直接写到,奴隶贸易史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现状是必然的,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应着眼于抗争和改变美国这个“阶级社会”。
此刻似乎正是回顾黑人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联系的契机。当下的抗议示威活动再度被编入民权运动叙事,中文媒体和社交网络也开始回忆和怀旧黑人运动领袖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毛泽东曾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以及《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就被广为传播和评论;中国外交官员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也被联系到这一政治遗产。
冷战时期的中国和美国黑人运动究竟曾经有过怎样的连结?这些合作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渐渐终止的?传媒研究学者罗伯逊·弗雷泽(Robeson Taj Frazier)的著作《东方黑:美国黑人激进主义想像里的冷战中国》(The East is Black)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