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话想说吗?端传媒非收费频道“广场”欢迎各位读者投稿,写作形式、立场不拘,请来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读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最近有一个名为“争取正名 - 2019香港亚太聋人运动会”的Facebook专页,里面提及香港确认取得2019年Asian Pacific Deaf Games的主办权。事实上,香港曾在1984年主办第一届亚太聋人足球锦标赛(事后获亚太聋人运动委员会追认为“第一届亚太聋人运动会足球比赛”)。事隔35年,香港再次主办这项聋人运动盛事。可惜的是,负责筹备这次运动会的委员会却将是次运动会命名为“亚太聋人/听障运动会”,执意加上“听障”一词。一班聋人朋友、弱听朋友和健听译者朋友对此极之失望和难受,坚决不妥协,决定聚集起来争取正名。
可能有人会问:“也不过名称一个,为什么要这么执著?”话可不是这样说呢,当近年“你会称呼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中国香港人,还是香港中国人?”的讨论越见频繁之际,我们便知道称呼并不只是一个称呼,背后盛载著的是与身份认同、文化、历史、价值等有关的坚持。同样,对聋人社群来说,“聋人”和“听障”两个称呼,正正反映两种对立的价值。
这次,请容许我尝试整理一些资料,尽管不尽完整,但也许仍能让我们轻轻窥探聋人社群如何理解自我、并与以声音主导的社会连结。
态度 (Attitude) 影响用词 (Terminology)
如何称呼一个群体,特别是小众 (minority),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当中牵涉的除了是人们对一个群体的理解外,更可从中分析人对该群体的内隐态度 (implicit attitude),甚至可引伸至分析社会偏见、隐性歧视 (subtle discrimination/ microaggression)、权力失衡、健全霸权 (Ableism) 等等的社会议题。
从病理角度看“聋”为残障、缺陷的态度,正正堕入了“健听霸权主义”的思考模式。
举个例子,例如英文中的”Person with Disability (PWD)”,中译时有人会译作“伤残人士”、近年则有人译作“(社会)受障人士”。前者聚焦的是“那人是伤残、有缺陷”,后者强调则是“社会导致那人(被逼)承受障碍”。的确,假如社区里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沟通做得完善,而我们每一个亦不带歧视态度地去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话,障碍就不再存在。可见,每个指称 (referent) 背后的象征意义是最值得我们关注、也是必须重视的。
说回聋人朋友。一直以来,指称聋人朋友的词语有很多,“聋哑人士”、“失聪人士”、“听障人士”、“弱听人”、“聋人”等。今次让我们先看看“听障”和“聋人”两词。
“听障人士”(Hearing-impaired)——从医疗模式看缺乏
聋人朋友表示,过往在香港多用“失聪人士”一词称呼聋人,在医疗、福利申请等各范畴皆是。直至200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举办Deaflympics的地方,并将Deaflympics的中文名称定为“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听障”一词始由台湾传至香港,被广泛使用。然而,在广泛使用之前,其实我们曾否想过这词背后的意思?
“听障”指听力上的失去或障碍,背后反映的是医疗模式 (Medical model) 中认为人若在身体机能或功能上有未符合常规的地方,便需要治疗和补救的想法。可见,这模式视耳聋 (deafness) 为一种缺憾,认为主流的“声音世界”才是正常的、好的,并认定健听人比聋人有更高的层次和地位。于是,生活在“无声世界”的聋人是“不正常”、“有障碍”、是需要接受治疗的病人,更应及早接受口语训练以便与健听人沟通和融入社会。
原谅我狠狠地总结以上态度:“因为我 (健听人) 是社会的主流,所以与我不一样的人应该使用我的方法,努力克服他的‘障碍’,去融入我的社会”。这种因著自己能听到声音,而在有意无意间表露出的高傲,称为“健听霸权主义 (Audism)”。Humphries (1977) 曾为Audism下了一个的定义—“the notion that one is superior based on one’s ability to hear or behave in the manner of one who hears”(中译:“一个人认为健听人、或能表现得与健听人无异的人是较优越的”)。而上述从病理角度看“聋”为残障、缺陷的态度,正正堕入了“健听霸权主义”的思考模式。
“聋人”(Deaf) - 从文化语言模式看独特之处
“聋”并非一种残疾或损失,而是一种的特质,亦是让聋人成功创造其他独特之处和文化的元素。
文化语言模式 (Culturo-linguistic model of Deafhood) 是由英国聋人社会学学者 Paddy Ladd 在其著作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中提出的;更早的说法是来自1975年伍德华教授(Prof. James Woodward Jr.)的一个演讲,当时伍教授已提出”deaf”与”Deaf”的分别。
文化语言模式视“聋人”为一种身份认同,并提出聋人实拥有其独特的文化 (Deaf culture)、社群 (Deaf community) 和语言 (手语;Sign language)。因此,从这角度出发,“聋”并非一种残疾或损失,而是一种的特质,亦是让聋人成功创造其他独特之处和文化的元素,当中包括手语、De’VIA (Deaf Art)、对视觉空间拥有极高的敏锐度 (Deaf Space) 等。聋人 (Deaf) 对于聋文化和手语有较强的归属感,亦已内化一些共同、正面价值(如“聋人与健听人有不同之处,但不代表较低等”)。最重要的是,聋人朋友对他们“聋人”这身份,感到无比自豪。
明白的,或许对健听人来说,“聋人”好像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词。我曾经也这样认为,觉得“聋人”是一个负面的词语,聋人朋友知道后会不开心;而“听障”会是一个较礼貌的称呼。然而真实的情况却相反,聋人朋友真正在乎的,是词语本身的含意——视他们为一个人(聋人)、还是只看到他们的障碍(听障)。原来“聋人”才是对他们最合适、最舒服的称呼,亦是尊重其聋文化和社群历史的表现。
改变用词、改变态度
“聋人”和“听障”所表达的是两种对立的态度——前者重视人的特质、视人为一个有不同面向的整体;后者聚焦于人的障碍,且以一个病征指称一个群体,其怪诞的程度就跟称呼别人为“鼻敏感”、“香港脚”无异。把两词并列于一起,绝不恰当。
或许“听障”真的今期流行,但流行绝不代表恰当。这篇文章、这次争议的出现,切切反映当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啦”,或当我们需要有意识地、甚至小心翼翼地三思到底该用哪个名称去称呼一个长期被欺压的群体时,那就代表社会上有某种意识形态、以及对这个群体的贬低已根深柢固地植于我们的思想和词库当中。
用词背后所表达的是怎样的态度呢?这态度或价值观从何而来?当语言能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和理解事物时 (Whorf, 1997),是时候我们使用更合适的语言,去塑造更正确的个人、甚至社会态度。当我们观察到这状态、并愿意坦白承认并身体力行的改变用词、改变态度时,便是减少伤害和歧视的好开始。
我亦恳切地希望,这次运动会的筹委会成员愿意切实地尊重聋人社群,以最恰当的名称命名是次运动会。
参考资料:
Evelyn H. (2013, July 13). Deaf-Mute, Deaf and Dumb, Hard of Hearing, Hearing Impaired, Disabled, Handicapped, Hearing Loss, Deaf.
Humphries, T. (1977).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deaf-hear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n.d.) Agreement on Terminology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Ladd, P. (2003).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Multilingual Matters.
Laszlo, C. A. (1994). Is there a hard-of-hearing identity?.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18, 248-25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n.d.) Community and Culture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oss, M. (2000).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Retrieved June, 1, 2000.
Whorf, B. L. (1997).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 (pp. 443-463). Macmillan Education 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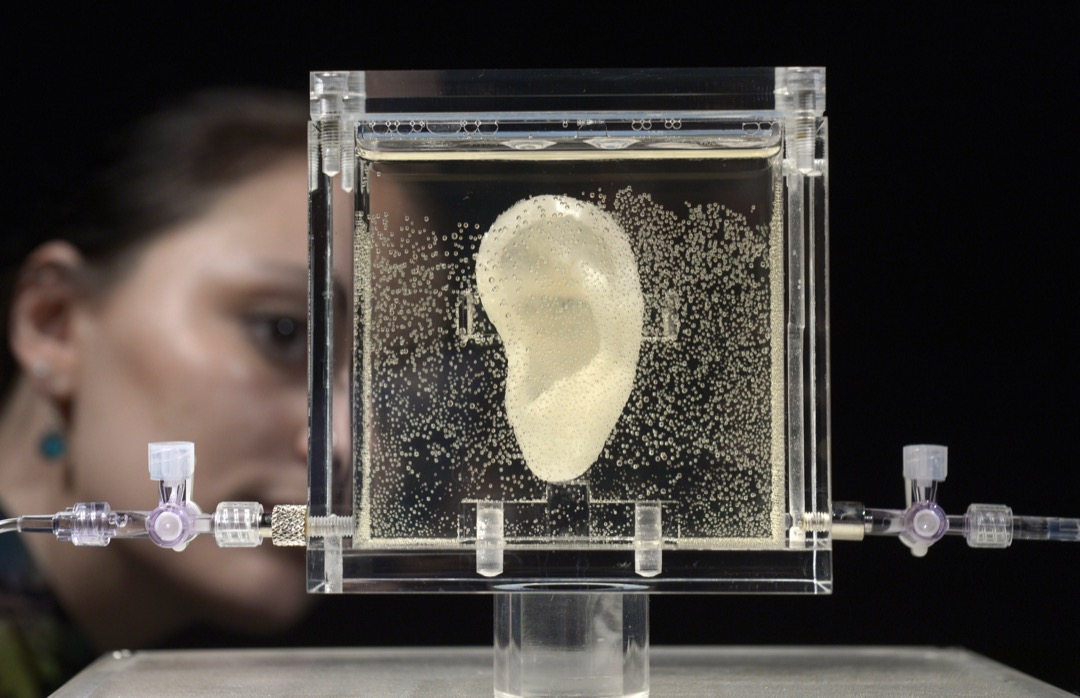

另:文中“当时伍教授已提出”deaf”与”Deaf”的分别。”内引号有误,请留意。
本以为这会是一篇冷门文章,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讨论。
读过文章和大家的讨论以后,我还是觉得“聋人”比“听障”更是含有贬义的称谓,不知道是不是身边的文化环境使然。
譬如:小时候有段时间摔跛了脚,如果有人叫我“瘸子”、“跛子”,我觉得是比叫我“脚摔跛了的人”更不尊重我的。在这里我觉得“摔跛”这个伤是客观的,就如“听觉障碍”是客观的、是先天或者后天的一样、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而“跛子”、“聋人”这样的称谓让我感到反而是一个附加了贬义感情的、对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蔑称。
看到讨论里有一个热点在于“障碍的客观存在”:有的朋友认为障碍的存在是社会给特殊群体带来的,生活上的障碍;而我认为这个障碍是存在于听觉系统里的,是生理上的、医学上的、不带感情色彩的障碍。
什麼"「聾人」和「聽障」所表達的是兩種對立的態度..."簡直是沒話找話說。
@sekii 对于日语词的一些补充:
失聪者在维基的词条为:聴覚障害者,但通常称之为「耳の不自由な人」。
这个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大学老师提过,认为「耳の不自由な人」,或者对失明者「目の不自由な人」的称谓比「聋人」、「盲人」更为友好亲切。
人權的核心在於人性尊嚴,其中稱呼是最容易與尊嚴相關連的事物,許多罵人的話語,就是用各式貶義的詞彙稱呼他人。
而此次的問題就是出在何者帶有貶義“聾人”亦或“聽障”,這一點十分困難!
因為在一個不尊重人權的環境中,這兩個詞彙都被用來歧視。
所以最重要的是改變態度,用尊重來面對這個問題。
籌組委員會為何執意要加上聽障,是為了何種目的,沒有人知道,最好的處理方式,應該是用尊重的態度來處理,而不是一意孤行。
何謂尊重的態度:我想要怎麼叫我自己,就請用這個詞彙稱呼我。(例如:台灣原住民曾被迫取用和名與漢名,如今可選用傳統原住民人名,就是逐漸尊重的態度,雖然程度還是不夠友善)
抱歉,墙内人士问些傻问题。如果“聋人”的重点落在“人”,那么“听障”加上“者”不就可以了吗?
另外,聋和听障的区别、听障一词的所含意义我想我理解了,但是,聋就没有自这个词诞生以来所被累加的歧视含义了吗?还是说直面是最好的平权运动?另,日语的话可能就因此会再找或造新词。
對「障礙」之是否客觀存在的回應。:
這樣看吧,大部份智人,擁有聽覺,少部份人因先/後天原因沒有,單從擁有一種特徵(感官)與否而言,這只是一種 deviation
障礙或殘障,則是disability
意謂缺乏做某些事的能力
聾人的確難以與人通過聽覺交流,部份先天聾人在發音上也面對一定困難
但交流有多於一種方式(手語,文字)
他們並非完全缺乏交流能力
若社會配套上能助他們無礙地與其他社會人士交流溝通
則此聽覺交流能力之缺失不再構成日常生活之障礙
此時雖則他們的確缺失聽覺交流能力,但生活並無障礙,此「障」究在何處?
若生活無不便,但只要無法以社會主流方式溝通即為有「障礙」,此看法本就有問題。
這篇文章在論說的正在於此
在於指出不存在所謂「客觀的障礙」
因為一種deviation是否被視為障礙,一則取決於其於日常生活有否不便,二實乃是社會主流所形成的一種觀感,兩者互為因果,而後者究為一種主觀的意見
對「障礙」之是否客觀存在的回應。:
這樣看吧,大部份智人,擁有聽覺,少部份人因先/後天原因沒有,單從擁有一種特徵(感官)與否而言,這只是一種 deviation
障礙或殘障,則是disability
意謂缺乏做某些事的能力
聾人的確難以與人通過聽覺交流,部份先天聾人在發音上也面對一定困難
但交流有多於一種方式(手語,文字)
他們並非完全缺乏交流能力
若社會配套上能助他們無礙地與其他社會人士交流溝通
則此聽覺交流能力之缺失不再構成日常生活之障礙
此時雖則他們的確缺失聽覺交流能力,但生活並無障礙,此「障」究在何處?
若生活無不便,但只要無法以社會主流方式溝通即為有「障礙」,此看法本就有問題。
這篇文章在論說的正在於此
在於指出不存在所謂「客觀的障礙」
因為一種deviation是否被視為障礙,一則取決於其於日常生活有否不便,二實乃是社會主流所形成的一種觀感,兩者互為因果,而後者究為一種主觀的意見
@Rainbow 讀完你的分享,突然想到一些場境:想問一下,假如在一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際會議上,有一位使用華語的朋友需要粵語/普通話的即時傳譯,那麼你會否認為這人有障礙?
又另外一個場境:如果有位媽媽推著嬰兒車,在車站處發現原來車站沒有自動電梯或升降機,只能走樓梯。但她真的難以抱著嬰兒車走樓梯呢,那你會說是她有障礙嗎?
以上兩個處境題,相信尚說道理的人都會回答「不是他們有障礙,而是需要為他們提供設備/服務」,相信你也一樣,對嗎?那麼為什麼聾人朋友不說口語、而打手語,我們會說是他們擁有客觀存在的障礙?如果社區的無障礙資訊(如手語傳譯)做得完善,障礙就不存在於聾健群體之間。那到底這是他們的障礙,還是我們的社會未夠好、因而令他們不得不承受障礙?同樣,像你也有提及的無障礙設施,如果做得好,斜道的斜度、闊度和位置有切實考慮輪椅使用者的需要時,阻礙達致通達的障礙也不復存在。
你所提及的那句「不管是處於殘障人士的角度還是健全人士的角度,下意識地認為殘障人士是有障礙的這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看來在有意無意間把責任歸咎於「殘疾人士」,認為他們應該盡力去克服自己的「缺陷」,融入主流社會。其實,你也曾提到應加強做好無障礙設施,這很對,我十分同意。但請不要忘記,「無障礙設計」的目標是達致「共融社會」—共融,該是雙方都共同努力去嘗試了解對方、照顧彼此的需要;而並非單一地要求社會上的小眾配合我們。這樣的想法不是「融合」,這只叫「配合」,而「配合」並非文明和人道社會該高舉的價值。
Sorry, 應該系@Yilin
@Yilln 我的出發點是從身體健全人士的角度,但我覺得,不管是處於殘障人士的角度還是健全人士的角度,下意識地認為殘障人士是有障礙的這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這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不管怎麼稱呼,障礙就擺在那裡,所有人都不可能假裝看不見。然後回到健全人士的角度,被人認為有障礙的並不是令人羞恥的事,而如果「殘障人士」認為這樣的稱呼是有損他們尊嚴的話,這反而讓他們更加特殊化。所以,我們與其去爭論對殘障人士的稱呼,不如在社會上多添加無障礙設施,這樣能夠讓殘障人士感到溫暖的同時又可以令他們的生活相對更方便。
假设一下:假如一直以来都没有“聋人”这样的称呼,只有“听障”这个词语。想必这部分群体还会发生更名运动,要求称之为“聋人”,依然会有很多的理由讲出来。
语言和词汇的发明没有歧义贬义。只要有称呼,就意味着这是一类群体。社会对一类群体有一个特定的称呼难道有什么错么?老人、孩子、女人、男人、聋哑人…如果大家都这么玻璃心,以后就改成年龄偏大人士、年龄偏小人士、染色体XX人士、染色体XY人士好了。
Rainbow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也混淆了聋人的自我感受和健全人对聋人的立场这两方面问题。聋人固然要学会不必理会他人的看法,但是社会对聋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重视称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称呼影响个人对事物的看法,称其为听障人士其实就是下意识的认为聋人是有障碍,和社会接轨有问题的;而称其为聋人是肯定了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好像现在用rainbow来表示同性恋群体一样,艳丽的七彩色一下子就给予了人正面的印象。
当初要把失聪改成听障的是你们,现在要把听障改聋人的又是你们,我麻烦你们能不能不要有事没事就头脑风暴一下来指挥社会大众。这样指挥来指挥去是真的认为整个世界都是NPC别人不会觉得困扰是吧。
“視他們為一個人(聾人)、還是只看到他們的障礙(聽障)。”我认为这句话是本文的核心观点。
喜歡這篇文章。就像禿頭人士被稱呼為「生髮障礙」,平胸的女人被稱呼為「發育障礙」,有明顯虎牙的人被稱呼為「齒列畸形」一樣。這些都不是所謂的缺陷,就是個人的特質而已。想像如果聾人是主流的世界,國際語言是手語,以現在的流行用法來說,讀不懂點字的我應該就會被稱呼為殘障吧。
本文的中心,我理解為「將有聽力障礙的人」看作為一個人所以要稱呼他們為「聾人」,而若稱呼他們為「聽障人士」則是著重於他們的障礙。但我想問的,一個存在「障礙」的人為什麼要因為其他人覺得自己有障礙而煩惱?不管用什麼稱呼他們,他們身上客觀存在的障礙是不會變的,而且即使社會的無障礙設施再完善也好,他們的生活障礙是客觀的存在的,不受外界的變化而變化,亦都不受他們自己的主管感受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要不是侮辱性的詞彙,怎樣稱呼他們又如何?「身體存在障礙」本身就是這類人群的客觀的固有標籤,以平常心對待這些身體障礙,接受障礙的存在並且努力習慣它,那怎麼被稱呼又有什麼所謂呢?所以我覺得這是小題大作了。
感謝您的對比分析與解釋,讓我學習到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