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日本独立记者铃木智彦风尘朴朴地来到台湾。这位以报导日本黑社会闻名的记者,为了日本鳗(Anguilla japonica)鱼苗的犯罪问题,已经潜伏调查多年。他发现亚洲各国有条隐形走私链,台湾扮演关键角色。
鳗鱼饭是日本美食代表,夏季节庆吃鳗鱼的习俗从江户时代延续至今,带动周边国家捕鳗苗养殖外销。1970年代台湾曾是“鳗鱼王国”。但因过度捕捞,欧洲鳗、日本鳗双双陷入濒危,2014年日本鳗被列入IUCN濒危物种,引发社会反思:“我们正在吃像熊猫一样稀少的生物吗?”
2007年开始,台日双方都互相禁止出口鳗苗,保护国内渔业资源。吊诡的是,日本养殖场还是能取得大量鳗苗。
铃木智彦向日本国内业者多方打听后,得知每年冬季,日本养殖市场上就会流通著标签为“产地:香港”的鳗苗,但香港本身并没有渔民捕鳗。
这些假装成香港出口鳗苗究竟哪来的?业者告诉铃木,多半来自台湾,这已是行之有年的公开秘密。每年秋冬鳗期,日本走私业者就会飞来台湾寻求合作,宴请台湾鳗商吃吃喝喝。
“伪造产地的情形是否真的存在?”抱著这样的疑问,2018年铃木飞到台湾,造访传闻中“真正的产地”。

他驱车来到宜兰,当地渔民很开放友善。有船长邀请他登船参观,带他参观豪华的自宅别墅,素昧平生的鳗苗批发商也宴请他吃饭,没人避谈捕鳗带来的丰沛利润,仿佛这是稀松平常的大自然恩赐。
他也见到了传说中的走私业者,对方对于是否出口香港的回答很暧昧,认为自己只是进行国际贸易,他好奇打听:“除了鳗苗之外,你们平常还从事什么生意?”得知对方还经营地下赌场和性产业。这些中间人通常也有合法公司作为掩护,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
鳗苗的转运因为涉及黑道,他还曾经被其他记者警告:“再深入调查台湾来的走私,你会飘在东京湾喔!”
他写下这段经历,收录在2021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サカナとヤクザ: 暴力団の巨大资金源“密渔ビジネス”を追う》(台译:《鱼与黑道:追踪暴力团的大金脉“盗渔经济”》)
事隔七年,铃木接受端传媒访问,仍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情况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们:“鳗苗的流通,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
经过这次田野调查,他大致确定了日本鳗苗是从地下管道输入的情况确实存在,业界普遍心知肚明。他也曾拜访台湾渔业署的官员,询问走私问题,得到类似“我们有在取缔啦!”的表面回答,他没有具体收获,倒是拿到一堆政府印制的赠品。
依据台湾大学渔业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曾万年整理日本养殖新闻统计,以2019年为例,台湾鳗苗捕获2.7公吨,却入池量只有0.1公吨,相当于有96.3%的鳗苗凭空消失。
兰阳溪出海口:冬季游牧聚落
鳗苗去哪了?在此之前,鳗苗又是从何而来?
距离台湾东南方3000公里的马里亚纳海沟(Mariana Trench),地球最深的幽暗冰冷海域,就是日本鳗产卵的地方。
孵化后的鱼苗是细小叶状的柳叶鳗,顺著北赤道洋流漂动,到了菲律宾外海又被温暖的黑潮带向北方,北漂半年终于来到台湾。入境随俗,柳叶鳗一到了咸水淡水交会之处,身体拉长变化成细长又会扭动的玻璃鳗,准备游进台湾的河川,这一刻,就从出海口被人类拦截了。
跟著铃木智彦的脚步,我们实地走访台湾北部最大的鳗苗捕捞区:宜兰壮围兰阳溪出海口。全台各地沿海都可以捕捞,但是以兰阳溪口地理位置和潮流最佳,台大渔业科学研究所教授韩玉山曾形容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全台有超过五成的鳗苗收获都来自这个区域。
此地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冬季游牧聚落,在每年10月至隔年2月的合法捕捞期,沙滩会聚集汉人渔民、花东原住民、零星打工的散户,近年还多了许多移工骑著电动车来加入,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都有,韩玉山说他们是“八国联军”。
其他地区的捕鳗社群相对封闭,只有兰阳溪口是海上的自由牧场,只要你有工具,有一套青蛙装,都可以来沙洲上搭个帐篷,入夜就下海淘金。

我们请地方文史工作者张峻浩带路,从壮围郊区荒芜的羊肠小径进入沙滩,这日低温下探9度,东北季风夹带细雨打在身上。就在我冷到全身发抖萌生退意时,终于出现几个人,他们手上带著阿比(注:一款养生药酒)和食物,赶紧上前攀谈,表达想采访的意愿,他们一口答应,还邀请我们:“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像花东原住民这种外县市来的捕鳗人,会用废弃帆布搭建帐篷,离乡背井在野外生活长达四个月,这是他们仅有的私密空间。每座帐篷都有门牌,是地方政府发的“鳗寮搭建许可”,目的是确保他们离开时会拆除。帐篷内内部简陋克难,但应有尽有,发电机、灯泡、小厨房、床组沙发俱全,有的帐篷很大,甚至还能隔出一房一厅和简单的淋浴间。
也有半圆形小帐篷,是当地渔民用的鳗寮“小乌龟”,可以存放工具也可以吃饭休息,体积轻巧,机车一上就能拖著走。
龟山岛前,大大小小的鳗寮散落在绵延数公里的沙洲,与垃圾、漂流木、动物尸体共存,是宜兰冬季沿海荒凉壮丽又魔幻的风景。流动的人与流动的鱼,年复一年在此相遇。

邀请我们的是阿美族人荣哥,还有族人Kalon、马耀和秀英一起在他家烤火,大家对于记者来访司空见惯,自在地捡木头、丢进火里烧得劈哩啪啦,又把浓黑的阿比倒进塑胶杯,一杯杯劝我们:“喝啦。喝一点比较不会冷。”
Kalon说今天纯粹是来找朋友,以前冬天他会跟族人来抓鳗,现在收获大减,他改去桃园做工地。“这几天放假,我知道他们都在宜兰,就买点小酒来一起喝。”冬天的兰阳溪口可以找到很多族人,是他们第二个家。
荣哥是纺织厂退休工人,马耀平常在部落种田,他们的自我介绍方式是:“我们都是一些没有用的老人啦,才在这里捕鳗,可以做别的工作早就去做了。”
阿英是少数的女性捕鳗人,来自三莺部落,她在荣哥的帐篷里煮鲭鱼罐头面条给大家吃,看到相机,板著脸说:“不要拍我啦。”过一阵子,又忍不住说:“我朋友许哲嘉(编按:纪录片导演,作品《捕鳗的人》入围2021金马奖最佳纪录短片)也常来拍,你们认识吗?”
阿英看我们人多,又开了一罐罐头、加入仅剩的面条,点燃卡式炉,再用矿泉水冲洗一把小白菜丢进锅子,随著汤汁沸腾、面条软烂,她才缓缓地说:“不是我不给你们拍,之前很多电视台来拍,我的姊姊,我的婆婆,我的嫂嫂,她们一个一个被拍到,后来不到两年就死了。真的。”不少三莺部落族人会在冬天来捕鳗,阿英的女性长辈这几年陆续往生,迷信是面对命运无常的敬畏。
接近满潮时间,海滩上已经出现许多捕鳗人,黝暗的夜里亮起一盏盏头灯,不远处海面也点起灯火,许多船只靠近,传来动力马达的声音还有柴油味。

马耀这样的个体户会穿上青蛙装(编按:连身防水衣)抬著圆弧形的手拖网下水。他走进及胸的海水,迎向潮水打来的重量和震荡,保持平衡,同时祈祷鳗苗游进自己的网子里。
若不慎跌倒,水会立刻灌进青蛙装,离岸流也会把人扯进海里。一位捕鳗人陈振辉曾告诉我:“每天都有人沉下去,我们有看到会赶快用网子去捞他,今年救了好几个。”
早期有占到地盘的汉人则可以使用定置网,不用常下海走动,只要在陆地和海上分别固定杆子。量多也较省力,定置网的地盘甚至会在渔民之间交易,一块捞捕区要价20万元(新台币,下同)。
在沙滩等待半小时,马耀拖著湿淋淋的身子上岸,我们赶紧凑上去看他的渔获,看只见大量菜叶、树枝混杂泥沙,塑胶垃圾,死掉的小鱼小蟹,还有厨余,要在这一团难以形容的混沌中找到细小的鳗苗,实在非常困难。马耀说:“我们都觉得自己在做环保。”
张峻浩说,兰阳溪出海口位于农村和工厂的交界,海废充满沿岸的农业垃圾和家庭垃圾,也有工业废水。他曾在花莲溪出海口看捕鳗,海水就相对干净。
马耀熟练地在网子里挑拣翻动,不时就抓一团树枝甩动到地上,他说:“鳗鱼会装死,你要这样丢,牠就会动。”但丢了好几团都一无所获,他无奈地笑了:“你看,我现在很会掷骰子,十八骰仔(台语:si̍p-pat-tâu-á)!”
第三次起网,才在树叶下发现扭动的细小生物,通体晶莹剔透,就是值钱的玻璃鳗,马耀赶紧小心翼翼捞起来,放进自己的小水桶。“终于开张了,赚到一尾10块,可以买一瓶饮料。”
鳗苗当天的收购价是一尾10元至11元,但在三个月前,一尾可以高达140元,价格波动极大。我们去看了阿英和其他捕鳗人的网,也是大同小异,草盛鳗苗稀。早期捕鳗人一个冬季就能赚到一栋房的时代,似乎已成都市传说。
真正要赚钱要靠船,在外海放下拖网来回逡巡,船员就在船上等待起网。有渔民用简易竹筏船,也有一艘要价五百多万的船只。但旺季时,一晚就可以捞到上万尾鳗苗,赚到一两百万,收获诱人,因而许多渔民会像渔会贷款买船,或与朋友合伙投资。
根据统计,有九成以上的鳗苗都由渔船捕捞。Kalon也说,船越来越多之后,捕鳗人能捞到的就越来越少。
到凌晨我们离开前,马耀上岸数十次,挑挑拣拣,排除那些长得很像但是不值钱的鲈鳗幼苗后,收获了真正值钱的白鳗苗15尾,可以卖到150元。马耀说:“你们要叫小孩好好念书,不要像我们一样来抓鳗苗。”他会一直在海里捕捞到天亮。
漆黑的出海口昏暗无星,上百人在海水里默默走动,只剩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映照河口对岸罗东市区繁华灯火。
隔天,他们会把收获交给当地盘商,盘商再仔细清点数量结帐、排除伤鱼病鱼死鱼后,搜集起来再给中上游的贸易商。接下来这些鳗苗,就在暗夜潮流被带向没有光的地方。

濒危的物种,求生的产业
铃木智彦结束台湾的取材后,飞往下一站:香港。
他告诉端传媒,走私的方式是这样:“鳗苗体积很小,先装在有水的塑胶袋,打入氧气和冰块,再放到手提行李就可以了。从台湾出发,经由厦门转运,再从陆路带去香港。”也有空运路径,要提前打点好X光机的检验人员,各家有各家的门路。
线人开车带他到香港深圳交界,放满铁皮货柜的郊区,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后,他在这里亲眼看到饲育用的巨大水槽,老板是专营活体贸易的商人,但唯一的货物也只有鳗苗。老板告诉铃木,他的客户是日本的养殖场。
这一趟取材,他确实追查到走私的现况。但铃木认为,问题不在捕捞的渔民和中间人,“说到底,台湾人会去抓、会去卖,也是因为日本人要吃。”
“虽然以前有人呼吁过鳗鱼问题,但现在日本已经没人关心这件事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吃鳗鱼。”铃木在视讯中的表情看起来忧心忡忡,“我自己已经是不吃鳗鱼的,当然还是要尊重别人,只是我认为以现在濒危的情况,最好可以有十年的禁渔期,让鳗鱼喘口气。”
他直言:“如果最后鳗鱼灭绝了,一定是日本人的责任,这我非常确定。”
“想像一个没有鳗鱼的世界,会很困难吗?”瑞典记者帕特里克·斯文森(Patrik Svensson)在他的书《Ålevangeliet》(中译:鳗漫回家路)写下这个提问。

人们都会心想“不可能有一天没有鳗鱼吧?”但他梳理了近代科学证据绝望地发现,鳗鱼确实正在经历大灭绝的过程,就像15世纪印度洋群岛上的多多鸟和18世纪白令海上的海牛一样。
世界上共有19种鳗鱼,有的品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超过四千万年,对人类来说无比熟悉又神秘。
“但鳗鱼的神秘却成了牠自己最大的敌人。”帕特里克忧伤地写著,如果人类难以解开鳗鱼的谜团,就难以培育繁殖来抢救这个物种。
直到今日,鳗鱼仍然是科学家无法完全掌握生态的鱼类。
2025年初夏,我们重返兰阳溪口,跟著学者韩玉山去采样鳗苗。“配合潮汐的时间,这次应该是六点半,如果你们想在渔民家吃饭,就提早来。”他嘱咐我们。
宜兰沿海绵延防风林、沙丘、废弃鱼塭和低矮民宅的景观,2018年铃木智彦来台采访时,曾形容为“让人以为身处战前的简陋风景”。
这其实是台湾沿海聚落的典型地貌,终年咸咸的海风吹拂,土壤多属沙质,盛产哈密瓜、花生和马铃薯。壮围本地人是从清朝时移垦至此,除了种田、做工、养鱼,在冬季捕鳗几乎是家家户户的重要副业,很多人同时兼具农民与渔民的身份。

2007年起,韩玉山开始系统性地记录全台湾的鳗鱼资源,他与各地渔民合作搜集样本,宜兰的鳗苗就是委托渔民陈振辉捕捞,两人已经合作18年。每个月韩玉山会亲跑产地取样,再把鱼苗样本载回台大实验室,风雨无阻。
这一天,出海口很冷清。韩玉山站在滩头观测海象,一边交代学生纪录水温、水流。“没有什么学术产值,但这是科学家该做的工作。”他在1999年进到台大攻读博士,一头栽进鳗鱼的研究,至今已26年,仍然深深著迷。
“鳗鱼身上真的太多秘密了。”他投入鳗苗复育,但鳗鱼对环境极为敏感,即使成功孵化,如何模拟洋流、让柳叶鳗进食并长大成玻璃鳗,仍是难题。日本自2002年开始技术培育,台湾则在2024年由韩玉山团队成功养出玻璃鳗,但远追不上物种消逝的速度。
“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台、日、中、韩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开会,讨论该怎么办?”虽然因为政治问题,中国大陆只能派出民间代表与会,但2012年至今,这个非正式的网络一直密切合作著,讨论著鳗鱼的未来。
韩玉山曾统计,在1970年代以前,这四个国家一年可以捕捞超过1000公吨(约50亿尾)的鳗苗 ,近年来,捕捞量已经小于45公吨,是雪崩式的减少。
“听说欧盟今年一定会有动作,可能就是今年会提案了。到时候不只日本,包含台湾的鳗鱼也不能对外贸易,整个产业都会出现很大问题。”

他的担忧恐怕即将成真,根据日本养殖新闻报导,欧盟(EU)正准备在今年11月乌兹别克的IUCN大会上提案:“将包含日本鳗在内的全19种鳗鱼列入《华盛顿公约》附录Ⅱ”,意即科学家观测到这个濒危物种已经是“需要管制交易,以免影响到存活”。
“所以日本人很紧张。”韩玉山指出,黑市交易影响国际观感,日本政府虽知“香港鳗苗”多为洗产地,但难以抵挡产业压力。夏季鳗鱼节对日本意义重大,为赶上节庆养成期,养殖场须在冬天高价抢购台湾“头期苗”,即品质最佳、健康度高的鳗苗。
黑市价格远高于行情四倍。为解困,日本近年积极与台湾协商,欲将贸易透明化,并承诺若能合法进口台湾鳗苗,将禁止自香港进口,但台湾迟未回应。
“最大的阻力,是台湾内部养殖业。每次谈到鳗苗政策,就有立委出来施压。”韩玉山说。
云林口湖养殖业者除了认为“台湾鱼苗该留在台湾”,也有商业考量:若日本能合法取得台湾苗,其养殖场成本就降低,台湾养大的鳗鱼外销日本时,可能失去竞争力。

韩玉山分析,继续维持现况对大家都不好。禁止出口的初衷是保育,却导致市场地下化,各方自顾利益,致使鳗苗濒临,假若最后透过国际贸易全面冻结,产业恐怕也将陪葬。“如果我们管不了自己,当然只能靠别人来管。”
此外,从台湾走私出去的利润惊人,但代价却非常轻微。韩玉山说:“现场抓到人也是直接放走,没收鳗苗和罚钱而已。” 财政部关务署一位不愿具名主管表示,要查一定查得到,活物经过X光机一定会被发现,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说,至少每年都有查缉到走私鳗苗的新闻:“证明我们有在抓。”
根据渔业署提供给端传媒资料,台湾自2007年禁止出口鳗苗以来,18年仅查获11件走私案,处以行政罚锾并没收鱼苗。渔业署副署长陈建佑对端坦言,曾提案将走私比照毒品提高刑度,但未获通过,且许多问题牵涉跨部会,意见难以整合。
捕捞数量也长期是黑数。韩玉山指出,渔船采自主申报,毫无约束力,“每次问渔业署什么时候要管,他们都说明年。”他说:“养殖场和渔民都是朋友,我想要的是平衡。”这个接近百亿的产业,亟需各方共存之道。
2016年起,韩玉山透过“台大渔推会”公开每日收购价与渔获量,打破盘商垄断资讯,引发不少盘商与渔民不满,质疑他“为何要公开行情”。即便如此,他仍坚持透明,如今追踪社群已超过2600人,多为一线渔民。
这晚,陈振辉从海里拉网上岸,捞到的只是一些叶子与小鱼,没有玻璃鳗。直到夜晚九点,我们离开时,他们仍一无所获。

记者与捕鳗人孙女,携手温柔倡议
台湾其实有一份自己评估濒危鱼类的名单:《淡水鱼红皮书》。在2024年的最新版本中,生物学家发现,日本鳗的等级是“国家濒危”(NEN)——这种生物在台湾的栖地严重破碎化、族群量少且下降,并且,在五年内灭绝机率超过20%。
顺带一提,在这份名单里,樱花钩吻鲑的等级仅是“接近威胁”(NNT),灭绝风险比鳗鱼低。我们吃不到樱花钩吻鲑,但走进日式料理店就能吃到鳗鱼,令人感受复杂。
如今,有人试著把这些沉重的议题,用更柔软的方式放进大众视野。
2025年2月,春寒料峭的宜兰海边,壮围沙丘生态园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食鱼教育”,现场学员好奇地围著两只透明塑胶桶,里头沉著数条细如冬粉的灰白色半透明线条。桶子稍微摇晃,牠们就扭动起来,大家一阵惊呼。这是由独立记者陈志东策画、农游超市举办的“兰阳溪口鳗鳗玩”活动,参加者有农友、学生,也有外县市来的游客。
讲师林芷晴拿起麦克风,对小朋友喊话:“有谁可以当小老师?大家猜猜看,哪一只是鲈鳗,哪一只是白鳗?”桶内的冬粉,竟是鳗鱼饭的鳗鱼本人,众人啧啧称奇,有小朋友问:“牠可以摸吗?”她赶紧维持秩序:“小老师,帮我告诉大家,鳗苗非常非常脆弱喔,请勿拍打。”

25岁的林芷晴是韩玉山的学生,也是捕鳗人的孙女,她的阿公(外祖父)陈茂富先生是壮围在地人,捕鳗已超过50年,这天也有来到现场,害羞地躲在后面。
“小时候,我跟阿公阿妈一起住,他们平常务农,秋冬东北季风时就去捕鳗。”林芷晴分享道,“我跟阿妈坐在小乌龟里,等阿公上来,就赶快帮忙找鳗苗,我眼睛利,很快就能发现。但后来发现,鳗鱼似乎越来越少,阿公都抓不太到了。”
为了更理解产业,她考进台大渔科所。她观察到,“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捕捞者或船只都需牌照,为何台湾不用?”她说,这行业长期欠缺制度管理,每年冬天都有捕鳗人溺毙的新闻。林芷晴比较了各国鳗鱼政策,搜集了台湾历年捕捞事故新闻,最后在硕士论文中提出了鳗苗牌照制度的建议方案,供政府参考。
这场活动的策划人陈志东为资深记者,原本就很关心台湾农林渔牧的产业动态,但一直到2021年疫情蔓延后,台湾活鳗无法外销日本,价格崩盘到接近史上最低,他才注意到这个议题。
“很多养殖户赔钱退场,我跑去口湖采访他们,才发现原来台湾留下来的鳗苗是少数,大部分的是被走私去日本。”云林县口湖乡是全台最大的鳗鱼养殖区域,陈志东在当地采访了大大小小养殖户,发现鳗鱼产业非常复杂。
“捕鳗苗本身是一个产业,收购又是另一个产业。鳗苗到了养殖场怎么养?温度、饲料、水质和气候都是技术,甚至有跟光电抢地的问题。鳗鱼养大之后,成鳗要内销还是外销?通路也是一种专业。最后进到餐厅里怎么料理?有蒲烧和白烧,还分关东派和关西派。”

但陈志东也知道,一般人要了解这些没那么容易:“你想亲眼看捕鳗很难,因为是深夜,你也不熟悉位置,所以需要设计和安排。”
他注意到林芷晴和阿公的故事后,非常感动,于是和农游超市精心策画了这场活动,除了邀请林芷晴讲课,请厨师料理友善餐桌鳗鱼饭,还设计了体验环节,由阿公示范,大家也可以穿上青蛙装,轮流下海体验捕鳗。
林芷晴也表示,这活动对她们全家都很重要。“我也想给阿公一个说故事的角色,以前壮围人觉得抓鳗鱼是穷人、没有读书的底层在做的,你才要去跟大海拚搏,赚这种辛苦钱。”
“可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也想让阿公知道,他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遵循的传统的渔法,其实是对环境友善的。”林芷晴眼中闪烁光芒,当她更了解鳗鱼后,反而更珍惜自己的出身。“我们量力而为,这样的工具也抓不了太多,这是我们跟鳗鱼平衡的自然之道。”
兰阳溪口的文化,是不是即将随著鳗苗消逝?至少现在学者、记者、关心鳗鱼的人们,他们的倡议和努力,是想让人能生存,其他物种也有明天。
暗潮汹涌的海水里,鳗鱼可以逃过天敌、穿越垃圾和泥沙,仍能溯游千里。也许对台湾人的启发就是,我们在未知的混沌中也要清晰辨认自己的路径,伏流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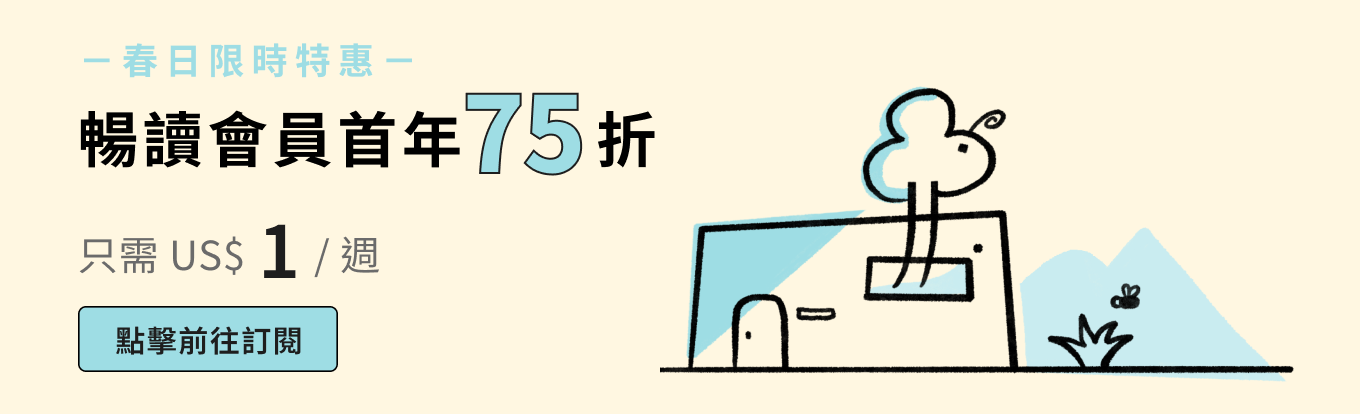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