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5年8月,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成立“民主思路”智库,在政改否决后的对峙氛围中,鼓吹回归温和沟通路线、促使各方重建互信,来推动香港民主发展。然而,在中国强势管治、香港社会撕裂的大环境下,不少人都质疑:“温和政治”在现实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线,是香港当前核心问题。《端传媒》将在本周连续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论,提供各界讨论的参照。前两篇文章,将从理论面上讨论何谓“温和”、何谓“民主”;后三篇将回到现实面,阐述温和派如何看待中港关系,以及中港经济融合的利益与代价。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中长期战略,即使现在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但综合地缘政治、历史、贸易、科技等各方面的观点,欧亚大陆的建设及整合可说是地缘政治的大趋势,甚至是历史的必然──一种新的欧亚大陆主义(New Eurasian Continentalism)正在形成,而一带一路只是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而已。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的出台,令中国有望跻身为掌握“心脏地带”(Heartland)的关键国家,继而主宰欧亚大陆命运。同时,一带一路的实行及成功,将推动传统中华文明转型,为中国文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从中找出新出路。本文旨在探讨目前中国所面对的重大历史机遇,以及此机遇将为国家、为香港带来的种种可能。
首先,我们须了解欧亚大陆对中国的重要性,才可认识到一带一路对中国的重要性。顾名思义,欧亚大陆是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合称,面积5473.8万平方公里,乃地球表面面积最大的洲,蕴含世界上大部分人口、资源与财富──包括世界人口的75%,全球GDP的60%,以及全球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
列强对欧亚大陆的争逐与征服由来已久,以前匈奴人和蒙古人均有此企图,可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力与组织来征服整个欧亚大陆。但时移世易,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发现,现代化及科技进步带来两大发展:大幅的人口增长及横跨大陆的运输系统(如铁路),令有效组织及整合欧亚大陆变得可能。这将大幅强化欧亚大陆上陆上强权的实力,继而影响陆上强权(陆权)与海洋强权(海权)的既有权力平衡,形成重大的改变。
麦金德认为,能最有效运用这发展趋势的,是能够控制“心脏地带”(Heartland)的陆上强权。“心脏地带”指的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央与北方,范围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面积约900万平方英里的广阔区域。一方面,心脏地带资源丰富,海权势力无法介入;另一方面,其大型低地平原很适合具高交通运输能力的陆权势力,从而令心脏地带成为欧亚大陆,以至“世界岛”(欧、亚、非三大陆的统称)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地理特征。
麦金德甚至预言,掌握心脏地带的国家将会不断强盛,逐步扩张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之后就能动员丰富的大陆资源来建造舰队,击败海洋强权,最后成为一个海陆皆强的世界强权。
面对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麦金德就他的“心脏地带论”提出了著名的“麦金德格言”:
谁掌握了东欧,就等于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掌握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
谁掌握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
麦金德在这里强调东欧,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几乎成功征服东欧与心脏地带,但实际上麦金德亦认为不论是俄德联盟,抑或是中日联盟,只要征服俄国领域,控制心脏地带,均有可能成为世界强权。因此,麦金德理论上并不排除中国自身或俄中联盟控制心脏地带的可能性。
英美海洋霸权忌惮欧亚大陆
麦金德的理论让海权势力重新认识到,一个不受海权挑战,并且拥有足够资源的大陆强权,对全球的权力平衡而言是一大危险,甚至足以击败海洋强权。因此,海洋强权非常忌惮一个可有效组织欧亚大陆资源的陆权势力。而历史上的世界战略形势,亦反映出海权与陆权在欧亚大陆上的对抗格局,直接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
故此几乎无可避免地,英美海洋霸权一直要靠干涉、挑拨、占据和分裂的做法,来阻止欧亚大陆整合,以避免被排除在欧亚大陆这世界中心舞台之外,并在与欧亚大陆强权的竞争中输掉。
美国荷兰裔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则指出,历史上多场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这意味着真正欧亚大陆的争逐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而历史也主要是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形成,因此世界政治的关键区域应该是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
斯皮克曼指出,历史上有条件争逐欧亚大陆的都是边缘地带强权,包括法国(拿破仑)、德国(德皇及希特拉(台译希特勒)),以至中国。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尽管麦金德在1919年已将其心脏地带的范围推进至长江流域以南,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则进一步阐明中国完全具备逐鹿欧亚大陆的条件。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及记者Robert Kaplan所言,中国是欧亚大陆中同时拥有热带和温带海岸线的国家之中,最大的大陆国家,占据着全球最有利的位置。
然而亦因为这样,斯皮克曼深信欧亚大陆的争逐,不该是海权力量对心脏地带的围堵,而是须防止任何势力控制边缘地带,这使他对“麦金德格言”加以改造:
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
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该主张令他成为了美国的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教父”。最初该政策是为了遏制及围堵苏联,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目标已转至位处边缘地带有利位置的中国。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殖民主义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传统全球化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撇开西方的侵略不说,其主要结果就是让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贫富差距,这差距到今天亦未得到平衡或扭转。同时间,针对中国历史而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联系:游牧民族西迁、帝国的兴衰、海权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这两条通道息息相关。两条丝绸之路也随着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扩张而逐渐消亡,揭开了西方海洋霸权支配世界500年的序幕。
整合欧亚大陆越趋容易
诚然,麦金德于20世纪初便提出“心脏地带论”,指出控制心脏地带的陆上强权可透过铁路等新技术整合欧亚大陆,最终成为世界强权,实在早了一点。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种由能源性的相互依赖关系,终于在欧亚大陆形成。其背后是由各国的经济增长、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能源互补所带动的,但一开始基本上是海洋性为主。
这种海洋性的相互依赖,建基于50年代起的石油运输,主要是连接中东的石油产出国及东北亚的石油消费国(日本及南韩),并于200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峰。后来随着中国崛起及成为石油进口国,一种陆地性的依存关系亦随之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形成,并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获得发展的动力。个中主要原因,是中国对于严重依赖由美国控制的海路来运输石油感到不安,于是转而从中亚和俄罗斯洽购石油与天然气,同时大举兴建石油与天然气的陆上管道。石油与天然气的管道,再加上铁路与公路网,造就了所谓的“新丝绸之路”。
这种陆地性依存关系的形成,令本来的海洋性依存逐渐转型为海陆混合性的依存,很大程度已超越了麦金德当初的想像,成为新欧亚大陆主义(New Eurasian Continentalism)的重心与基础。而这种海陆混合性的依存关系及新欧亚大陆主义,实质上亦构成了一带一路的雏型。
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以外,今天中国还可以透过上海合作组织,以近似联盟的形式来控制欧亚大陆,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亦令中国可以同时以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双管齐下,增加对欧亚大陆国家的影响力,并辐射到其他大洲。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手段与方式,以至新欧亚大陆主义及一带一路本身,均令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势力毋须再靠战争来征服或侵略欧亚大陆,反而可以藉油气管道、铁路和公路,直接组织及整合欧亚大陆。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等组织,亦令几个强国共同控制欧亚大陆变得可能。
换言之,掌握心脏地带和欧亚大陆已没有像麦金德当初想像般困难,各方面对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势力越加有利,并正逐渐改变陆权和海权的平衡。
同时间,新欧亚大陆主义的形成,意味着欧亚大陆正迈向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由北京到德黑兰之间的每一个国家,现在都比以前更富裕,且不说中国已在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占着中心地位──而最令西方担忧的是,西方事实上缺乏从外部约束欧亚大陆国家的板斧。
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
因应这新情况新环境,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对外合作的总纲领,更充当着区域国家的共同战略,希望一方面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与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一带一路的核心乃一个合作战略,提倡开放、合作与可持续,主动化竞争为合作,并以“互联互通”来作具体展现,最终达到建设及整合“大欧亚”的目的,实现欧亚大陆复兴。
为了针对过往西方殖民及帝国主义完全由海路主导世界政经格局的弊端,令那些原本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地区变得繁荣稳定,中国坚持不走西方列强扩张、冲突、殖民的旧路。习近平甚至主张“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索性让亚欧非搭中国的便车、互利共赢。从这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一个全球管治公共产品(global governance public good),旨在在制度上解决一些超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立新的全球管治制度。
一带一路专门针对位处全球管治真空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它们通常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联通性较差的瓶颈地区,以致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不强,令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非常困难,导致建设滞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缓慢。故此,一带一路须通过基建以至制度对接整合,改变经济要素流向,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农业进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塑造出有利中国长远发展的空间,如此将能更有效运用欧亚大陆的资源与潜力。
我们可预见,在不久将来,一个有效整合的欧亚大陆将会出现。这将重构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版图,有望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形成一个欧亚大陆,并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陆海一体的地缘空间新格局。这格局将扭转海洋霸权独大的局面,终止海洋霸权多个世纪以来干涉、挑拨、占据和分裂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以阻止欧亚大陆整合的做法。整合过程亦将带动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
中国未足应付一带一路文明层面
一带一路充当着全球管治公共产品的角色,当中与沿线各国的合作战略及“互联互通”,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客观而言,以国家改革开放至今所建立的一套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这里称之为中国模式1.0),目前实在不足以应付一带一路中有关全球管治方面的需要。其主要不足在于:
一、不够“软”,难以达到“五通”中“货币通”、“政策通”、“民心通”等属于“软联通”的需要(其余两者为“贸易通”和“道路通”,属“硬联通”);
二、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中国文明仍停留在地域性文明;
四、中国文明仍停留在陆上文明;
五、中国文明仍停留在农耕文明。
只要一天这些不足之处没有得到正视与相应的改变,国家将难以在亚欧非实现“五通”及与世界接轨,令整个一带一路的开展面临障碍。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包含着一个对其成败极具关键性的文明层面,但由于中国文明严重滞后,以致对一带一路和国家统一均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内地不少分析人士对一带一路寄予深切期望,希望能够借此为中国文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并从中找出新出路,例如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桅便明确指出“一带一路肩负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责任”──要做到具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中国必须先改变自身文明。
而一带一路对于推动传统中华文明转型,逐步形成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具以下积极作用:
一、一带一路见证中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商业─资讯文明的转型;
二、一带一路让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
三、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性文明迈向全球性文明 。
中国必须经过这几方面的发展,才有望实现与世界“互联互通”,成就中国梦。
香港已为中国提供答案
事实上,上述几方面基本上无一不与香港一直以来所担当的历史角色息息相关:
一、香港从以前一个小渔港逐步发展成目前的金融中心,正见证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商业─资讯文明的转型,足以为国家提供重要参考;
二、香港的普通法与其他制度是带有海洋性特质的,历年来行之有效,这对国家发展海洋文明,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至关重要;
三、香港更倾向属于全球性文明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担当着重要角色,帮助中国与世界接轨,协助中国突破相对狭隘的“天下” 观念,而迈向比较开放的“世界”意识。
因此,中国无论是要从地域性文明进化至全球性文明,抑或要补完其海洋文明发展,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最直接快捷和有把握的途径,莫过于经由香港吸收及学习,基本上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香港对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及中华文明转型的独特作用,可谓十分广泛。首先,香港的西化角色能够促成中国形成“中西互化,以中为主”的大环境,有条件为国家创造出具开放性和相容性的新文明,继而以此富有活力的文明进出西方,实现“互联互通”。同时,这有助中国文明从地域性文明提升为全球性文明,开创一个新时代。
此外,无论是香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抑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举将香港的资金、技术与人才引进到内地,在制度上学习香港,均显示中国需要借助香港达成它在经贸金融方面的全球合纵连横,而其成败亦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能否利用并吸收香港的制度及金融基础,促成自身的发展与进化,令自己进化成中国模式2.0、3.0。
一直以来,香港的历史角色就是为国家作好准备,踏上与世界接轨之路,这一点到了今天也没有改变。笔者坚信香港在过程中所累积的历史经验与智慧不会白费,也不会徒劳。而未来的中国模式2.0、3.0,亦必将包含香港模式及其宝贵经验。
一带一路打开两岸三地想像
一直以来,大陆强权都受到它们的地理及环境性限制,令它们不期然走上一条与海权势力对抗,但最后被击败并衰落的历史道路。历史上的大陆强权如法国(拿破仑)、德国(德皇及希特拉)及苏联,都逃不过这历史宿命与轮回。
中国虽是一个沿海国家,但却只能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等少数时期进出海洋,其他时期都是以陆权国家自居,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亦同样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及海洋霸权的蹂躏,几乎亡国。即使共产党上台也还没有改变这局面,以致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仍停留在农耕、陆上和地域性文明。
然而如上文所言,“一带一路肩负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责任”,推动传统中华文明转型,这不仅可帮助中国逃过被海洋霸权击败的宿命,亦能够根本地改变中国的一些大陆强权“习性”,为国家、为香港、为欧亚大陆带来新的启示与希望。
历史显示,陆权大国要不是须与财力和海军力量均更为优越的海权大国周旋(如法国),要不是就由于没有海洋阻隔,无可避免与其他国家接壤,以致强敌环伺(如德国),因此陆权大国不得不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这对它们经济、贸易、外交军事及对内政策均构成重大影响,令它们更难逃过被击败的宿命。
陆权大国为追赶海权大国,并应付庞大的国防开支,通常都要采行一种赶超型经济,经济和贸易上则多实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这种零和游戏式的做法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弹,亦难以令周边国家归心。
同样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陆权大国亦大多采用自给自足政策或方针,透过侵略与征服来达到资源和原料等的自给自足,代价非常巨大之余,亦难以持续。如此一来,这些陆权大国亦几乎无可选择地必须成为威权或专制国家,对国内民众施行不同程度的控制,迈向真正的民主自由遥遥无期,为此受到外界诟病。
我们可发现,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国际金融中心是从来不会在陆权大国出现的,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只能在长期受海洋性、商业性及全球性文明影响的地方(如纽约、伦敦、香港)出现。它几乎是海权国家的独有产物,甚至是“法宝”,使海权国家能够取得源源不绝的资金,令海权大国对陆权大国的财力优势更形明显。
我们也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尚未摆脱陆权大国的一贯模式,不过一带一路的确可为中国扭转这些现象和历史宿命带来希望。透过一带一路,首先中国再毋须考虑以侵略或征服来达到资源和原料等的自给自足──一带一路正是这种做法的反题(antithesis),专门针对这做法的流弊,现在中国反过来主动提供全球管治公共产品,并提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
此外,一带一路的出台帮助中国一方面逐渐摆脱重商主义,进一步拥抱自由贸易,这有助改善与各国的商贸关系。同时间一带一路亦促成中国的政策,从只重视地缘政治角度,到现在已发展成一种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兼备的视野及政策──一带一路再加上亚投行、金砖五国等倡议及建设,已让中国进化成一种新型的地缘经济大国,开始具备与美国争雄的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预期,如果中国能够贯彻一带一路的构想,振兴欧亚大陆,促成传统中华文明转型,逐步迈向工业─商业─资讯文明、陆海兼备的文明,以及全球性文明的话,将有望真正打破长久以来大陆性国家的专权问题──这样不就可解决目前香港及台湾人对中国最为不满的地方吗?
而国家形成了一种具开放性和相容性的新文明,亦会为欧亚大陆的整合,带来新的可能:一个由欧亚大陆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联邦或邦联将可能应运而生,令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之余,亦将为中国带来新一次台海统一的机遇──届时台湾除了可选择以一个省份回归中国之外,亦将出现以联邦形式与大陆结合的新可能性,为两岸统一带来新的转机。
至于香港,除了继续担当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外,香港的角色亦将日益吃重,成为比现在更具重要性的世界级“超级联系人”: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洲将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以至政治中心,香港在地理上实际上不仅处于亚洲及世界的中心,在连接中国与西方之余,更同时是两条丝绸之路(“一带”和“一路”)的交汇点,海洋亚洲(Oceanic Asia)与大陆亚洲(Continental Asia)的交熨点,以至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交汇点。
人们应该开始发现,香港的命运早已在不知不觉间与“中国梦”、“亚洲梦”以及“欧亚梦”紧扣在一起──这是香港的机遇, 也是中国、亚洲及欧亚大陆的机遇。
(袁弥昌,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民主思路总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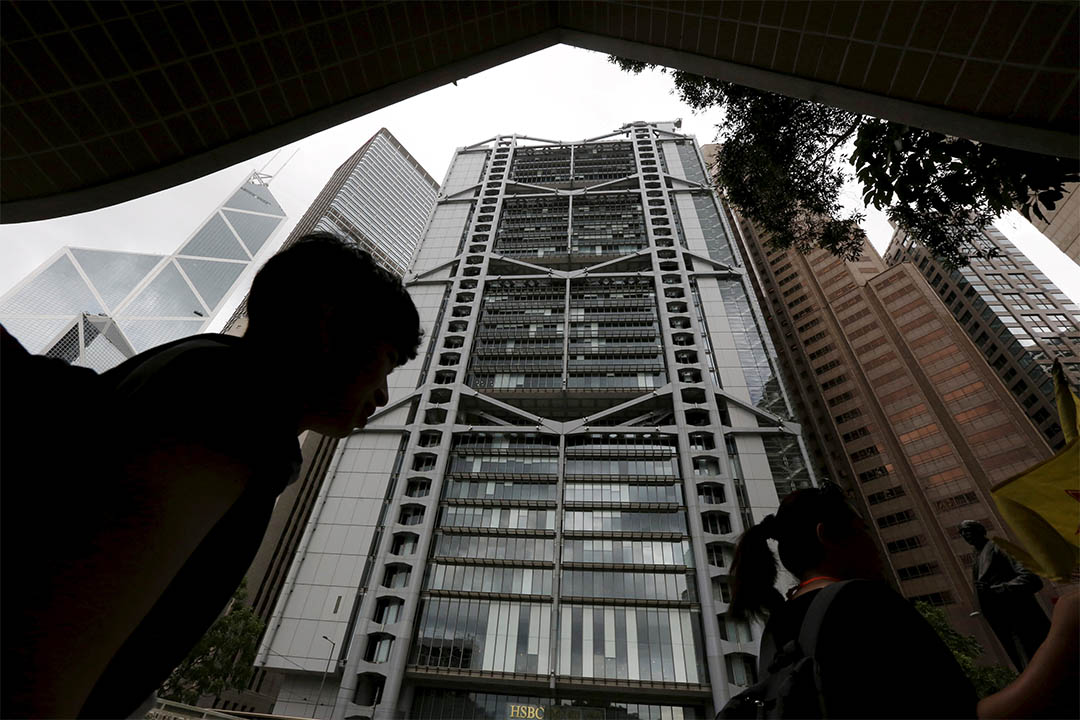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