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以淘寶和京東為代表的電商巨頭崛起,為中國帶來巨大的轉變,不但影響普通人的日常消費,還深遠地重塑中國的政商關係。
2024年11月,美國喬治城大學麥克多諾商學院助理教授、政治學系兼任教授劉立之出版專著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從點擊到繁榮:中國電商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勾勒中國電商奇蹟背後的政治經濟圖景。這本書基於十餘年的研究,既訪談電商從業者、政府官員、電商平台員工,又結合原始問卷、平台內部數據和一個跨越三省的隨機對照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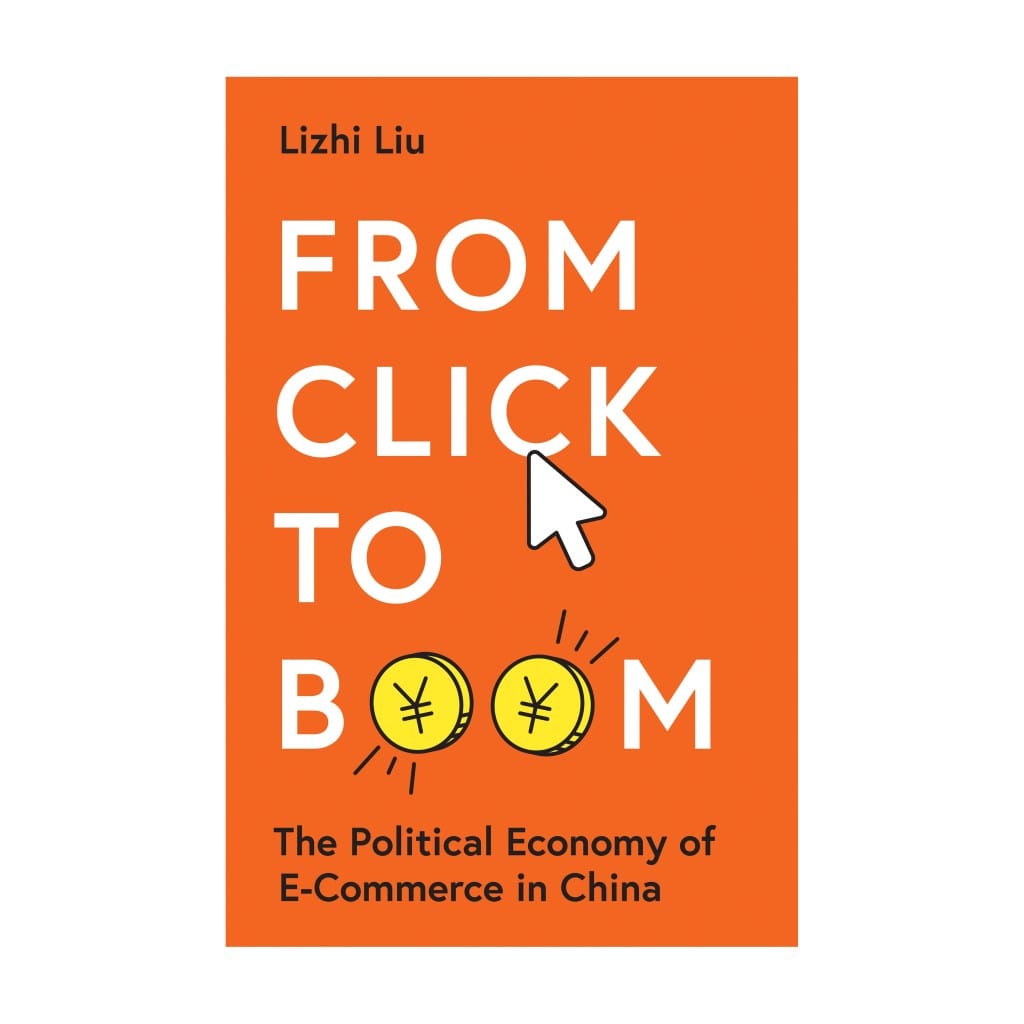
近日,端傳媒專訪劉立之,從電商的視角探討中國政治經濟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在這篇長篇專訪中,我們先深入田野,聆聽電商草根時代的創業小故事和世情之變;繼而回到電商的歷史窗口期,回顧政府和電商巨頭如何「一拍即合」推動電商扶貧,希望將電商下沉到中國廣闊的農村地區。最後,我們探討更宏觀的問題,分析電商巨頭崛起對中國政商關係和社會治理的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