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深圳結束全員核酸檢測名義下的「慢生活」、「軟封城」,重新恢復大規模人口流動的日常生活節奏,不少地鐵站也回歸了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滿負荷運轉場景。而在疫情時代,這種日常「擠爆」也成為了熱圖——解封了,深圳人難道就不怕傳染了嗎?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雖然絕大多數病例都在隔離觀察的密接者中發現,但深圳總體的感染數據並沒有隨着封控而明顯下降,在重點社區、重點人群之外仍有散發病例在社區篩查中檢出。也就是說,全城封控結束,「社會面清零」仍然沒有實現,深圳也暫時不再尋求加碼防疫手段。
對深圳來說,作為一個管理超過2000萬人口、GDP超3.5萬億元的超大城市,更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經濟特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範區——經濟和防疫兩手都要抓——這幾乎是必然選擇。然而在居民區大量外移的深圳,要選擇抓經濟,就必須要允許大規模、大範圍、高頻率的人口流動,這又和疫情控制的要求相悖。而本身就是流動人口聚集區和非正式經濟中心區域的關內城中村又正好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區域,更是雪上加霜,這還沒算上偷渡、走私之類的「灰色經濟」。
這其實也是近年來超大都市建設的必然結果——在「X小時通勤圈」 推動經濟和生活上一體化,在疫情時代各地卻優先選擇封鎖。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動難度,而人口真正流動起來以後,卻因防疫政策寸步難行。
這種困境其實是從疫情一開始就存在的矛盾:流動本身在防疫語境下指向流行病學意義上的風險,恰恰也是經濟發展和生活的必然需求。由於經濟外向性和人口密度高,城市規模越大,疫情爆發風險越大,而溢出到周邊經濟腹地的可能性也越大。隨着經濟壓力逐漸增大、各地疫情防控難度不斷增加,上海、北京、珠三角都出現了跨城、跨省通勤人群因為行程碼問題而進退維谷,甚至被困在路上、橋上過夜的現象。這其實也是近年來超大都市建設的必然結果——在「X小時通勤圈」 推動經濟和生活上一體化,在疫情時代各地卻優先選擇封鎖。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動難度,而人口真正流動起來以後,卻因防疫政策寸步難行。
當然,某種程度上這種矛盾也早於疫情。從「盲流」時代到現在,流動人口從來都是政府治理眼中的高危人群,也一直是難點。在中央已經發出「堅持就是勝利」的指令後,動態清零策略短期內不會改變,流動性控制和不控制的矛盾將會越來越日常化,也意味着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很可能無法「回歸」日常生活。

深圳「軟封城」:必須的流動
在疫情防控下,原本被稱為「生命力」的東西被等價為「高風險」。
深圳由於兼備邊境口岸、超大城市、特區規劃歷史等等特點,在諸多流動性矛盾的案例中尤為突出。
和大多數人想像的不一樣,「來了就是深圳人」的開放性,在早期作為特事特辦的經濟特區,根本不存在。確定寶安縣將會升格成為深圳市並建設經濟特區後,很快就確定了將會建立特區邊境管理線,也就是所謂的「二線關」,而這道國家內的邊境控制也在1984年開始建設。當時,想要來深圳就是一件難事,需要辦邊防證、單位介紹等等,遑論在制度上要跨越戶口遷移的大關才能成為深圳人。因此,深圳的頂層設計從一開始就不歡迎流動性。
特區的邏輯很簡單,要和內地區別,要有政策優惠,因此「二線關」內外就成為兩個世界。
然而特區發展遠超規劃預計,原本1982年規劃中定下2000年人口以八十萬為目標,實際上2000年人口達到了432萬。此時被城區包裹起來的老原住民在原先分配的村落宅基地基礎上,大量興建握手樓(形容樓距過近、不符合規範的樓房),成為了高密度、低價格的城中村,也成為了來深務工者最經濟實惠的落腳地。二線關也代表了很多設法進入特區的人需要付出一定代價,而關內經濟的欣欣向榮產生了難以比擬的吸引力,流動繼而變為一場有利可圖的生意,催生了大量灰色產業。
流動性雖然「不受歡迎」,但它為深圳帶來了旺盛的生命力,同時造成了混亂的風險。巨量的移民提供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需的勞動力,跨境走私也沒少為特區積攢第一桶金,「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就常常靠走私維持貨源供應,深圳更一度成為香港黑白社團產業上岸洗白的天堂。騎着深圳中央兩座山脈的二線關越來越像是障礙,不僅是物理上的障礙造成了交通擁堵,更因為「一市兩制」對人口的限制成為城市發展瓶頸。
而很快深圳也開始有意識地改變狹窄的特區空間形態,將關外也納入到規劃中,並不斷申請擴大特區、逐漸撤除二線關證件限制。隨着地鐵開始通向關外和2010年終於確定要將特區範圍擴大到全市,「來了就是深圳人」才真正能喊出來。而難以管理和價格低廉的關內城中村很快進入「城市更新」項目的拆遷範圍,更加強化了人口外移的形勢。工業區同樣大規模向城市周邊遷移,養育了一批新的城中村,還形成了在惠州、東莞居住,在深圳打工的跨城通勤。此後深圳就奠定了「關外生活、關內上班」的規劃格局,在上下班高峰期,溝通關內外的地鐵流甚至要從地下排到地面,而這之後深圳也順利實現了經濟總量超越香港的巨大飛躍。
然而關內城中村實在難以撼動,原因無他——便宜。即便是寫字樓密集的福田、南山兩區,大量上班族的飲食還是需要靠藏在城中村的外賣來解決,而外賣騎手當然也是城中村住戶。而城中村存在的二房東乃至三房東、短期租住、非正式合同等等現象,讓網格化管理的努力幾乎歸零。另一方面,由於毗鄰香港,不少城中村也形成了繁榮的港貨、娛樂、飲食等業態,極其依賴港人跨境消費。而意識到城中村無法一拆了事的市政府也一度叫停城中村舊改,轉向改善居住條件的「綜合整治」。
如果沒有疫情,這些業已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許會一直延續。儘管深圳已經開始控制人口規模,提高落戶門檻,被叫「人肉乾電池之城」,但是歷史經驗而言,經濟發展的需求總是超出規劃的。
但在疫情防控下,原本被稱為「生命力」的東西被等價為「高風險」。封城對深圳來說很容易實現,叫停城市公共交通運行後,跨區居住的大多數人口就難以上班,如果再加上機動車停運、控制居民區出行,經濟活動就基本歸零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深圳又搞出了把城中村居民連夜拉去學校宿舍的「奇招」:將城中村特殊的空間和社會形態化整為零,放到容易網格化隔離的學校裏去,對流動性釜底抽薪。
然而,本次暴疫的城中村流動性高,恰恰是最不好控制的。城中村不像中國流行的小區有明確出入口,疫情期間都是靠設置水馬等路障限制進出,而租客登記上一直難以規管,往往都是靠大規模核酸篩查的機會再進行符合實際情況的登記。一旦要徹底叫停城中村和外界所有的聯繫,整個城市的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恐怕沒有足夠的人手完成最基本的物流配送和生活服務。而在防疫人員普遍將偷渡視為疫情源頭的背景下,逐戶清查又成為必然要求。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深圳又搞出了把城中村居民連夜拉去學校宿舍的「奇招」:將城中村特殊的空間和社會形態化整為零,放到容易網格化隔離的學校裏去,對流動性釜底抽薪。但是這種手段又很有限,畢竟哪裏找那麼多酒店和宿舍去裝城中村的密集人口?何況很多中底層的經濟需求必須通過流動來解決。深圳不是一個只有騰訊和大疆的城市,還有富士康、還有隆江豬腳飯和水會。深圳去年大專及以上學歷就業人口占比41.27%,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7%,但畢竟還有59%的大多數。
在抗疫背景下,深港邊境活動在國內大政策要求下已經基本停滯,只剩下特批運轉的供港物流和少數的偷渡、走私活動。而這些少之又少但不可或缺的跨境流動還是成為了疫情源頭,兩地車司機雖然有嚴格健康要求,但也已多次在深圳造成輸入關聯病例。深圳是選擇面對外賣騎手夜不能歸等等次生問題,堅挺14天封城陣痛清零,還是在封和不封之間左右橫跳,並不容易選擇。和很多其他城市一樣,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樣折騰能持續多久?
邊境與中心:流動性的急剎車
這些邊境經濟的應有之義,在中國常態防控、動態清零的要求下,已經大部陷於停滯。即便還剩下一些,也面臨物流運輸人員容易成為傳染源的風險。
深圳由於集中了邊境經濟和中心城市的各種特點,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理解中國防疫工作現在在其他城市出現的很多問題。
例如東南亞的疫情不斷從滇緬邊境、滇越邊境滲透進入中國,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將漫長的山區邊境線拉上鐵絲網阻擋偷渡,甚至動員大量機關、事業單位乃至國企人員,組織巡邏隊。在2020年6月,還發生過有人搭船偷渡去緬甸結果翻船的事件。實際上,每年都有大量中國人偷渡到緬甸山區的賭場賭博,甚至是從事電信詐騙。不僅如此,大陸人力成本上漲,製造業開始轉移到東南亞地區,因此不少工廠僱傭了緬甸工人,甚至在緬甸開廠,在疫情封關後也難以開工。在疫情爆發後,大陸也開始清查海外詐騙人員,之後不乏有偷渡到緬甸的中國人主動投案自首以求回國的案例。
飽受長期封鎖之苦的瑞麗,原本就是一個口岸城市,承接了大量類似的邊境經濟活動,很多時候當地邊境本來就沒有那麼多檢查,而日常的經濟往來也往往可以通過小規模的偷渡迴避繁雜的程序成本。減少通行成本對於外向型經濟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要求。
這些邊境經濟的應有之義,在中國常態防控、動態清零的要求下,已經大部陷於停滯。即便還剩下一些,也面臨物流運輸人員容易成為傳染源的風險。例如深圳屢屢發生兩地車司機染疫後傳播到本地社區的情況,最近還爆出有人冒名頂替貨車司機代做核酸。換做往常,貨運司機下車吃個茶餐廳、找個地方按摩,甚至是尋找性服務,也是當地經濟的重要一環。

管理流動性的治理技術成為緊急課題,而對經濟造成的負擔則是不得不承擔的代價。
更加糟糕的是,由於Covid病毒在冷鏈條件下能夠存活較久,來自海外疫情嚴重地區的進口貨物流動也涉及「物傳人」風險,喀什、滿洲里等口岸城市就因此「破防」過,上海、青島、大連、北京等對外貿易發達的城市也傳出過類似的案例。如果連貨物流動都要封閉,幾乎不可能維持經濟正常運轉。
而這種高流動性不僅僅是外循環的特徵,也在「都市圈」建設潮流中變得在內循環裏也越來越顯著。
從2014年開始,中國大舉推進城鎮化,提出「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推動形成中小城市。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又明確提出「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也就是說,各省市要在已有的中心城市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城鎮化,通過重新調整行政區劃,例如在市內撤縣設區、合併鄰近縣區市,形成更大規模的都市圈,增大經濟腹地的輻射範圍。
實踐上有合肥拆分巢湖市、濟南合併萊蕪市、深圳吃進深汕合作區等等案例,同時還有成都代管簡陽市、西安代管西鹹新區的模式。行政級別上的變化,可以擴大相應行政單位的權力,將更大規模的土地、人口納入到規劃範疇內,成為更大規模經濟發展的基礎。但是在具體建設中,僅僅靠區劃吞併遠遠不夠,還需通過大規模基建減少通勤成本,建立「X小時生活圈」以可以實現經濟腹地的直接擴張,將周邊納入中心城市的經濟秩序,這在長三角、珠三角甚至京津冀都有成功經驗。但是,被超大城市吞併的周邊縣市由於沒有了落戶等方面的障礙,其人口更加容易進入中心城市,這不僅在流動人口管理上會極其困難,其中心城市公共資源也很難支撐起短期內新納入管理的超大人口體量,要想真正形成同城化生活,教育、醫療等等建設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跟上。
但是隨着疫情爆發,這些問題也集中凸現出來。最早爆發的武漢市其實也是強省會中心模式的代表,彼時疫情溢出的周邊縣市中,鄂州一直是武漢「吞併」的緋聞對象,同時也是疫情第二嚴重的地區。而深圳在本輪疫情中直接暴露了醫療資源相較其它超大城市過於匱乏的問題,2020年中國每千人口醫療衞生機構床位數6.46張,而深圳2019年的這一數字僅為3.83張,在日增感染病例僅有幾十例的情況下仍然需要徵用宿舍以實現嚴格隔離。更不用說燕郊-北京、崑山-上海、惠州-深圳這樣的跨省跨市通勤模式,一旦中心出現疫情,通勤市民就面臨兩頭不要的「難民」狀態,原本的高鐵上下班、一小時通勤,反而變成了家不能回、班沒法上。
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流動性,在成為「國之大者」而壓倒一切的防疫邏輯中,突然變成了高風險性,管理流動性的治理技術成為緊急課題,而對經濟造成的負擔則是不得不承擔的代價。

你敢動嗎?不敢,不敢
深圳和上海兩大城市的流動性控制措施不完全是防疫模式實驗,而是流動性控制的實驗:例如面臨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時如何控制涉事人群?如何把城中村真正納入網格管理?
奧密克戎(Omicron)強大的傳染性導致動態清零「破防」,中國很多大城市用的抗疫語彙「慢節奏」、「靜止管理」,其實都是在講如何對付流動性。其實早在2020年6月,國家衞健委就發布了《關於做好精準健康管理 推進人員有序流動的通知》,點明防疫需要「有序流動」。
可以說,確保「有序流動」一直被放在政策最核心,所有的健康碼、行程碼一是為了在保證日常流動的基礎上能夠實現流調需要的追蹤,二也是為了能夠以紅黃碼、帶星等方式,對風險更高的流動方向進行限制。這也導致平時流動性越強的地方,越容易恐懼流動。
為了杜絕兩地車司機違規下車,深圳市找來出租車實行車盯車戰術,以保證貨運流程閉環;依賴跨境流動的邊境生產和貿易基本停滯,原本出口國內的香蕉只能爛在緬甸地裏;邊境城市為了避免接觸境外人員,不惜將邊境附近的居民向內搬遷;各地基層防疫人員和普通市民談起城中村的流動人口、流調結果中到處吃飯逛街的人,即便心裏理解其存在的必要性、正當性,仍然會感到厭煩、恐懼。這些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都是過高的代價。
另一方面,中央政策從疫情後就開始越來越明確地遏制城市擴張,發改委曾在2021年提出「慎重撤縣設市」,國務院更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敲打了各大城市擴容的野心,「提升新型城鎮化質量,嚴控撤縣建市設區」,言下之意就是在已有的擴容模式下,城鎮化質量不高。發改委緊接着提出「健全省級統籌、中心城市牽頭、周邊城市協同的都市圈同城化推進機制」、「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嚴控省會城市規模擴張」,將中心城市擴容的重要性下降,而與之配套的是建設副中心城市,分擔單一中心城市的管理壓力。然而像廣州-佛山、深圳-東莞-惠州、武漢-鄂州、成都-德陽等不改變行政區劃,而實踐上逐步同城化的模式,仍然能夠形成可觀的人口流動,對防疫仍然是一種「威脅」。
而在超大城市中,高規格動態清零所需要的人手和開銷,即便對於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公共預算來說,也是難以長期維持的重壓。近一年時間內,因為防疫工作過勞猝死的公務人員恐怕比因為新冠而病故的人數還要多,如果再加上封控無法就醫造成的次生公衞災害、大規模核酸費用對醫保預算的擠壓,其成本難以估量。
因此我們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如果說吉林上千的感染數量已經擊破了公衞承擔的底線,實行封城、封省算是情有可原,而上海、深圳兩個 「經濟引擎」級別超大城市,在奧密克戎衝擊下無法形成有明確源頭和鏈條的流調,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卻採取了最微妙的「精準防控」手段,而其他城市在只有個位數病例且流調能明確顯示輸入鏈條時,卻敢於採取最猛、最徹底的封城。越是大體量、經濟輻射廣,越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封控難度也越大。
這也是習近平反覆強調的城市治理需要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也即通過疫情期間對個人流動更精確的管理,今後可以形成一套後疫情依然通用的管理模式。某種程度上如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評論所言,「擁有開放的紅利,承擔開放的風險,深圳的先行使命從未改變。」深圳和上海兩大城市的流動性控制措施不完全是防疫模式實驗,而是流動性控制的實驗:例如面臨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時如何控制涉事人群?如何把城中村真正納入網格管理?
很多人現在會想像,管住這一波就會逐漸恢復正常的,更糟糕也更可能的是,很多禁令、檢查會和深圳大運會之後的地鐵安檢、疫情期間城中村的路障一樣長期留存下來,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取消。
(戴娜,社會學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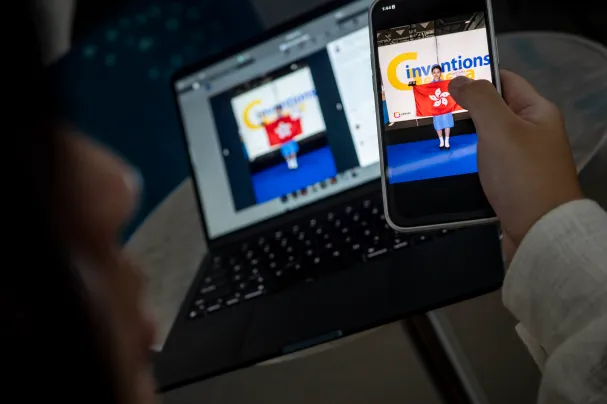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Billyliao 2021年以來 中國只有兩個人死於Covid 但是過程中因公猝死的過去一個月就不止兩個了
"近一年時間內,因為防疫工作過勞猝死的公務人員恐怕比因為新冠而病故的人數還要多"
這個假說有沒有資料來源?
每次看完文章都会再去找找EricChan有没有评论 真的很有见地
提一嘴繁簡互轉換的問題。
端傳媒的文章同時提供繁體字與簡化字版本,導致一些繁簡共用的字在繁體版文章不必要地用了繁體,例如本文繁體版提到西安的「西鹹新區」實質是「西咸新區」。希望你們找到解決方法。
所以呢?有什麼結論嗎?文裡就是東拉西扯陳述了很多事實,然後呢?
其實問題不在於「動態清零」與「開放」而在於怎樣動態清零和開放。你要搞動態清零,那麼最基本的物資要怎樣安排?原有的長期病人,孕婦等有醫療需要的人士怎樣處理?封閉採檢又要怎麼做?疫情過去了兩年,中國各地政府不論地方資源多寡都總會有一些值得詬病的地方。諸如西安死去的孕婦和父親,上海的封禁小區解禁半小時讓居民湧入超市搶購物資。這些是否還有提升的空間?政府是否需要以一個更謙卑的態度去聆聽?更不要說地方政府一面說不要擠佔醫療資源,一面將大量醫院劃歸為新冠治療醫院。在事實上也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匱乏。
「開放」就更加不是所謂什麼都不做了。疫苗效力如何?如何在疫情的不斷變化中調整開放與收緊的步伐?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醫療分級 適當的隔離乃至逆向隔離措施降低死亡率。需要準備多少劑特效藥的處方乃至呼吸機等醫療設備,其實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地方。現在的討論似乎被簡化成了「應否開放」又或者是「是否維持動態清零級別的防疫措施」。
“當時,想要來深圳就是一件難事,需要辦邊防證、單位介紹等等,遑論在制度上要跨越戶口遷移的大關才能成為深圳人。因此,深圳的頂層設計從一開始就不歡迎流動性。”这个结论有点太绝对了吧,二线关确实一直存在,但对于流动产生的影响就是进出要检查证件,更别说关口也有现场办理证件的。现在进出中英街也需要额外办理证件,但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是为了限制流动吧,中英街欢迎的就是大家进来买港货。深圳2000万人口,原住民也就30万,正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开始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深圳,才形成了现在的深圳。
因為封控、封鎖帶來的行政區劃疆界隔離,導致有家不能歸,看得見卻去不了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即便沒有封控,卻有可能因應部分地區出現確診而出現加碼檢查,而原本被設計的便捷通道也一律封鎖。雖然簡單粗暴,卻極為實用。
那些在市與市之間通勤的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為行政部門的藩籬,跨市的協調也顯得不便,很多時候。他們只能選擇被迫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門檻,他們已經選擇在新的地方落腳,卻因為手頭拮据而選擇了跨市通勤,但這兩年來的變化,更突顯了行政界線銜接區域的脆弱
作者提「X小時通勤圈」問題,真係令人心有戚戚。
我從來不相信甚麼「X小時生活圈」,我也懷疑有幾多香港人相信「X小時生活圈」(不論藍黄)。港珠澳大橋、深港高鐵都係用「X小時生活圈」做理由興建,但兩件object現在也成了廢物。價錢高又破壞環境,不提別的,誰會在兩件object在珠海生活,香港工活?相反亦然。
深圳的關外、關內之分,我都係讀了何偉的《甲骨文》才多少知道。深圳係中國城市的先行者,不管在好在壞的方面而言。
流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