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全美幾百個城市的街道再次被遊行的人潮所覆蓋。在年初的佛羅里達州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槍擊悲劇發生後,數名學生倖存者的倡議激發了全國範圍的討論,也成為了新一輪反槍支暴力運動的導火索。自去年華府的女權大遊行起,美國的進步社運走入了一個新階段,運動不再由成熟的社會運動組織所主導,更多的普通公民開始適應以街頭運動為核心的政治表達方式。很多人願意帶着孩子一起遊行,以親友為單位參與遊行變得愈發普遍。
就在同一時間,圍繞校園言論自由的爭議再次被推向高點。1月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Luigi Zingales邀請白人民族主義者班農(Bannon)到學校,參與一場關於全球化和移民的辯論活動,隨即遭到師生的激烈抵制。2月10日,保守派學生組織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廣場上舉行集會,被其他示威者包圍並發生衝突,其間又有五名參與者被捕。3月5日,密歇根州立校園內,反法西斯主義者和遊行的極右分子在Richard Spencer演講前發生激烈衝突。
特朗普(川普)任下,「抵抗」成了日常詞彙,「極化」成了社會共識,進步社運經歷了深刻的洗牌,也被迫面臨新的挑戰。在不同類型的運動中,女權運動和社會主義組織的復甦,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維度。前者對勞工、移民等運動有着明顯的輻射效應,後者則影響着所有進步運動的政治取向。它們的漲落不僅形塑着其他進步運動的規模,也在牽制着新時期右翼運動的策略。
女權運動:「多元交互」的主流化
2017年的婦女遊行,吸引了全美兩百多萬人參與。今年的規模略有下降,但僅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城,參與人數也突破了一百萬。過去一年,也是女權主義議題在媒體上得到大規模報導、在新媒體上迅速傳播的一年。《韋式詞典》的2017關鍵詞給了“Feminism”,《時代週刊》則把Metoo運動的Silence Breakers作為年度人物,連班農都不得不警告大家,女權運動不等於Metoo和反性騷擾,而是一場可能席捲各地的反父權制運動(anti-patriarchy movement)。
特朗普時代女權議題的成功,離不開多元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在進步社運中的實踐。自1989年Kimberle Crenshaw用這個概念來論證邊緣群體受到的種族、性別、階級等多重壓迫之後,社運界便用此指導和解釋實踐。到了2017年,多元交互性幾乎成了運動的標配理念。

馬里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Dana Fisher的團隊,在2017年華府女權遊行現場隨機發放了500份問卷。在一道關於參與動機的多選題下,勾選「女性權利」的人只有52%,其他的參與者給出了各種其他答案,包括環保、政治/選舉、種族、移民、勞工等等。另外,八成以上的參與者都不隸屬於任何正式組織,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這進一步說明了女權議題的巨大群眾動員能力。
某種程度上,美國的婦女遊行已經褪變成和香港維園六四和七一遊行類似的政治場,母題依舊鮮明,但各方勢力有自己的政治算盤,個人的參與動機也極度多元。比如很多左派組織都會利用這一機會吸引人氣。這兩年三八婦女節罷工和今年婦女遊行前夕,曼哈頓的左派組織紛紛在集會現場搭建臨時展台,宣講理念,售賣報紙,不少成員還會混在人潮中和人交流時事,獲取潛在支持者的信息。更極端的例子是,雖然遊行官方持支持墮胎的立場,遊行隊伍也不乏反墮胎的“pro-life”組織的成員,他們希望藉此抗議女權運動受到墮胎議題的綁架。
當然,所謂的多元交互,一直都有被濫用的危險。進步組織們熱衷於標榜自己推崇多元交互的原則,卻常常言行不一。2017年4月科學遊行前夕,多位執委會內部的女性和少數族裔因不滿男性科學家試圖與更激進運動切割的行為,憤而退出組織團隊。今年的婦女遊行前,也有黑人代表表示去年的遊行讓她們心灰意冷,不再想參與白人精英女權主導的遊行。白人精英女權的批評不無道理,Fisher的數據確實也顯示,關注種族平等的絕大部分是黑人,關注移民的絕大部分是西班牙裔。
但不管對現實的運動提出怎樣的批評,女權議題已經成為了各方博弈的基點。特朗普本人所喚起的普遍憤怒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以往運動所留下的歷史資源才是影響目前局面的關鍵。
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儘管未帶來顯著的政局變化,但運動的組織遺產卻頗為豐富:紐約等大城市新成立了不少基於社區的公民組織和藝術家聯盟。第二年,颶風桑迪襲擊紐約和新澤西,這些佔領後成立的合作社和志願者網絡發起了Occupy Sandy的行動,第一次把政治動員的策略運用到災難救援上。正是這些密集的城市居民網絡,為之後的運動打下了動員基礎。
女權議題與其他議題的有效結盟,也得益於之前少數族裔女性在進步社運中的參與。婦女遊行組織團隊的少數族裔代表之一Linda Sarsour,長期參與大紐約地區的各類種族平等、公立學校運動,在多個組織任職。作為巴勒斯坦移民的後代,她也一直都在與穆斯林的污名化做鬥爭。另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的多位發起者是女性和酷兒,其中Alicia Garza不僅長期組織族裔平等運動,更是出色的勞工運動家。她參與的「全國家政工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NDWA) 成立於2007年,專門致力於家政工的權利保障。最近,NDWA還積極動員成員參與 Metoo 運動,將底層勞工視角帶入常被精英話語綁架的女權運動。

社會主義運動:流行語彙還是時代思潮?
相比女權的遍地開花,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年輕人中的傳播,顯現出更多內在矛盾之處。
在組織層面,2017年確實是社會主義理念井噴的一年。這裏以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DSA)為例。DSA創立於1982年,是之前一些社會主義和新左派遺老的策略性同盟,早期成員也就幾千人,在第一代新左派去世後甚至發生了青黃不接的危機。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後,DSA的正式成員暴增了24000多名,目前的成員數目穩定在三萬名,其中大部分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在兩年前是無法想像的。人員的暴增並不是只有DSA才經歷。一些更激進的託派組織在2016年末的例會經常場場爆滿。
隨着DSA成員基礎的擴大,他們與主流民主黨之間的距離也進一步拉大了。1980年代DSA創立伊始,由於地位邊緣,曾經是以民主黨朋友的身份介入政治。創始人Michael Harrington從來沒想過要在民主黨框架以外從事政治活動。可是到了90年代,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人的努力下,DSA開始和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漸行漸遠。當時,DSA給克林頓(柯林頓)政府的評分已經是C級。到了2000年後,有DSA的成員開始公開支持綠黨,和民主黨決裂。
最近一兩年,很多年輕成員出於對民主黨選戰表現的極度失望而加入了DSA。他們對左翼思潮的好感源於對精英政治的憤怒,因此當然不可能指望他們短期內走和民主黨合作的道路。現在,DSA內部對民主黨的激進批評越發頻繁,完全否認民主黨貢獻的成員已經是大多數。
與其他激進左翼組織相比,DSA在選舉政治上傾注了較大的精力,成果也頗豐。目前,有15名DSA支持的候選人在地方選舉中勝出,最大的勝利是Lee J. Carter當選了弗吉尼亞州的參議員。目前,不少年輕成員也在緊鑼密鼓籌劃着參與接下來的地區選舉。在芝加哥等少數族裔聚居,左翼歷史濃厚的城市,DSA成員已經可以不以民主黨的名義參與競選。
但是,我們絕不能高估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社會的接受程度。美國媒體經常每隔一段時間就報導說,千禧年一代大都反對資本主義、支持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但事實上,大部分報導都是嚴重標題黨,他們引用的調查中的相關題目不僅極為抽象,這些調查也沒有一個說過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年輕人中的主流。
比如,蓋洛普2016年的數據顯示,對「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有好感的美國人比例(35%)自2010年以來就沒變過,甚至還有所下降。哈佛大學的研究則顯示,18到29歲的年輕人中,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是16%。相比之下,自稱是資本主義者的有19%,愛國主義者佔了32%,女權主義者則是27%。考慮到這是道多選題,還不能排除有人把所有選項都勾了一遍。
另外,社會主義組織成員的規模,放在歷史語境和現實比較重,根本就不算什麼驚人的成就。60年代新左派的弄潮兒「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DS),在成立十年內就吸引了十萬會員,是現在DSA規模的三倍有餘。橫向比較,左派組織的人員規模也無法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匹敵。比如正在被廣泛抵制的美國步槍協會擁有五百多萬付費會員,群眾基礎相當於一百多個DSA。

最後,組織成員的增長,並不一定說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流行。這批新加入社會主義組織的學生成員,和已有的左派成員往往出生於不同的家庭背景。我觀察過一些組織,發現老成員往往出生於新左派家庭,父母直接捲入民權運動和新社會運動,是典型的學運二代。相比之下,現在新加入左翼組織的學生往往出生於典型的民主黨中產家庭,加入左翼組織更多是出於對以往所接受教育的反叛,而不是出於對左翼理念本身的理解。大部分成員並不清楚美國其實有豐富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鬥爭歷史更是一無所知。因此,這些成員往往對線下活動,比如支援罷工、派發傳單、參與遊行熱情頗高,而對組織內部的理論培訓、讀書會等等活動不怎麼感興趣。
如果我們回顧四十年前民權運動中左翼組織「黑豹黨」的故事,可以看到和如今類似的發展軌跡。雖然黑豹黨最後的解體源於創始團隊的醜聞和內訌,但普通成員後期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從奧克蘭一路擴張到全國的過程中,只注重線下運動的組織,而忽略了內部成員的教育。
隨着民主黨元氣的恢復,這股左翼旋風是否還會持續?很多年輕人還都是大三大四的學生,等他們畢業後遷居到別的城市,是否還能保持如今的參與熱情?這都是目前享受着成員紅利的社會主義運動需要考慮的問題。
社會運動的創造性複製
對於美國的進步社運來說,不論是能夠兼容各方的女權主義,還是更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不論是校園內部的自由派社團,還是校園外的反法西斯力量,他們的各種行動都既未有超越國界的視角,也缺乏本土歷史的縱深感。太多的矛頭都指向右翼和特朗普本身,而不是造成這一局面的社會結構。比照之下,反而是美國極右組織常常與歐洲的盟友們同進退,也正是極右翼們在反覆將全球化、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辯論帶入社會運動的場域。
好在美國運動家的視野局限,並不會妨礙社運本身走向國際。Metoo 運動在全球的擴散,證明了運動跨國學習的無限可能性。運動的學習可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對口號的仿製,對精神的借用,甚至只是建立在誤讀基礎上的策略選擇。另一個國家的女權行動者並不需要了解 Metoo 在美國的來龍去脈,就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在這個一切事件和景觀都被媒體所過濾的年代,每一場運動都必然有它的國際取向,每一個運動發起者都無法預測運動的最終走向。對運動的學理分析,在真實的抗爭面前,也往往被打回乾枯的原型。
越是在這樣混沌的時刻,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國家下的進步社運,就越需要一種衝破既有思維定式的勇氣。人們一直以來想爭取的究竟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還是一種多元的修辭?抵抗是一種政治立場,還是文化衫上的一行點綴?究竟是要推動世界範圍內的改變,還是僅僅和敵人一樣,懷念着過去大家相安無事的小日子?那些右翼分子心目中種族隔離、階級分化、男權主導的理想世界,是否本來就是這個時代的樣貌?美國的運動家們已經開始去理解這些問題,但還遠未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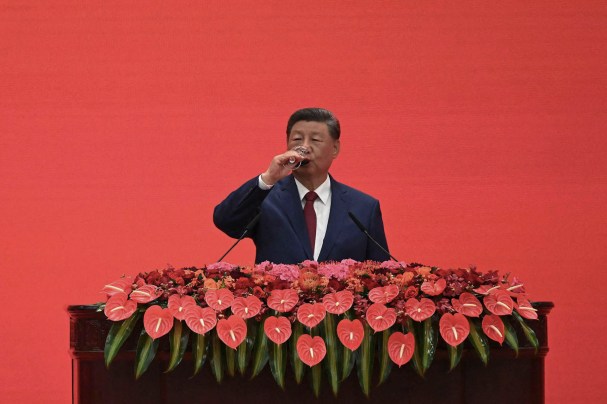


左翼的问题在于议题太多,很多时候不能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川普是让左翼暂时放下成见形成合力的重要因素。作为温和中间偏左派,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川普式的中左翼人物当权。
首先,“白左”一词本身就是内地有些人对自由派白人带走蔑视的称呼。而阅读完全文,也只有DSA相关的一段在讨论美国左翼是否在变红。并且文中的讨论是否变红的左翼也没有限定白黑还是棕。我对这篇文章非常失望,完全是标题党?
【密歇根州立校園內】這分句,是不是改成【密歇根州立大學校園內】會更清楚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