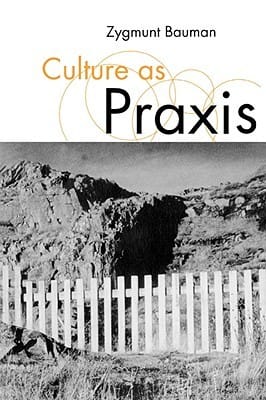
鮑曼先是短暫流亡以色列,之後移居英國,在利茲(Leeds)住下。他筆耕不綴,直到去世。儘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離鄉,鮑曼仍然更關注社會主義與解放之類的宏大論題。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為實踐的文化》,點出知識分子在當代的責任。60年代末的社會學界仍然盛行「解釋事實」,而鮑曼卻說,不能將社會文化當成靜態的、可以觀察的東西,不論是作為概念或是結構,都沒有辦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轉而強調要從實踐(praxis)來理解文化:文化對我們是矛盾且愛恨交織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縛,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類行動的潛力。鮑曼一生常年保持高產的研究、寫作與公共發聲,正是這一判斷之下的親力而為。
反思大屠殺
儘管出生在猶太家庭,但直到1980年代,鮑曼才開始認真介入思考半個世紀之前的大屠殺。1989年,他出版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其著重點是:現代社會如何讓大屠殺成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