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資本市場上中國企業接連發生意外:從馬雲抨擊中國金融系統的管制引來監管部門嚴查螞蟻金服導致其上市被叫停,到滴滴無視中國網絡安全監督部門對其推遲上市的希望、強行赴美上市從而遭到網信辦責令禁止新用戶註冊、最終懲罰升級至全線程序下架,再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對校外培訓行業造成毀滅性打擊。這些事件,在國際資本市場法律語言里,都被歸於所謂的「監管風險」(regulatory risk),一般指由於法律法規和執法環境對企業的經營造成的不確定性因素。資本市場對螞蟻和滴滴事件的描述也確實都將其定性為「監管」「法規」造成的問題,不同的只是前者是來自於「金融監管」,後者則是「國家網絡安全監管」。
但如果說對滴滴的調查和懲罰尚且有表面上的法律依據的話,那麼對於教育培訓的禁令,甚至沒有通過太多法律的包裝,直接通過文件的形式下達、由各地教委等主管機關制定細則。即便如此,新東方的新聞稿仍舊將其稱為「法規」(Regulations)的變化,表示「公司將在提供教育服務時遵循《意見》的精神、遵守相關規則和法規」「公司正在考慮合規舉措」「將主動向政府當局尋求指導、提供合作,以遵守《意見》即相關規則和法規」,完全符合國際通行的法律語言對監管風險的描述。
這些問題不僅是法學和法理學的學術探討,而且涉及到怎樣理解和回應當下日益強大的中國敘事及中共政權對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爭奪。
然而,無論怎樣用國際通行的法律語言包裝,比起法律意義上的監管,這些事件背後的政治因素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雖然對螞蟻的監管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而言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從發生在馬雲砲轟監管當局之後上市前臨門一腳的時間點、並結合事後各方對決策背景的分析看,顯然帶有敲打馬雲和阿里系資本的意味。而即便滴滴在數據處理上的安全問題屬實,如果不是涉及政治敏感的國安領域並且發生在沒有和政府達成一致就搶跑上市的背景下,也無法想象會遭到停止註冊、全線下架的重拳處罰。至於教培(教育中的補教、補習、培優等)行業,則更是處在當下中國政治議程的風口浪尖上——少子化、階級固化、「內卷」嚴重都是會危及中共政權穩定的趨勢,必須嚴加遏止。
但在更深的層面,螞蟻和滴滴的上市風波和教培禁令所折射出的問題是,中國的「法律」與「法治」到底是怎樣一種存在?國際通行的法律概念與對「法治」的理解,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夠應用於中國?這些問題不僅是法學和法理學的學術探討,而且涉及到怎樣理解和回應當下日益強大的中國敘事及中共政權對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爭奪。簡單將中共的「法治」話語斥之為「獨裁」「反民主」,並不是一種有效的回應,也掩蓋了公共生活和法律專業領域中的缺乏反思。

新時代的「法治」建設策略
目前看來,中共這種高調推進「法治」建設的策略不可謂不成功。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積極推進「法治」建設,而其動機並不能一概而論。首先,全國人大加快了立法的進度,不但快速完成了從李鵬時代就一直在討論但未能制定的《民法典》,在部門立法上也動作頻頻。《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立法的主要目的明顯仍然是加強國家權力、加強對公民的監控,但確實也有試圖平息公眾對網絡安全的擔憂及對大型互聯網企業拿著用戶數據為所欲為的不滿的目的——比如《個人信息保護法》就專門針對「大數據殺熟」等性質惡劣的商業手段進行了限制。
第二,與胡錦濤時代法院地位低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習近平時代中國進行了一系列法院組織建設、賦予法院更大的財務和人事權、實行「員額制」等制度以提高法官專業性和地位、通過「立案登記制」防止法院拒收案件、鼓勵法院「當判則判」而不是一味調解「和稀泥」,同時增強了法院執行判決的能力,還創設了巡迴法院作為最高法院的派出機構,設立了一系列專業法院如京滬穗三地的知識產權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等。當然,中共同時反覆強調了法院需要接受黨的領導,所以這些措施目的並非真正的司法獨立,但依然大大提高了法院在官僚系統中的地位。
耶魯大學張泰蘇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金斯堡(T. Ginsburg)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確實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集權,但它以高度法律化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賦予法院對抗其他國家機關和黨組織的權力、堅持法律專業精神」。2018年中國《憲法》修正案去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引起巨大爭議,但張泰蘇和金斯堡指出,由於中國憲法下的國家主席一職實權有限,如果只是想要繼續掌權,習近平完全可以只留任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務,但他願意消耗巨大的政治資本進行正式的修憲,恰恰體現出中國《憲法》不再是一紙空文。所以,張泰蘇和金斯堡認為,「即使中國確實在深化其獨裁統治,它仍然是通過利用法律的組織能力和賦予合法性的能力來這樣做的, 而不是規避法律」。
甚至遭到西方國家和香港民主派人士一致批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其實也正說明中共對法律工具的濃厚興趣。比起直接派駐港部隊鎮壓反抗運動或是針對在港人士跨境執法,香港國安法顯然提供了更加名正言順的治理和干預工具。香港國安法第一案「唐英傑案」的判詞對於法律條文的分析亦顯示立法本身極度寬泛,法官若是忠實執行其文字,就會起到中共所想要的壓制反對行動、限制反對言論的效果。至於因此產生的使人敢怒不敢言的「寒蟬效應」、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本身就不在中共的顧慮範圍內——毋寧說,產生這種效果乾脆就是國安法的意圖所在。
在明確拒絕了自由主義政治、拒絕繼續給予西方「中國可能有一天走向民主自由」的虛假希望以換取國際空間的前提下,中共全面擁抱「法治」敘事,是一個從其自身存續和發展的視角來看不失正確的舉措。
目前看來,中共這種高調推進「法治」建設的策略不可謂不成功。國際上,西方國家雖然已經不再對中國民主化抱有幻想,但仍然期望至少中國的司法改革特別是對政府和司法機關法律素養的提高能帶來的營商環境的改善——比如中國知識產權法的進步特別是京滬穗三地知識產權法院的運作,就得到了國際法律服務界的讚許。而從統治的角度而言,在大陸地區推行的種種強化司法機關權威和執行能力、使用法律工具反腐並且讓下級政府的為所欲為有所收斂的舉措,也獲得了民眾的認可。
在香港問題上,強力推行的香港國安法,從北京的視角來看無疑是成功的:香港國安法生效導致壓力團體紛紛遇挫、抗爭活動也基本平息。而「唐英傑案」更是產出了一個符合國安法立法意圖、同時又在普通法法律技術上正確的判例,意味著香港的專業司法體系也接受了國安法的邏輯。國安法被「順利」植入香港普通法體系,從此無可爭議地成為香港法治的一部分。
中共的「法治」策略無論是在內還是在外、對內還是對外,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明確拒絕了自由主義政治、拒絕繼續給予西方「中國可能有一天走向民主自由」的虛假希望以換取國際空間的前提下,中共全面擁抱「法治」敘事,是一個從其自身存續和發展的視角來看相當正確的舉措。

中共「法治」觀的變遷
這種態度與中共十年前對法治的態度可謂截然相反。
這種態度與中共十年前對法治的態度可謂截然相反。2011年中國「茉莉花運動」期間,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外國記者要求提供禁止採訪中國茉莉花運動的法律根據,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回答:「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對於抱有這種動機的人,我想什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在那之後的數年間,「法律不是擋箭牌」成為網絡上嘲笑當局無法無天的標誌性語句。
姜瑜的回答代表著中共傳統上對法治的態度。首先,中共傳統上的法治觀本來就是一種自認為更加強調樸素的「實質正義」觀念的進路。2014年《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就提到,「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質主義思維根深蒂固。正如孫笑俠教授所指出的,法官在司法實踐中注重法律的內容、目的和結果,而輕視法律的形式、手段和過程,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上堅持實質正義優先,具有平民意識,善於運用『情理』。」在這種法治觀下,「壞人逃脫制裁」是比「嫌疑犯正當權利受到侵犯」更加應當避免的後果。直到2010年前後,中國都一度缺乏西方法律制度下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中國傳統的法治敘事中,律師通過法律技術排除證據(如刑訊逼供或者非法搜查取得的證據)讓有罪的人脫罪,導致「惡人沒有惡報」,是天大的不公。對於一般刑事犯罪尚且是這種思路,,在針對國家的犯罪裡面使用法律技術的「奇技淫巧」來脫罪(「把法律當作擋箭牌」)就更加不可容忍。
第二,「法治」原本是西方社會的舶來品,以司法獨立為基礎、節制政治權力、保護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其本質是自由主義的,所以中共在加以採用時,自然需要嚴加提防。所以說,姜瑜的發言體現了當時中共對待「法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為了政權合法性和經濟利益,中共不得不在治理中採用「法治」的話語,其後果是外界有機會質問其限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法律依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強烈警惕用法律來保護個人權利的努力,而這種警惕感恰恰是默認了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法治」觀的正統地位,所以必須在一切可能威脅政權的場合對這種法治觀加以敲打。
理解了這兩點,作為對「茉莉花運動」的相關人士的警告,「對於抱有(鬧事)動機的人,什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就並不是什麼石破天驚之語了。
無論是大陸的司法改革還是香港國安法的制定,都代表了一種新時代的、看似更為自信的中共的法治觀。這種法治觀認為,「法治」不必然是關於個人權利與自由,自由主義的法治觀也並非正統,所以中國不但不需要參照西方國家現有的對於法治的理解,更應該努力與西方國家爭奪對於「什麼是『法治』」的解釋權。
而近年來,無論是大陸的司法改革還是香港國安法的制定,都代表了一種新時代的、看似更為自信的中共的法治觀。這種法治觀認為,「法治」不必然是關於個人權利與自由,自由主義的法治觀也並非正統,所以中國不但不需要參照西方國家現有的對於法治的理解,更應該努力與西方國家爭奪對於「什麼是『法治』」的解釋權。此外,既然認定自由主義對「法治」的闡釋並非正統,那麼中共自然也無須畏懼「法治」話語,只要牢牢抓住黨對法律的控制權,就可以大膽徵用西方的「法治」要素(如一定程度的程序正義和司法獨立)和話語,理直氣壯地以「法治」的名義推行國安法等高壓舉措,同時不用擔心被「法治」話語反噬而危及政權的穩定。
這種轉變的背後,是中共的中國特色「法治」理論基礎的形成和完善。創建中國特色「法治」話語的終極難題,在於如何處理「黨的領導」與「法治」之間的關係。在改革開放、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過程中,無論是中國官方的翻譯還是民間的理解都逐漸形成共識:中文的「法治」一詞,對應的是英文的「rule of law」。2014年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英文版第一卷在談及「法治」時,也多採用「rule of law」的翻譯。
這不僅僅是一個翻譯的細節問題——如後文所述,中共推進「法治」並且堅持採用「法治」話語的一大目的,便是參與國際政治經濟事務、贏得內外合法性的考慮,因此如何將自身話語與國際通行的表達對應,是一個重大的根本性問題。譬如,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國」曾經一度被人權人士翻譯為英文中帶有負面意義的「rule by law」(使用法律來統治),暗含「披著法律外衣的(專制)統治」的意味,所以中共在將「依法治國」翻譯成英文時,特意生造了「law-based governance」(基於法律的治理)這個表達。而「法治」繼續翻譯成「rule of law」,顯然也並非沒有經過考慮。
現代「rule of law」最基本的含義,公認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法學家戴雪(A.V. Dicey)在《英憲精義》當中作為對英國憲法體制的總結最初加以闡述,包含三大原則:第一,對任何人進行的懲罰都必須基於通常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並經常設法院所審判;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人能高於法律;第三,基於普通法判例保護個人權利。值得注意的是,戴雪的第一條原則是形式法治的最基本要件,幾乎任何具有現代國家機器的國家都可以表面上做到,第三條又僅局限於英國(美國憲法保護人民權利的基礎是成文的憲法修正案,判例也需要有憲法文本的基礎),因此,第二條「法律至上」的原則,在後世的發展中往往成為討論「法治」時的焦點。
當然,「法律至上」並不狹隘地意指法院在所有場合下都是最終裁決者。在實踐層面上,立法機關和選民都有渠道可以推翻法院的某些判決(如議會修改法律否定司法機關的解讀、美國憲法第五章下各州通過發起修憲會議修改憲法等)、歷史上也偶然發生緊急情況下司法機關被無視的情形(如內戰期間林肯總統無視最高法院判決、暫停人身保護令),但這些都不能說是制度上給予任何具體的人或者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地位。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法治的「核心價值」和「形式要件」的區別。法治的實踐當然需要體現在一系列形式要件當中。除了戴雪提出的法治原則之外,後世的富勒(L.L. Fuller)所提出的「法律的內在道德」(inner morality of law)也常常被引用為評價法治的標準(富勒提出,法律必須是可以一般性應用的,必須明文公開、不溯及既往、清晰明確、內在一致、現實可操作、相對穩定,且官方行動須能與法律保持一致)。
最終能否達到法治的標準,仍是在於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法治之下,「無人能高於法律」。中文的「法治」對應的是英文的「rule of law」、有向通行的法治觀念靠攏的意味,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共也確實曾經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通行的法治觀。
但無論是哪種版本的法治標準,都包含若干不涉及具體社會型態或是政法關係、只涉及法律本身的形式要件。而即便是非法治國家的法律,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滿足法治的形式要件。如戴雪的第一條原則「對任何人進行的懲罰都必須基於通常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並經常設法院所審判」,在絕大多數現代國家顯然是基本得到滿足的。同樣,即便是二十年前,中國的法律體系下大多數的法律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富勒所言的具有一般性、明文公開、不溯及既往、清晰明確等要件。
所以,雖然說滿足這些形式要件對於法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但最終能否達到法治的標準,仍是在於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法治之下,「無人能高於法律」,即法律是最高的統治者、沒有人(於是也就沒有任何組織)能夠高於法律,政治權力的行使需要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受到法律的制約。
此外,不僅中文的「法治」對應的是英文的「rule of law」、有向通行的法治觀念靠攏的意味,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共也確實曾經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通行的法治觀。1982年中共十二大時在黨章的序言部分寫入,「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明確了黨在憲法和法律之下,而非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

「黨大還是法大」的難題
然而,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法治思想雖然沒有明面上否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文字本身,但其實側重點已經有了重大轉移。
然而,時過境遷,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法治思想雖然沒有明面上否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文字本身(一如中共仍舊承認「鄧小平理論」的領導地位),但其實側重點已經有了重大轉移。早年提倡「司法獨立」、進而主張「憲政」的人,其隱藏的最終目標是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即中共眼中的「和平演變」,中共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所以早在習近平主政之前,中共就反覆強調過反對司法獨立的西方法治思想。2009年3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吳邦國發表了堅決抵制「三權分立」的談話,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也表明,「在中國,人民法院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人大監督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絕不能簡單套用、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能搞三權分立式的司法獨立。」
而習近平主政後,對政權安全更加高度的重視,也同樣體現在法治思想領域裡。在這方面最突出的證據是習近平親自作出的一系列集中論述。對於「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近平在講話中多次針鋒相對地提到,「『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而中共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總結起來就是,黨(作為一個整體)和法治是統一的,因此不存在黨作為一個整體違憲或是違法的問題:「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願的統一體現,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
對於「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中共官方是這樣解釋的:「我們說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是把黨作為一個執政整體而言的,是指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而言的,具體到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幹部,就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就不能以黨自居,就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
對於「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近平在講話中多次針鋒相對地提到,「『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
這一論述,實質上是將黨章中「『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的主語變成了「黨員」和具體的各級黨組織。由於代表黨整體的是中共中央,憲法、法律和各種行政規章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決策的結果,「憲法和法律」是中共中央的意志體現,所以在實踐中,「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文字無法對黨中央形成制約、其約束的是下級黨員和黨組織。因此,通過將「黨」的整體(具體實踐中為黨中央)與「憲法和法律」等同起來、將違憲違法的行為主體從「黨」變成了「黨員」,中共的法治理論徹底排除了「黨」違憲違法的可能性的同時,使得「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承諾變得沒那麼空洞。這樣至少在非法學專業人群的理解裡,「黨大還是法大」「黨領導下的法治還是不是法治」的問題得到了表面上的消解。
只是,如果說當初「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原文還帶有那麼一點「黨也要遵守其立下的法律」的社會契約的意味,那麼當今這種「黨與法律是一體的」、「黨員在法律之下」的二分法,則完全放棄了這種社會契約精神。若是深入探究其法學內涵,這個答案更是無法令人滿意的。無論是說黨與法治是「一體」的、還是説黨「領導」法治,其內核依然是在講「黨就是法律」、是在論證黨(實質上是中共中央)對於憲法和法律有絕對的支配地位。結果就是,高層政治決斷仍然不受任何外部約束——包括來自憲法和法律的約束。所以,這種法治理論終究無法回答,「黨的領導」如何與法治精神兼容——法治所要求的「沒有人在法律之上」,自然也意味著無論是作為一個整體還是包括中央領導集體在內的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與法律之上、必須受到憲法和法律在形式上和實質上的約束。
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在憲法正文第一條第二款中明確寫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與上文「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和下文「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條文一起明文規定了黨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但這仍然無法消解「黨的領導」如何與法治精神兼容這個難題。
毋寧說,這反倒給黨眼中的「不懷好意之徒」創造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既然憲法和法律是黨的意志的體現、憲法也明確規定了黨的領導,那麼自由派所提倡的司法獨立、公開的違憲審查制度等制度,就並不可能在法理上威脅黨的領導,反而是在維護黨的意志的內部邏輯、維護黨的領導。如果一個法律或者政府的某個做法違反了憲法,而憲法是黨的意志更為根本的體現,那麼違憲審查恰恰是維護了憲法這一更為根本的黨的意志的表述,黨應該支持才對。顯然,自由派這種「承認黨的抽象領導地位,但在日常政治中要求『法大於黨』」的觀點,與中共的法治論述是無法兼容的,因為中共所強調的是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在更深入的理論層面上繼續懸而未決。

「法律多元主義」的難題與「主權代表常在」的悖論
為了進一步消解這個問題、論證黨的領導和法治並無衝突,熟悉西方法學理論的中國國家主義法學家群體,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可謂「煞費苦心」。
為了進一步消解這個問題、論證黨的領導和法治並無衝突,熟悉西方法學理論的中國國家主義法學家群體,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可謂「煞費苦心」。北大法學院強世功教授引用西方的法律多元主義理論,認為中國的法治模式「既不是議會主導的『立法法治國』,也不是法院主導的『司法法治國』,更不是政府主導的『行政法治國』,而應當看作是執政黨主導的『政黨法治國』」。
強世功著重批判了「『國家法中心主義』的法治觀」——這種法治觀認為國家正式立法才是法律、法治必須基於正式法定程序通過的法律法規。值得一提的是,這正是戴雪法治三原則中最基本的第一條,也是本來最無爭議的一條。強世功則認為,國家法中心主義的法治觀無法解釋中共法治體系下黨和國家「政策」的法律效力,儘管「實踐早已證明,無論是黨的政策,還是國家政策,都是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規範政治和社會生活,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規範性力量,甚至是憲法修改和國家立法活動的規範性依據。」
因此,根據強氏的法律多元主義理論,黨的綱領、文件、政策,同樣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強世功聲稱,「正是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中國法治建設中實現了一次歷史性飛躍,⋯⋯標誌著中國法治走向了一條涵蓋黨規黨法、國家法律和法規以及社會性規範和道德習慣法在內的多元一體的法治模式。」
強氏的論述雖然表面上能夠解釋諸如「為什麼國辦中辦的一紙《意見》可以產生比法律還要強的市場效果」這些現象,但實際上與十八大以來的「法治」進路並不匹配。如上文提到,張泰蘇與金斯堡指出,中共近年來的法治化走的恰是以正式法律手段為中心的法律主義路線;中共正是努力將綱領、文件、政策通過法律手段變為正式的國家法律法規,並強化法院系統的能力加以執行;而 2018年修憲去除領導人任期限制的舉措,亦說明成文憲法地位的巨大提高。此外,從前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紀委)在調查中使用「雙規」手段(「在規定的事件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曾被質疑涉嫌非法拘禁和審問,中共在2018年修憲中也專門將國家監察委員會(監委)寫入憲法、為紀委掛上了監委的牌子,並且在《監察法》中規定了「留置」以取代「雙規」、為監委對被調查人採取強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這同樣是正式法律手段受到重視的體現。雖說「承認綱領、文件、政策的法律地位」與「更多地採用正式法律手段」在理論上並不衝突,但這種學說顯然無法解釋十八大以來的法治發展動態,更不能被強行標榜為新時代的中國法治道路的特徵。相反,強世功的「法律多元主義」學說,恰恰是與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法治進路背道而馳的,頗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之嫌。
而同在北大法學院的陳端洪教授則援引類似於美國憲法學界的「主權者」理論,論證中共代表人民、作為「主權者」的唯一代表,確實有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地位。誠然,西方(至少是美國)的法治觀,其實並不排除這種超越憲法和法律的存在。耶魯法學院的著名憲法學家阿克曼(B. Ackerman)教授所提出的「二元憲法」理論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阿克曼的理論是對司法審查中的「反多數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的一種回應:所謂「反多數難題」,是指在民主社會中,立法機關代表的是多數人民的意志,而非民選的司法機關推翻立法機關的立法,便有違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主義原則之嫌。阿克曼對此的回應是,美國民主政治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決斷:在根本國是問題上,公民可以通過更為廣泛的、充分的動員,形成深思熟慮後的決斷,即「美國人民」的決斷,這種決斷被憲法或憲法範式的變更所固定下來——阿克曼將這種極少出現但極其重要的時刻稱之為「憲法時刻」;而定期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代表的是某一次選舉中一時的民意,他們所產生的法令,是「美國政府」的日常決斷;所以,法院根據憲法推翻「美國政府的決斷」(包括民意機關的立法),是在維護更為根本的「美國人民」的民主決斷。在這個體系下,憲法最終來源與「人民」這個主權者,人民當然是高於憲法的存在;而與此同時,法院的判決又能夠約束日常政治、維持法治體系的正常運轉、節制政治權力。
類似地,陳端洪認為,中共中央是「作為主權者的中國人民」的終極代表,而憲法僅僅是「以『全國各族人民』的口吻宣告了、衛護了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原則而已」,「像任何代表制一樣,在中國,主權者人民也不能親自出場,而需經由代表行使主權」,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代表,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事實,也是根本的憲法原則」,中共中央是「人民制憲權的常在的代表機構」,也是「主權意義的制憲權代表」。
不過,與阿克曼的理論下「人民制憲權」門檻極高、只在極其重大時刻出場這個設定不同的是,陳端洪的理論下,中共中央是一個「常在」的主權者代表,「在常態下,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下活動,如同憲定權」,而「當憲法和國情嚴重衝突時,執政黨便行使制憲權代表機構的權力,以發佈政策的形式對民族的生存方式做出總決斷」,事後再進行正式的修憲和修法程序。陳端洪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良性違憲」。
無論是否認同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不可否認的是,陳端洪的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中國現行《憲法》的憲制安排,是對中國制度下黨與憲法的關係的準確描述。而且,陳端洪與強世功的對政策的法律效力的描述,在最終效果上不謀而合:中共的一紙文件雖然表面上可能違憲或者違法,但修憲或修法程序事後補上就可以了,而多年的政治實踐中各方也都習慣了這種安排。
施米特正是因為在《政治神學》等著作中對超越日常憲法和法律秩序的「主權者」的闡釋,被擁護中共制度的中國國家主義憲法學者們奉若神明,但如卡恩所解釋的,即便是施米特所說的「主權者」,也同樣是這樣一個「例外」的存在,而非陳端洪的理論下中共那樣「常在」的主權者化身。
然而,十八大以來中共官方的論述下,並不存在黨作為一個整體違法或是違憲的可能,因此陳端洪的「良性違憲」便也無從談起。拋開這個技術問題不談,一個更為致命的問題在於,「常在」的主權代表,本身就是與「法治」不兼容的。即便阿克曼、卡恩(P. Kahn)等美國憲法學者承認了超越憲法的「主權者」的存在,他們同時強調這個主權者是極少出場的。卡恩在這個問題上引述德國法學家施米特(C. Schmitt,施密特)解釋說,主權者的出場是一種「例外」,有如宗教奇蹟一般改變了日常政治的根本範式。但這也必然意味著,神蹟之後主權者(神)需要退場,日常政治才能在新的範式下繼續進行。阿克曼的「憲法時刻」,同樣是侷限於內戰(重建)、新政等近百年一遇的重大變革。
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正是因為在《政治神學》等著作中對超越日常憲法和法律秩序的「主權者」的闡釋,被擁護中共制度的中國國家主義憲法學者們奉若神明,但如卡恩所解釋的,即便是施米特所說的「主權者」,也同樣是這樣一個「例外」的存在,而非陳端洪的理論下中共那樣「常在」的主權者化身。
如果說法律意義上的「主權者」最初對應的是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的話,「法治」的興起意味著君主從台前退到幕後,將日常政治委託給政府、議會和司法機關,即便君主名義上保留著在例外狀態下干預的權力。否則,君主動輒出場顛覆日常立法、干預行政和司法,顯然又回歸到了君主「人治」的狀態下。同樣,即使是以「人民」作為主權者,主權者的頻繁出場同樣會導致日常政治的法律規則被頻繁的主權決斷所擾亂,使得「規則被例外所吞沒」(exceptions swallowing the rule),從而令法治消亡。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人民」這個抽象概念的力量,恰恰來自於其神秘性和其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感——想像一下,如果「人民」指代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群,「以『人民』的名義」顯然不可能有同樣的政治能量。所以,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動輒出場,也會削弱「人民」本身的憲法地位、最終無法受到認真對待——這恰恰正是中國社會中「人民」一詞的現狀:政治生活中「人民」無處不在、政府和公共團體處處被冠以「人民」,其結果就是「人民」變成一個極度空洞、令人麻木的概念。因此,無論是基於君主主義還是基於人民主權的「主權者」法治理論,都需要極其嚴格地限制「主權者」的出場;陳端洪所設想的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常在」主權者代表是不可能與法治兼容的。

自立門戶,或是向普世價值的「法治」靠攏?
無論是中共官方的敘事還是中共法學家們的努力,都並沒有能為「黨」和「法」的關係提供一個既符合通行的法治準則,又符合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實際的解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共官方的敘事還是中共法學家們的努力,都並沒有能為「黨」和「法」的關係提供一個既符合通行的法治準則,又符合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實際的解釋。那麼有人可能要問,為什麼中共的「法治」必須要符合通行的「法治」準則?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努力,難道不恰是為了形成自己的「法治」標準、擺脫西方尤其是美國對「法治」話語權的壟斷?
確實,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法治」理論建設,本來就沒有以任何外部標準前提。然而,既然如此,外部同樣可以質疑,如果到最後中國特色的「法治」因為已經不符合外界所理解的「法治」的基本定義的話,為什麼還硬要把它稱之為「法治」呢?如果真的有「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話,為什麼不能堂堂正正挺起胸膛說,「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黨治』」是個好東西、西方鼓吹「法治」只不過是在鞏固資本主義法統和剝削秩序?
這是因為通行的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經歷二十世紀民主自由的浪潮,已經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品牌價值,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對國外,都是一個正面資產。對內而言,「『法治』優於『人治』」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民眾親眼看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確實是以吸收了通行的法治理念(維護公民權利、保持法律關係的穩定、實行程序正義、政府依法行政等)為基礎。此外,對於絕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相比「自由」和「民主」這些更加難以定義和衡量的概念,「法治」是一個更為明確的、清晰的正面價值觀。由於法律的道德權威,「違法行為可以被默認為不道德的、至少是有問題(questionable)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無需認真思考就可以接受的結論。
這是因為通行的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經歷二十世紀民主自由的浪潮,已經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品牌價值,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對國外,都是一個正面資產。
而如果當局能夠基本符合通行的法治形式要件、不去選擇性執法也沒有超越法律授權的話,那麼就更沒法輕易質疑其道德合法性。畢竟,人們早已習慣了無論多麼開明進步的社會都有自己不喜歡的法律這個事實。比起忍耐自己所不喜歡的法律,法治的崩壞代表著秩序的崩壞,是絕大部分普通人更不願意承受的滅頂之災。
即便中共的「法治」建設是以鞏固專制、強化黨的領導為目的的,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也並非完全與通行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馳:雖然中共中央依然凌駕於法律之上,但通過法律加強對下級黨員官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讓政府的行政有法可依;即便法院仍然無法審查立法、亦無法對受到中央政策影響的企業和個人提供救濟、更無法伸張公民的憲法權利,中共還是在其體制內提高了法院系統的地位、增強其執行能力、在有限的範圍內使得法院可以獨立辦案不受(地方)官僚幹擾,也確實是與通行法治理念相符的效果。所以,要達到「法治」建設的內政效果,無法避免在形式上承認通行的法治理念和做法。
在對外的場景下,無論是招商引資還是參與國際公共事務,都也是以基本認同通行的法治理念為前提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資本和為其服務的買辦階層(投資銀行、國際商業律師等)在這個過程中走在了為中國「法治」話語背書的最前列。上文提到的例子裡,如果說基於金融監管和國家安全立法的審查還算是有明面上的法律授權的話,中辦、國辦一紙的《意見》,即可置教育培訓產業於死地,甚至在尚未有任何立法程序動作的階段,便已經有眾多教育培訓機構關門大吉,顯然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應當出現的現象,所以引起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擔憂。
然而所幸在菁英國際律所的精心包裝下,無論是如何違反法治原則、侵犯公民和企業憲法權利的黨政行為,業者被迫作出調整,都不過是要像「開車遵守交通規則」一樣「在業務中遵守相關規則和規定」的稀鬆平常之事而已。幾十年來在國際交易中涉及中國內地的缺乏法治所帶來的風險,無一不是被律師們這樣用「監管風險」這樣格式化的法律術語一筆帶過。為了配合中國吸引國際資本,投行業者和律師們需要假裝中國的法治與西方並無本質區別、只是程度上有所欠缺。這樣做恰恰是符合金融業的邏輯的:如果只是程度上的欠缺,意味著風險可以被量化、從而使基於概率和數學模型的定價成為可能。
同時,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企業自身也不可能公開與政府叫板,反而要幫助政府維護其法治話語、旗幟鮮明地支持政府依據「法律法規」進行的「監管」,一如新東方即便因一紙文件遭受了滅頂之災,仍舊不得不在新聞稿中顯示出對政府「法規」的順從。
所以,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中共的「法治」建設,為了達到其效果,都不可能脫離通行的法治定義而另起爐灶。中共當然一方面希望用通行的法治理念的金字招牌來收攬人心、吸引資本、管控下級黨員官僚,同時另一方面拒絕接納通行的法治理念的核心價值、亦拒絕把黨完全置於憲法和法律之下。但如果「中國特色」的「法治」完全變成中共的自說自話、與通行的法治明顯毫無關係,自然也就無法沾到「法治」的光、達不到「法治」建設的功能性目的了。
因此,中共的目標是兩面佔盡好處,而不是另起爐灶從而被當成朝鮮的金氏王朝、利比亞的卡扎菲那樣的異類。
因此,中共的目標,實際上是一方面維持黨對法律的絕對領導、拒絕上文談到的法治的「核心價值」(法律至上、對政治權力形成實質約束),另一方面又企圖通過實踐法治的「形式要件」(如專業的司法機構、公開明文立法)來聲稱自己確實在實行「法治」從而搶佔國際通行「法治」理念的話語權,這樣才能兩面佔盡好處,而不是另起爐灶從而被當成朝鮮的金氏王朝、利比亞的卡扎菲那樣的異類。
只是,這種混水摸魚式的模糊操作能走多遠,還是一個未知數。香港國安法對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已經大白於天下;《網絡安全法》《英烈保護法》等一系列明顯意在對社會進行管控和壓制的法律,並不會「依法辦事」的名義就變得形象光鮮起來。受過英美法律教育、供職於國際律師事務所的菁英律師們在為中共的「法治」進行包裝時,面對質疑固然可以振振有詞地說,西方國家也會有政治風向的突變和法律法規的改變對業務產生重大影響。但他們閉口不提的則是:在法治國家,執政黨的政策宣示能否落地本身就需要經歷輿論、民意代表、立法或行政程序等多重考驗,越是影響巨大的政策越是會慎重進行,給予相關當事方更多爭取改變的機會和準備應對的時間;而最終生效的法律和規章還可能遭到反對者提出的司法審查訴訟、若是違反憲法和法律則會被法院認定無效。即使是選舉造成政黨更迭所引發的行政方針的變化,仍要受到現有法律法規的限制。以美國行政法為例,行政機關制定、修改行政規章的行為要受到憲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制約,除了不得侵犯憲法權利之外,還須遵循法定程序、亦要考慮長久以來對既定做法的依賴即所謂的「信賴利益」(reliance interest)。
反觀中國的諸多立法與行政規章,不但未經任何充分公開聽證和公眾辯論、也常常沒有明確憲法或法律授權,企業和公民更無法提起行政訴訟或違憲審查訴訟、與政府對簿公堂挑戰其合理與合憲性(中國的行政訴訟法下,政府文件、規章本身屬於「抽象行政行為」,法院無權審查);因為立法是黨的意志、黨又領導人大,所以人大常委會的違憲審查(即使真的被運用)也從來無法讓黨受到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制約。
對於這些,國際資本也許會時不時選擇性無視,但隨著中美對立的持續、各種政治事件造成的對立升級,中國在多大程度上還能以「法治」取信於國際社會,是需要持續觀察的。香港國安法造成的國際震動和「監管」動作造成的中概股暴跌,也許只是中共的中國特色「法治」話語所要面臨的艱難歷程的一個開端。
(作者為美國法律博士、紐約州執業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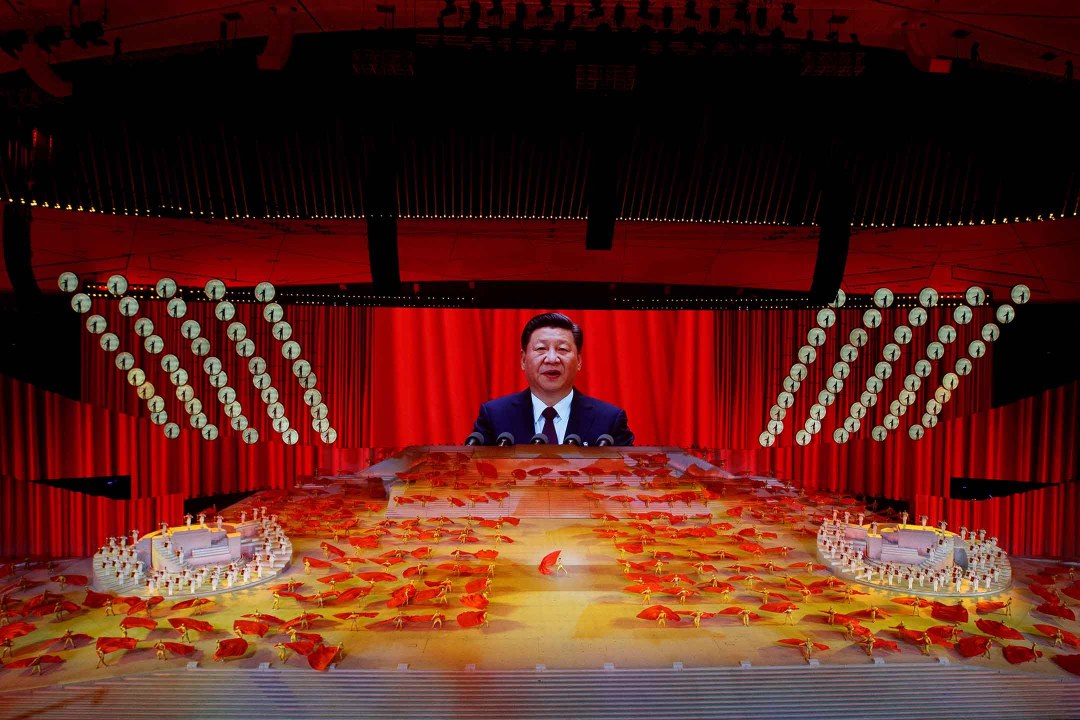

现在看来也不过时!
再次重读,依然有所收获
哈哈哈,这篇文章啥时候都能再拿出来品一品
好文章的时效性是真的长,今天看来仍非常有启发
“双规”手段(“在规定的事件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是否应该是规定的“时间”?
反驳一下文中“……在有限的範圍內使得法院可以獨立辦案不受(地方)官僚幹擾,也確實是與通行法治理念相符的效果”这个观点:
在中共的组织架构里,政法委书记一般由本级党委副书记担任,而法院院长一般是政法委委员。在这样明显的上下级关系里,法院获得更大的独立地位,不受干扰地进行独立审判是不可能的。
用狗屁不通的逻辑和文字,强抓着权力和控制。
任何试图从法律角度来解释中国法律所得出的结论都是表面的。最近的释放两个迈克请问法律专家怎么解释?对中国法律太认真只会让自己不被认真对待
确实是一篇好文章,够深入,基本上算是把这个问题讲透了。
中国的法治概念感觉更接近战前德国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概念,只要求形式上的确定性而可以不用考虑内容的正当与合理性(至少不用向自由主义的民主程序寻求正当性,当然也不会为了自由主义式的合理性而分散、限制政府权力)。不过既然党拥有凌驾一切的专断权力,那不管国师们怎么努力也掩饰不了法律只不过是党的政策之一的事实。对任何机构来说,中国的整个法秩序都存在政策性风险。
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日後拉清單 karma’s a bitch winnie
专业好文👍
目前的法=以前的圣旨,只是披了一层皮,用多少理论去粉饰都无法改变其实质
補充一點吧,軍隊權力掌握在軍委主席手裡,規定只能管下面的人,權力運行就是這樣的
想想蛮讽刺的,一纸文件,就能让一个名人在网络上的痕迹消失的干干净净。要是哪天针对普通人,更是没人关心了。
@嘿嘿哟呦 这个前提就不成立。中共常委和总书记不需要遵守党章。比如党章有“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
党章是来约束下级党员的。
显然这种情况是由权力运行方式决定的。
总之,就是土共想要确保独裁党治、帝治,同时又想用“法治”为自己贴金,装点门面。
非常好
既然可以良性违宪,那或许良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是可以的
虽然法律理论部分看的有点吃力,来来回回思考几遍才基本理解。但是逻辑清晰,耐心读下来收获了很多,非常喜欢修宪其实反证了党重视法治的思路,作者一一反驳御用法学家的部分读的也是非常过瘾!必须赞好文~!
專業好文
好文章!正好解开了我最近一个困惑(明明天天强调法治中国,但中央却为何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市场,与法治模式背道而驰),而且给我间接科普的宪法发展。当今的法治模式更像是商家的霸王条款:“最终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平安无事的时候极大多数就按原来条款执行,但有特殊情况或冲突的时候,就会搬出来这条。
當「執法彈性」、「不得主張不法的平等」、「法不溯及既往」及「良性違憲」推到極限,例外已無常規可言,還能稱為法治嗎?
我觉得中共本质并非为了"法治",或者他们愿意在与其独裁地位不太相干的领域更加"法治",比如处理日常民事纠纷。但我觉得其强调"法治"最重要的目的是披上羊皮。随意制造恶法,然后依此"法"而行,这不能叫法治,法治在最初的立法源头就走样了。
这篇文章真是对应了独裁者无论做出多么离谱、恶劣的行为都会有一群学者出来装模作样地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用来欺骗民众,当然民众自己也没有真正选择的权力,欣然接受这样的欺骗。
作為一名法律系學生,這篇文章讓我感覺像是再上了一次憲法的基礎理論
裡頭提到的「刪除憲法關於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側面反映出中共近年對法治的強調」的觀點,也是我從未想過的
很喜歡這篇文章
最近看了《失踪人民共和国》里面提到指定监视居住,结合这篇文章,非要挂着一张皮,而且民间其实反弹很大。除却小粉红群体,我身边的普通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里子,毕竟才70年嘛。
文章不錯
@Rosarella
你的例子,令我聯想起北京如何選擇性引用、僭建基本法。
文章不错。
提供一个现实注脚:
新中国史上第一例决议成立的“违宪审查”即发生在2020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判定《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等关于民族学校应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安排,违反宪法中关于“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规定。(可参见 https://npcobserver.com/2021/01/20/recording-review-pt-7-constitutionally-mandated-mandarin-medium-education/ )
此案的现实背景应该路人皆知,不必重复。单就宪法本身来说,宪法亦规定了各民族使用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个决定无疑是单薄且片面的。然而木已成舟,中共就是成功地将这万众期盼的、法制史上光辉的第一次强夺过来,为一个很可能实际是在损害宪法权利的镇压背了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嘿嘿喲呦
很久沒見,最近還好嗎?
我想最大的疑問是,假如真的要參照習慣法,還需要尋找習慣的來源。香港還有「大清律例」,台灣的《中華民國民法》第一條也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還有視為如何才可視為習慣的明文參考條件,而我不認為黨章會有這樣的份量和約束力。
事實上,世上的確除了海洋法系和大陸法系以外的混合設計,像伊斯蘭國家還有宗教法庭。但本篇文章已經提示了,即使是不熟悉法律和法律學的普羅大眾,對於法律(和法治)能否帶來公平也是高度敏感(不然就不用以一整篇文章來描述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我的確不懷疑會有附合中國「國情」的法治,但當中離公平及背後最重要,對人的關懷有多近,我真的非常懷疑。
@玄米津師 個人認為用品牌來做例子並不是太恰當。如果要我說,我會說就像一個賣素雞肉的硬要說自己賣的是真正的雞肉那樣可笑。指鹿為馬莫過於此。
明明是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因為自己心虛(是的,我就是覺得他們心虛)硬要把它混淆在一起說,還要大肆宣傳。中文世界語言的墮落,就是因為這些無恥的筆桿子。
讲的很细致,把特色法治背后独裁者既想大权独揽,又要装点门面的小算盘给推论出来了。
不容易,把中国法制就是党治心平气和地说明白了。
好文章。
我來做個devil advocacy,所謂‘主權人’(即當本身)沒有得到有效限制的這一對中共法治的核心質疑,可否用黨章來反駁呢?也就是說即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也要受到黨章和‘中共中央辦事條例’的制約和限制呢?雖然黨章和辦事條例不是正式法規,但可否以類似英式普通法中大量存在的習慣法來視之呢?
其实全球法治也并不是只有英美普通法系和德法西大陆法系这两种”品牌”,不少国家的法系都存在混合普通/大陆,宗教,自身习惯法的做法。难道中共就不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体系吗?
大陆还称不上是寡头,寡头是贵族民主或者精英民主堕落,大陆不具备成为寡头条件,最高领导人说的话可比一小撮人管用的
@俊偉
因為還未到這一步,而且也可能不需要走那一步。試想想兩間做名牌包包的公司,一間百年老店世界楷模,另一間新興的。挑戰傳統往往較困難,但自創一套,再反過來說「我這才是傳統正宗的,看我做得比你更好」可能較容易。在國際舞台上,我的感覺是這種玩法,我們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有這些這些優良傳統文化,你小美國立國才二百年沒資格說三道四這樣。
非常棒的分析,獲益良多
以此反思台灣現狀,雖然沒有到黨即法的程度,但執政黨的確藉著疫情,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下,肆意的規範人身自由和疫苗政策,也以選擇性的態度使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箝制人民的發言。
可惜多數人民對此並沒有警覺,我們需要更多在法治這部分監督政府
讀起來暢快淋漓、獲益良多,讓中共對法治的詭辯無所遁形。
假如法律的制定只為保護現有政權,而不是用來保護人民,人民應該遵守嗎?
不只是法治,還有自由,民主,平等等等。。都在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裡面。
認真說,真的那麼自信,直接說獨裁就是比民主好,沒自由比自由好,不就好了嘛?說一大堆中國式法治和民主的,虛偽到令人作嘔。
從宏觀來看,法治(法律治國)需要健全的法制(法律制度)。立法,司法及執法,需要同樣的建築在「全民」基礎上。
只有一小撮人立法,而此法律卻被執行涵蓋全民。這種法制必然導致惡法。這小撮立法者只對寡頭政權負責,一廂情願,住在象牙塔。
所以健全的法制,必然是全民選出的立法代表。以此而立的法律,才能涵蓋全民。硬軟之間才能拿捏得當,才能說什麼法治。
写得真是专业
以常理推斷,一個不能引用憲法的法院,不太可能保障法治。違憲的法律,基本談不上法治(中國有很多違憲的法律)。
文章写的很好。作为法学生表示,其中的很多表述非常专业,对中国的观察也很敏锐。个人觉得自从2012年以来,中央对于“法治”的强调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文中提到的修宪、司法改革,还是公开庭审一些重大的政治性案件,最高领导人来政法学校调研,对于过往“严打”时期诸多冤案的司法重审,以及十九大专门强调的“合宪性审查”,种种现象都表明了这种对政权“合法化”的高度重视。这是之前的领导者未曾达到的地步。
同时也能感受到民众的法律意识的确在不断增强,即使大多数人的法律意识只是朴素的法律观念,但相比于过去民众一谈起法院就“为之色变”的态度,这些年来中国基层法院案件的数量飞速增长,大多数民众都乐于运用法律武器、也更加看重法律在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在我看来这种法律意识更多的是“权利”意识,却缺少了道德意识和义务意识)。如近年大火的罗翔教授所说:自己之所以被捧红,根本上是源于民众内心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这种渴望其实就是法律精神在国民心中的体现。这种民众观念的转变,也要求领导者必须借助“法治”理念为自己提供舆论支持。
但是,这种中国特色的“法治”观念究竟能否解决理论上法治的核心价值(作为目的本身)与现实中法治的表面功能(作为治理的工具)之间的深刻矛盾呢?公众法治观念的逐渐提升,能否可以让大多数人意识到这种应然与实然存在巨大裂缝的吊诡之处呢?恐怕只能让时间给予答案了。
勘误,简体版的“着”全部是“著”
感謝,都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