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寫關於宗教學與醫療問題的論文,讀到一本研究夏威夷原住民的著作《Healthy Ancestor》,是加州大學醫療人類學家 Juliet McMullin 十年前出版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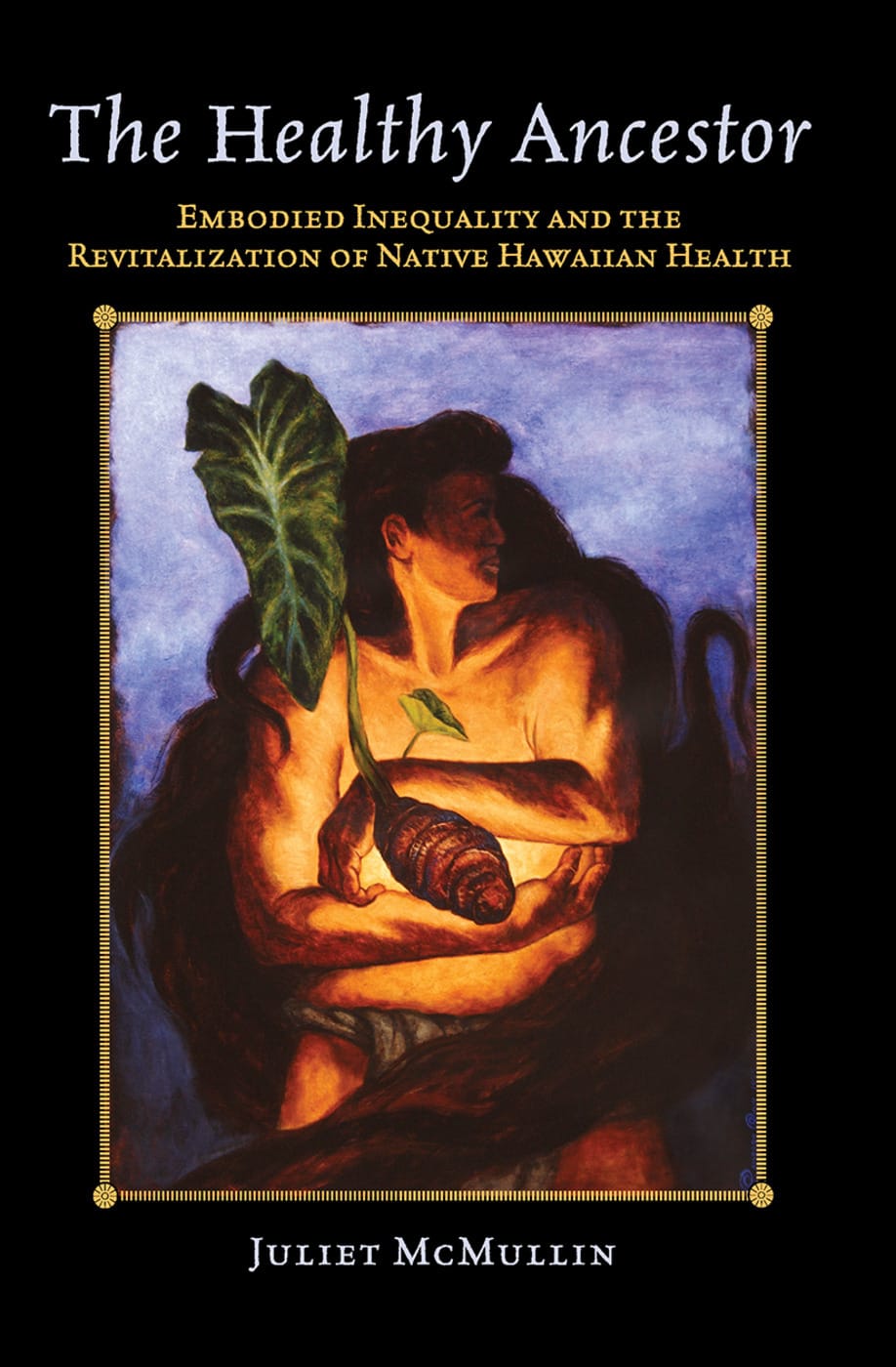
夏威夷原住民不少已經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有工作也有醫保,但利用西方醫療系統的比例仍然偏低。很多原住民生病時都選擇服用傳統草藥,或者去做原住民傳統的按摩治療(loti-loti)。McMullin 發現,許多原住民口中「健康」的狀態,完全不是生物醫學定義的「無病無痛」和「可以正常工作」,而是「像祖先一樣,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奔馳,在神聖的土地上獲取我們需要的資源。我們還可以從河流捕魚,拿漁獲去做夏威夷傳統菜色……」
失去土地以後,原住民要做傳統菜 poke 的話,就只能在超級市場買魚。抗拒西方醫藥不是因為他們不在意健康,而是因為他們的身體就是記憶與反抗的一部份。西方殖民者來到夏威夷,將他們從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趕走,為打壓集體意志阻止他們進行傳統宗教儀式,將他們的生活方式視為「野蠻落後」,強逼他們進入「現代社會」,參與資本生產。原住民視土地為生命之源,但現在土地只是私人財產,待價而沽;而自然界的一切草木河川對殖民者而言只是商品,沒有任何神聖的地方。原住民不去看「白人醫生」是因為他們記得,記得這一切都不是原來的模樣,生命曾經是遼闊而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