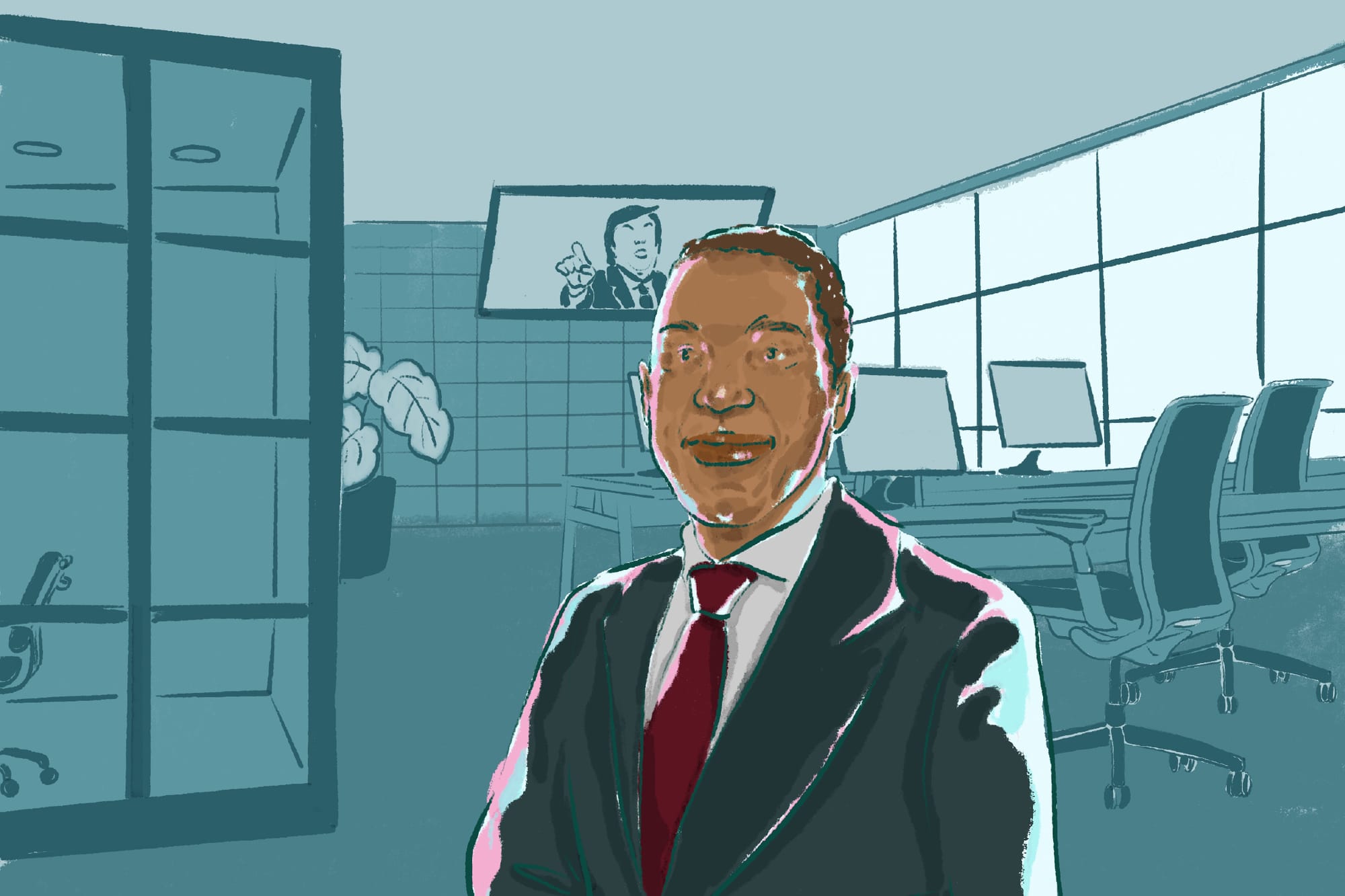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來臨之際,端傳媒記者通過面談、電話或視訊的方式,走訪了生活在美國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職業、不同膚色的人群。這些人裏,有生活在中西部的共和黨白人,有來自亞洲或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或移民第二代,有退伍軍人、小企業主、農民、自由職業者,也有科學家、教授和政府僱員。
他們中很多人從未接受過媒體訪問,幾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聽說端傳媒的名字——向中文讀者講述自己在過去四年的經歷,有的人興奮,有的人辛酸,有的人警覺,有的人五味雜陳。拋開那些枯燥、艱深的時政報導,我們希望藉由這些鮮活、真實的個體故事,向讀者展示政治的另一面:四年一屆的總統任期是如何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與事業?
從本週至美國總統大選日,端傳媒將在每個週末為讀者呈現這些故事。第一輯是三位「千禧一代」在這四年中的喜怒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