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載 《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端傳媒》受權轉載,有節略。
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而在中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的存量中,有超過一半是國有企業佔據的。餘下的非國有企業中,也有許多是國家參股的股份制企業。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是一種跟其他投資海外的跨國私人資本不同的資本嗎?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的李靜君教授在其新著《全球中國的幽靈:非洲的政治、勞工和外國投資》中,從「積累邏輯」、「生產政體」、「管理氣質」這三個面向入手,闡述了投資非洲的中國國家資本與大多數跨國私人資本的不同。儘管對「國家」的性質和作用有所浪漫化,但這部著作還是做出了不俗的理論貢獻,它充分揭示了「資本的多樣性」:不同資本的行為、決策因不同的積累邏輯、社會壓力而不同,其關鍵在於,不同類型的資本帶來了不同的社會鬥爭的空間。此外,它提出了「充滿事變的全球中國」這一方法論概念,並進一步發展了「拓展案例法」。
《全球中國的幽靈:非洲的政治、勞工和外國投資》
作者: 李靜君(Ching Kwan LEE)
出版社: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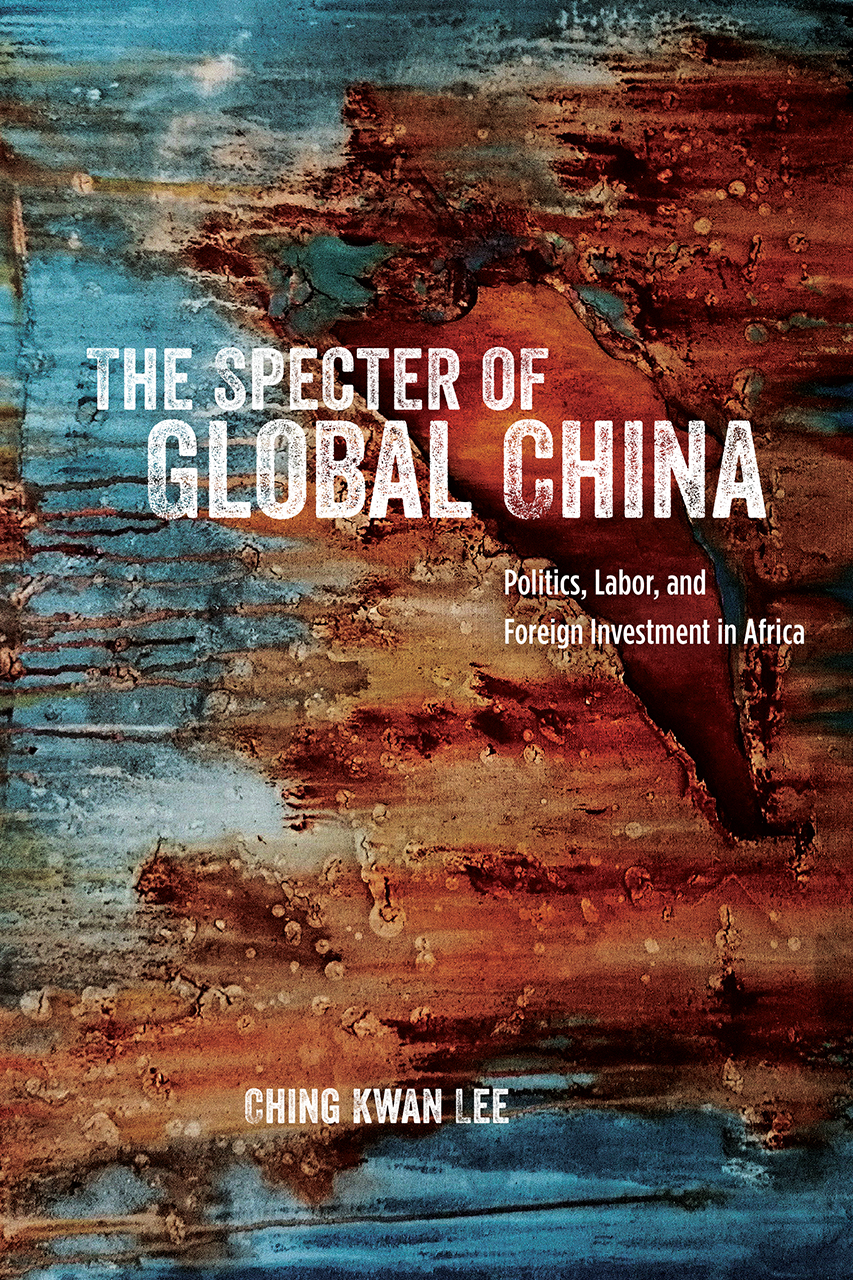
多重目標還是短期逐利?
學者王碧珺蒐集了1500多個中國海外投資項目的最終投資行業信息,發現主要是採礦業和製造業。再考慮到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巨大規模,可以認為採礦業、建築業、製造業是中國資本對外輸出、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輸出的主要行業。在此背景下,李靜君將運轉於贊比亞銅礦業、建築業的跨國私人資本與中國國家資本進行比較,試圖挖掘出後者的特殊性。
不同種類的資本有着不同的特性,其首要方面就在於不同的積累邏輯。李靜君發現,相對於跨國私人資本,中國國家資本對贊比亞當局做出了更多妥協。中國國企在對外投資時,除了獲取貨幣利潤之外還承載着國家戰略——獲取自然資源與擴大中國在非洲的政治、外交影響力。中國國家資本對這些戰略的承載,使得中國國家資本更容易對來自贊比亞國家與社會的壓力作出「即興」的反應,包括參與談判乃至讓步。
投資贊比亞銅礦的中色非洲礦業有限公司(NFCA)自稱「中國海外資源開發的前線部隊」,因為中國對銅資源的需求量不斷增大,其自身儲備卻很少。而爭取非洲國家在國際議題中親近中國,並使其遠離台灣當局的影響,也是中國國家資本的重要議程。國家政權的政治戰略在這些資本的決策部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國家資本並非不追求利潤,它和其他資本一樣也要謀求盈利。只是中國國家資本並不像許多跨國私人資本那樣純粹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或者說,它所試圖最大化的是一種「多維度的利潤」。如李靜君所述,中國國家資本遵循的是一種「涵蓋性積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的邏輯,除了貨幣回報的維度之外,還包含着政治影響和產品資源等維度。或者更嚴謹地說,對中國國家資本而言,這些非貨幣回報的維度更加突出。
這一點在採銅業表現得很顯著。首先,在2008年經濟危機時,銅價跌到生產成本以下,KCM(印度資本)、MCM(瑞士資本,但有許多南非、秘魯管理者)紛紛宣布縮小生產、大規模裁員。而NFCA則宣布不裁員、不減產、不減薪,因為它着眼於銅礦資源的長期供給穩定以及與贊比亞政府的良好政治關係,寧願承受短期虧損。其次,不同資本對贊比亞政府推行「意外利潤税」的反應也體現出這種區別。當銅價漲到最高點時,贊比亞政府在民間與反對派的強大壓力下,加收「意外利潤税」。KCM、MCM等對此強烈反對,而CNMC(NFCA的母公司)的高管則表示支持。再次,中國國家資本積極承擔了贊比亞礦區的多功能經濟區的建設工作,這個經濟特區是贊比亞試圖提高銅礦產業附加值的發展戰略的核心。KCM、MCM等跨國私人資本並不支持該項目,因為無利可圖。CNMC的高管也承認這一點,而因為中國政府只提供40%的補貼,他們不得不承擔巨大的經濟壓力,但為了提高中國公司對贊比亞政府的影響力,這項任務必須完成。從這三個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贊比亞政府在銅礦行業與外國資本的博弈中表現出一定的主動性。正因為中國國家資本承載着獲取自然資源與擴大政治、外交影響力的使命,因此需要比跨國私人資本更加適應贊比亞當局的要求。也就是說,中國國家資本的涵蓋性積累邏輯給予了贊比亞當局更多發揮主動性的機會。
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贊比亞方面需要有相應的精英意志和國家戰略,才具有利用中國國家資本的先決條件。在這一點上,建築業和採銅業形成鮮明反差。採銅業是贊比亞政府和社會各界眼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所以贊比亞政府有動力在採銅業更積極地與外資博弈。而建築行業在當地幾乎沒有政治敏感性,贊比亞政府也就沒有動力與中國資本進行協商。相反,贊比亞政治精英為了短期政治利益,從中國獲取大量貸款作為建設資金,加重了債務負擔。
贊比亞政治精英之所以熱衷於中國貸款,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可以快速而充分地滿足贊比亞政府的資金需要。對於贊比亞政府的基建項目,世界銀行會認為其回報率較低,還會要求政府進行某種改革(比如提高對艾滋病的防治),導致貸款有限、緩慢,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則不會有這些問題。但李靜君認為,這種速度優勢潛藏着風險,因為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建築商主動找到贊比亞政府要求進行某項建設,同時跟中國進出口銀行商定好貸款。在此情況下,贊比亞政府只能接受單一的投標出價。儘管中國政府貸款本身是「優惠貸款」,但考慮到定向招標所導致的建設價格昂貴,其成本實際上高過了世界銀行等提供的貸款。然而贊比亞的政治精英出於個人政績考慮,依然積極推動這些貸款基建項目落地,其中一些還被技術官員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政治項目」。在李靜君看來,贊比亞國家發展的利益在此受到損害,因為這種貸款模式對贊比亞國家債務的可持續性有着直接的負面影響。
對於中國來說,這種貸款模式有助於通過選擇性放貸來增強在非洲的政治影響力,為龐大的外匯儲備提供投資渠道,併為國內各種過剩產能開闢市場。與此同時,在非洲的中國建築公司也獲得了比在祖國高得多的回報率。可見,中國國家資本的涵蓋性積累邏輯在建築行業仍然適用,但這並未被贊比亞當局有效利用於某種長期發展戰略。

穩定剝削還是靈活排斥?
在李靜君看來,生產政體(production regimes)是反映不同資本特性的第二個面向,我們需要比較不同資本的生產過程,進而比較其中的勞資關係。在贊比亞,不論是銅礦業還是建築業,不論是中國國家資本還是跨國私人資本,都在同樣普遍地使用臨時工、外包工。不過在具體用工形式上,中國國家資本與跨國私人資本存在顯著區別。在銅礦行業,NFCA只與一家分包商合作,而KCM、MCM則使用了大量分包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是因為NFCA在生產過程中強調產量的穩定,更多的分包商會導致管理困難與更多的不確定性。KCM與MCM使用許多的分包商則是源於追逐短期貨幣利潤:KCM試圖利用分包商的競爭來壓低成本,MCM則是因資本短缺而想利用分包商的資金和設備。這兩種不同的用工形式帶來了不同的勞資關係:中國國家資本僱傭的贊比亞工人工資較低但工作穩定,甚至給予工人「永久僱傭」的保障;跨國私人資本僱傭的正式工人工資較高,但分包工人則要承受靈活用工的同工不同酬乃至隨時失業。在李靜君看來,這兩種生產政體中的勞資關係分別就是「對勞動力的穩定剝削」 和「對勞動力的靈活排斥」。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國家資本和贊比亞工人僱傭關係的「穩定」並非自然存在,「永久僱傭」等權利是工人通過鬥爭取得的。換言之,中國國家資本並不比其他資本對勞工更為友好,但因為其生產過程注重穩定、只使用一家分包商,這種生產政體使得工人們的分化程度較弱、鬥爭效果更強,因此為工人抗爭創造了組織條件,使得工人更有可能通過抗爭來與資本「討價還價」。為了爭取同工同酬和簽署永久僱傭合同的權利,NFCA的贊比亞工人在2011年進行了兩次罷工,並從外包工人蔓延到正式工人,管理者最終妥協。在KCM的礦山,外包工人也曾爭取過同工同酬的權利,但KCM掌握大量的分包商,工人難以形成有效組織,罷工最終草草收場。
在銅礦工人向中國國家資本爭取權益的過程中,政府偶爾的互動支持也顯得十分有效。2011年,反對黨「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大選取勝,工人趁勢發起了要求加薪的罷工,新政府也對此作出了熱切回應。但李靜君發現,建築業缺乏政治關注度,政治精英對工人的支持在建築業並不存在,政府甚至更傾向於幫助資方規訓工人,同時工人的集體力量也弱得多。相比於銅礦業,贊比亞的建築業是一個低工資、高度零散化的部門。不論是中國資本、其他外國資本、本地資本,都存在不依法提供勞動待遇、勞動防護以及拖欠工資、粗暴管理的問題,而且都使用大量的臨時工,這使得工人更難組織化。在中國國家資本資助並承包的項目中,政府可能更傾向於維持紀律並提高效率,甚至迫使工人接受高強度、低待遇的勞動,並且禁止其工會化,乃至直接打壓工人抗議。「愛國陣線」上台後,建築工人的罷工抗議也沒有引起政府足夠的重視,建築工們仍普遍批評政府監管不力。
《二十一世紀》
2019年八月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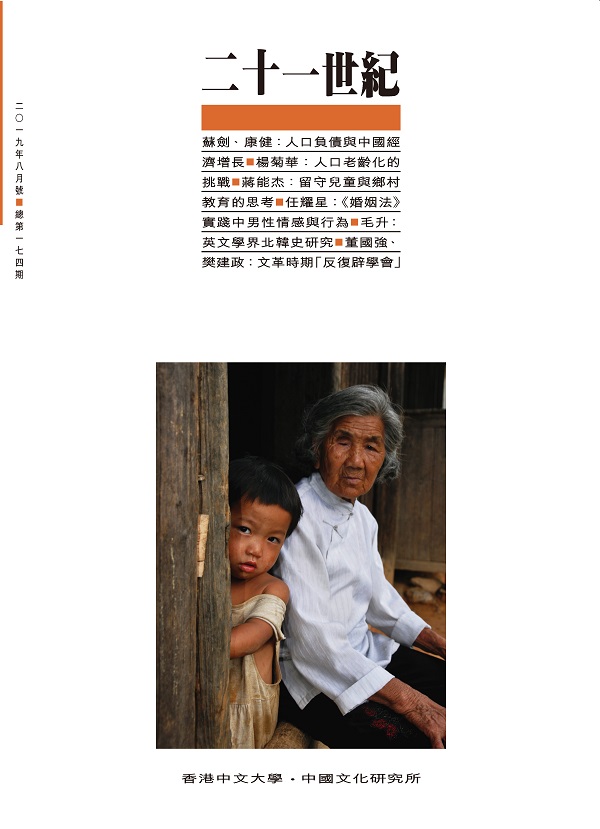
集體禁慾主義,還是個人職業主義?
反映不同資本特性的第三個面向,就是資本派駐在贊比亞擔任管理職位的人員所呈現出的管理氣質(managerial ethos)。從內部管理者的精神特質來看,可以清晰地區分出中國國家資本的「集體禁慾主義」與跨國私人資本的「個人職業主義」。中國國家資本派駐在贊比亞的管理者非常強調「吃苦」的文化。很多中國管理者出身貧困,許多人的節儉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中國管理者在當地往往集體生活在一起,從而壓低了個人消費。NFCA的中國人會被公司的大巴車接送,集體上班、就餐、休息、購物,如果臨時外出還需要報備,有的人只能週日在宿舍偷偷做飯來排遣苦悶。他們與家庭相脱離,許多公司都禁止員工將配偶長期留在贊比亞。
與此相反,在KCM等跨國私人資本的管理者那裏,存在着高度的個人主義與職業主義,公私界限分明。他們會帶家人一起來贊比亞,在當地給子女提供教育;他們更注重個人生活質量,有私人住宅、私家車,妻子、女傭烹飪飯菜。他們會僱傭當地的家政工與家教,還會參與當地的宗教、慈善、志願活動,而中國管理者與當地社區更加隔絕,許多偏遠建築工地裏的中國人更是很少外出。對跨國資本的管理者來說,當地生活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比如子女教育),他們會尋求跳槽到教育資源更好的國家,這在中國管理者中很少見。
中國人為什麼能接受「集體禁慾主義」呢?李靜君認為,從客觀層面來說,中國國家資本需要更可控的管理者,其集中化的管理組織機制發揮了作用。從主觀層面來說,首先,這些中國管理者面臨着中產生活的巨大經濟壓力,所以才會選擇離開家人外出掙錢,在集體生活中節儉度日;其次,他們對當地社會安全程度、友好程度的懷疑,使他們寧願封閉在集中生活區;最後,中國管理者所接受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發展」的話語,強化、合理化了這種集體的「吃苦」文化。
李靜君強調,中國管理者將「吃苦」的精神當成一種劃分道德、民族差異的界限。他們往往會將中國人與贊比亞人做比較,贊比亞人的「懶惰」、「不能吃苦」、「只想索取」被認為是贊比亞文化、道德中的缺陷,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而中國人的「努力工作」、「推遲享受」則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印度等國的管理者也常會以本國為標準指責贊比亞工人「懶惰」,但很少會將自身的「勤奮」視作一種民族美德,而是當作一種競爭激烈且貧窮的社會環境的產物。李靜君也指出,這種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將「吃苦」賦予道德性、民族性內涵的話語,讓中國管理者看不到自己也在承受資本的剝削,更模糊了中國資本與贊比亞工人之間的階級剝削關係。
「集體禁慾主義」給中國資本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是,當地普遍流傳着中國派囚犯來工作的謠言,這甚至成為了政客和主流媒體口中的「事實」。諷刺的是,也有中國管理者抱怨,每天往返於宿舍與辦公室就像「從小監獄到大監獄」。在此,文化的反制與適應同時存在——中國管理者一邊把外界的攻擊理解成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敵視,用「吃苦」精神合理化中國資本的工作環境,一邊也感受到與其他外國管理者的差距,開始向上爭取提高工資與福利待遇。與此同時,中國資本的管理氣質也在影響着贊比亞社會。

資本多樣性與全球中國
一項研究對於學術共同體的意義,首先不在於它提供了怎樣的答案,而在於它提出了怎樣的問題。而李靜君在書中提出的核心問題——「中國的國家資本是一種跟跨國私人資本不同的資本嗎」——啟發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全球資本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高度發達的今天,似乎資本的邏輯越來越趨同,似乎全球經濟越來越被一種單一的資本邏輯所主導。但本書的核心問題提醒我們,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並不是同質的。雖然從根本上說,所有的資本都是為了積累和自我增殖,但不同的資本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維繫和擴張中扮演的角色並不相同,體現出不同的積累邏輯、行為方式、勞資關係。換句話說,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應該被理解為資本越來越同質化的過程,而更應被看作是行為方式不同的資本之間不斷相互遭遇、碰撞的過程。其結果有可能是資本的同質化,但也可能是競爭的加劇,或者是進一步的分層和割裂,抑或是積累邏輯發生新的變異。資本的多樣性和異質性,也印證了托洛茨基的經典論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不均勻的」、「混合的」。
李靜君所提出的「資本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概念,也是對近年十分熱門的「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學派的回應。後者的分析往往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探討一個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怎樣的特點,通過跨國比較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多樣性——比如說,德國的資本主義更注重統合和勞資協調,而英美的資本主義則更放任自由競爭。但這種將每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看做一個獨立系統的分析方式,已經很難回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高度發達的現實。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早已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往往受到世界其他地區資本力量的深刻影響。討論「贊比亞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怎樣的特點」是一個意義不大的問題,對贊比亞而言,它所面臨的關鍵現實恰恰是各種不同邏輯、特點的外國資本使得「贊比亞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本身難以成立。更有意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類型,而是不同資本的類型。這裏的「意義」指的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意義,更是實踐的意義。通過區分資本的類型,可以弄清不同資本所具有的特性為反制資本提供了怎樣的空間,從而能採取相應的策略,促進勞動者爭取權益的鬥爭。
在 「資本多樣性」理論的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在某個資本的積累邏輯特別到什麼程度時將它區分出來?我們又該如何區分表現類似的資本?譬如,同樣是謀求穩定的銅礦生產,如今投資於贊比亞的中國國家資本和殖民時期在贊比亞興修基建的英美資本有何區別?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更加模糊。當我們探討資本的多樣性時,應該思考如何應對分類界限模糊這一可能的挑戰。
媒體和學界對中國資本的海外投資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大量討論,但往往流於表面。李靜君的系統觀察和細緻分析,則真正展示了中國國家資本在海外的運行邏輯。她指出,中國國家資本既不像許多海外媒體所說的那樣,比它的西方同行們表現出更多的「殖民主義」特徵,也不是如胡鞍鋼、盧荻等學者所言,其本身具有某種「進步性」、能夠對抗乃至超越和替代體系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和資本之間有所不同,但並沒有哪種資本比其他資本更加「優越」。中國國家資本的確更加註重生產過程的穩定和可持續,但這是因為它要滿足中國資本整體積累對銅礦石的大量需求,而不是因為更在乎生態環境和勞工權益。最重要的區別在於,中國國家資本所具有的特殊積累邏輯,使得它在和政府、工人互動時提供了不同的空間,當地政府與工人有可能利用這些空間來進行博弈。換句話說,決定中國資本海外投資帶來怎樣後果的,並不是中國資本本身,而是當地政府與工人能否針對其特殊邏輯來採取適當的策略。
李靜君在書中所使用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充滿事變的全球中國」(eventful global China),這一概念也為我們思考「中國究竟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分析中國」提供了啟發。隨着中國走向世界,理解中國勢必需要我們去捕捉中國在全球的蹤跡。同時,隨着中國越來越深地嵌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要理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必須把握其中藴含的全球性因素——比如中國近年的土地改革與全球糧食市場新一輪資本投機的關聯。總之,「中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分析對象,不能將分析局限在中國國界之內。「全球中國」的概念,有力地挑戰了至今仍佔主流的「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另一方面,李靜君對「事變」(event)的強調挑戰了「結構決定論」(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觀點。在對全球資本主義動態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一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中國資本以什麼方式擴張和流動。但李靜君指出,結構的力量固然重要,但資本的具體行為方式並不是完全被結構與經濟形勢變化所決定,而是同時取決於具體情境下,帶有偶發性(contingency)的政治博弈的動態過程。偶發性的政治博弈進而也可能改變資本所處的結構位置。中國的崛起與資本輸出,就是一種受結構制約但又充滿政治交鋒、結果不確定但又有改變結構位置的巨大潛力的「事變」。

「政治合力」:對贊比亞政府的浪漫預設
李靜君指出,中國國家資本在其三個面向(積累邏輯、生產政體、管理氣質)都遭受了贊比亞當地的挑戰——來自上層的精英意志和國家戰略,來自下層的罷工、騷亂和負面輿論。在李靜君看來,正因為政權意志與社會抗爭在銅礦業形成合力,才更好地迫使中國資本讓步。她認為,贊比亞人民若想讓外國資本妥協,單靠自下而上的抗爭是不夠的,還必須靠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與自下而上的抗爭運動之間形成政治合力(political synergy)。
李靜君對「政治合力」的強調,很大程度上源於她對當地勞工抗爭現狀的失望。李靜君用一整章來討論贊比亞工人運動的脆弱和撕裂,揭示罷工、抗議等直接行動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儘管這些行動已經比缺乏與當地緊密聯繫的跨國企業監察等活動有效得多。李靜君着重討論了工人內部的不團結和不信任問題。90年代的改革從制度上擊毀了工會的力量(諷刺的是,改革由曾經的工會領導人所推動),生產過程本身的零散化也使得工會的根基難以穩固。在這一背景下,普通工人並不信任工會的力量,他們常常認為工會領導人收受了資方的賄賂。與此同時,老一輩工人與新一代工人、正式工與臨時工之間也存在裂痕。在工會威信下降、工人被不斷分化的情況下,雖然工人依然可能發起罷工行動,但隨着國企的拆分、行業工會的瓦解,銅礦工人的罷工往往只能停留於企業內部的經濟訴求,不再能夠造成行業性乃至全國性、政治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小額貸款的泛濫和對個體創業的幻想也在瓦解着工人的階級團結意識。
對於脆弱、撕裂的贊比亞工人運動,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怎麼辦」?李靜君的答案,是將自下而上力量的薄弱視作既定條件,希望自上而下的國家干預能夠彌補它,形成「政治合力」。這一思路其實反映了她對國家權力的過分信任和浪漫預設。在底層抗爭乏力時,我們只能寄希望於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意志嗎?為什麼必須將「底層抗爭乏力」當做無法改變的條件,而不是試圖改變它?為什麼不去思考更好的組織動員策略?正如李靜君自己所揭示的,底層抗爭固然脆弱,但政府的「善意」干預也不長久。在Michael Sata的領導下,「愛國陣線」在執政後的確推行了限制外資的措施,但這一路線既充滿局限(比如未能惠及建築工人,未能實質性提高銅礦工人的組織能力),也隨着Sata的去世和「愛國陣線」的內鬥而無法持續。
有利的國家干預並不會自然地發生,國家更不會主動去尋求和底層形成「合力」。對於贊比亞工人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向國家施加壓力,如何保證那些號稱捍衞工人利益的政黨在執政之後不變質。若想長久地影響國家政策,推動政治合力的出現,根本的動力還是工人自身的組織、行動能力。工人和底層民眾唯有不斷壯大自身的階級力量,通過各種行動來捍衞自身的階級利益。而李靜君恰恰沒有討論「如何增強工人自身的組織和行動」這一重要問題。
李靜君在書中多次使用「贊比亞利益」(Zambian interests)或「國家發展」(nat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時,沒有批判性地反思這些概念本身是否應被使用。她雖然揭示了工人所訴求的利益與政府當局所宣揚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卻又表現出對贊比亞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利益」的肯定。這也體現了李靜君對國家的浪漫預設和缺乏批判性。當她提出「贊比亞政府如何更好地駕馭外國資本來服務贊比亞利益」這一問題時,無意中進入了一種敘事——「發展」是一個後發民族國家最根本的利益,是社會各個階層都需要的,而政府應成為這一根本利益的代言人。但縱觀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強調「國家利益」的反殖民主義敘事,實際上往往給國家統治精英、民族資產階級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說辭,而未能真正惠及底層民眾。因此,當我們看到「國家利益」、「國家發展」這樣的概念時,應該追問:這究竟是誰的利益、誰的發展?當贊比亞政府向外國採銅企業徵收「意外利潤税」被形容為捍衞「贊比亞利益」時,我們應該像書中的工人那樣追問:這一政策是不是服務於贊比亞政治精英和民族資產階級?接受「贊比亞利益」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實際上說明作者缺乏與贊比亞政治精英之間的批判性距離(critical distance)。
更理論化地說,當李靜君提出贊比亞政府作為「守門員」(gatekeeper)與工人階級產生合力可以更好地應對外國資本時,她實際上忽視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邏輯與資本邏輯在根本上的重疊與同構,而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尤為強調的。「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它的邏輯是追求無休止的價值增殖,利潤最大化只是一種普遍的手段和表現,犧牲一部分利潤來換取市場資源、政治影響也是實現資本長期積累的重要手段。而對於將資本所推動的「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推動資本長期可持續的價值增殖正是其重中之重。因此,當國家權力迫於一些社會壓力而向資本施加了影響、使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時,它或許算得上是抵抗了「特定的資本」,但這決不意味着它具有了「抵抗資本」的屬性。國家權力往往仍然在其他層面上維繫乃至強化着資本的運動。甚至可以說,在國家試圖掌控和干預資本時,其最首要的動機就是保障資本的長期積累,而資本在國家力量面前所做出的任何改變和妥協也都服務於這一根本目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國家的目標在根本上一致,並對立於工人階級、底層民眾的長遠利益。因此,贊比亞政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工人民眾形成合力來對抗資本,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更正:本「文」作者
方然被捕日期爲 2021年8月26日
本書作者之一、港大社會系博士生方然8月26日在廣西南寧被國安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即秘密關押)。
資料來源:鄒幸彤fb貼文 轉載 方然父親的微信訊息截圖
https://www.facebook.com/505789300/posts/10160054247884301/?d=n
赞比亚的富贵病得的有点早啊~
底下不就是中國資本正面的影響?過去東亞經濟發展也有冷戰前線,美國策略性的給予市場與投資協助這樣的背景。本文作者似乎只提不利的一面。反倒我變成是自幹五了。
贊比亞政府和社會,在銅礦價格上升、資源和民族主義捆綁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政治協同,向中國國家資本討價還價。而央企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穩定的戰略資源供應、建立政治影響力及認受性),而作出比全球資本更多的妥協。例如,中國在贊方要求下,建立了經濟特區,讓贊有機會發展銅產品工業, 而不停留在採礦;而其他跨國資本都以「不賺錢」為由,對贊比亞說不。
原文:《專訪社會學家李靜君:在非洲,中國是全知全能的「殖民者」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14-opinion-cklee-china-in-africa-colonization-accusation/?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贊比亞政府與工人合力抵抗資本?“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與國家的目標也許根本上一致,但不見得必然對利於工人階級與底層民眾的長遠利益。累積資本,提高生產力,地層民眾的利益增加了,於是長遠來說,可能是有利的。對於這個低度開發國家來說,國家需要有發展策略,由礦業累積的資本與人力資源去發展自主的產業,可持續的,分配平均的。資本的多樣性就是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多樣性。
所以,除了比較工人在印度瑞士中國公司的遭遇,與政府對工人的保護等等,究竟中國資本如何影響該國發展,並沒有具體陳述。世界銀行只會要求愛滋應防治?沒有任何”結構改革“以提高回報率,降稅,方便外資賺錢?如何影響銅礦價格?有誰的基礎建設項目價格還會比中國國營公司低,以至於單一投標價格昂貴?我有點懷疑正確性。中國造的肯亞鐵路評價如何?也許這個中國幽靈對非洲是正面的,為了與中國打新冷戰,西方會用更有利於非洲長遠發展的方式提供協助。
等了那麼久,終於談到李靜君了。最後那一點對贊比亞精英階層的浪漫想像,我猜想她本人也是沒辦法駁斥的。不過想到她這個研究能夠深入也是由於她本人與贊比亞當地的友好關係,也就不難理解了。不過瑕不掩瑜。中國國家資本與當地政府的互動,中國管理層的禁慾集體主義都是相當客觀與獨特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