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節選自手民出版社新出版的譯作《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原著是西敏大學民主政治研究中心的政治理論教授尚塔爾.墨菲,譯者為東京藝術大學博士生楊天帥,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首先,我想明言,此書並不打算在已過於興盛的「民粹研究」範疇中增磚添瓦;我也無意走入民粹之「真正性質」這種貧瘠呆板的學術討論。本書是一種政治介入,並不掩飾其黨派性質。我將會定義我所理解的「左翼民粹」,並說明為何它在當今時局能提供適切完善的策略,以恢復並深化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平等與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之理想。
作為政治理論家,我的理論模式受馬基雅維利影響——如阿圖塞所言,馬基雅維利總是把自己放在「時局之中」,而非在「時局之上」。我會以馬基雅維利為榜樣,將自己的反思銘刻於特定時局之中,即我們正在西歐國家中見證的「民粹接點」,以尋求馬基雅維利所言的「事物實質真相」(verita effetuale de la cosa)。儘管民粹問題亦與東歐相關,我仍將本書的分析框定於西歐——因為東歐國家有其特殊的共產主義歷史,其政治文化特徵亦與西歐不一樣,故當地情況須另作考慮。拉丁美洲形式多樣的民粹主義亦然。儘管不同民粹之間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它們均有其特定的時局背景,必須按個別脈絡理解。我唯一期望的是,我對西歐時局的反思可以為其他地方的民粹討論帶來一點啟發。
由於我為之辯護的左翼民粹策略源於反本質主義的進路,即使目的具政治色彩,我反思的重要部份仍具理論性質。這種理論進路主張,社會永遠處於分化狀態,可以透過統識實踐,以論述建構。許多針對「左翼民粹」的批判正是源於對這種進路的不解。我將在本書的部份論點引用反本質主義的核心原則,並於書末的理論附錄中更清晰地闡釋那些原則。
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首先會具體地說明自己理解的「民粹主義」。傳媒往往把這詞彙套在一切反對現狀的人身上。我將摒棄這層負面含義,採用厄尼斯特.拉克勞創立的分析進路,藉此有效地討論民粹主義的問題。
在《論民粹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一書中,拉克勞將民粹定義為一種論述策略。該策略透過建構政治疆界,將社會分成兩個陣營,從而動員「敗犬」(underdog)對抗「權勢中人」(those in power)。(註1)它不是一種意識型態,無法歸分到特定的程式化內容。它也不是政治體系。它是一種做政治(doing politics)的方法,可按不同時空採取不同意識型態,亦能與不同體制架構兼容並存。「民粹接點」出現於主導統識身處政治或社會經濟轉變的壓力下,因各種不滿訴求而失穩之時。在這樣的處境中,現存體制為了守護固有秩序而失落民心。如此,為統識提供社會基礎的歷史集團 (historical bloc)便會被拆解(disarticulated),我們便有可能建構新的集體行動主體——人民,重新配置(reconfiguring)曾被經驗為不公的社會秩序。
「民粹接點」出現於主導統識身處政治或社會經濟轉變的壓力下,因各種不滿訴求而失穩之時。在這樣的處境中,現存體制為了守護固有秩序而失落民心。
我主張,上述正是當今時局的特點,亦是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民粹接點」的原因。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統識構形一直活躍於西歐,而民粹接點則是它陷入危機的信號。在二戰後三十多年來,社會民主的凱恩斯主義式福利國家模式(Keynesian welfare state)一直是西歐民主國家的主要社會經濟模式;其後,新自由主義統識構形取而代之,目標是引入市場規則——包括解除管制、推行私有化與財政緊縮,並限制國家的角色,加強保護私有財產權、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正是用以描述這套新統識構形的詞彙。此一詞彙遠遠不止適用於經濟範疇,更包含着一套完整的社會概念和建基於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哲學的個人觀念。
這種自1980年代施行於多國的政經模式,過去一直運作無礙;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它始才嚴重地曝露自身的限制。是次危機的觸發點是2007年美國次按市場崩潰,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次年因此破產,引發全面的國際銀行業危機。國家必須給予金融機構大規模的紓困援助,以遏止環球金融系統崩潰。全球經濟衰退隨之而來,影響數個歐洲經濟體系,引發歐洲債務危機。為應對是次危機,大多數歐洲國家實施緊縮政策,招致國內的激烈反應,尤以南部國家為甚。
在經濟危機之際,一系列的矛盾凝結成葛蘭西所言的「空窗期」(interregnum):即圍繞統識建構的多項共識原則備受挑戰的危機時期。在當下的「民粹接點」,危機的解決方案仍然無處可尋。這些年來,新自由主義統識大行其道,造成了種種政治與經濟轉變,「民粹接點」正是反抗這些轉變的表現。這些改變導致我們所稱的「後民主」(post-democracy)狀況,象徵着兩支代表民主理想的巨柱——平等與人民主權——受到侵蝕。我稍後會解釋這種侵蝕是如何發生,在此之前,容我先探討「後民主」的涵義。
這些年來,新自由主義統識大行其道,造成了種種政治與經濟轉變,「民粹接點」正是反抗這些轉變的表現。這些改變導致我們所稱的「後民主」(post-democracy)狀況,象徵着兩支代表民主理想的巨柱——平等與人民主權——受到侵蝕。
《寫給左翼民粹主義》
原書名:For a Left Populism
作者︰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翻譯: 楊天帥
出版社:手民出版
出版日期:20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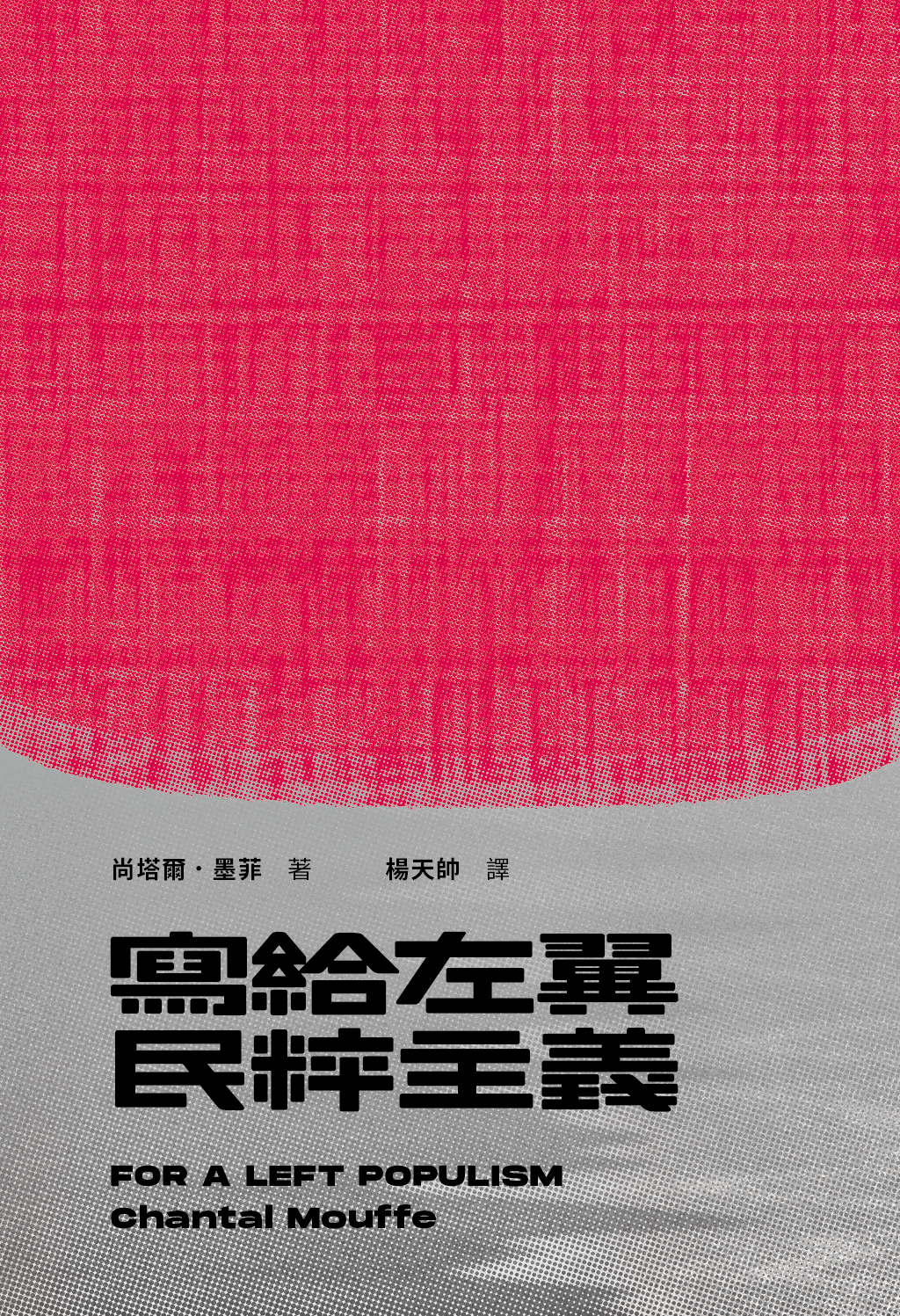
「後民主」一詞源於科林.克魯希(Colin Crouch),指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的議會角色衰退與主權喪失。克魯希指:
當代政治中民主的衰退,主要歸因於企業與幾乎所有其他群體之間的利益失衡。這失衡伴隨着無可避免的民主消退,使政治再次變成前民主時代中封閉精英的事務。(註2)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亦曾使用此一詞彙。他如此定義:
後民主是民主的管治實踐和概念合法化,這民主求諸民眾(demos),消除人民的顯現(appearance)、錯算(miscount)與爭執,因而被還原為僅是國家機制和社會能量與利益各種組合的相互作用。(註3)
我對上述兩個定義並無異議,但我使用此一詞彙的意思略有不同。透過對自由主義民主性質的反思,我期望凸顯新自由主義的另一種特質。眾所皆知,「民主」的詞源來自希臘語的demos/kratos,意即「人民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eople)。然而,當我們在歐洲談及「民主」時,所指的卻是一種特定的模式。這種西方模式來自於特定歷史脈絡中所銘刻的民主原則。這種模式有許多不同的名字:代議民主、憲政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多元民主。
不論定名何為,問題都在於由兩個不同傳統接合而成的政體。一種傳統是政治自由主義傳統,強調法治、權力分立、保障個人自由;另一種則是民主政治傳統,其中心思想是平等與人民主權。這兩種傳統之間並無必然關係,只有或然(contingent)的歷史接合。正如 C.B.麥克佛森(C. B. Macpherson)所示,這一接合源於自由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聯手對抗君主專制(absolutism)體系。(註4)
有些作者——像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聲稱,因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相互悖逆,這種接合模式製造出不可能成功的體系。另一些則沿襲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觀點,堅持自由與平等原則的「共生」(co-originality)關係。施密特正確地指出,自由主義的「文法」與民主平等的「文法」之間存在衝突,因為前者假定普遍性與參照「人性」(humanity),後者則劃出「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疆界,建構出人民(people)的概念。然而我認為,施密特誤將「我們」與「他們」的衝突,描述為導致多元自由主義民主走向自我毀滅的矛盾。
在《民主悖論》(The Democratic Paradox)一書中,我設想將兩個最終無法融合的傳統接合到一套悖論式配置中,亦即張力的軌跡(the locus of a tension)。這軌跡將自由主義民主的特質定義為「理想國 」(politeia)——一種保證多元性的政治共同體形式。(註5)建構人民和捍衛平等主義的民主邏輯對定義民眾、逆轉自由主義論述中抽象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傾向尤為重要。而將民主邏輯與自由主義邏輯接合,則有助挑戰其中的排他性──內在於政治實踐的排他性決定哪種人民獲得管治權。
民主自由主義政治包含的,就是在上述構組張力中,不同統識配置(hegemonic configurations)持續不斷的協商過程。這種張力表現在左右疆界中的政治用語,透過政治勢力之間的務實協商,才得以暫時穩定。這些協商總是建立在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統識之上。回望自由主義民主發展史,我們可見自由主義邏輯與民主邏輯交替地佔據上風。不論如何,這兩套邏輯仍大行其道,而自由-民主體系中特有的左右翼「競勝」協商(negotiation)始終活躍地進行着。
上述的討論單純將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想像為一種政體,但是顯而易見地,這些政治制度從未能獨立於經濟系統之外。以新自由主義為例,我們處理的是一套由特殊的自由主義民主形式與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 capitalism)接合而成的社會型態。儘管我們在研究特定社會構形時須要考慮這種接合,但在分析層面上,我們亦可探討作為社會政治形式的自由-民主體系的演化,以便揭示其特徵。
自由主義與民主原則之間的競勝張力是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的組成元素,但近年由於自由主義統識橫行,這種張力被消除了,因而當下時局可被稱為「後民主」。伴隨着平等與人民主權這些民主價值的死亡,允許不同社會方案相互較勁的競勝空間消失了,公民被剝奪了行使民主權利的機會。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一詞仍掛在眾人口邊,但它已被矮化到只餘自由主義的部份,僅僅作為自由選舉與人權保障的象徵。而為自由市場護航的經濟自由主義地位則日益提升,政治自由主義的多個面向若不是被直接取消,就是被貶抑至次要地位。這就是我所說的「後民主」狀態。
在政治舞台中,藉由我在《論政治性》中提出的「後政治」——一種模糊左右翼之間政治疆界的現象——「後民主」的演變得以表現。(註6)在全球化強加的「現代化」託辭之下,社會民主政黨接受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強制命令(diktats),並接受它限制國家的介入與重新分配政策。
本來,國會與政府機構賦予公民政治決策影響力的角色,但由於上述原因,這角色的力量被大幅削弱。選舉不再提供讓人民透過傳統的「政黨政府」(parties of government)獲得真正選擇權的機會。後政治唯一容許的,是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的兩黨權力輪替。所有反對「中間共識」、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外別無選擇」教條的人,均被打為「極端分子」或不入流的「民粹主義者」。
政治因此變成純粹是管理現有秩序的議題,一個專屬於專家的範疇,人民主權被宣稱為陳腐無用。後政治取消了不同社會方案之間對抗競勝的空間,而這卻是實行人民主權必須的條件,民主理想的重要象徵支柱之一——人民的權力——因而遭受破壞。
要理解後民主狀態的成因,除後政治外,我們還要討論另一政治動向——就是在西歐社會日盛的「寡頭化」(oligarchization)。
要理解後民主狀態的成因,除後政治外,我們還要討論另一政治動向——就是在西歐社會日盛的「寡頭化」(oligarchization)。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出現新的調控形式,牽引着政治層面的改變。伴隨着經濟金融化,金融產業大幅擴展,生產式經濟(productive economy)則被犧牲。這是近年有目共睹的不公問題日益嚴重的原因。
私有化與放鬆管制政策使工人生活狀況急劇惡化。加上去工業化、推廣科技變革與工業遷至廉價勞動力國家等趨勢的複合影響,工人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
2008年經濟危機後實施的緊縮政策,使大部份的中產階層受上述情況影響,他們亦難逃貧窮化(pauperization)與就業不穩化(precarization)的社會趨勢。因此,寡頭化導致另一根民主理想支柱——捍衛平等——同樣從自由-民主的論述中被剔除。現在掌控主導權的,是頌揚消費社會與市場所提供的自由之個人主義式自由主義觀點。
要理解「民粹接點」,就要將之放回剝蝕人民主權與平等兩項民主理想的後民主脈絡之中。
要理解「民粹接點」,就要將之放回剝蝕人民主權與平等兩項民主理想的後民主脈絡之中。它的特點是各式抵制運動百花齊放,它們反抗的是一套被精英操控的社經系統,這群精英對社會其他群體的訴求充耳不聞。起初,大部份針對後民主共識的政治抗爭來自右翼。1990年代,右翼民粹政黨如奧地利的「奧地利自由黨」(FPÖ)和法國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開始宣稱他們的目標是將被精英奪去的話語權重新交回「人民」手上。他們透過在「人民」與「政治建制」之間劃出疆界,成功將自覺被排除在主流共識外的民眾訴求,轉譯成國族主義的語言。
譬如說,約爾格.海德爾(Jörg Haider)就是如此把奧地利自由黨改造成對抗「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的反對黨。他透過動員人民主權的議題,成功地將日益高漲的反對聲音與精英聯手治國妨礙真正民主辯論這情況掛鉤。(註7)
這一政治局面,早在一系列反全球化運動中展現出左翼基進化的跡象,卻於 2011年大幅改變。其時緊縮政策開始影響廣泛階層的人的生活,數個歐洲國家發生了多場重要的民眾抗議,後政治共識開始崩解。希臘的「憤怒的公民」(Kínima Aganaktisménon-Politón)與西班牙「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的M15(May 15) 佔領中央廣場,高呼「即時民主!」(Democracy Now!),隨之而來的是在美國誕生的佔領運動,此運動後來亦在歐洲多個城市爆發,尤以倫敦和法蘭克福為甚。新近的運動有2016年法國的「不眠之夜」(Nuit Debout),它正可歸類為「廣場運動」的抗爭形式。
這些抗議象徵着社會經歷多年相對的政治冷感後的政治覺醒。可惜,這些橫向主義式運動(horizontalist movements)拒絕與政治體制交手,限制了自己行動的影響力。它們由於未與體制政治作任何形式的接合,很快就失去動力。雖然這些抗議運動肯定在政治意識轉化上發揮一定作用,但唯有緊接着有組織的政治運動、做好參與政治體制的準備,這些行動才能取得關鍵的成果。
在希臘與西班牙,我們目睹了首批以民粹形式開展、旨在恢復和深化民主制度的政治運動。在希臘,基進左翼聯盟(Syriza)的出現,象徵着旨在以議會政治挑戰新自由主義統識的新型基進政黨的冒起。該聯盟是社會聯合陣線,誕生自以前歐洲共產主義政黨「運動和生態左翼聯盟」(Synaspismos)為主的左翼運動連合。透過建立社運與政黨政治的協同效應,基進左翼聯盟成功在集體意識上接合一系列民主訴求,進而於2015年1月成功上台。
可惜的是,歐盟以「金融政變」(financial coup)粗暴地回應基進左翼聯盟的訴求,並強迫該黨接受三頭馬車(Troika,按:指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強制命令,基進左翼聯盟未能實施其反緊縮政策。這結果並不等於幫助該政黨上台的民粹策略無濟於事,反而指出了一個重要議題:歐盟成員國要施行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依然備受限制。
在西班牙,「我們能」(Podemos)之所以能在2014年平地一聲雷地冒出勢頭,有賴一群年輕學者善用「憤怒者運動」開闢的空間。他們藉此發起了一場旨在打破共識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僵局的政黨運動——共識政治是藉由向現已氣竭形枯的民主政治靠攏而建立起來。「我們能」的策略是在「建制精英」( la ‘casta’)與「人民」之間建立疆界,創造民眾的集體意志。此策略雖未能把右翼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趕出政府,但「我們能」的成員卻能藉此走入議會,罷黜了一群重要的國會議員。從此,他們成為了足以撼動西班牙的政治力量,深遠地改變了西班牙的政治面貌。
類似的發展在其他國家亦有出現:德國的左翼黨(Die Linke)、葡萄牙的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與法國由莊-洛.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創立的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其中,創辦僅一年的不屈法國於2017年6月便在議會奪得十七席,成為現時反伊曼努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政府的主要勢力。最後,同樣在2017年6月,英國工黨在郝爾彬(Jeremy Corbyn)領導下獲得出人意表的好成績,是為新型基進主義在歐洲部份國家興起的又一信號。
社會民主黨派雖在許多國家擔任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旗手,卻無法掌握民粹接點的性質,無力應對它代表的挑戰。他們是自身後政治教條的囚徒,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無法辨識許多由右翼民粹政黨接合的訴求實屬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必須給予切實可行的回應方為上計。這些訴求多數來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主要輸家,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方案不可能令他們遂心如意。
社會民主黨派雖在許多國家擔任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旗手,卻無法掌握民粹接點的性質,無力應對它代表的挑戰。他們是自身後政治教條的囚徒,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無法辨識許多由右翼民粹政黨接合的訴求實屬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必須給予切實可行的回應方為上計。
將右翼民粹政黨歸類為「極右」或「新法西斯」,將其魅力歸因於民眾缺乏教育,這些處理手法對中間左翼勢力而言當然十分方便——如此便可輕而易舉地剝奪右翼民粹接點的存在意義,不需承認中間左翼自己在此事上的責任。透過建立一條「道德」疆界,將「極端分子」排除於民主辯論之外,這些「良好民主派」相信如此就能阻止「非理性」的激情抬頭。這種妖魔化兩黨共識之「敵人」的策略,或能夠令人在道德層面上心感寬慰,但就政治層面而言卻是消極自弱的(disempowering)。
我們應當透過左翼民粹主義運動,連結所有對抗後民主現狀的民主抗爭,為制止右翼民粹政黨抬頭,設計一套適宜的政治答案。我們不應該先驗地排除投票給右翼民粹政黨的民眾,指他們被原始狂熱操控,譴責他們永遠被囚於狂熱當中。反之,我們應當辨識到他們的眾多訴求皆源於民主的內核。
左翼民粹的進路應當嘗試提供一套不同的語言,將那些訴求導向更平等(egalitarian)的目標。這不是說包容右翼民粹政黨政治,而是不再追究投票給他們的人,因為投票的人不過是選擇能接合他們訴求的政黨。我不否認有人在右翼民粹政黨的保守價值中自覺適得其所,但我同樣深信另有一批人感到唯有這些政黨關心其困境,才成為它們的追隨者。我相信,如果有另一套語言以供選擇,許多人或能對自己的處境有不同的體會,並加入到推動革新的抗爭之中。
已有不少案例證明這套策略切實可行。例如在2017年法國立法選舉,莊—洛.梅朗雄與其他「不屈法國」的參選人如法蘭索瓦.胡凡(François Ruffin)就成功贏取曾票投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選民支持。好些選民受民族陣線引導,將他們匱乏的苦況歸咎於外來移民;社運份子(activists)透過辯論,成功改變這些選民表達情緒的仇外語言,引導他們以另一套詞彙,闡釋自覺被遺棄的感傷和在民主制度內獲認同的渴望,將悲憤對準另一個敵人。類似的情況亦曾在2017年6月的英國選舉發生,當時16%的右翼民粹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選民選擇轉投郝爾彬一票。
現在,進步政黨同樣提出反建制的論述,左翼政治力量正在「人民」與「寡頭」之間劃出疆界——我們確然處於「民粹接點」之中。在這關鍵的接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接合抵制後民主狀態的運動,思考如何建構「人民」。達到上述目標的方法林林總總。然而,即便民粹主義以權力歸於人民之名拒絕現存的政治系統,也不代表民粹主義建構的所有政治疆界必然具有實現平等的目標。
兩種民粹主義均致力與未滿的訴求結盟,但他們採取的方法卻截然不同。其中的差異在於兩派如何構作「我們」,又如何定義敵手——即「他們」。
右翼民粹聲稱自己將奪回人民主權並恢復民主,然而這裡的主權被理解為「國族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只預留予那些真正的「國民」(nationals)。右翼民粹無視平等訴求。他們建構的「人民」排除了許多類屬的人,其中以外來移民最為常見。外來移民被視為國民身份與國家富強的威脅。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右翼民粹接合了許多抵制後民主的運動,但它不一定將人民的對手表現為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因此,將他們反後民主的舉措視為抵制新自由主義,實是誤解。他們的勝利可能帶來國族威權式的新自由主義,並以恢復民主之名,行限制民主之實。
相反,左翼民粹希望恢復、深化並擴展民主。左翼民粹策略致力將民主訴求聯繫成集體意志,從而建構「我們」——一群攜手對抗共同敵人「寡頭」的「人民」。我們須要在工人、移民、就業不穩的中產階級與其他擁有民主訴求如LGBT社群之間建設等值鏈。建設這條等值鏈旨在樹立新的統識,讓民主基進化得以開展。
參考文獻:
註1: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5).
註2: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4), p. 104.
註3: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102.
註4: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註5::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0).
註6:Chantal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05).
註7:在〈『政治的終結』與右翼民粹主義的挑戰〉(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我曾分析在約爾格.海德爾統領下的奧地利自由黨之發展。見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5), pp. 50–71.


香港警察嘅惡行去到呢個地步,警察自身同埋支持者必自食惡果,暴徒就係暴徒 暴警就係暴警,兩邊都要追究到底,特別係警察,請撫心自問 你退休後 仲要做20多年嘅普通市民的日子,你會安心兒女生活在一個冇真相冇公義的極權社會嗎?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