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據中國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7月23日的報導,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昨日(22日)深夜逝世,終年90歲。李鵬因被指有份下令武力鎮壓「八九民運」,最終釀成「六四事件」慘劇,多年來備受爭議。本文由葉劍英養女、前記者戴晴所寫,收錄在今年5月底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在1989》一書中,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鄧小平在1989》
作者:戴晴
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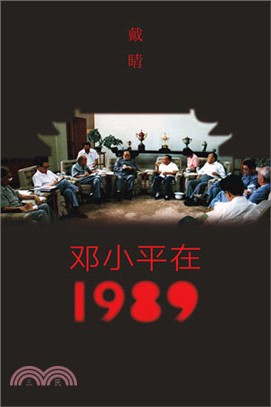
6 月3 日
凌晨,戒嚴部隊按既定計劃向警戒目標開進。北京的形勢陡然緊張起來。
午夜1 時許,市民學生有所察覺。消息傳遞到廣場。廣播站發出的呼籲,竟然是「請同學們、老師們、廣大市民們立即行動起來,到各個交通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中國「六四」真相》)
據吳仁華:
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一批批呼喊着奔赴建國門、復興門、朝陽門、永定門、宣武門、木樨地、曹各莊、車道溝、公主墳、新街口、西單、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幾十個路口,阻攔軍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
部隊這天遵奉的軍令,包括攜帶的裝備,與5 月20 至21 日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大家還記得在六裏橋,65 軍那位「兩道槓」對北大教師苑天舒怎麼說麼?這天,民眾「阻攔」的結果,可想而知——流血與死傷連連發生,雙方。
李鵬6 月3 日日記:
下午4:00 在勤政殿,由喬石召集戒嚴的緊急會議,研究天安門廣場清理問題。我和尚昆、遲浩田、李錫銘、周依冰、羅乾等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中央的同志和戒嚴部隊一致認為,當前形勢十分緊急,今天軍隊已和暴徒發生了正面衝突,不能再給他們以喘息的機會。今天如不及時採取行動,明天是星期日,將有更多的人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將更加困難。
會議決定:今晚從北京各方向集結待命的戒嚴部隊,星夜兼程向天安門進發,與已隱蔽在天安門四周的戒嚴部隊會合。工人糾察隊的引導下,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但也議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攔,造成軍隊傷亡,軍隊有權實行自衞。
李鵬的日記不同,據《真相》記載,這次會議的召集人不是喬石一人,而是「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四人。
會議由楊尚昆主持。楊尚昆做完開場白,請李鵬講話。李鵬講話的要點是點明:「從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陳希同對「反革命暴亂」的描述:
其一、武警部隊吉普車在木樨地發生重大車禍的消息,被「暴亂的組織者」所利用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進城開道車故意撞死市民,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攔解放軍進入市區執行戒嚴任務。
其二、從今天凌晨起,在建國門、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橋、南河沿、西單等幾十個主要路口都設置了路障、攔截軍車、圍困並毆打解放軍,一些軍車的輪胎被扎破,還有暴徒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受到衝擊。
接着,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作了進一步補充。他沒有使用「反革命暴亂」和「暴徒」的提法:
今天凌晨,部分戒嚴部隊奉命進赴市區執勤點。開進途中,幾乎所有的部隊都遇到了市民、學生的阻攔,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軍車,朝戰士們吐口水,我們在建國門立交橋上被圍困的一些士兵,他們的上衣被扒得精光,當眾受辱;朝陽門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軍被市民用石塊亂砸;虎坊橋着便裝進來的一支部隊,被人發現後四處追打,現在還有一些士兵不能在大會堂西側集中,隊伍整個被衝散了;被堵在南禮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強行搜身。總之,現在戒嚴部隊一些士兵忍氣吞聲,肚子裏都憋着一股氣。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癢。各部隊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釋工作,以穩定情緒。
之後,李鵬的講話利用了連陳希同、周衣冰都沒有來得及引用的「暴亂」的最新的事例,並提出了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的底線。李鵬說:
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在六部口,那些暴亂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搶我們部隊的武器裝備車,並在車頂上架起機關槍炫耀。還公然衝擊中南海西門、新華門。剛才中南海高度緊張,被迫向這些暴亂徒施放了催淚彈。所有這些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決不能讓這些暴亂分子以為政府軟弱可欺。(以上會議記錄,《八九民運史》)
關於「六部口暴徒搶劫武器裝備車」,吳稼祥的親歷是:
這天(1989 年6 月3 日)中午,我拿著飯盆去食堂打飯。剛走出樓門,被聚集在樓外的一群穿白色制服的大漢們嚇了一跳。他們正在狼吞虎嚥,我的同事們殷勤地在給他們送水打飯。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是從陝西精選來的警察【63】,個個膀大腰圓,功夫精湛。看著他們,你理解什麼叫虎狼之師。
他們來幹什麼?對付正在六部口駕着一輛麪包車的大學生們。那輛車是前一天夜裏被人開進城,車上放着一些沒有子彈的槍支,故意讓學生們攔截,製造(暴徒搶奪武器的)「暴亂」假象的。學生們果然上當,現在他們正開着那輛車,車上架着一挺機槍,(學生本意是)讓市民看官方和軍方的殘忍,(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此行為,同時為當局提供了暴徒阻擋戒嚴的畫面)。
戒嚴指揮部的目的達到了,這會兒要派陝西警察去把槍支搶回來——大漢們吃飽喝足之後,從中南海西門出去,帶著催淚彈和棍棒,一路打出去,得手後,從中南海新華門進來。我聽到的,就是發射催淚彈的聲音。(《真相在文件背後:談「天安門文件」事件》)
而李鵬在會上說:
所以,我們決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對極少數暴亂分子決不能手軟。凡妨礙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執行勤務的,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一切後果由其自己負責。」
以上諸項,就是「6 月3 日凌晨,在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的事實依據!
楊尚昆最後告訴與會者,他剛才「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
小平同志要我轉達給大家兩句話,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我們戒嚴部隊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一句是曉之以理,深明大義,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清場任務之前,要利用電視、電台各種宣傳媒體向北京的市民、學生講清楚。奉勸市民、學生千萬不要上街,留在廣場的一定要自願撤離。總之,一定要把宣傳工作做到家,要讓所有的人知道我們是對人民負責的,要千方百計盡力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
楊尚昆特別強調:
戒嚴部隊指揮部一定要向各部隊交代清楚,要儘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開槍。我在這裏特別重申,決不能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不走,我們戒嚴部隊架也要把他們架走。決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見,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們大家一致意見。(以上會議記錄,《八九民運史》)
下午,常委和軍委——所有與戒嚴有關各方面——「就嚴峻局勢緊急磋商」,制定清場堅決措施。楊尚昆傳達鄧小平的兩句話和一個意見:
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
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措施;
決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同上)
天安門廣場?南北長880 米,東西寬500 米的這一片空地兒麼? 38軍隊從西向廣場開進,沿途可以殺——殺到何種程度?
接下去,發生了什麼?
三十年來,對接下來的24 小時(以及至6 月9 日之間的六天),很多研究者包括親歷者,都給出描述。
這裏,僅引入一段當時一名現役軍官Y 的親述:
……到了6 月3 號,整個氣氛已經很不正常。
當時已經有通知下來:儘量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部隊有可能執行戒嚴什麼的,但不知道具體會是什麼時候。
軍隊的班車已經不能開了。長安街上見到軍牌車,常常會被堵住。我們那些日子上下班,都是穿便衣、騎自行車。
那天下午下班回來,我發現有軍車停在路邊,在六裏橋那個方向。我拐過去問了一下:是54 軍的車。我找了一個幹部,出示軍官證,問怎麼回事。他說「任務下了,晚上要進城。準確時間不知道。在這裏待命。」
知道有行動,我趕快回家吃過飯就又出來,站在公主墳行道樹邊上。這中間不過半個多小時,發現大街上原先縱向的隔離帶,怎麼全橫過來了──這得多少人幹哪?沿途的百姓都下手了。說「部隊要進來」,就把樁子都推到路中間,一段一段地,橫着擺。
當時,已經有軍車停在公主墳環島那邊。看車牌,是38和63 的,想開向京西賓館方向,進不去。我站在路邊,看見軍人和百姓互相扔石頭。還看見部隊開過來一輛剷車,意圖把路樁鏟開。
這時候,我看見大約100 米外,一個女的騎自行車過來,像是機關的下班的,戴眼鏡,穿着裙子,白連衣裙。我見她騎過去,跟戰士招手,居然把軍車攔下來。接着,見她把自行車停到一邊,爬上車去和當兵的說……我老遠地看着她,軍車隊停下來好一段時間。
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後邊有命令過來,讓車繼續前行。她呢,像是不讓他們走。後來……你知道,她人還在車上,但(得到前行命令的車)猛地往前衝,一下子把她甩到地下。
接着,我看見過來一堆人把她扶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摔得很重。
這時候,剷車開動,嘩嘩地剷起來。部隊車緊跟在後邊。路邊上的老百姓就往車上扔石頭──你知道,部隊的車上也是有石頭的,預先放了很多,雙方對扔。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7、8 點的樣子:天傍黑,人還看得見。
就在這時候,我聽見了槍聲——不是從天安門方向,像是翠微路、萬壽路那邊。接着西邊的車開了過來。我看見那輛首車,是63 軍軍長帶着誰……軍長和那參謀我還認識……
我在路邊呆了一個多小時。車從我身邊衝向京西賓館的時候,還有一塊石頭扔過來。但後來就開槍了,而且是連續開槍。再後來,估計車到了木樨地,槍聲就很響,也很密集了。
38 和63 是一塊兒進來的。
北京軍區這種安排,就是讓這兩個軍——這兩個軍本是死對頭──同一時間從公主墳出發向天安門開進。搶着打,打比賽一樣,誰準時到,誰立功,以殺人為比武。哪有這麼上的?
27 在石家莊,保定是38。63 在太原。
63 軍軍長,趙什麼,坐在車裏跟着第一梯隊往前衝。前邊幾十輛車,後邊就是軍長的車,比着往裏衝──兩路。
最早到是38。我看見了。38 往裏衝得最厲害。
在六裏橋,我爬上車問了,知道今晚部隊要進城,但是根本沒有想到會開槍,而且這麼肆無忌憚。因為真用不着啊!
這樣安排、指揮,楊也好、軍委也好,基本就是沒人性。你有沒有想到,夜間,如何對付赤手空拳平民?我們的野戰軍是沒有這種訓練的。
當時部隊農村兵為主,他們哪裏來的——上千公里外。北京啥樣?立交橋怎麼走?
記得當時站在公主墳往東這邊大街上,想着——我倒要看看,這是要幹什麼。最沒想到的,居然開槍了,而且是真槍實彈——說空爆彈,我一看就知道是真子彈:前面出火花,打到地上、牆上,56 式衝鋒槍呀……部隊就像打群架一樣,閉着眼睛打。所有人,裹脅而下,再有人性的戰士,你也得打了,沒法控制。
你讓他們來處置這樣的民事問題——懵頭懵腦的農村戰士,面對着一腔熱情的學生。你告訴他們你是人民子弟兵,前邊面對着的是暴徒,與對敵作戰有什麼不同?戰士知道什麼?幹部也不知道呀——當時說得很重,「維護共產黨的體制」、「境外敵對勢力」、「推翻共產黨」、「改變中國的顏色」、就和上前線打仗一樣,「表忠心」,戰士聽了,認為就是使命。
但面對的學生市民——這樣的敵人?白天,為什麼部隊停下來了?因為眼見民眾在勸,對方不是壞人,怎麼能開槍? 到了晚上,農村兵,腦袋被扔過來的石頭砸了,你給他槍,讓他開,他會怎麼樣?打架的時候,誰拿着槍都會開。子彈射出去,都不知道傷的是誰。
我聽得很清楚:在公主墳,砰砰幾槍;從京西賓館那邊過來;到木樨地,槍聲密集。再聽,怎麼太平路、翠微路、萬壽路、永定路、五棵松這邊,也響起槍聲。怎麼南邊,也響槍了。
我知道全面打了——非常嚴重。我轉身回家,立刻就給一位老帥家裏打了個電話,把剛看到的都說了:部隊今晚進城,而且,開槍了!打死人了!你們出來看一眼,不要錯過這個歷史機會,做一個自己的判斷,會永遠記在心裏。
打電話之前,我看到海軍司令、副司令們,穿着便衣,都到路邊去看了現場。
著者曾多方向職業軍人請教:你們覺得,「不計一切代價」命令,誰發的? 6 月3 日晚上麼?
他們只能按經驗推測,綜合起來,當年軍人的大致印象是:
通常沒有文字命令,就是電話通知,「請示電話通知」,誰也不發文字命令,一級級傳下去。
各軍區、軍,他們這樣說:軍委就說「幾月幾號出發,什麼方向,幾點幾分,到達天安門廣場」。接着,就給各軍布置了。
到軍一級,可以再加碼,各軍各師團自己下達的命令就是這樣的。
前線執行任務的戒嚴部隊士兵又是什麼狀態呢?一位某軍的軍人:
晚上(6 月3 日)……我們坐在卡車上待命。整整一個白天,沒吃沒喝。到晚上10 點了,還堵在那兒(木樨地一帶),走不了。那次給下的死命令,是12 點到達廣場,否則軍法處置。
正着急,見有人從22 號樓,用小口徑步槍向他們射擊。這第一槍,並不是我們解放軍先打的。然後,我嚷了一聲:抄傢伙!接着跳下車,朝天開槍,這是我打的第一槍。
車上兵也跟着下來,先往地下打,從地下反彈的子彈,打到了圍觀的人群。這時有人喊:別怕,解放軍用的是橡皮子彈。於是,市民繼續圍着,阻攔前行。
實在沒辦法了,只好橫掃。但也不是連續不斷地掃。因為前邊有人中槍,見血了,後邊的人就散開了。到這時候,我們根本就沒再上車,而是朝前跑(朝天安門廣場)。只要槍擊一停,人群就又湧上來──北京老百姓就不怕死!後邊人不知道,還以為是橡皮子彈。我們只好重複地開槍:朝天、朝地、橫掃。真的不想傷人,只想警示,結果……沒辦法呀……就這麼停停跑跑,終於到了廣場。
到廣場之後,才見到團長呀什麼的,都出來了,部署誰誰在哪……這才知道,到這裏的,不光我們軍,而是每個軍抽調一個團。然後集合,宣布紀律:廣場(即欄杆圍起來的)內,絕對不許開槍。誰開槍誰違反紀律。但是廣場外邊,比如馬路上,不屬於廣場。馬路上,要是誰阻擋清場,就可以朝他們開槍。
一到廣場,最迫切是憋尿——朝着金水河就撒。就在這時候,人大會堂的北門、東門突然大開,軍人潮水般地從裏邊湧出來。咔咔咔前行,推倒一切障礙。這時候,聽見侯德健他們在喊;看見他們過來談判;看見東門出來的兵砰砰槍擊高音喇叭……
廣場本來滅了燈,這時突然嚓的一下亮了——開始清場。這個時候,要是有阻擋,是會開槍的。但自己很注意:在廣場過馬路的時候,想着:我不能打死人。也是在這時候,我突然悟出,(今晚將傷人死人)是有準備的。因為,就在這同時,從天安門兩邊的過街地道里,上來好多穿白大褂的,要是有人受傷直接就搶救。所以這裏是有準備的。
開始清場。確確實實,在天安門廣場內,沒有屍體。帳篷,基本上也都是空的,人已經撤了,從廣場南側,都撤走了。到天矇矇亮的時候,基本上清完了。
這時,命令我們「從西邊進來的」,全部進入中山公園。真正恐怖的,是在中山公園。
到了公園裏,已是極度疲勞:一天一夜沒睡了,人好像不知昨天干了什麼,有些人有點精神錯亂,拿着槍掃射起來。好些戰士就是在這時候被自己人打死。當官的急了,立刻朝天開槍,同時命令「把槍放下」,全體繳械。
在中山公園裏死多少?根本不知道。後來就是繳械。
在六月三日下午的會議上,至少有多名決策者提到了侯德健等四人的絕食,沒有人想到他們將在關鍵時刻起到的關鍵作用。
晚10:00,各路部隊奉命開進……
這天,曹思源、高瑜被抓捕。他們一直在分別運作人大常委會提前召開。民間法學家曹思源遵循的宗旨:「開會總比開槍好。」
長安街上、天安門的平民又看到了什麼呢?當時的軍報記者江林決定無論如何要去看看:
我想知道,我們穿軍裝的軍人們是如何舉起槍射向自己的同胞的;我想知道,我的同胞看着他們的子弟向着自己射擊,內心深處湧動着的是什麼情感?我想成為這次重大事件的目擊者,向我的讀者報告他們最關心的事實。我出門走向街頭,是沒有任何猶豫的。因為我是記者。
我告訴了張勝。他說,那我就跟你一塊去吧。他一說,劉含妮(妻子)也說要去;他兒子小亮也要去。我們四個人,騎上他們家的自行車……
先到木樨地看了開槍的慘狀,然後我們沿長安街一路過西單、六部口,想從西華門那邊進到午門……
還沒走進去,就被一群手執高壓電警棍的武裝軍人擋在東西華門之間的公共通道上……
他們揮棍就打,先擊中我的背部,一股強大的電流和刺痛把我打倒在十幾米外的空地上,緊接着第二棍,第三棍……我至今清醒地記的,那種痛,是非人能忍受的。不遠處,一個行人被打得慘叫起來,我從未聽過這樣的叫聲,這是一種死亡前絕望的聲音。
當時,我只要說明身份,就可以免遭毒打。可是,我沒有吭聲,準確地說,已經沒有這樣的想法。在目擊了復興路到西單的慘景後,我已經把自己開除出「軍隊」——我已經不是軍人,也不是軍報的記者。
我就是西單路口的市民,就是廣場上的學生。
我從地上爬起來,還沒站穩,軍警又追上來,不容分說,揮棍就打,他們瘋了!這個社會瘋了!
在日後的審查中,清查組的人推斷出我的被打傷,一定是罵了人,或參與了什麼活動。其實,我沒那麼勇敢,不過是咬緊牙關,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捱打,也比同流合污好。
我被追打着到了午門。由北向南的第一個照明燈下,我感到頭上左邊一股熱血往上湧,天昏地暗,「我要死了!」我大叫着倒了下去。
有人夾住我往外拖。張勝……又有軍警過來了,他們又舉起了警棍。我聽見張勝說:「別打了,她已經給打死了。」那些人叫着:「就是要打死你們這些人,誰讓你們聽到『通告』還不
走。不打她,打你!」
張勝繼續拖着我,終於,被拖出了午門。他扶着我,問:「怎麼樣,傷到哪了?能走嗎?」我吃力地搖搖頭。他說:「你趴在我肩膀上,我把你揹出去。」誰知,剛靠近他的背,他自己也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說:「你也受傷了吧?」他說:「沒事,再來一次。」我小心地趴到他背上,聽見他大聲地喘着氣。
不知是鼓勵我,還是鼓勵他自己,他反覆說:「能出來就好,哪怕有一個人活着也好。」
我頭上的血往下流,把他的汗衫染紅了。
他把我背到東華門口,自己趴在一個鐵柵欄上,大口地喘着氣,之後說:「好像肋骨被打斷了。」我勸他趕緊離開這裏,萬一那些軍警們回來,我們會喪命的。他伏在柵欄上,用低得只有自己才能聽得見的聲音說:「兒子和妻子都在裏面,我怎麼能走?」
天安門廣場方向,槍聲鞭炮似的密集。這時,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見我滿臉是血,上來攙扶我,要送我去醫院。我聲嘶力竭地拉着張勝:「我不離開你,我要和你一起去醫院,你也受傷了,也是重傷。」他直起身來,對那個年輕人說:「我不要緊,我還要進去找我兒子和妻子。拜託你了,一定把她送到醫院。」
這時又來了一位騎自行車的陌生人,他讓小夥子把我放在他的車座,騎車送我去。我頭昏目眩,根本坐不住,小夥子決定由他在後面扶着我,陌生人推着車,兩人一邊跑,一邊大聲喊:「有人受傷了,快叫出租車!」。
在東華門出租汽車站,只有車而沒有司機,還有一些外國人,他們被我的樣子驚呆了,「是中國人,她是中國人!」一個男人喊着:「快用手壓住頸動脈,否則血會流乾的!」他們攔住了一輛剛剛發動的小汽車:「有傷員,請你們停下來!」車門打開,一車的金髮碧眼。我認出來,這是在午門遇到的外國同行。他們見有傷員,不由分說,立即開動,把我們送往協和醫院。
協和醫院門口,一輛公共汽車堵在門口,我們的車停在旁邊的岔路上。那位挎相機的外國同行打開車門,扶我下車。只見從那輛公共汽車上跳下來一位老大爺,他淚流滿面的喊:「醫生們,快來救我車上的人,他們全是被槍打中的,死的死,傷的傷,快救救他們吧!」協和醫院門口跑出數十個身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撞到了那位外國女記者,照相機掉在水泥地上,我看到馬達和機身分裂了,我想幫她拿,小夥子不讓,架着我往裏跑,我回過頭來問:「你是哪個國家的?」小夥子急了:「都什麼時候了,命要緊,快走吧!」「你快走,我們還要去發稿。」女記者說着消失了。
幾天後,當我頭纏紗布躺在床上,看到一本朋友送來的《參考消息》,上面刊登:「我們的記者救了一名中國姑娘」。
看到這條消息,我哭了,我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普通公民,而不是中國記者。因為我再也無法把自己看到的所見所聞報告給外界了。我所目睹的一切都成了「反革命謠言」。所有的輿論工具都在反覆刊登和播放由「戒嚴部隊新聞處」提供的「新聞」材料。
對著者講述的軍官記得,他是在第二天接到張勝電話的:「小亮——」張勝說,「人丟了,幫我找啊。」自己的事,他不便出面……畢竟涉及黨內鬥爭。他爸剛寫了信,你孩子又丟了。宣揚出去……我趕緊聯繫北京軍區/ 戒嚴指揮部;他那邊是通過軍委辦公廳,還有北京市公安局……幾條渠道。兩天之後才找到。張小亮,小手指頭都打斷了,也是咬死了什麼都不說。
6 月4 日
子時,各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連續廣播。廣場上十多萬市民學生,剩下數千名。
醜時,6 月2 日參與絕食的四君子,在紅十字會醫生陪同下,出面與金水橋邊的部隊談判。38 軍112 師336 團政委季興國上校出面接應,許諾立刻報告。
正在此刻,「準備清場」時間(4 時)到。廣場上燈光關閉。
數分鐘後,有新的命令下達——雙方決議達成:留出廣場東南口,儘快帶領人群撤出。軍隊在限定時間內不開槍。此突發情況,依照38軍序列,直報到天安門指揮部,羅幹從天安門指揮部跑到中南海。李鵬、喬石和楊尚昆當即做出決策。
廣場的地面上,沒有形成如柴玲所「期盼」的血流成河,而是不折不扣執行按照鄧、楊的部署,真的沒有死一個人。
但事實是,即使在已經清場、學生撤離之後,還在流血。一名大學教師的講述:
6 月3 日深夜,學校派車接回一車(或本校、或外校,總歸是廣場的)同學後,該校一名共青團幹部……同車的團委副書記說,「不行,我還得去一趟。」說完自己轉身就去了。第二天(6 月4 日)早晨,我在校門接到他:一臉的驚恐。
我問怎麼了?他說,本想到廣場看看還有沒有學生。到西單,看見的,全是新的戒嚴部隊,新進來的」……他沒再往廣場那邊走,站在西單路口朝學生喊:「都跟我回去!往學校跑!」
好多學生跟着他跑。跑到西四那兒,聽見後邊跟着打槍了!聽見後邊「通」的一聲。跟在我身後的一個女學生說:老師,後邊有人倒了。他頭也沒回的喊:什麼也別管,自己趕緊跑。女生說:不行,我得救他呀……那學生一回身,砰,又是一槍……他回過頭,親眼看見那女學生要去救那倒下的男生的時候,又一發子彈過來……
這名團委書記說:無論如何我得走了。他說:我絕不在這個國家待着了。實在受不了了。怎麼能這樣!?
過了兩天,他真走了——到澳大利亞去了。
徐勤先將軍,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早在決策剛剛形成、命令剛剛下達時所預料的,終於難於避免。
寅時,「戒嚴部隊一舉完成了清理天安門廣場的任務。被動亂分子佔領長達40 余天之久的天安門廣場終於回到人民的懷抱。」(《李鵬「六四」日記》)
「人民」——新華門影壁上那金光閃閃的大字麼?
但是,人民確是有的——五十天來,從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身上,我們真切地看到了何謂赤子蒼生、何謂禮失求諸於野。
連拉帶拽、帶呵斥、帶懇求,周舵帶着傷(非槍擊而是棒戳——這又是什麼武器?),從廣場東南口、到新文化街、到六部口,一路連勸帶罵,最後隨撤出人群來到西單路口。25 年過去,這位温煦君子面對著者鏡頭述說這段經歷……說到這裏,竟哽咽着語不成聲——「滿地狼藉啊:衣服、鞋子、自行車、血跡……但沿街櫥窗,不見絲毫破損」——他站在那裏,呆住了。北京沒壞人?小偷呢,盜匪呢,都罷工了?
四十年來,毛共口中的「人民」、「群眾」,繳納貢賦、下工地幹活、上戰場賣命……如此而已!而這五十天,他們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好青年好孩子們、為了未來與正義,似乎是,胸中激盪着的一股凜然之氣,往日間小小的妒忌、猥瑣、貪婪……似乎是,在一個新的、幾近全民對未來的呼喊中,一掃而光——自己真正看得起自己了!
自尊,基於對正義、對自身權利切實認可的自尊——這,鄧小平,孜孜於「大權不可旁落」鐵腕專權的鄧小平,你知道麼?
這裏,再為讀史人加進的兩個小花絮。
一是6 月4 日上午,著者在家中接到的一個電話,一個當年發小、彼時現役軍官打過來的電話。
我拿起話筒。對方遲疑了一會兒,說,「我,XH。」
我驚問:「XH,你……在哪兒啊?」
他答:「武警總值班室。」
我朝話筒喊起來:「你們乾的什麼呀!!」
XH 只說了一句:「鄧小平讓乾的」。
再一個,為讀者補入一點開槍後的餘緒:
友人YL,大約在6 月5、6 號(或者9 號以後)吧,突然接到李先念兒媳電話,請YL 到她家坐坐。她與YL 算是認識,但並非知交,也不常走動。幾句天氣之類閒話後,主人不鹹不淡地說:6 月3 號那天夜裏,爸爸被槍聲驚醒,叫起秘書。秘書也不知怎麼回事。爸爸讓他聯絡陳雲那邊,問陳爸爸知道嗎。秘書立辦。沒多久秘書報告——陳處答覆說:陳爸爸那邊也聽到了,不知怎麼回事。
YL 說,不知道聽到槍聲、打電話問云云是真是假。也不知她叫他過去說這一番話什麼意思,除了本著者,YL 也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提過此節。
而真有其事的是後發的戒嚴部隊,在這天早晨:
7 時許,數以萬計的民眾將28 集團軍的車隊堵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民眾向官兵們宣講屠殺情景,官兵們起初不相信,有民眾從附近的郵電醫院拿來血衣展示,官兵們軍心浮動。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帶頭消極抗命,不顧中央軍委派來直升機在上空下達的強行進軍命令,最後棄車而去。
該集團軍包括31 輛裝甲車、2 輛電台通訊車在內的74 輛車被燒燬。(《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
這天,依照代表中央主管黨報王維澄(李先念前秘書)之安排,出現在《人民日報》一版的,是轉發《解放軍報》社論——標題:《堅決擁護黨中央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開篇第一句:
自6 月3 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人民日報》值班總編輯陸超祺問:暴亂髮生,怎麼不見政府(包括國務院、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電台、電視台向人民宣布,而要在一天之後,由軍報發社論宣布?
這篇斷言6 月3 日凌晨發生嚴重反革命暴亂的文字,是從哪裏、又是怎麼來的?
《人民日報》自從4 月26 日發表社論之後,此後的四十多天裏,公開發布的官方(正面)意見,只有消息、講話、報導,直到6 月16 日,也就是在鄧小平的6 月9 日講話(新華社消息)兩週之後了,《人民日報》社論才第二次出現——《統一全黨思想的綱領性文件》。在這五十多天裏,不僅《人民日報》,其他報紙一概沒有動靜。
到了6 月4 日。這天,《解放軍報》推出通欄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怎麼回事?
前一天晚上,在軍報辦公室值夜班林冬,收到一紙文字——來人語氣決斷:「社論。立刻發。」
林冬瞟了一眼標題。強壓住內心悲憤的湧動,對來人說:「作為社論發表,必須有人簽字。否則不行。」來人楞了片刻,見這小值班員語氣毋庸置疑,抓起文稿,返身走了。沒多久,社論稿再次送達。簽發人(唯一):楊白冰。
林冬說,社論在他手裏壓了兩個小時。楊白冰非常生氣。
6 月5 日
這天,據吳仁華:
戒嚴部隊僅控制了天安門區域,以及東長安街天安門城樓至建國門立交橋路段、西長安街天安門城樓至復興門立交橋路段。20、24、27、38、63、65 集團軍、空降兵15 軍、北京軍區炮兵14 師、天津警備區坦克1 師等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區域。(《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
戒嚴部隊擁擠在廣場區域,情況混亂,楊尚昆說:「若有一個班部隊譁變,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昨日緊急將鄧小平嫡系部隊、南京軍區的12 集團軍空運進京,作為督戰隊。12 集團軍在國共內戰時期隸屬第二野戰軍,鄧小平任二野政委。
李鵬擔心戒嚴部隊面對北京各界民眾的普遍抗議而士氣低落,凌晨1 時,與王震一起到人民大會堂看望部隊官兵,為他們打氣。
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情緒十分緊張,要求成立北京市區級戒嚴指揮部,實行區自為戰,保衞廣大居民和機關的安全。辦法是以區委和政府為主,同時配備一定數量的戒嚴部隊,加以配合。李鵬同意李錫銘的意見,並通知戒嚴指揮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
《李鵬「六四」日記》記載:發動在京機關為部隊送主食,戰士食宿雖已有安排,但沒有蔬菜吃。幾萬官兵都擠在大會堂各大廳內地板上睡,特別是廁所不夠,大小便困難,室內空氣污濁,如不迅速解決,部隊難以為繼。
李鵬等認為,目前至關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門各方的交通幹線,保證部隊給養暢通。於是,天津坦克1 師和38 軍坦克6 師,多次奉命出動,武裝押送戒嚴部隊的給養車隊。
於是這天上午,在長安街上,一列坦克車隊由西向東駛去。30 年來,作為中國人抗暴的典範,一直在全世界傳布的「坦克人」(至今不知他是誰,也不知他後來的下落),就站在這列坦克前邊。
著者有幸採訪到一位現場目擊者、當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教師、不肯放棄任何精彩鏡頭的攝影迷王歐。下邊是他的講述:
6 月5 日早晨,我騎車從家裏出來,往南騎,在軍委兩棟大樓那兒,右轉,上了北長街。從南長街出來,沿着長安街朝東,這時候……
在公安部門口,我看見街面上有新鮮的血跡,兩攤——不像是前兩天留下的,那已經發黑了。是新鮮的血……
過公安部,往東跑,翻過一個鐵欄杆,到了北京市委那一帶。我們一群人站在正義路臨長安街的路口。旁邊還有幾個人,但都不認得。
這時候,聽見一陣坦克車駛過來轟轟轟的聲音。
就在這時候,看見了坦克人。
他在坦克前邊,不是十多米,不是兩三米,好像還要近。我看見他小步左挪右挪。
(坦克人爬上坦克的場面,敘述人不記得了。)
後來又過來幾個人。大家看着他,都特緊張。
有個騎自行車的,就過去把他拉過來了——跑着,拉到我們這邊的圈子來了,拉到正義路,靠東單這邊的路口。
這人看上去不像學生,也不像北京人。個子比我矮一點(我180cm)。我朝他喊:你不要命啦?別傻了,坦克……要死也不能這麼死啊!你還可以做點事兒的啊!
他什麼都沒說,臉色煞白,懵懵的樣子——就是特別茫然那種神情——也不一定是茫然,就是經歷生死那一刻、驚魂未定那種感覺。
他也沒回答,時間很短。就在這時候,我們正說着,看見坦克車裏的軍人出來,端着槍,滴溜滴溜沿着牆,慢慢往這邊走,槍口正對着我們這邊。
我們當時也沒害怕,因為剛剛看到,「坦克人」想死它都沒壓,我們不過在旁邊看,應該也沒什麼事兒。我們還在那說……(從坦克裏邊出來的人,向我們這邊)走到離我們差不多20 米的時候,端起槍,突然掃射了。
掃射,在白天,子彈射出是看不見的,就聽到打到旁邊的草裏嗖嗖的。我認為在當時,那幾個解放軍沒打算打死我們。他如果朝人掃射的話,我們不給打死也會受傷。他就是嚇唬我們。
他還是很有準兒的,那個槍。我們沒什麼事,但沒有選擇,大家轉過頭,撒丫子就跑……跑的方向、快慢,誰也不掌握……就是跑。當時年輕,我也就三十多歲吧,一口氣就竄出好幾百米。我記得還拉了一個女的一塊兒跑……但是,「坦克人」在哪裏,已經不知道了。再也沒見到他……後邊的事都不記得了。
在此採訪基礎上,著者曾就「專業訓練之便衣」、「手語」等說法,請教相應領域人士。他們認為,這些,都屬於臆想:
當時無論警方軍方,絕對沒有可能預知、布崗並且策劃。別說北京市局,就是劉華清,他都因為得不到具體及時的報告心裏沒底,竟然讓他的保健醫生騎上自行車到廣場看,回來跟他說。
結束了,「鎮壓反革命暴亂」?
6 月6 日
下午,「反革命暴亂」平息之後第一次六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會議,在西山舉行。鄧小平再談「四項基本原則」,再談「穩定壓倒一切」。
在這次會上,確定了6 月19 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和緊接着(6月21–3 日)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再走一趟中共自延安定盤以來,粉飾規則的過場,以合法方式認定非法幹下的事情。
江澤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發表。——讕言歸讕言,國人受到十足威懾。
6 月8 日
下午,通過鄧辦,李鵬把三天以來的情況和目前採取的措施都詳細報告了鄧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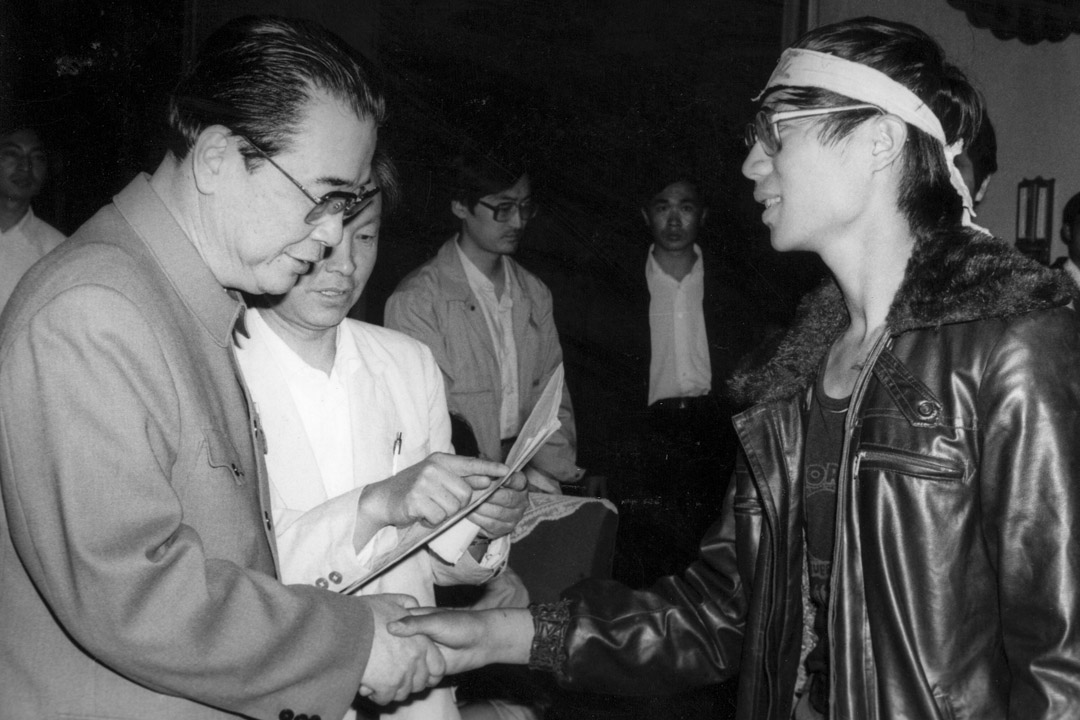




这书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戴晴这文章真棒👍
戴晴好样的
@李理 也带来了官商勾结,新封建主义思维,害人不浅
如是大陆的人应感谢李老和邓老,老革命家维护了新中国完整,带来了改革开放。
历史功过后人自会评价
好久都没听到像这样的好消息了
只能说可喜可贺
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