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母語不是中文的人而言,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發音有些困難。「用荷蘭語發的話是 hwah-way 對嗎?我說錯了嗎?」「Wah-wah?中國?」幾年前的一個網絡視頻裏,剛剛受到華為贊助的一支新西蘭球隊,正讓球員、教練和球迷手持印有華為商標的隊服,反復練習「Huawei」的咬字。除了在2016年以600萬歐元天價簽下足壇巨星梅西為代言人,近些年,這家中國企業贊助的世界球隊名單已經很長:在歐洲,就有AC米蘭,巴黎聖日耳曼,阿森納等等,還有2018年世界盃主辦國俄羅斯的國家隊。
這些笑嘻嘻嚼字眼的球員可能不知道,他們蹩腳發出的「華為」二字,取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多年前在牆頭看到的標語:「中華有為」。華為創立自1987年,位列中國民營企業之首已久。在中國,從任正非的軍人背景到廣告語「您手中的世界500強」,都是華為作為「國產品牌驕傲」的標誌。華為的國際化志向,也與中國政府在千禧年前提出的「走出去」海外投資戰略緊緊相扣。在2012年的一個座談會上,任正非說,華為的國際化戰略布局,「唯一覺得困難的是美國,別的國家沒有困難。」
的確,以結果論,華為在國際市場的征程已有明顯傾斜:相比美國,華為在歐洲的成功顯得尤為突出。2017年,華為在芬蘭、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等國的出貨量已超過蘋果。歐洲已是華為最重要的國際市場。但在大西洋另一端,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2012年一份措辭嚴厲的調查,直指華為和中國國企中興通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市場自此成為華為難以啃下的骨頭。
「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讓人擔憂……華為的企圖到底是嚴格意義上商業性的,還是帶有政治性質?」
華為的中國 DNA 是美國公部門抵制其進入美國市場的主要原因。直接面向外國立法者和行政者的「高層關係」是華為「走出去」後,不得不面臨的挑戰。華為在美國多年的努力不見效果,2018年4月,這家企業消減了在美國的遊說支出,在華盛頓辦事處裁員5人,其中包括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轉過頭深究華為在歐洲的表現,「高層關係」也是一條不可或缺、但鮮少提及的線索:華為到底怎樣處理與歐洲各政治中心政府的關係?
獲取信任
英國前外交和國防大臣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2013年給英國議會提供的報告裏,總結了英國對華為的疑心:「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讓人擔憂……華為的企圖到底是嚴格意義上商業性的,還是帶有政治性質?」
華為進入英國公眾的視野是在2005年前後。那一年,華為成為英國電信(BT)網絡升級項目的供應商之一。因為華為的中國背景,華為與BT的合約在英國引發爭議:啟用中國供應商是否會造成安全隱患?
2010年,英國政府與華為終於就安全問題作出一些安排,其中便包括華為在英國設立的「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華為德國分公司的副總裁和企業及公共事務總監庫佩爾(Torsten Küpper )說,這個被稱為「The Cell」(暫譯「小室」)的評估中心「像消毒隔離室,華為的產品進入英國市場前,會在這裏受到技術檢測,以確認產品沒有風險後才能在英國市場銷售。」在這裏,華為的電路板和代碼都會被「拆解」分析,檢查這些產品是否存在能被惡意利用的缺陷。
歐美政府從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對華為的商業活動提出質疑,並不難理解:在一應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依賴數據交換的今天,華為所在的通訊網絡行業,類似能源、交通產業,同屬「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理論上,電信網絡設備的供應商擁有一個「後門」,可以掌握在這些設備上流通的數據。「後門」也給經濟或政治情報刺探提供了可能。儘管華為是私營企業,為維護客戶利益理當保證數據保護。但華為來自中國。在中國,政治與商業緊密而不透明的聯繫是常態。這讓人疑心華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懷疑華為設備的安全性。

但是,要將華為拒之門外很難:一個開放的市場歡迎物美價廉的供應商。而電信行業又恰恰國際化程度極高,全球幾乎所有通訊網絡都有使用非本國的技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更是大量電子設備和元件的來源地。自2012年起,華為已是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製造商,超過瑞典的愛立信(Ericsson)和美國的思科(Cisco)。
兩相權衡,2010年11月,象徵華為與英國政府的妥協的「小室」,在離倫敦一百多公里的城市班伯里(Banbury)成立。按與英國政府的協議,「小室」為華為所有,員工工資由華為支付,但它必須經過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的背景調查才能聘請負責技術「隔離」和檢測的技術人員。
「小室」建立不久,2012年,華為再次因美國眾議院的安全調查成為頭條新聞。調查發布後,英國議會情報和安全委員會也對華為及「小室」展開評估。2013年6月,提交給英國議會的評估報告指出,小室的安全檢測功能在華為與BT要在正式簽約7年後才全面展開,故此要求英國通信總部加強監督「小室」,並建議評估中心的員工不受華為僱傭。華為的庫佩爾說,如今「小室」員工雖然收取華為的工資,但並非華為員工,而是「由政府篩選的獨立僱員,不向華為報告。」
報告提交後,英國通信總部、華為和其他政府及行業的代表一起成立針對「小室」的監督委員會。委員會2015年的報告顯示,「小室」依然僱有未達到要求的員工——「小室」僱人很難,因為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的人選極少:具備技術和商業背景,能夠通過英國通信總部所要求的「DV」調查(Developed Vetting,英國最高級的忠誠度調查,用於調查國防等部門的僱員),並且願意在小城市班伯里工作。
之後,委員會幾份報告還提到華為給小室總監每年發放獎金的做法:「扣除或獎勵獎金(不論工作表現)⋯⋯可以作為工具來激勵總監的某些行為。」不過,報告最終並不認為年終獎會帶來嚴重利益衝突。
庫佩爾強調,華為建立小室「是自願行為,而非法律義務。」對於華為而言,即便不得不面對英國方面反復的評估,「小室」依然是成功案例。它讓英國公眾看到華為願意與當地政府合作的正面形象——除了通訊基建,華為的智能手機也在進入歐洲普通人的視野,品牌的意義變得愈發重要。
不過往後看,在歐洲其他國家,華為也許不再需要「小室」這樣小心翼翼的做法了。在華為歐洲總部德國杜塞多夫的辦公大樓裏,庫佩爾不假思索地說:「我不認為它會成為範式,其他國家類似的需求並不高。」在他看來,「2010年時,人們對華為尚不熟悉,而在這些年裏,人們對華為的信任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
而庫佩爾口中的「人們」,既包含購買華為智能手機的普通消費者,也包括對華為在通訊基建領域的市場佔有率而提出質疑的政府官員和政客。「據我所知,華為是第一家在首都圈——也就是柏林、倫敦、布魯塞爾——都建有辦公室的中國公司。」庫佩爾說,「這是因為我們在學習,到這個市場一段時間後,我們必須看到,還能做什麼來促進業務發展,而不被人認為我們只是賺錢回中國的外來者。」
如果說,圍繞着「小室」的一系列安排可被視為華為「應對」來自英國政府的持續質疑,那麼,華為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和柏林等政治中心長期的遊說投入,則是在「主動」鋪就對其更為友善的大環境。
學習遊戲規則
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遊說」是一個給懂得遊戲規則的人提供的「開放賽事」。
與布魯塞爾其他提供遊說服務的公司一樣,諮詢公司「Bureau Brussels」(布魯塞爾站)在介紹核心業務時,通篇不見「遊說」字樣,而以「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專家自稱。總裁 Friso Coppes 把辦公室安在聚集歐盟核心機構的舒曼廣場,還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習福思」。在布魯塞爾遊說十多年的習福思苦笑解釋:「遊說的名聲早被毀了。我要是直接說自己是說客,可能得先解釋許久我不是黑手黨。」
「相比歐洲的汽車行業,或是美國的谷歌、亞馬遜、蘋果公司在布魯塞爾試圖改變法律措辭的『硬遊說』,華為是新來者,他們的遊說更為軟性。」
但是歐盟的日常工作不會、也無法避開來自各個利益集團的遊說活動。「遊說」常給公眾帶來政商「黑箱操作」、利益交換的負面聯想,但它卻是當代政治經濟生活的常態。以歐盟委員會為例,這裏平均每年產出近2500條法律和法規,但為這些政策服務的專職公務員人數卻極低,平均一個政策單元只有17名員工。這意味着歐委會大量依賴「業務外包」,尋找以十萬計的專家——其中很多人很多來自跨國企業,加入專業委員會,一同參與議題制定、提供解決方案,直至撰寫法律草案——這整個過程,便是「遊說」的賽場。
歐盟的官方定義中,「遊說」擁有一個的中立形象——「透過任何渠道和媒介,所有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歐盟政策的規劃或實施、以及歐盟機構的決策過程的活動」。這個定義的關鍵詞是「影響力」和「開放」,有能力的持份者都可以入場,包括公民社會和工會,但是,活躍在布魯塞爾的絕大多數說客依然為企業服務。

2017年出版的《SAGE國際企業與公共事務手冊》中,常年研究歐盟遊說的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里納斯(Rinus van Schendelen)寫道:「信奉實用主義的公共事務專業人士要……尋找最好的獲勝路徑,並且保證不會輸掉(不輸本身就是一場漂亮的勝仗)。」
回顧華為這些年的歐盟遊說事務,「不輸」也許是其入場時的預期——在2012、2013年前後,歐委會貿易委員德古特(Karel De Gucht)將對華為進行反補貼、反傾銷調查的意向時有出現。那也是華為剛剛進入布魯塞爾遊說場域的時間點。當時,華為急切的遊說嘗試還導致了一個爭議重重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事件。
「旋轉門」是常見遊說現象,有的政客或公務員在離開公職後,會帶着常年積累的人脈資源和內部信息旋轉至盈利機構。但是,高級官員的「旋轉門」常引發極高的公眾關注度,輿論通常會批評可能的利益衝突。
2013年7月,華為正式聘請在歐盟工作過三十年、前歐盟駐中國大使安博(Serge Abou)為政策顧問。據德國媒體《明鏡週刊》當時的報導,2011年7月,安博從歐委會退休不久,華為就在巴黎的一個會議上接觸到他。安博的履歷對華為極有吸引力——除了在北京擔任六年的歐盟大使,他還主持過歐盟對外關係和貿易保護事務。
當安博向歐盟委員會報批加入華為的意向時,後者要求安博不得在退休兩年內,即2012年底前,接受該職務;並要求他「不參與與歐盟委員會有關的任何遊說活動」,「不代表華為與歐盟委員會直接接觸」。根據在布魯塞爾研究歐盟遊說的非營利機構「企業歐洲觀察」(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這是歐委會第一次給退休官員提出「冷卻期」(cooling-off period)。
但是,「企業歐洲觀察」評論說,華為仍然可以獲益於安博的內部知識,並認為對如此資深的官員,歐委會應該給出永久「禁令」。《明鏡週刊》的報導更為直接:「誰能保證,擁有一連串聯繫人的安博,不會偶爾打電話給他在貿易部的老朋友?」
雖未具明原因,2014年1月,歐委會向「企業歐洲觀察」確認,安博已經退出他在私營企業中的任職。
很快,圍繞安博的爭議逐漸消散,但是華為在布魯塞爾的遊說才剛剛開始。
「軟着陸」布魯塞爾
2017年春節后不久,布魯塞爾位於皇宮附近的「Bozar」藝術中心外墻上打出了「Huawei」的標誌。
巨大的展廳被深紅色燈光佈滿,在舞台屏風背後,數名身姿綽約的舞者圍繞一尊菩薩的影子、伴著現場樂隊演奏翩翩起舞。好幾位大廚現場燒製精緻的食物,巧克力、香檳、雞尾酒源源不絕……
這是華為在布魯塞爾的新春酒會,會場頗為隆重,數百位歐盟精英齊聚,人頭攢動。
歐洲議員、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萊恩(Jo Leinen)常會參加華為類似的活動,他告訴端傳媒,在布魯塞爾,華為的遊說活動非常顯眼,在中國企業中最為積極。
「相比歐洲的汽車行業,或是美國的谷歌、亞馬遜、蘋果在布魯塞爾試圖改變法律措辭的『硬遊說』,」萊恩說,「華為是新來者,他們的遊說更為軟性。」
尼娜(Nina Katzemich)是非盈利機構「遊說控制」(Lobby Control)的歐盟研究員,研究歐盟各利益團隊的遊說策略和權力結構已有十多年。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尼娜說,華為與歐盟的關係,僅透過華為這些年自願提交在「歐洲透明度註冊處」(Transparency Register)的數據,已經能夠看出端倪。

2011年,由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設立的「歐洲透明度註冊處」啟動,要求所有在歐盟層面進行遊說的機構,主動提供遊說活動簡況。歐盟委員會是歐盟最重要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歐洲議會也是立法機構,而且是歐盟唯一直選民主機構,議員的發言影響到公共議題的討論和走向,兩者都是遊說活動的重要陣地。2013年6月,華為開始在該註冊處上報自己的遊說活動,最近一次上報是2017年11月。
一個名為「遊說事實」(Lobby Facts)的平台,蒐集整理自2012年以來的「歐洲透明度註冊處」數據以及歐盟委員會官網上公布的高層級遊說會面。據「遊說事實」統計,自2014年11月以來,華為與歐委會高層的見面次數已有40次。
尼娜說,這是個讓人吃驚的數字,「尤其考慮到見面的對象包括厄廷格(Günther Oettinger)這樣位置重要的委員。」厄廷格是德國指定的委員,如今負責歐盟預算,還曾經負責數字單一市場。華為與厄廷格及其內閣高級成員的見面次數,已有9次,商議內容包括數字經濟、電信政策、5G、文件安全等等。此外,華為還與負責工作與發展的歐盟副主席卡泰寧(Jyrki Katainen)及負責數字經濟的歐盟副主席安西普(Andrus Ansip)各有兩次見面。
「其中,華為與歐委會的很多見面並沒有具體議題,而是類似與華為員工再見或歡迎新員工這樣的活動,」尼娜補充說,「這與其他公司帶着具體討論事項安排會面的做法很不一樣。」她覺得這種作法也許是華為為與歐委會搭建更好的關係而做的努力,「短短幾年內能有40次見面,證明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一位熟悉華為在布魯塞爾遊說過程的知情人士告訴端傳媒,華為在2011年前後剛開始與歐委會負責具體政策的各個總司接觸時,對方會派出類似「國際關係」的部門與華為對接,「明顯把華為視作是歐盟與中國關係的參與者。」回顧在英國和美國的教訓,這恰恰是華為在歐洲遊說時盡力避免的形象。而後,當華為更多地展示出在業內的技術優勢,它與歐盟各層的接觸才更為深入。

遊說需要長期的人力與物力投入。華為在布魯塞爾的遊說預算(不包含歐洲其他地區),在2012和2014年都是300萬歐元,2015年為280萬歐元。據「遊說事實」2016年的統計,在公司這一門類下,華為的遊說預算在歐盟已經進入前十,位列德國西門子、美國谷歌和微軟等大公司之後。這些預算的去處,除了在歐盟總部附近租賃辦公室、聘請內部說客、僱傭其他遊說公司、組織公關活動之外,還包括華為在各個行業協會、跨行業協會和智庫交納的會費與獻金。
華為上報至透明度註冊處的,就有12個不同的協會。在「入會」選擇上,華為十分「懂行」:「歐洲企業協會」(Business Europe)是布魯塞爾最重要的遊說集團之一;「數字歐洲」(Digital Europe),會員包括各大信息技術公司,這些公司的歐洲 CEO 建立了諮詢委員會,直接遊說歐委會和歐洲議會;而「歐洲互聯網論壇」(European Internet Forum),更乾脆由歐洲議員直接搭建和領導。
這些協會代表會員的利益,對歐盟各層級都有影響。藉助這些平台,華為的說客能夠在布魯塞爾的各種早餐會、雞尾酒會上找到機會與歐盟政策制定者展開討論。
尼娜說:「布魯塞爾的政策制定就是這樣,很多活動都會出現好些委員或者高級內閣成員,然後你能跟他們喝一杯,聊一聊。有效的遊說常常這樣就做到了。」
無論是人力、物力的投入,主動展現自己的品牌,還是在極具「影響因子」的各大協會中佔據一席之地,用尼娜的話說,「華為已經很好地降落在布魯塞爾的遊說場了。」

「建造整個生態系統」
在這個以「影響力」為目的、建構良好輿論以掩蓋衝突的激烈賽場上,華為也許是帶着中國基因登場歐洲的「一號玩家」。
庫佩爾曾是律師,在英國電信企業沃達豐的德國分公司工作過9年,2010年起加入華為德國分公司。如今,身為「公共事務總監」的庫佩爾在華為的工作重心便是遊說。這位語速極快、說話精明的德國人直言不諱:「在我看來,遊說就是一切。影響力則是做遊說的原因,我們希望去影響大眾輿論、政治觀點、技術觀點等等一切。」
不過,與廣告、銷售、研發都不同,遊說並不能給公司帶來保證絕對的「投入產出」比。「很難給遊說明碼標價,」庫佩爾說,「我們給公司帶來的不是政府的訂單,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建造。」
「創造一個接受我們產品的市場環境⋯⋯併為此消除障礙。」庫佩爾如此總結自己用來說服華為高層開展遊說的理由,「也要應對那些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我的數據是否安全?你會偷我的資料嗎?你會與政府分享我的數據嗎?這些疑問都要去回答,而不能像屋子裏的大象那樣不聲不響,所以我們要採取措施,並且試圖提供一些安慰。」
在回答關於遊說的問題之前,庫佩爾談起華為的研發投入:「華為在歐洲的專利申請排名第一,比德國西門子還高。」以5G的發展為例,華為自2009年在5G領域的投入已達6億美金,2018年還將追加8億美金。據諮詢公司 LexInnova 2017年初估計,中國已經擁有10%的5G關鍵的知識產權。其中,華為研發的「極化碼」(Polar Code)被負責制定無線標準的「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3GPP)認準為控制通道的編碼方法。
「但是,有創新是一回事,」庫佩爾話鋒一轉,「你還必須讓市場準備好來接受你的產品。市場的發展必須與技術的發展同步,否則,不管技術多好都找不到市場。」
「因此,要教育政客和監管機構。他們被選為議員,卻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和通訊技術背景。」

如何教育政府、如何構建市場環境呢?
首先,「得找到一個有西方臉孔的代言人、要稍微理解中國,但不以中國人的方式思考。」庫佩爾指了指自己,又說華為在歐洲處理外部事務的,多是來自當地的僱員。
「有時我的中國同事與德國方面接觸,然後就說已經掌握了『一手信息』。」庫佩爾舉例說,「但是我會明確告訴他,不是的,這些只是(德方)說給中國人聽的。他們在跟我對話時便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只有母語,才能說出言外之意。」
庫佩爾對於這些年華為在德國的遊說效果信心滿滿。他舉例說,在德國重要的行業協會裏,「華為不僅是會員,透過持續的貢獻,我們可以在協會裏拿到高級的決策席位,指導或引導整個行業協會的方向。」
在智庫和學界也類似,「我們把華為的研究者帶到德國國家工程院,華為還擁有院裏參議員的席位。」公私合作平台也有接納華為的地方,「在由政府主導的數字峰會上,CEO級別的高層代表中也有華為⋯⋯在那裏,我們可以與部長級人物一起定義和設計德國的數字未來。」
以「全局」為指標,固然可以顯得「公共關係」的效果無處不在,但也有劣勢。畢竟,從「全局」看,歐洲的輿論場依然充斥著對「中國」的顧慮,中國因素越顯眼、質疑聲也越大。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在2018年初發佈的一份報告,便警告中國在歐洲開展的「全面并靈活」的「影響力」活動,「對自由民主以及歐洲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重大挑戰」。
後來者
在這個以「影響力」為目的、建構良好輿論以掩蓋衝突的激烈賽場上,華為也許是帶着中國基因登場歐洲的「一號玩家」(企業層面),但一定不會是最後一個。
目前,主動留下游說檔案的中國企業還很少。用關鍵詞「中國」檢索歐盟的透明註冊處,除了在所有指標上都遙遙領先的華為,來自中國的公司只有三家:無人機公司大疆創新(預算20-29萬歐元)、電商平台阿里巴巴集團(預算5萬-10萬歐元)以及吉利汽車集團(預算少於1萬歐元)。
不過,嘗試過遊說嘗試的中國企業一定更多。只是相較華為多年的影響和滲透,很多「初來乍到者」尚不熟悉遊戲規則。「布魯塞爾站」的總裁習福思,就向端傳媒講述了一個被他歸類為「文化差異」的經歷。
一個透過層層朋友介紹的中國公司曾聘請習福思政策遊說。歐盟有一系列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規則,抵制人為壓價或者製造商獲得國家補貼的廉價商品。習福思說,「這家公司希望能與歐盟聯絡,證明自己出口的具體產品不應受反傾銷制裁。」
習福思認為這是可行目標。他將這家公司帶到歐盟委員會中專職負責該產品所在領域的公務員面前。但是,在歐委會隨後提出的問卷上,這家公司並未提供真實數據。
「很少能有中國公司會走到那一步,因此他們已經受到嚴密的審視了,」習福思小心地措辭,「也許是不同文化對規則的解釋不同。」他依然希望有更多中國客戶,「但必須誠實。」
(感謝 Felix Wadewitz 對此次報導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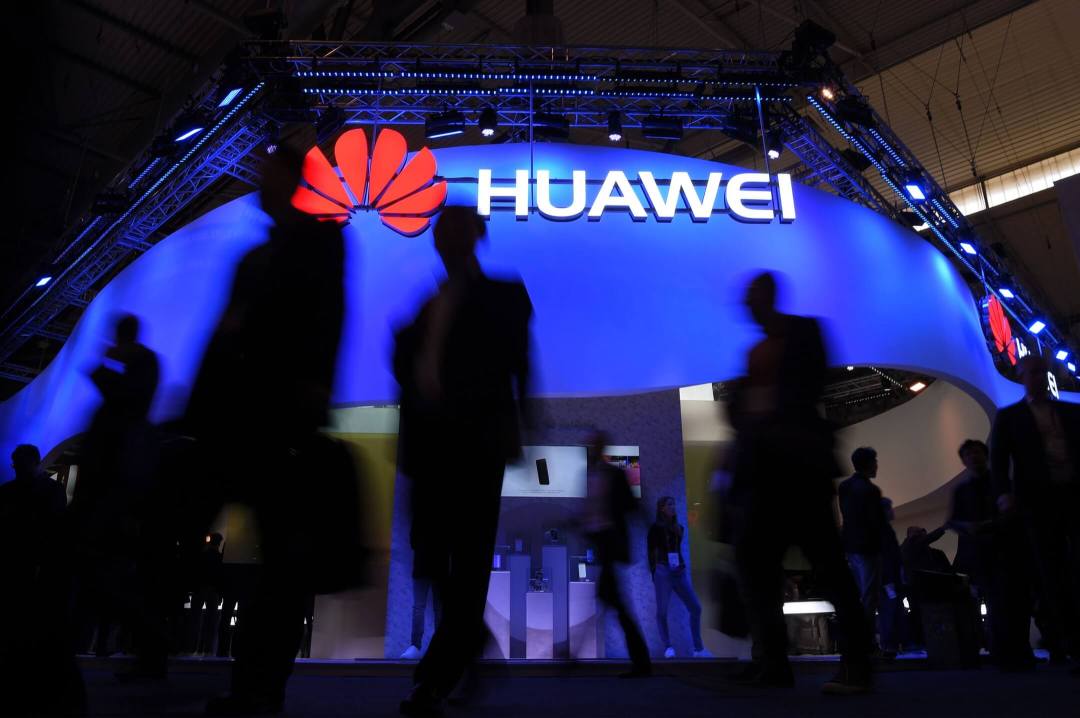




「短短几年內能有40次見面」,「几」宜作「幾」字。
摆数据,讲事实。很多中国企业总是口头讲着要全球化和国际化,但是真的能摸透西方规则的极少,从对游说的投入上就能看出来。从文章中了解到,游说竟然在欧洲竟然也是透明化的,真的让我惊讶,仔细想想也有道理,与政策相关的利益团体进行合法游说,避免因各方面原因导致政策过度损害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是透明必须是前提,对政策的影响应该是讲道理不是利益输送,而透明化,也更有利于减少游说而产生的腐败。
最后一句(苦笑)
这才是正道
通用苹果都有在游说,华为与其说是一个中国企业,更像是一个欧洲企业。没有说客在议会为你辩解,你就会遇到重重税制和罚款。西方总认为共会窃取西方的政治机密,然而共如果为了这些放弃庞大的发达国家市场,无异于杀鸡取卵。而西方恰恰认为共会这么做。可笑的是奥巴马政府监视了那么多年默克尔的电话与邮件,美德依然是坚固的盟友。如果不是意识对抗作祟,那么就是美国既80年代过后,又一次面临话语权被争夺的局面。当时的日本家电巨头也是被美国制裁,与今天何其像也。只不过日本对美的出产业难以触及战略核心罢了
华为这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是否能当作普通的商业竞争来分析?可能需要一套新的分析模式。
P.S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付费文章区少了很多上来骂骂咧咧,乱搅浑水的五毛,看来付费墙内才是净土啊。
苹果手机随便查,反正都是Made in China
那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怀疑苹果手机有安全隐患,来个安全调查呢
我不认为文章把华为淡化为普通中国企业的分析是有价值的,对问题的本质避而不谈
華為是民營企業......一笑
说个笑话,民企第一是民企。
西方的法律严格,监管相对可靠,在那里的中国企业,也确实十分守规矩。 反观国内咱就不多说了。
华为现在也被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