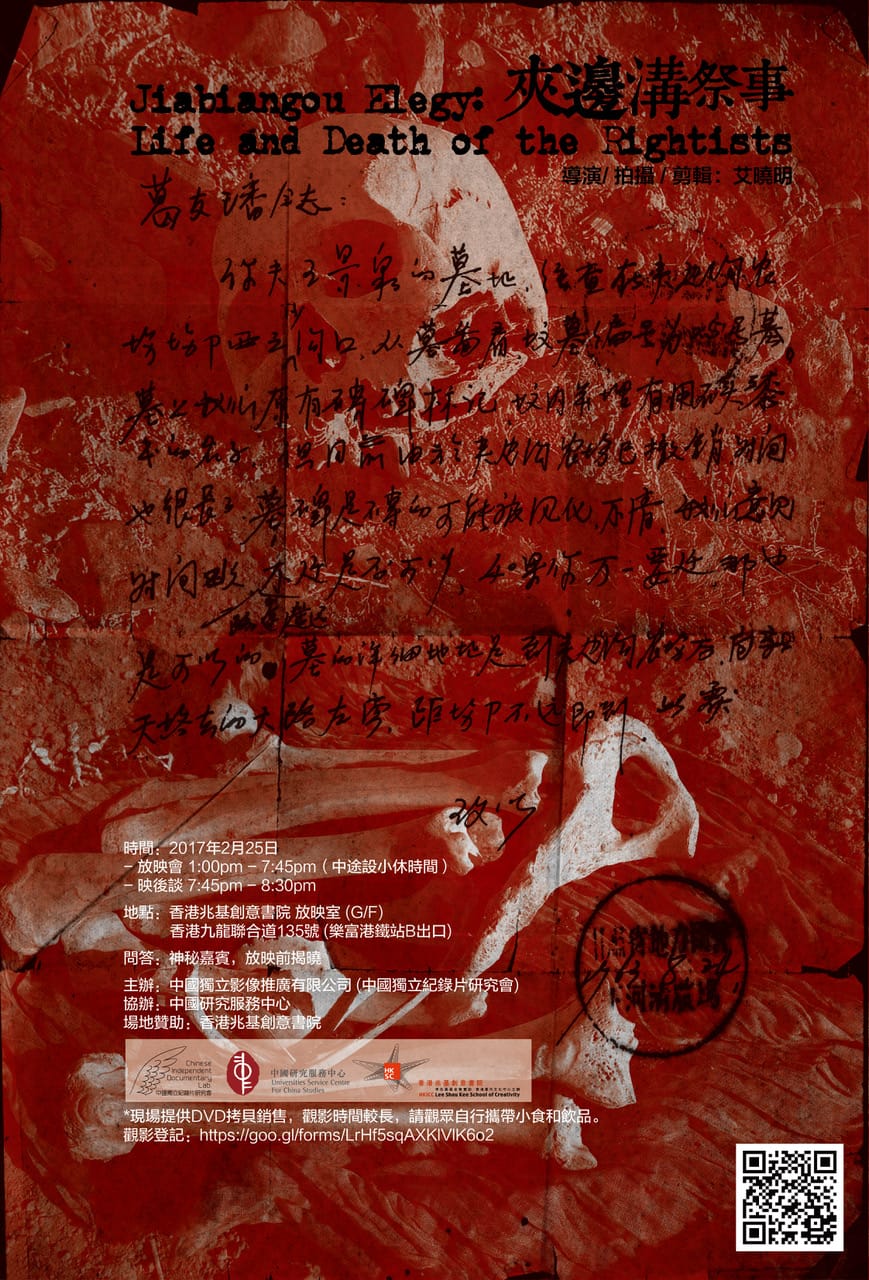
問:過去你的紀錄片作品一般跟維權抗爭運動相關,這次為什麼會做「夾邊溝」這個歷史題材的紀錄片?
艾:這可以說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肅敦煌旅遊,計劃中也包括順便去夾邊溝看看。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裏的右派老人說起清明節要去夾邊溝紀念,還說起他們建了紀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重要線索,這裏出現了一個衝突,這個衝突是我非常關注的。近年來各地開始出現有關過去悲劇事件的紀念碑,碑是一個記憶,紀錄片也是一個記憶。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做?但我沒有想到要拍片,因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經有了不少關於夾邊溝的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