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於美國時間2月11日病逝。孔飛力的中國研究領域,涉及國民黨史,太平天國叛亂到中國地方政治社會史,海外華人史。其中一脈相承的是「一種對於理論和比較方法的深切關注,以及優秀的智力精確性。」正如他的老師,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教授所說:「通過某種非同尋常的方法,孔飛力將歷史學這種方式,與對人類意識生活和知識分子歷史運動的深層關注結合起來......」
1980年至1986年,孔飛力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在學術界,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的四本著作(《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他者的中國人:現代社會移民》),雖然題材各異,卻在不同層面、角度反映了中國的權力文化。
其中《叫魂》一書1999年首次推出簡體中文版,就在中國知識界引起極大反響。中國現代官僚體制和乾隆時期相比,情形自然不同,但權力文化卻區別不大。孔飛力1984年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接觸到一批乾隆年間的官方檔案,詳細記載了當時在江南的「剪辮案」引發的「叫魂」危機。《叫魂》一書正是從此案入手,觀察帝制衰弱趨勢下,皇權與常規權力如何博弈;案情、騷亂在皇帝、官僚、民眾三者眼中又分別是怎樣的故事。
權力如何運作,是紛繁的社會事件背後值得研究的問題。官僚體制從來不是一套僵死的機制,而是內外聯動不斷變化的。無論是今天的雨傘、魚蛋,還是昨天的巫師、辮子,如果沒有人仔細研究事件背後不同角色的位置、心態、應對手段,那它們將只是作為一段時間的高頻字眼,在網絡信息流中漂浮。
我們回顧《叫魂》的第十章,感受孔飛力對中國權力文化的精準把握。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出版時間:1999年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作者: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
譯者:陈兼 / 刘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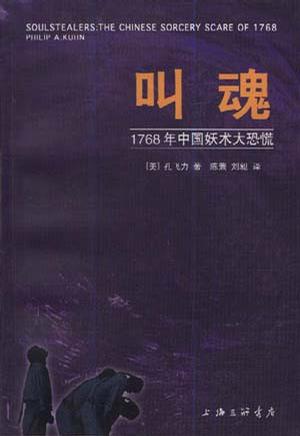
第十章 主題和變奏
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但並不是單一同質的。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像「叫魂」危機,這樣讓全社會捲入的事件──雖然不同的社會群體對這一經驗的表述(representation)是各不相同的。
我們已經看到了繡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襤褸的囚犯之間的文化差距。但是,人們在社會等級上存在距離,並不意味著他們互相之間不能理解。這種距離有時意味著人們對於種種相同的符號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
儘管「邪術」讓所有的人都感到害怕與憎惡,但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將妖術傳說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使之適應於自己的世界觀。這就是為什麼像妖術大恐慌這樣一個「事件」會同時「發生」在王公貴族和農夫平民身上,而「發生」的條件則是因人而異的。
對這一事件的不同表達(expression),取決於人們不同的社會角色及生活經歷。從這一角度來看,「叫魂」主題被賦予不同的變調,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所表達的則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恐懼。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伴隨著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來的兇險。
君主:真實和幻影
為了探討弘曆的思路,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這樣一個事實:1768年後,叫魂恐慌又於1810年和1876年至少兩次出現,但這兩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發動全國性的清剿。
1810年時在位的是弘曆的兒子颙琰(即嘉慶皇帝),他不願對剪辮妖術的謠言神經過敏。他寫道:同樣的怪異卻漸漸自行銷聲匿跡了。因此颙琰明確禁止地方當局「株連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後來鎮壓1813年八卦教叛亂時那樣強迫嫌犯招供同夥,造成廣泛株連。)
相反,地方當局應進行秘密調查並秘密奏報,以免「衙門胥吏濫及無辜」,擾亂地方(如1796年白蓮教大起義爆發時的情況那樣)。結果,這一事件無疾而終。
1876年的事件發生時,光緒皇帝年幼,其時慈禧太后攝政,日漸權傾朝野,清政權正面臨內亂外患。其中特別令人頭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有時並會釀成暴力事件。
這些因素構成了那年春天起源於南京,並蔓延波及長江沿岸數省的「剪辮恐慌」大背景,地方當局奏報說,某些被捕嫌犯承認他們是民間教派或秘密社團的成員。他們的「邪術」包括把人的髮辮黏在木人或紙人上,然後施行法術把它們變成活人,使之成為主人的打手。
有人還相信髮辮是被術士們派遣的侏儒割去的。兩江總督沈葆楨則相信這些術士來自白蓮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確證」的案犯被處斬首(這是自太平天國起義以來行省權力大為擴張的一個方面),以便「安定人心」。
像往常一樣,地方當局面臨的難題是,要在清剿妖術(其風險是法律的濫用)和任其銷聲匿跡(其風險是引用民間的憤怒)之間找到一條中庸之道。
民眾的情緒被傳教士的活動煽動起來。許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國教民積極捲入了妖術活動,民間的反妖術活動更是帶上了反洋教的傾向。根據沈葆楨的報告,由於某些術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勢變得更為複雜。
在當時的情況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亂,因為這會引起列強的干涉,當局於是警告民眾不要「捕風捉影」。來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員們不得聽任事態發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亂。
在這兩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於很充分的理由而沒有像1768年的弘曆那樣對妖術大肆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這些後來的統治者顯然也缺乏站得住腳的理由從事清剿。
我們現在不得不回過頭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何種看法或何種形勢,導致了弘曆對妖術作出這樣的回應?
弘曆對異端的兩次最嚴厲清剿,都發生在清政府軍事行動受挫,他因此對其軍隊的表現身為不滿的當口,這大概並不是偶然的。1751至1752年的危機──包括「偽稿案」和對馬朝柱的瘋狂搜捕──恰好發生在鎮壓川西金川土著的漫長軍事行動之後。
在這場戰役中,清軍對金川土著的損失如此慘重,進剿如此不利,以致于弘曆以貽誤戰機為由,處決了清軍的兩名最高將領。
而當1768年的危機發生時,征伐緬甸之役正毫無指望地被困在瘴疬肆虐的熱帶叢林裏,弘曆則以無能和謊報軍情為由,撤換了他的戰地指揮官。當清軍陷入困境時,難道弘曆不會將震怒和沮喪發洩到國內事務中來嗎?
然而,雖然這種沮喪可能會給弘曆對妖術的清剿加溫,但清剿的實際進程卻有著自己的邏輯。弘曆的憂懼亦幻亦真。真實的部分在於,他難以打破官僚體制自我滿足、常規裹足的積習。君主要維護鞏固自身利益,就必須不斷訴諸於專制和無常的權力,而提出政治最指控則是使用這種權力的絕佳機會。
幻影的部分(但誰能說幻影非真呢?)則在於,他對於無法為他所見的勢力心存恐懼。妖術,當然就是這樣的一種勢力。但還有來自謀反和漢化的雙重威脅。
即便像弘曆這樣一位已經漢化的滿洲君主,也無法將謀反與種族因素區分開來,而當一個案子牽涉到辮子的象徵意象時,便足以成為使他疑慮爆發的導火索。
與謀反危險相伴隨的是漢化問題,這一威脅雖然並不急迫,但卻更為險惡。弘曆的反應是文化的(推崇滿族語言和歷史,通過發動全國範圍的文字獄來清楚反滿意識),同時也是政治的(清楚已成為漢族官僚體系特徵的種種「惡習」)。
江南是問題的關鍵。危險來自於富庶文明的長江三角洲,並正沿著運河兩岸向北蔓延。在弘曆看來,南方是漢族官僚文化的罪惡淵藪: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偽。強健的旗人可能會陷入江南的魔咒;弘曆會用最嚴厲的語言,斥責受到江南文化蠱惑的滿洲官員。
現在,某種罪惡又從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場中的腐敗習氣和社會上的妖術陰影。人們可能會提出異議,認為弘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種,而是第二種危險。確實,弘曆在公開場合是妖術的嘲笑者,說妖術是荒誕不經的迷信。
但是,他在許多奏稿上的批示又顯示,他對妖術的細節與目的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究竟是否「相信」妖術的存在?最好還是這樣提出問題:對他來說,術士的妖術,比之漢文化的蠱惑,是否就更不可信?術士們竊取人們的靈魂,腐敗的漢文化則竊取滿洲的品德,哪一種危險對他更為真實呢?
知識階層和大眾對妖術的看法
普通百姓的妖術信仰,和君主視妖術為謀反的認識,是有區別的。這使我們聯想到,在歐洲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起鄉村巫術,和出現在宗教法庭上的「博學的」或「魔鬼橫行的」巫術之間同樣存在著區別。
在Richard Kieckhefer對歐洲巫術迫害的研究中,他寫道,大多數村民指控鄰居使用巫術,是因為他們相信鄰居用巫術傷害他們,但並不一定認為鄰居這麼做時與撒旦有任何約定。
……正是審判官和其他「專家」們,把「魔鬼契約」概念強加到了村民們單純的對巫術的恐懼之上。這些人以「邪惡的眼光」嘲笑民間的信仰,並以自己充分理性化的,將人生視為上帝和撒旦之間鬥爭的觀念來取代這種信仰。
和歐洲教廷的法官們一樣,弘曆也將一種因自己的恐懼而產生的意義,注入到民間妖術中去。這是有一個例子,揭示出妖術如何得以在一個複雜而龐大的社會裏,跨越階級的界線而傳播開去。對妖術的看法可能同時存在著兩個或更多的版本。
皇家的版本以對滿洲統治、歸根結底也是對整個整體的威脅為中心,農民的版本所集中關注的則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靈魂丟失而造成的突發與隨機的死亡。但是,君主和農民使用的並不是完全不同的語言。
對弘曆來說,陰謀家門也是外人(所謂「奸狡僧徒」和「失意文人」),即儒教秩序的放逐者。他們沒有確定的文化歸宿,要麼不受儒教家庭制度的限制(如那些違背父母,拒絕結婚生子、傳宗接代的僧徒),要麼不理會正統科舉官僚制度的約束(如那些科舉考試失敗,轉而反對科舉官僚制的文人)。
弘曆在叫魂危機中的政治行為,對我們進一步認清「專制」這一概念或許會有所幫助,而「專制」正是後期帝國的特征。在弘曆的行為中所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他本人的個性。即位之初,他就立誓要在他過於仁慈的祖父和過於嚴厲的父親之間,尋找出一條中庸之道。
他確實找到了這樣一條中庸之道,但其方式卻是奇怪的:他在寬容和嚴厲這兩極之間來回擺動,因此,他的「中庸之道」並不是一種常態,而只是一種均衡。這種行為是否表明了他的專制的有效性?
從他的朱批中流露出來的,卻是他的慍怒和急躁。面對真實的或許只存在於他想象之中的威脅,他的反應看上去不僅過分而且滿懷惡意。由於滿清王朝這第四位,也就是最榮耀的君主身上的這些品質,他要實行個人控制,也許就非要訴諸於「政治罪」不可了。
但是,我也常常禁不住設想: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帝國制度本身,是否已達到了非使「政治罪」成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此時此刻,任何一個君主想要維持對官僚制度穩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變得十分困難。
弘曆的父親胤禛是最後一位為此作出了認真努力的皇帝。他整頓財政體系,建立對邊疆地區的行政控制,強化彈劾制度,並加強帝國通訊體系的機密性。在所有這些問題上,胤禛都做了不遺餘力的嘗試。
但是到了弘曆手裏,這些制度建設不是停頓了,就是出現了倒退。這或許並不能簡單地歸之於弘曆缺乏他父親那種耐力。到弘曆的時候,官僚體制已是盤根錯節,征服者已不可逆轉地進一步漢化,以至於君主對官僚的常規控制已經捉襟見肘。
如果情況卻是如此,那麼政治罪可能便為弘曆提供了一種恰當的替代性手段:它既可以像1751年和1768年時的情況那樣,讓他圍繞著謀反危機對官僚體制實行動員;也可以像18世紀七十年代時的情況那樣,讓他通過文字獄對文人騷客進行恐嚇。
弘曆並未蓄意這麼做,但可能是在他睚眥必報的個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的引導下,他依賴於這樣的手段,來達到非如此便不能達到的目標,即君主對於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控制。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