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發揮的作用引發了很多關注和爭議。在一些學者看來,媒體在大選報導中表現出的問題並非偶然,而是美國媒體制度的深層弊病導致的必然結果。
賓夕法尼亞大學Annenberg傳播學院副教授Victor Pickard就持有這樣的看法。作為媒體政治經濟學流派的學者,他着力於批判商業媒體模式及壟斷資本對傳播環境的破壞。2017年1月底,特朗普就職一週後,我對他進行了一次訪談。我們的談話從大選開始,延伸至媒體制度,涉及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討論了媒體的黑暗現實和對未來的想像。雖然我們談到的具體問題基於美國語境,但對思考其他國家的媒體問題也有啟發。

特朗普從大選報導中獲益
問:有不少中國人認為,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美國主流媒體存在嚴重的偏向性,沒有做到客觀平衡報導。你同意這種說法嗎?你如何評價美國媒體的大選報導?
答:首先要說明的是,人們總是會認為媒體的報導存在偏向性,這往往反映的是人們自身持有的觀點立場。
不過,確實有證據表明:唐納德・特朗普比其他候選人得到了更多的媒體報導,至少在電視新聞中如此。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媒體偏向他嗎?不一定,但他得到的報導數量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同樣有證據表明:和希拉莉・克林頓比起來,伯尼・桑德斯得到的報導數量非常少。
在大選階段,美國的主要報紙絕大多數都選擇了給希拉莉背書,而不是特朗普。你可以說,它們是更偏向希拉莉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大選期間,特朗普的很多政治主張沒有得到足夠細緻的監督考察。媒體輕易放過了他的不少問題。哈佛大學教授Thomas Patterson的一項研究顯示,大選期間新聞媒體對政策主張方面的報導是極少的。所以,如果從更大的畫面來看,我認為特朗普從媒體報導中獲益更多。
問:特朗普得到了更多的報導,但是針對他的報導看上去也是更為負面的。
答:我還沒有看到相關研究證明這一點,不過針對他的報導確實很有可能大部分是負面的、對抗性的。但是我認為,特別是在黨內初選階段,媒體報導的數量對特朗普的幫助很大。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特朗普得到了價值大約20億美元的免費電視時間。我認為,對他來說這是極大的優勢。特朗普符合了商業新聞的很多價值取向——媒體被爭議性的人物和話題吸引,因為爭議會提高收視率和發行量,而收視率和發行量則會吸引廣告商。我想,正是這樣一種商業衝動驅使媒體對特朗普大作報導,而這種報導規模又給特朗普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此外,希拉莉的電子郵件得到的討論和批評,和特朗普的醜聞及存在問題的政策主張受到的關注一樣多,甚至更多,這是一種虛假的平衡(false equivalence)。

問:你提到「虛假平衡」,能再詳細談談這個概念嗎?
答:這是美國式的新聞操作中非常有症候性的一種現象。它和美國新聞專業操作的基石——「客觀性規範」有關。人們經常批評這種操作是「他說XX、她說XX」。因為客觀性規範的假定是,一個故事有兩面,而這兩面在新聞中需要得到同等的時間和篇幅,不管這兩面是不是真的值得那麼多的關注。
如果追溯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史,你會發現這同樣和商業驅動有關。當時,報紙的出版商和編輯們為了吸引足夠多的廣告,就需要得到足夠廣泛的讀者;而為了得到足夠廣泛的讀者,他們就要通過呈現不同方面的觀點來避免捲入具有爭議性的政治議題。當然,這種客觀性規範的出現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是經濟方面的原因是很重要而且經常被忽略的。
問:簡單來說,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媒體並沒有真正做到客觀報導,它們只是在假裝客觀。
答:可以這麼說。這種報導方式在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有非常破壞性的影響。一方面,科學界的絕大多數人達成了共識:氣候變化是由人為因素導致的;另一方面,有一小群科學家持相反的看法。但是雙方往往在新聞中被給予同樣的篇幅來呈現,這就給公眾帶來了困惑,也污染了圍繞這些重要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公共討論。
與之相關,Lance Bennett曾經提出一個叫做「indexing」的理論:很多新聞報導只是記錄下美國兩黨建制派當中的不同觀點,這就導致媒體總是侷限在建制派的意見之中。
問:有人說,美國主流媒體成了建制派的「喉舌」,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答:實際情況總是比這種簡短的論斷要複雜。我想,在這次採訪開始的時候我就應該說明:媒體不是鐵板一塊的。在媒體中,可能有的部分更貼近建制派的意見,但也總有一部分是可以容納異見的。實際上,我認為活動分子們應該利用主流媒體中存在的機會。大家應該意識到:即便是通過主流媒體,也有機會傳達出激進的理念。
基於以上這些前提,回到你的問題。是的,可以說美國的新聞媒體通常反映的是它們所處政治體制的價值觀。說它們是「喉舌」可能有些誇張了,但是它們確實更傾向於反映精英的意見。這背後也存在經濟方面的考慮: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更高的讀者,更有商業價值。所以工人階級的問題得不到足夠多的關注。
問:這和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日益下降有關嗎?
答:我想這可能是導致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過去幾十年間形成了一個右翼的媒體生態系統——包括保守派的廣播和電視脱口秀、Fox News、Breitbart,以及很多右翼網站、博客。它們製造並且不斷放大了這種看法:美國主流媒體有深刻的、系統性的自由派偏向。這是人們(至少是保守派)不信任主流媒體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媒體的信任度下降還有其他原因。很多左派也不信任媒體,尤其對媒體在報導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失望。過去也出現過不少失實和醜聞。還有一個原因是,媒體越來越傾向於一種新的黃色新聞、譁眾取寵的新聞——同樣,也是由經濟原因造成的。媒體僱不起那麼多記者了,記者不再能夠投入那麼多精力做真正的新聞了,在網絡平台上越來越依靠標題黨了。此外,主流媒體的網站越來越依靠獲取用戶的隱私信息來獲得收益。所有這些都是導致公眾對媒體信任度下降的原因。

公共媒體是理想的模式
問:你多次提到媒體的商業驅動,認為這種商業模式是導致很多問題的根源。我知道,你是公共媒體系統的倡導者。英國的BBC和日本的NHK都是這種公共媒體的代表。但是我們也看到,有BBC的英國退出了歐盟,有NHK的日本選出了右翼的安倍晉三。這是否表明,公共媒體的作用有限?或者,公共媒體還不夠強大?
答:不能因為右翼運動在這些國家抬頭,就簡單地認為公共媒體系統沒有發揮作用。導致右翼抬頭的原因很多。
不過,公共媒體確實還面臨很多問題。當公共媒體鑲嵌在一個強大的商業媒體系統中時,這些公共媒體就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一些時候甚至開始模仿商業媒體,習得它們的一些糟粕。在美國,PBS和商業媒體基本上看不出什麼區別。所以,公共媒體系統需要建設得更強大才行。有研究表明,在具備強大公共媒體系統的國家,人們普遍對國際和公共事務了解得更多。
問:大選之後,《紐約時報》等媒體的訂閲量以及ProPublica得到的捐贈額都出現了激增。你認為這是不是預示着一種積極的改變?或者,僅僅是短暫的應激反應而已?
答:我更傾向於後者。我希望這種情況能夠持續更久,但這很可能是一次轉瞬即逝的機會。人們突然意識到,擁有一個活躍的、得到強大支持的第四權力是多麼重要。然而不幸的是,將媒體吹向深淵的經濟風向並沒有發生變化。大選之後突然得到一批新的訂戶,當然是好事,但是支持了美國媒體大約125年的商業模式已經遭到了無法逆轉的破壞。我們再也回不去了。我所說的這種商業模式就是由廣告收入支持的模式,現在美國新聞業依然依靠這種模式,但是它已經崩潰了。所以我們需要新的模式,新的結構。
問:《紐約時報》最近發布了一則「2020報告」,其中說:「簡單而言,我們是訂閲者優先的模式。」你覺得依賴訂閲者是一種可持續的模式嗎?
答:我希望如此。訂閲當然會帶來新的收入,《紐約時報》選擇力推訂閲模式,也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但不幸的是,我不認為這種模式足以產生足夠多的收入以支持一個民主社會所需要的新聞媒體。就算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紐約時報》是可行的,它對中小型報紙來說也行不通。即便是大型的都市報紙,也不一定行得通,比如《費城問詢報》。所以,很遺憾,訂閲模式不是解救新聞媒體的方法。
問:說到《費城問詢報》,我對它們正在進行的非營利模式轉型很感興趣。你了解更多的細節嗎?
答:我想它依然在轉型過程中。我認為這是一場非常有趣,並且可能相當重要的實驗。我希望更多報紙意識到:轉型為非營利或是低利潤模式,對於它們來說其實會更好。《費城問詢報》更多採用的是一種非營利和營利的混合模式。應該鼓勵這些實驗,但它們能否成功還有待觀察。
我們前面討論了公共媒體。我認為公共媒體模式是最理想的,次之是非營利媒體模式,這些媒體可以由訂戶、基金會、進步的慈善家支持,它們可以生產我們所需要的新聞。而營利模式沒有太多的前景。
Facebook應該接受外部監督
問:我們已經談了很多關於主流媒體、傳統媒體的話題。在這次大選中,也有很多另類媒體出現,甚至一些Facebook的專頁都成了散播謠言和假新聞的重要力量。不知道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特別是從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答:有人認為,是假新聞導致了特朗普上台。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我們不能把什麼都怪罪到假新聞頭上。但是,我確實認為假新聞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經常忽略了這個問題的根源:壟斷權力。Facebook是一個不受監管的壟斷者,它從平台上的各類內容獲利巨大,其中就包括假新聞。但直到現在,它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媒體公司,只願意說自己是科技公司。當扎克伯格否認Facebook是媒體公司,他的潛台詞就是,Facebook不需要承擔特殊的社會責任。我認為我們需要討論這個話題,需要探討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人提出了一種組合方案來解決假新聞問題,包括眾包、算法,以及Facebook僱傭人工編輯。我想,這些方法可能都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但同時也需要一些外部監督。Facebook需要坦然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因為它已經是事實上的全球性新聞編輯了,它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新聞把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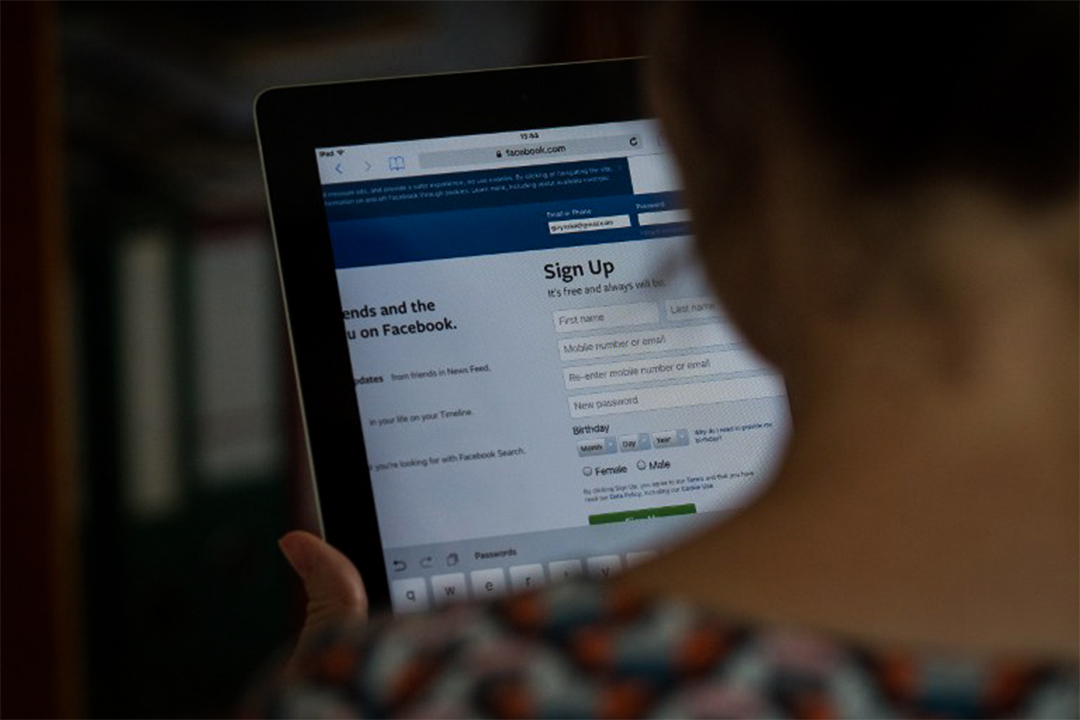
問:誰來做外部監督?監督哪些事情?
答:可以是技術人員、記者、公共倡導者的組合。他們應該監督Facebook的各個方面,並且保證算法和編輯的透明。我沒法給出所有的答案,但我想這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討論的話題——不僅是在美國,而且在全球其他國家。
問:的確,中國也有一家很有影響力的新媒體否認自己是媒體公司。我想,外部監督的設想很好,但是估計很難實現,畢竟Facebook是商業公司。
答:是的,特別是在美國,有人說這裏面還有第一修正案的問題。但至少,我們可以有監察專員(Ombudsman),可以有一個獨立的媒體委員會。這都是在美國發生過的實驗。外部監督不意味着需要讓政府來管制Facebook。但是如果不監督,讓Facebook自行決定,結果可能很危險——Facebook至今都沒有表現出很強的責任感。當一家企業對我們的新聞媒體系統擁有如此強大的權力時,這種權力就需要被分散。
問:你剛才提到監督算法。Facebook可能會說:算法是商業機密,不能公開。
答:這種說法是不能被接受的,是需要被挑戰的。如果我們讓Facebook的商業利益凌駕在社會利益之上,那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失衡。所以我們必須開始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我還想指出的另一點是:Facebook和Google正在鯨吞新媒體上的廣告收入,這等於是將本來就很稀缺的資源從苦苦掙扎的新聞媒體那裏奪走。當媒體轉向互聯網之後,它們得到的新媒體廣告收入比之前的紙媒廣告收入少得多。現在大約85%的數字廣告收入都被Facebook和Google拿走了。這一點很重要:Facebook不僅對新聞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而且把原本屬於媒體的廣告收入拿走了。而我們還在期待傳統的新聞機構投入資源做事實核查,去抵消通過Facebook等平台傳播的假新聞的負面影響。這是新媒體時代新聞業的黑暗一面。
問:有人說美國很多大學生都活在「自由派泡泡」(liberal bubbles)裏,你覺得確實存在這種「泡泡」 嗎?
答:我不認為是所謂的東西海岸自由派精英泡泡導致了我們今天的困境。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民主黨至少自比爾・克林頓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民主黨在羅斯福新政時代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被拋棄了,這就給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空間。此前有強大的勞工運動,有支持着民主黨基本盤的左翼民粹主義運動。後來,民主黨精英們和這個基本盤失去了聯繫。這才是更重要的泡泡,而不是所謂的東西海岸自由派精英泡泡。是新自由主義創造了讓右翼得以興起的真空。
問:你對於希望參與改變社會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嗎?在這個越來越民粹的世界,年輕人、大學生能做些什麼?
答:重要的是不要接受現狀,繼續為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抗爭。同時,年輕人也要參與政治,不僅要走上街頭,也要參與投票,跟蹤政策辯論,聯繫政客,等等。
(方可成,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在讀博士、原《南方週末》記者)
編注:本文原載於土逗公社,一個反思常識的內容合作社。作者方可成,原標題《未來屬於不追求利潤的媒體——專訪賓大教授Victor Pickard》,端傳媒獲授權後轉載。>




公共放送不可能成为主流 只能作为一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