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中風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國大陸記行,當作一本小集郵冊⋯⋯
有一年我在香港,參加了一個沒有開放聽眾的座談會,我記得那次的題目叫做〈小說中的時間〉。那樣形式的文學沙龍,我之前沒有參加過,印象裡裏台灣也不太有這種似乎正式宴會,並不是在酒館或某人家的客廳,亂七八糟胡說;有 buffet、有年輕女孩幫作家們遞上飲料或紅酒,在一潔淨有空調的會議室,與會的來賓可能都是香港頗有名氣的老中青作家,他們可能互相熟識,交錯着攀爬着。它不是一場文學會議後的飯局,它本身就是一場文學活動,但又要在那狀態中,呈現在大家拿着餐盤(西式的銀叉,可能因為食物有廣式撈麵、炒飯,所以也有筷子。但混搭了叉燒包、奶油起司通心麵、娘惹糕、德式火腿、薑絲蒸魚、小總匯三明治、沙拉、西式小蛋糕),可能是社交、禮儀,或一種放鬆狀態下的「各言爾志」。
但那時我太年輕了(其實那時我也快四十歲了),我的聽看辨位觸鬚太貧乏了,或是參與這樣的「文人聚會」的經驗太單薄了。怎麼說呢?我好像一個揹着一個大兜袋,裏面全是各式不同形制不同年分的機械鐘錶,滴滴答答。我好像以為每一次這樣的「文學論壇」,就是一次關於你兜袋裏全部機械鐘要傾囊倒出,作一次關於以金屬細針、彈簧、各式小齒輪、小鎚礦石蕊心、或錶面刻度……觀念或技術的總 PK。但這種幻想,或應是在一大型的文學論壇的公開講廳,或是在某個前輩家,大家拿着啤酒、高粱、小米酒、威士忌……抽着煙徹夜激辯。我不知道,人生將會有許多許多,這樣的文學活動。它們像將賽場上奔蹄廝殺的戰馬,一匹匹隔在玻璃櫥窗,將那觀看的某個截面慢動作播放。它其實有點像一個現代性的「流觴飛羽」,或印象畫派式的電影:看哪這就是文學。
那時我作了一個不得體的表現。一位我極尊敬的大陸前輩女作家,先發言了(但你後來知道,她這是在無數次這樣的文學活動中,一種免於疲憊,而誠摯交心,比較隨興直觀的感性發言),她說了一些中國詩歌中的時間觀,提了李白、杜甫。我忘記了大部分的細節,只記得當時我被那回歸到古典、遠景、空曠天地的「那種時間」描述,弄得非常焦躁。中間可能還有幾位香港前輩或同代的作家發言,都是拘謹而溫和,之後輪到我,我說:「但是我有一種『今夕是何夕』之感,我們在這樣的城市裏,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怎麼可能假裝沒有發生過,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怎麼可以假裝沒有經歷過波赫士、卡爾維諾、昆德拉、奈波爾,或是魯西迪?」然後我侃侃而談波赫士的「三種永劫回歸」哦,我如今回想,真想把臉深埋進我的雙掌裏。當時我就感到我把氣氛弄得非常僵。一些前輩們,先是詫異的抬頭(手上還拿着餐盤),之後皺眉露出不以為然,甚至憤怒的表情。那位大陸前輩女作家也困惑的笑着(她是個溫厚的人),這不是一個輕鬆閒聊的餐敘嗎?這孩子怎麼弄得舞刀弄劍,要把它變成一場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裏的,充滿激情、狂膽、爭辯的戲劇場面。後來在我之後發言的前輩(我記得有一位滿頭白髮、文質彬彬的學者),嘟嘟濃濃說了幾句(似乎被我把場面弄得這樣,氣得想走了),說了句:「總之我支持某某(就是那位大陸前輩女作家)。」
我記得那天晚上,我站在旅館下面的街道旁不斷抽煙,心裏懊悔羞愧。我並不是那樣好戰,炫耀軍火的恐怖分子,或想要攻擊前輩以出名的啊。但那晚在場全部的人,一定都這麼認定我了。
第二天我遇見那位大陸前輩女作家,我面紅耳赤、口齒不清的向她道歉。我說了一句,如果時光更拉長,對我自己之後文學路將持續反芻、思辨的話,我說:「我不是那樣的人啊。」那位媽媽型的女作家也是個感性、溫柔的人,她也真誠的說:「我也覺得你說的特好,但我也好沮喪你誤會我說的了。」最後我們擁抱和解。因為那整個活動,其實是一個國際作家交流計劃。在那個團體中,只有我和這位大陸前輩,完全不諳英文。於是那一個月的時光,我們和另一位馬來西亞的女作家(她英文非常好,但個性有點孤僻,或是不忍看這兩位大姊、大哥陷於啞巴慌亂之境,便充當保護者的角色),三人幾乎每天都混在一起。白天我們各自躲在房裏寫稿,到了晚餐時我們,再加上這所大學一位年輕女助理,我們四個,非常有趣的組合,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香港,成了像家人那樣的好朋友。
我不是那樣的人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在過渡着並不想傷害、或被對方判讀為敵人的蚌殼裡柔軟的肉,或許是互相上萬條觸鬚軟軟擺動着,交換着訊息:在那樣發言、或實踐着其實我們各自接收的「西方」、「二十世紀」、那些卡夫卡啊、波赫士啊、班雅明啊、大江健三郎啊的文學列陣後面,我在我所從出的國度、社會、文明,並不該、不會,無意義的暴衝、攻擊他人,讓人受辱而陷於窘境,或是,我其實是在一個中國人式的長幼尊卑的人情秩序裏。或是,我們是否可以不要從杜甫李白、《三國演義》、《紅樓夢》,為起點來談「時間」這件事?或是,這件事其實已極難極難被這樣討論了。「時間」的描述一旦被啟動,似乎那種鐘錶被拆解、金屬生鏽的尖銳感、或機油的腥味,都刺扎進我們的舌蕾、衣服貼處下的身體、說話帶着的腔調、我童年玩的小汽車玩具小火車玩具廉價太空船玩具、街景的那些殖民建築遺跡,或是我父親、母親各自差異那麼大的家族故事……。它好像和那個我想到描述的、透明搖曳的、或抽象的「時間」、愈泅泳往它的池底探去,就愈層層被隔擋在撥手的多出來的膠膜外,眼壓和耳壓愈大,到最後鼻孔也冒出一縷縷血絲,這個「我」反而愈往上浮。
(本篇為《有一年我在香港》上篇,敬請期待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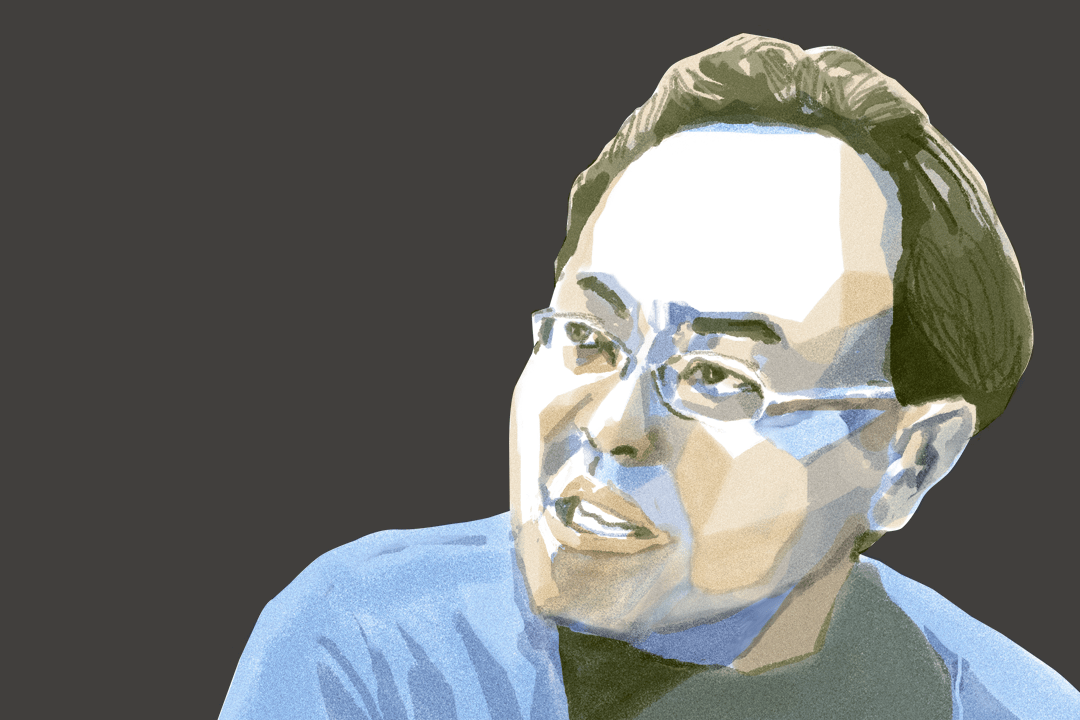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