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張炳良教授,我腦海中總會浮現一個學者的形象;即使進入政府,政府通訊錄的名稱仍是頂着「教授」的名銜,與其助理閒談,也總是說教授的意見是什麼,而不是局長的意思是什麼。
與龍應台先生以一個文人的姿態走入台北政府相類似,張炳良不只是一個普通學者,還是民主黨內的前匯點派(匯點是香港早期的論政團體,後來與香港民主同盟合組成民主黨),以非建制在野學者的背景,在2012年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政府中,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由於張炳良的研究及政治背景,其出任局長時,公民社會及政黨均對其如何處理香港房屋問題,有相當大的期望。
自1998年之後,香港便再沒有一份指導未來香港十年的房屋政策藍圖,而張氏制訂的「長遠房屋策略」,則是他在局長任內(2012-2017)的一項主要工作。張炳良在新作《不能迴避的現實》中,便回顧了2012年至2017年的局長生涯中,在房屋及運輸的政策層面上,所推動的措施及面對的挑戰。對於關心香港房屋及運輸政策制定過程的讀者,此書是很好的參考。
身為香港民間房屋政策的倡議者,筆者曾多次以智庫及倡議團體「影子長策會」的身分,多次與時任局長張炳良就其主力推銷的「長遠房屋策略」交流。如何掌握「長遠房屋策略」的成敗,是評價張政策成敗的關鍵,亦是理解本書脈絡重要的切入點。因此本文主要集中回應張氏書中的房屋內容。
《不能迴避的現實》房屋篇
作者:張炳良
出版日期:2018/07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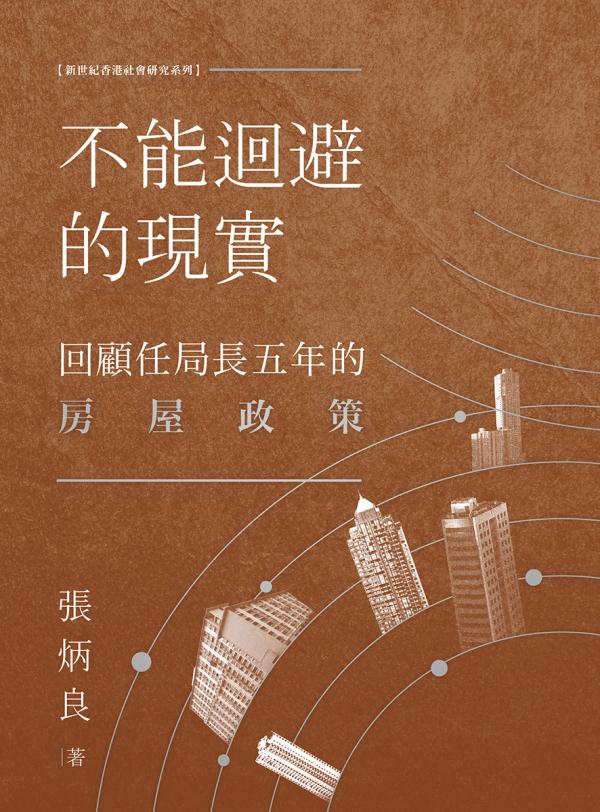
「長遠房屋策略」的歷史背景
講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必須要理解其歷史背景。現時香港公營房屋(即類似內地的公租房及安居房)與私人樓宇在整個房屋市場中各佔大約一半的比例,其實並不是香港的歷史常態。雖然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推行「十年建屋計劃」,計劃用十年為香港市民提供可供180萬人口居住的公營房屋,但並非是什麼殖民政府的德政。因為當時殖民政府的這種考慮,是基於六十年代香港發生的六七暴動為民怨基點,以及受到當時英國工黨勢力抬頭、歐洲福利主義成為全球政府施政參考的影響。張炳良將這種施政思想稱為「剩餘主義福利觀」(welfare residualism),認為「十年建屋計劃」是一種捨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背離「積極不干預」傳統,接近社會主義式的十年出租公屋興建大計。
這種高速興建公屋的計劃,同時配合着香港衛星新市鎮的興建,以現代主義工業城市規劃為藍本,使得香港出現大量「新型」的廉租房屋,同時為新興工業帶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較早期的新市鎮,例如荃灣及葵青等,都帶有居所鄰近輕工業的規劃格局。
當然,隨着日後輕工業大幅撤出香港,經濟結構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居民要尋找工作機會就只能離開新市鎮到服務業工種集中的市區。這為整個香港帶來沉重的跨區交通壓力,亦為張炳良的交通規劃帶來極大挑戰;然而,他在任內卻始終未有推動「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並未解決「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懸而未決的交通規劃失衡格局。
經過大規模的建屋和規劃改造,香港的公私營房屋比例,遂出現張氏所指的「私營較大、公營稍小」的格局:截至2018年第1季,香港共有30.8%的人口居住在出租公營房屋,再加上15%的人口居住在各種由政府補貼的資助房屋,總共約有45%的香港人居於政府全資或半資擁有的公營房屋,其餘約55%的人口則是私人樓宇的業主及租戶。

「長遠房屋策略」抗衡住屋商品化的嘗試
可見,香港的房屋策略,其實一直以私人市場為主導。早於1987年,港英政府便提出「私營部門優先」的概念,提供大量貸款計劃讓公屋住戶離開公屋到私人市場置業;1995年又提出夾心階層置業計劃。到了特區政府成立,不論是董建華時期提出七成香港市民自置居所的目標,還是曾蔭權年代大幅減建公屋的舉措,都是為求穩定私人房屋市場。
張炳良在書中自稱擁有「親公營房屋」的DNA,其2013年提出的「長遠房屋策略」的焦點,是確立此後十年內(2016-2025年),新增房屋單位公私營比例為六比四的政策目標:在新增的480000個單位當中,有28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當中包括200000個出租公屋單位。這個房屋比例和單位需求的推算,亦直接套用於現時香港「土地大辯論」中未來三十年所需要的房屋用地估算。
經歷董建華年代的「八萬五」政策(註一),很多香港人都抱有「興建公營房屋=推倒香港樓市」的迷思,在張炳良上任之前,香港的公營房屋供應創下歷年新低,更有好幾年停止興建居屋,令香港的公營房屋供應出現短缺;更重要的,是全球各地推動的金融量化寬鬆措施下,國際熱錢湧港大幅推高香港的樓價及租金,「劏房」再次成為基層住屋的關鍵詞,公屋的輪候人數年年創新高。筆者和一班民間學者、基層房屋團體和關心房屋政策的研究員共同創立的「影子長策會」,便希望能夠遊說張炳良,在2013年的「長遠房屋策略」訂立幾項有助改善基層住屋狀況的政策建議。
「影子長策會」向政府建議
可惜,似乎最後張炳良仍然不敵壓力,只能夠提出「新增」房屋單位公私營比例六比四的政策目標,意味着未能夠完全扭轉香港房屋「私營較大、公營稍小」的格局。我作為倡議訂立公私營比例的民間團體的一員,對於政府未能完全落實新發展區提升公營房屋、尤其是出租公屋的比例,自然會覺得「長遠房屋策略」未竟全功。
由於在張炳良任內未能夠完全確立「公營房屋優先」的講法,他卸任局長後,不但有部分新發展區未能夠守住公私營六四比的界線,新政府更引入大量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包括撥出部分出租公屋供應作為「綠置居」出售;甚至近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要將啟德發展區及安德臣石礦場發展區九幅私樓的地皮,轉為公營房屋發展,其實亦很有可能只提供給首次置業的港人購買「首置上車盤」。至此,張氏於「長遠房屋策略」抗衡住屋商品化的嘗試,已經被破壞得所剩無幾。儘管他於書中強調不希望評論現屆林鄭政府的舉措,但正如周永新教授在明報的評論文章所指,香港的房屋政策左搖右擺,公私營房屋比例將在「置業主導」下再次失衡,這正是特區政府「不能迴避的現實」。

不能迴避的現實:有供應不等於可負擔
整本《不能迴避的現實》一直迴避的問題,是為什麼香港的房屋政策,一直未能夠突破「供應主導」的窠臼,把香港房屋不能負擔的現實,歸咎於地區人士和政團的反對。
張炳良在書中回顧當時推出《長遠房屋策略》的考量,認為要改變香港長期以來,房屋供應依靠私人市場,公營房屋只是補助中低收入階層,而非供應主流的「共識」,只能夠靠訂立一個「十年延展房屋供應目標」,因應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供應數目作出靈活的評估及修正。
問題是,這種以「供應」為主導的應對思維,其實完全忽略了「需求」對房屋價格的巨大影響。筆者亦曾經多次撰文提及過,政府只顧重建所謂的置業階梯,過份強調住屋的交換價值,那麼即便提供大量的土地及房屋供應,在投資需求熾熱的現況下,再多的供應,亦只會成為房價繼續越升越有的助燃劑,無助令香港住屋變得可負擔。
除了1998年特區政府成立初年,香港公營房屋的比例有短暫上升之外,基本上過去三十年整個公營房屋比例,都是處於穩步下降的趨勢,私營房屋的比例卻是不斷上揚(註二)。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房屋私有化浪潮下,香港的高房價現象,在沒有諸如第二套住屋空置稅、及沒有重置1998年被取消的「租金管制」等需求管理措施的情形下,無論提供多少的供應,都會轉化成為「剛性」的投資需求,而其又進一步(錯誤)印證提供更多「供應」之必需,直至樓價泡沫爆破。
最後簡單回應書中張炳良的感慨:他認為政府房屋供應的大局,「為多方及多重的小局所包圍、所肢解,處於膠著」。我的回應是:那要看政府所看重的,是什麼樣的大局;而被視為是小局的,又是什麼。
民間的確未必有全面的,或所謂「正確」的方案可以全面照顧所有人的需要,但我們所提出的,卻是最弱勢、最迫切、而又最為人所忽略的群組需要。當年影子長策會提出以「住屋權」滿足基層的住屋需要,以提升劏房戶的基本人均居住面積作為房屋政策的目標。到了今時今日,「基層」除了在政府的土地大辯論中淪為其騎劫環保團體保育訴求的籌碼,現時的政府代表,又是否有真正的大局觀,去改變現時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放棄以公私合營的方式圈地興建首置上車盤,而從真正的公眾利益出發,興建更多公眾可負擔的出租公屋,以及與市場炒賣隔絕的居屋呢?
看不見的公義:大局觀下被消音的弱勢
張炳良在書中直言:「房屋土地供應本應是當前最大的公義問題,可是不少社會團體和有影響力人士卻在時刻搬弄龍門大談其他的社群公義。」這句評論,反映出張氏「效益主義式」(utilitarianistic)的價值觀:政策只要能夠讓最大多數人達致最大的利益,這便是一個合乎公義的政策。
問題是效益主義之所以能夠達致最大的效益,往往是倚靠犧性少數人的權益來實現。在這種價值觀下催生的政策,往往會令弱勢被消音,或者在主流的論述下,被扭曲為一班但求為一己私利而反對開發的「地區人士」。在這些政策制訂者的眼中,房屋不再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所,而是被化約為可加可減可調整的「單位供應」與「資源分配」,如何「最大化」供應才是他們所關注的,當中被犧牲掉的,例如因為爭取健康社區環境而被標籤為「鄰避效應」(Not-in-my-backyard,形容社區人士反對在居住社區興建厭惡性設施或者是影響居住環境的發展計劃的現象)的居民,都可能成為他們眼中的障礙和旁枝末節。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最觸動人心的核心理論,就是要建立一個制度安排是對社會最為弱勢的人最為有利(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的社會。原因並非是張氏所指的「社群公義」,而是由這種價值觀引申出來的政策和政治制度,才最能夠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最能夠反映在社會之中經歷種種不幸的人,如何透過一個公平互惠的合作體系,成為一個也能夠有自己人生計劃、有能力實踐這些計劃的自由人。
張炳良自己在書中,其實亦提出了一個效益主義政策觀所帶來的兩難,只是他可能並不自覺:原來香港的土地分配,往往是重私人輕公營,分配給香港房屋委員會(即香港負責興建公屋的法定機構)用作興建公屋的土地,絕大部分並非「熟地」(即已經平整好的土地),仍需要進行大量的進行清拆、平整地盤、重置設施及提供基建的程序,以至由搬出土地至興建公屋,往往至少需要三、四年的時間;但私人發展商從發展局勾出的地皮卻大多是熟地,可以即買即動工。
為什麼會這樣呢?筆者認為,在興建公屋與私人樓宇之間,負責公屋興建的運輸及房屋局在整個的政府架構「大局」中,淪為眾多包圍「大局」的「小局」之一,只是看顧提供公營房屋的「社群公義」,未能為香港整體的經濟效益最大化,所以必須讓路予代表香港私樓買賣與房地產利益攸關的發展局,調撥大量優質的熟地予私人發展。這個格局到了今時今日的土地大辯論仍是沒有改變,整個東大嶼計劃填海過千公頃,也不是用來興建住宅的,而是讓位予有國家戰略價值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在整個大灣區的經濟格局下,為小民提供公營房屋的社群公義,又算得上什麼?
張炳良自己在書中,其實亦提出了一個效益主義政策觀所帶來的兩難,只是他可能並不自覺:原來香港的土地分配,往往是重私人輕公營。
不得不指出一個關於公私營地皮比例的常見誤區:不少論者認為公屋與私樓的供應比例是零和遊戲,卻忽略了兩者之間發展密度的巨大差異。其實公營房屋使用地皮的效率更高,每公頃土地能夠比私樓提供更多的單位,所以只要稍稍增加公營地皮的比例,便可大幅提升全港單位供應的效益。然而政府恰在此處體現了其矛盾的「大局觀」:「大局」上必須保障私營單位供應,但卻有意不提及密度差異的決定性影響,使得公營地皮的比例無法增加。
歷史不能重寫,假如張炳良就任的,是「房屋規劃及地政局」局長,而不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其全部行政資源得以投入在一個板塊上時,或者他的「長遠房屋策略」能夠更為扭轉整個私人為主導的「房屋政策傳統」。他自己也寫得明白,「土地規劃」和「房屋政策」分屬兩個有不同KPI(主要表現指標)的政策局各自統領,房屋局成為弱勢也是可預期的,在大格局環境難改的前提下,只能訴諸於公屋的「資源分配優化」,並把供應不夠的問題歸咎於社區的反對。
張炳良的五年任期過去,結果可以說是對提倡公營房屋優先者的最大反諷:2012-17年公屋的平均興建量約為每年13000個,大概僅有過去香港三十五年每年平均(22000個)的六成,這種供應滯後與公私營比例失衡所反映的,就是香港這個城市對生活方式選擇和城市規劃遠景的價值觀。
(龍子維,香港民間房屋倡議團體「影子長策會」成員)
註一:「八萬五政策」,指董建華時期每年建屋(公營及私營)不少於85000個單位的政策目標,令10年內全香港有70%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註二: 出租公屋的比例於1991年升至最高峰超過全港人口比例的35%,其後回落到30%左右,而公營自置居所的比例則在2001年達至最高峰,其後一直維持在15%左右,所以香港公營房屋的比例一直維持在45-50%,並呈緩慢下降的趨勢。整理自《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


Wiki: 先生是称谓,字面的意思表示: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以此外延为对有一定地位,学识,资格的人可以称为先生。
漢語中「先生」一詞的原意是對有學問、知識者(老師)的尊稱,男女皆可用,但並非所有人都可稱為先生。
噢!是的。把女性稱為先生,五四時期已有。但我不知其出處。
可以把男性稱為女士嗎?似乎這個時代,這樣稱呼更合乎潮流。跨性别、跨稱謂嘛!
公私營房屋的餅圖,四個數字加起來是99.5,小編也意味深長地留了一小塊未標出的灰色塊。那0.5%,莫不是「無居所人士」?
女性向來亦可以稱先生,先生並不是男性專用指謂詞。
那是敬称啦。。
「與龍應台先生以...」我知道台灣有一位女士叫龍應台,不知文中這位龍應台先生是何許人。
哪有什么大局,只有利益。
要說「大局」,除了公私營比例外就不可能忽略每日150的入口住屋需求和新界高球棕地等反映官商紳黑的問題。迴避根源而盲目尋找解決方法,未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