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已於2020年2月18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閲。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周雪光講了自己家庭的故事。
「我母親快85歲了,本來家裏有保姆每天上門照顧,現在因為疫情隔離,保姆不能上門,只能一人在家。母親住在單位大院裏,雖然獨自生活,但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得到關愛⋯⋯春節期間存了很多食品,對她的基本生活沒有太大影響。母親跟我講,她困在樓上,下去倒垃圾很困難。但對門鄰居很有愛心,伸出援助之手,讓母親把垃圾放在門外,她幫助把垃圾倒掉⋯⋯」
日常生活困難通過鄰里相助解決了,周雪光想,這是一筆民間社會的文化資源。
疫情中,來自海內外的公民互助和自救是觀察中國民間的一個重要窗口,而「吹哨人」李文亮的去世,也在民間掀起極大波瀾。周雪光認為李的故事是眾多人慘烈遭遇的一個活生生的具像,「這類情景普遍存在,是大的官僚體制環境造成的。只有政府和整個社會進行認真反思,在制度上做出實質性改進,才會避免類似的災難。」
「反思才能對得起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周雪光說。他再次跟記者提起李文亮那句被廣為傳頌的遺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應該是我們反思這個疫情災難的起點。」
如何看待政治邏輯與民眾生存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以下為端傳媒和周雪光的訪談節錄。

端=端傳媒
周=周雪光
端: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運作邏輯是什麼?是否仍符合從上到下層層加碼、越到基層執行似乎越厲害的運動式治理模式?運動式治理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周:對這種大規模突發事件,任何一個國家、組織都會全力動員起來應對,也都會採取緊急動員的形式。中國這方面的現象比較特別,因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通過運動式治理來執行政策、解決問題,整個官僚體制可以說是按照運動式治理的方式構建的,已經高度適應這種方式。
關於層層加碼,在學術文獻中已有很多討論。在我看來,層層加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各級政府向上負責的定勢,因為擔心執行過程出問題,做不下去,所以給下級更大壓力,以便可以確保完成任務,不出紕漏。
但這種說法用在現在的疫情動員似乎不太合適。我認為運動式治理、或者說自上而下推行指令,對武漢疫情和SARS來說,都是非常有效的。這次疫情和SARS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針對疫情的最好對策是相互隔離、各自為政,各個地方嚴加看守,杜絕人口流動;而民眾因為擔心傳染危險,也積極配合。在這個事件中,中央政府關於各自隔離的政策意圖、與解決流行病危機的基本原則、與地方性利益和民眾期待十分吻合,所以從中央到地方到民眾,可以非常有效地執行下去。
但並不是說這種自上而下的動員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效。舉個例子,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許多地區的民眾食不果腹,飢餓而死。根據已有研究,有些地方的饑民試圖外出討飯為生,甚至有的村莊集體組織起來外出討飯,這樣的舉措可以為饑民提供生存機會。但當時的官僚機構把外出饑民攔截下來,困在當地,造成了大面積的飢餓死亡,成為歷史上的巨大災難。
也就說,本來可以通過信息流動誘導食品流動或外出逃荒,讓飢民存活,但在官僚機器的強制下,這些機會都失去了。在這裏,我們看到,自上而下的意圖與民眾利益是對立衝突的。在這種情形下,政治的邏輯與民眾的生存權利發生了尖鋭衝突。
舉國體制、剛性政府在應對危機中如何行為才是良策,需要具體場景具體分析。如果以為嚴格執行指令的剛性政府和運動式治理就是成功樣板,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們可能正是導致危機的淵源。運動式治理的力度越大,導致的災難就會越大。

端: 中央早在1月25日成立小組「全國一盤棋」管理防疫工作,可是到現在為止,中央似乎都是一個「缺席」的狀態,那種高效劃一的效率和領導人的在場感都並不強。尤其是在武漢,似乎物資一直不到位,人們想像中的舉國之力大舉進入武漢和湖北的情況,似乎除了醫療隊進駐之外也沒有發生。各地也有指揮混亂的情況。你怎麼看這樣一種「舉國體制」的想像和現實的落差?(採訪時間是2月5日,2月13日,中央調整了湖北的官員任命)
周:在這樣一個重大突發事件面前,所有人包括各級領導官員措手不及、應對慌亂,這是不難理解的。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封城,民眾大面積受災,需要巨大規模的人力物力救援,起初的混亂和各種問題是可以預期的。
「如果目標確定,路徑清楚,那麼舉國體制與頂層設計有優勢來集中資源來推行政策執行。但這種突發事件打亂了常規的決策過程和行為,需要各級政府有高度的靈活性和應對能力。」
在我看來,如果目標確定,路徑清楚,那麼舉國體制與頂層設計有優勢來集中資源來推行政策執行。但這種突發事件打亂了常規的決策過程和行為,需要各級政府有高度的靈活性和應對能力。而這種能力又恰恰是現在這個越來越剛性的官僚體制所匱乏的。
在早期階段疫情突發事件面前,決策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和好的信息,這兩者在起初的決策過程中都缺位,拖延了決策時機,而官員們都在等待自上而下的指令才能有所行動。這種體制恰恰表現出了它的僵硬性和脆弱性,不適合應對這類危機事件。
端:關於政府的應對措施,公眾討論得比較多的是政府採取不同程度的檢疫隔離等舉措,減少了人們的流動自由。你怎麼看這些做法?
周:我不是流行病學領域的專家,不能提出有價值的判斷。直觀上,檢疫隔離是應對流行病的基本對策。但我要強調,這只是針對目前傳染病疫情的這個例子而言,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把這個場景下的成功對策推廣成一般性政策,則是一個「組織學習」的陷阱。我們不能毫無區別地為剛性體制唱讚歌。
端:從區域角度看,中國不同地方政府應對疫情的措施似乎各有特色。一種觀點就認為,相比湖北,像四川、河南、上海等地就要做得好得多。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它們之間又有什麼類似的地方嗎?
周:我的觀察是,在應對疫情這個突發事件時,中央政府一開始也沒有明確具體的指令,只是一些原則性說法,這就給各個屬地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可以按照當地情況採取各種措施。所以,我們看到了這種不同省份明顯的差異性。
這種地方性差異在中國一直存在,也是中國特色,只是有時是大張旗鼓的,有時是隱蔽行事的。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和流動已經減緩了地方性差異,集權體制也在試圖消除區域性差異。
但我們可以看到,在重大的危機面前,各地政府和地方性組織因地制宜的對策反應,適合當地情況,所以行之有效。如何在國家權力和地方性自治間保持一個良好的平衡,對於一個規模大、地區性差異大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端:這是否也是短暫的無中央狀態帶來的「自由」空間?或者說是倒逼出來的反應?技術官僚在其中的角色是什麼?你強調官僚體制的自上而下造成了政府(及官員)的惰性,也造成了執行的延遲。但我們似乎也觀察到一些「自上而下」失效的現象。比如說,許多城市實行「封閉式管理」,有些物業為了隔絕病毒傳播,還不讓快遞員進小區,地方之間還互相搶奪物資,而中央部委需要不斷「矯正」這些行為。為什麼中央協調在這裏似乎失靈了,地方會藉此擴充權力嗎?
周:可以說,在應對災情事件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一個短暫的「放權」階段。中央政府只是提出一些原則性說法。各地的多樣化舉措,反映出各地在利用自己的地方性資源來應對危機。因為每個地區的疫情不同,資源不同,所以具體舉措上可能有不少差異。
但到後來,又可以感受到各地官員的口號表態趨於雷同,在象徵符號上和中央保持一致。「隔離禁流」這個控制流行病的基本原則在各地都是明確無疑的,所以在大的方面,各地還是很相似的。
另外是,我們也看到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對外地人,特別是來自武漢人的排斥,缺乏基本的同情心。聽說許多地方的賓館都拒絕武漢人入住。在防止病毒傳染的場景下,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總是要給流落失所的武漢人有所安置吧?民眾有恐懼心理,那麼政府官員呢?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沒有聽說各地政府有所作為。在中國大一統體制下,政府官員會產生這麼大的排斥性,令人吃驚。
一個社會需要有對人類最基本價值的尊重,對於落難的弱勢群體伸手相助。這麼多年來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到底在教育、培養什麼樣的社會價值,這很值得反思。
端:除了政府,民間社會在此次疫情應對中也發揮了作用,你對這次民間社會在應對疫情方面的表現有什麼觀察嗎?它背後反映出怎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制度結構?
周:我倒覺得恰恰相反,民間社會在這次疫情裏發揮的作用非常不明顯。舉個例子,在當年汶川大地震時,民間社會裏的救助活動,包括捐款和參與救助,熱情高漲,行為踴躍。這次我看到的是民間社會或者社會組織的萎縮。在武漢封城的早期階段,除了個別例子如個人組織起來為醫生開車之外,沒有聽到太多有關民間組織活動的情景。最近一段時間才聽到讀到更多的民眾自發組織起來互助的故事。海外的許多華人、留學生也積極募捐救援,這是多年來一直有的傳統。
但我們讀到許多各地救援的事例,似乎大多是在政府統一動員下發揮作用,比如說居委會或社區幹部,他們屬於政府組織或者政府組織的延伸機構,而不是民間社會本身。在重大災難生死攸關面前,在醫生、患者面臨病毒傳染的生命危險關口,居然規定所有捐贈資源必須經過官方紅會,實在是匪夷所思。
如果政府把所有方面都管起來,所謂無死角,無縫隙,這需要多大的組織體制和人員才能做到?政府現在也成立了很多所謂社會組織,但它們更像是政府延長的臂膀,而不是自主運行的主體。他們的行為邏輯和政府沒有太大區別。當政府不作為的時候,它們也不能作為。當政府作為但出現失誤時,它們也難以糾偏彌補。
當政府沒有民間社會對它的約束和平衡,極易產生重大失誤。在這次疫情中,我們正感受到民間社會、包括醫學界專業性萎縮,所導致的惡果。
「在這次疫情中,我們正感受到民間社會、包括醫學界專業性萎縮,所導致的惡果。」

端:和民間社會相關,這次公眾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問責,但是至今為止沒有看到如2003年「非典」時那樣的情況,如何解讀這種現象?包括很多人這次看新聞,也覺得中央和地方、不同部門之間都在「甩鍋」,推卸責任。你怎麼看?
周:這麼大的一個事件,造成了這麼大的生命損失,家庭破碎,對民生產生了這麼大影響,大家都情緒激動悲憤,各種問責的呼聲很高,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認為,關於早期階段的信息收集、傳遞過程和實際發生的決策各個環節,我們現在知道的很少。現在談「問責」為時過早。
與對具體當事人的「問責」相比,我覺得更為重要的是反思體制上的問題,推動體制改革,才能減少這類事故對生命、民生的傷害。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許多當事的官員都是在按照制度給他們規定的習慣行事。例如,訓誡李文亮醫生的民警,和發出訓誡指令的上級官員,他們都在扮演這個體制給他們規定的角色。如果不改進體制,其他官員還會扮演同樣的角色,從事同樣的行為。
端:你在論文《黃仁宇悖論與帝國邏輯——以科舉制為線索》中提到,當前中國依然面臨着國家治理中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兩者間的基本矛盾,相反還誘發出新的表現形態,特別表現在強化的組織力度與各群體之間不同訴求之間的緊張和衝突。你認為要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
周:不同社會中有各式各樣的組織制度,各有優劣處。不同國家的制度結構也有各自的特點。從正式制度上來看,如果說從集權到分權是一個連續光譜,那中美在最極端的兩端,中國是在最為集權的一端,美國是在最為分權的一端。
我們需要區分「分權」與「放權」這兩個概念。分權指在法律上固定下來的不同權力的劃分。例如在美國聯邦制中,有些權力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有些權力屬於地方政府(州政府、縣政府等),這些權力的劃分是根本法如憲法所規定下來的,不容改變,這是一個分權結構。
而放權是指中央政府大權在握,擁有無限權力,它有時會下放一部分權力給地方政府,但隨時隨地可以收回來。
分權的好處是化解或分散了很多政治壓力。例如,在美國,公共教育的權力主要在地方政府。如果在這個領域出了問題,地方政府首當其衝,聯邦政府不會承擔壓力,沒有人會到白宮抗議。當政府擁有了所有權力和功勞,它就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和過失。權力和責任是對稱的。
中國國家治理基本矛盾是:一方面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但另一方面又有各種地方性差異,所以這兩者之間產生非常大的基本矛盾。我經常拿中國和歐洲比較,因為中國領土和歐洲差不多,內部差異也非常大,我們可以想像中國國家治理所面臨的挑戰,就相當於整個歐洲要通過一個中央政府管理起來這樣艱難。
有人問,你為什麼不和美國相比?我之所以沒有和美國比,是因為美國這個制度確實非常不一樣。美國的聯邦制在許多方面緩和或解決了這種矛盾。當然,聯邦制可能產生其他問題,比如它資源動員能力比較差。
我覺得基本矛盾在近些年日益突出,因為現在的一統體制越來越剛性,越來越強化,它和有效治理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從很大意義上來講,這次疫情的發展過程,包括官員的思維習慣,都是其中的表現形式。
「社會發展越來越多元、複雜,但是中國用來管理社會的官僚組織反而越來越單一、剛性,官僚組織越來越龐大,等級色彩越來越強烈,向上負責傾向越來越凸顯,因此產生很多惰性,導致了這個基本矛盾日益突出。」
社會發展越來越多元、複雜,但是中國用來管理社會的官僚組織反而越來越單一、剛性,官僚組織越來越龐大,等級色彩越來越強烈,向上負責傾向越來越凸顯,因此產生很多惰性,導致了這個基本矛盾日益突出。
當然,中國各地政府組織還不是像正式制度要求那樣單一僵硬,這是因為中國在實際運行裏面有很多非正式制度來緩和與平衡這種剛性的正式制度。社會正在越來越多元化,有各種利益呼聲。
當務之急不是社會去適應政府,而是政府要適應社會。政府需要有更多元化的結構來適應多元化的社會。最重要就是允許大家可以討論,把問題提出來,通過討論、爭辯和各地在不同方向上的嘗試實踐,找到行之有效的治理架構。
端:比如有哪些可參考的治理架構?
周:比如類似聯邦制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可以討論?很明顯,在這麼大一個國家裏面,如果什麼事情都要中央政府來掌控,地方政府沒有制度上保證的權力,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矛盾永遠解決不了,只能一鬆一緊,周而復始。要建立制度上的分權,而不是臨時性的放權,才能有穩定的制度保障。但這個思路和現在運行的政治邏輯不一致,所以我覺得很難做到。
還有一個,建立更多可以替代政府功能的其他組織形式,比如說有些事情政府可以不管,可以交給民間社會來做,但這個又和現在推動的一元化領導相沖突。
我希望這是一個中國政府組織學習改進的機會,這樣才能對得起民眾付出的這麼大代價,對得起那麼多失去的生命。荒謬的決策剝奪了這些生命,影響了多少家庭,包括這些患者將來可能的很多後果,很多民眾的正常生活、企業的運行被打亂了。許多後果我們現在還很難預測。
周雪光也推薦了兩本思考疫情相關的書:
1、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貧困與饑荒》。這本書提出,大規模餓死人的饑荒,在市場社會極少發生,而更多發生在高度集權的強政府社會。當某地糧食不夠導致饑饉情況時,市場信息流通就會導致糧食流動進入這個地區,或者人們可以流動出去。武漢疫情的危機也提出了相關的問題:什麼樣的治理模式有利於民生?有利於人最基本的生活價值?有利於避免或更好地應對這種大的災難?這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2、法國漢學家魏丕信寫的《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主要講述分析了清朝政府怎麼應對大的自然災害,其中也涉及到信息流動傳遞、皇權與官僚制間關係、動員體制,以及民間社會參與賑災救荒的一系列相關問題。這次抗疫也再次提出了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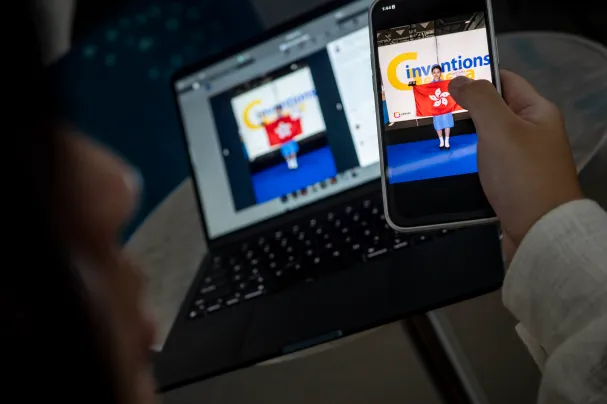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好大的格局,没有太多主管色彩,不失为一家之言。
好文章,平和冷静的思考
@學長,為什麼威權可以建立並長存?為什麼人為災難可以一次次發生和擴大?為什麼每次災難后都有人由衷地歲月靜好,忠誠支持?難道將所有原因怪罪於體制就可以成為無辜受害者角色?那麼自己作為體制的一部分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微小得扇動了一下翅膀?
捉个虫,是不是把黄宗羲定律搞成了黄仁宇定律
周老师真的很敢言,社会学家少有的站出来发出应有的声音,不过以后恐怕大陆院校再难听到他的讲座了
樓下,有什麼樣的people就有什麼樣的government這種話只適合有選舉的地方。怪罪一個威權獨裁體制下人民,怕是你打錯了方向。
微信上查不到周雪光了
放权的话就会有薄的存在,这是习惧怕的
大部分都完全同意。只是我感觉他没太了解到民间救助的力量,可能是他看的新闻来源的问题。比如他明显不知道封城当天就出现了自发的志愿者车队。但我是参与了这次的志愿者活动的,我的感觉反而是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规模的民间自我动员。虽然很混乱但是已经看到了潜能。
學者和記者喜歡採取从治理者角度的一種“从上而下”分析,但容易忘了另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有什麼樣的people就有什麼樣的Government,不信這次風波過後我們來看,其實多次循環已經無須贅言,唉!
好文解惑。关于中央的缺席、迟迟不问责、地方政府响应缓慢等。一个不太认同的点,民间力量其实不弱。甚至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在不能出门不方便交流的情况下,还能组织物资援助和各方面协调,其实比地临时的援助更为强大。
我相信寧左勿右可以改變物理定律,可惜這世界不只沒有普世價值,連普世物理定律也是沒有的。
据我观察还有一个相当令人悲观的事实
尽管大灾面前舆论变得似乎宽容了一些,允许质疑武汉政府
但是我同样看到有许多人抱着一种“都是下面的错!”,“你敢质疑制度?”的态度在攻击发声者,仿佛制度是个死区碰不得
好文
中共成功的在十七年後再次完全複製了SARS瘟疫,徹底反映了這個政權毫無一點改變,就是瞞瞞瞞,鬥鬥鬥,洗洗洗。
如果這就是所謂即將取代西方的“中國模式”,那我寧願它被西方孤立起來徹底打垮。
最近歸納起來的聲音都是需要體制改革。但問題是除非生死存亡,有人拿槍指著黨中央的頭,或許他們會改。而事實是現在任何人光是拿起磚頭都會被中共拿槍指著頭,錄上一段公開認罪視頻。別忘了,隨著肺炎病毒進化的,還有老大哥的大數據AI追蹤分析技術。
非常精彩有深度的訪談,分析一針見血。
這篇訪談真好,這就是問題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