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兩個月,輿論情緒由「四月之聲」傳遞的肅穆和悲情,轉變爲有強烈割席意味的「最後一代」。
「最後一代」出自5月11日流傳的一段視頻,視頻中,上海一個穿着防護服的警察威脅一位不願意集中隔離的居民:「如果你不執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對你進行處罰,進行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居民立即反擊:「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這段自白引起大量共鳴,人們在社交媒體重複這個口號,並注入自己的理解。一位微博網民形容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這是在報復誰,但我的確有種報復的快感。」1984年的電影《譚嗣同》中一句台詞也被重新找出作應景註腳:「這樣的中國,多一個孩子不是多一個奴隸嗎?」審查系統很快在社交媒體屏蔽了關鍵詞「最後一代」,切斷民意的聚集。
「最後一代」,敵人的顯影
「影響三代」具體指的是,如果拒絕隔離的居民被行政或刑事處罰,他的親屬和後代有可能因此在考取公務員的時候無法通過政治審查。
上海警察的「影響你的三代」並非隨口胡謅,相反,這是執法者對民衆恐懼的準確把握,也是策略性選擇的行之有效的話術。「影響三代」具體指的是,如果拒絕隔離的居民被行政或刑事處罰,他的親屬和後代有可能因此在考取公務員的時候無法通過政治審查。把政審當作威脅,背後是體制對自己吸引力的自信。事實上,「上岸」(指參加公務員考試併成功被錄取)的確是最近幾年大學畢業生的主流職業選擇,熱門程度已經超過進入大型互聯網公司。
在經驗分享型社交媒體小紅書上有關「上岸」的討論中,一位網民問自己的爺爺年輕時因打架而坐牢,會不會影響自己考公務員,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會,影響三代」。但是,且不論幾十年前的刑事案底是否完整保留在今天的系統中,實際上不同政府部門在招聘時的政審內容和範圍都有差異,「影響三代」是十分不準確的概括,但這一說法卻在年輕一代的求職經驗分享中沉澱爲不可撼動的「常識」。
這種「常識」具有極高的認受性,同樣在小紅書,一個律師提出「一人坐牢影響三代公平嗎」的問題,評論是壓倒性的「支持」。在一個幾乎不討論政治議題的平台上,小紅書用戶無意中袒露的意識形態傾向,更能讓人窺見主流意見的模樣。「影響三代」繼續演繹,是體制掌握對個人生活的絕對裁量權,不僅影響職業,還在身體上徹底支配個人,上海封城提前揭開了這種裁量權的謎底——全員核酸,強制轉運,入戶消殺,個人退無可退。
「最後一代」不是憑空出現的口號,在自由主義者的論述中,「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一度非常流行;在女權主義運動的脈絡裏,不婚不育(包含在6b4t中)也早已是反抗手段。「最後一代」沒有創造更多內涵,它的號召力來自對「影響三代」威脅的直接反擊,並整合爲另一種和體制解綁的生活態度,和「影響三代」所代表的主流生活態度分庭抗禮。
在「最後一代」出現之前,「躺平」作爲一種消極反抗的觀念已經流行了一年。《躺平即正義》宣言的提出者駱華忠明確把矛頭指向「工作」,他指出「奮鬥」成功學的虛僞——「我們是不可能富的,因爲人口基數擺在這裏,你平攤一下有多少錢」。「躺平」瞄準的敵人是「內卷」,在2021年「反壟斷」的風潮中,它更多被用來批判資本而不是體制——儘管黨媒旗幟鮮明地駁斥了「躺平」。年輕人「躺平」所反抗的,更多是996的企業文化和剝削的資本家。
直到2022年,清零運動需要動員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個人,先是私人財產(包括寵物)權利被踐踏,再是所有人都失去身體自主權。資本家的靶子無法解釋荒謬的現實,「潤學」由此成爲顯學,潤學的支持者要逃離的是這片土地。「最後一代」比「潤學」更進一步,明確回應的是「影響三代」所代表的體制——要求人民配合集中隔離、配合生三胎的體制。到了這一步,公權力才終於被框定,被確定爲「最後一代」口號所反抗的對象。

媒體人連清川在「最後一代」事件前幾天寫的文章,也和這種情緒不謀而合。連清川因上海封城被隔離在家,想盡辦法都無法回福建見病危的母親最後一面。在母親去世後,連清川悲憤撰文:「但是今天,我和這個體制有了私仇……我期望,所有在這場滅絕人性的事件中,遭到傷害的人,都把自己所收到的傷害,當成一場私仇……我會用私仇的方法,去報復那些阻止我去見媽媽最後一面的人。也不要說,這個體制,都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我確切地知道,誰是我的仇人。」
「最後一代」和「私仇」論都有不加掩飾的報仇心態,前者通過漫長的自戕來報復,後者援引孝道賦予「私仇」道德力量,但即便滿腔怒火,「和這個體制有了私仇」的宣言也不會轉化爲行動。兩種自白宣示的是對公共的不信任和與體制的決裂,是把政治力量看作個人悲劇的最終肇因。
境外勢力敘事難以爲繼
無論多麼違和,境外勢力敘事一旦啓動就無法減速,宣傳機器也只能按照設定好的敵人運轉。
「最後一代」是上海封城集體創傷的民間敘事,體制被錨定爲始作俑者。與此同時,體制也在爲不斷涌現的敵意尋找一個策動者——這是一貫的做法,從香港反修例運動到清零運動,異見者一定是被陰謀反華的境外勢力矇蔽和指使的。但上海封城造成的種種人道災難,卻顯而易見地無法把責任推給境外勢力,要勉強聯繫二者,只能提出「美國投毒」(以舉報爲生的民粹主義領袖孤煙暮蟬正是持這一看法)的陰謀論,但在眼前的社區悲劇中,地緣政治的敵人太過遙遠。
但是,無論多麼違和,境外勢力敘事一旦啓動就無法減速,宣傳機器也只能按照設定好的敵人運轉。4月28日開始,微博、微信公衆號等社交媒體平台開始顯示用戶的IP屬地。這是網信辦「清朗·網絡暴力專項治理行動」的一部分,這一新舉措基於的假設,正是互聯網上針對體制的反對聲音,是境外勢力的水軍行爲。
2021年12月,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新聞發布會上指認民進黨的水軍(「1450」和「塔綠班」),他指責民進黨「豢養各式各樣的網軍來攻擊、誣衊、造謠、抹黑大陸,挑撥離間,破壞兩岸關係」。這一看法在民間也十分普遍,今年3月份,「台灣停電,微博流量狂跌30%」的消息廣爲流傳,儘管微博官方很快出面闢謠,但輿論場的民粹力量相信,微博上藏着大量台灣網軍在傳播謠言、煽動情緒。
新華社下屬的雜誌《半月談》5月1日發文評論「IP屬地」新政,其中有一段寫道:一大批在敏感熱點事件中發表不實言論、煽動網民輿論的「正義人士」們也紛紛「現形」,要麼IP屬地壓根不在當地,要麼批量來源於某些特定國家和地區。這段準備好的判詞撲了空,IP屬地新政並沒有如預期中的揪出境外煽動者,反而意外地讓離岸愛國人士現形。
除了轉型愛國寫手、多次發文承諾不會離開中國、力勸讀者不要移民日本以免被毒死的連岳被發現已經身處日本之外,以號召網絡出征台灣聞名的民粹領袖「帝吧官微」也被發現身處台灣。對於後者,國台辦發言人只能以文不對題的模版尷尬回應:「之前出現過島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有關網站平台蓄意製造事端,破壞兩岸交流氛圍,挑撥兩岸同胞對立的事。這項措施(IP新政)能幫助兩岸同胞擦亮眼睛,更精準辨識和反對離間兩岸同胞感情的惡劣行爲。」
更令IP新政的初衷難以爲繼的是,在社交媒體上,IP屬地爲國外的網民,不僅沒有被當成境外勢力攻擊,反而收到許多豔羨的留言,最被廣爲使用的是「帶我走」。異曲同工的是,5月9日,冰島駐華大使館官方微博發布了一條微博,內容爲冰島取消入境限制,越來越多人準備到冰島旅遊。這條微博的留言區沒有外國大使館常常招致的冷嘲熱諷,只有行爲藝術般的「投誠」,被點贊2.5萬次的留言是「什麼時候接我回家」,此外還有「你們能不能在評論區抽獎發國籍」、「讓我去冰島爲建設冰島出一份自己的力」。
清零運動和IP新政根植於同樣的邏輯,即邊界清晰的「總體安全觀」,實體的邊境關閉對應網絡防火牆,健康碼對應IP屬地,方艙醫院則對應禁言封號的「小黑屋」,病毒和異見的歸宿都是被清零。這一邏輯驅動的是一個身份即立場、流動即危險的社會,它所要抵擋的是來自外部的威脅。但正如IP新政和預期相悖,清零運動的民意基礎也已經非常鬆動,「總體安全觀」要求絕對忠誠、能隨時被動員起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人民。「潤學」和「最後一代」則代表兩種不同方向的反抗,前者是逃離,後者是對索求無度的家長制政府說「不」。

「爲了下一代」和「最後一代」
「最後一代」指向的是行動不可能之後,一代人用沉淪來收場。在這個意義上看,它既是悲壯的,也是犬儒的。
一位網民關於「最後一代」的批判性回應指出,1989年天安門運動時一位騎着單車往廣場去的學生說的是「因爲這是我的責任」,而2022年最激烈的聲音是「這是我們最後一代」。這一批評尖銳地指出,「最後一代」不是一種積極的行動,沒有推動現狀改善的動能,它反映的只是心態的轉變,只是輿論情緒的變化。
須要承認,「最後一代」是悲鳴而不是吶喊,它無法被放在社會脈絡的運動中檢視。社會運動或集體事件,幾乎總是和「下一代」有關。在中國大陸,從2008年汶川地震後推動校舍質量問責的民間人士,到2018年因長春長生疫苗問題而上街示威的家長,「下一代」始終是行動者強烈的動因。在香港,從2012年毛孟靜撰文呼籲「不甘做最後一代香港人的站起來」,到後來佔中運動和反修例運動不同參與者都提及過的「爲了下一代」,基於歷史目光的一代人的責任感從未散去。
但如果存在線性的歷史進程,很難分辨「最後一代」處在歷史的哪一個當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前的集體不滿,還是一個已經被拔去全部反抗獠牙的社會面對高科技時代的威權統治的最後哀鳴?換言之,如果非要比較,香港的「爲了下一代」之後是「最後一代」,還是大陸的「最後一代」後會有「爲了下一代」?
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最後一代」指向的是行動不可能之後,一代人用沉淪來收場。在這個意義上看,它既是悲壯的,也是犬儒的。現實地討論,不婚不育儘管切實妨礙了體制想象一種人丁興旺、維持人口紅利的偉大復興,但它所能造成的傷害也是有限和緩慢的。更何況,「最後一代」是不可能實現的預言,生育一定會繼續(無論多麼勉強),如果期待這一觀念蝴蝶掀起現實政治的風暴,一定是失望收場。
只不過,與其猜測觀念的變化有沒有可能推動歷史進程的改變,還不如說這一心態的轉變,本身就是現實政治風暴的結果,而這場風暴還遠遠未到結束的時候。這可能才是我們能夠從「最後一代」的悲鳴中嗅出的一點歷史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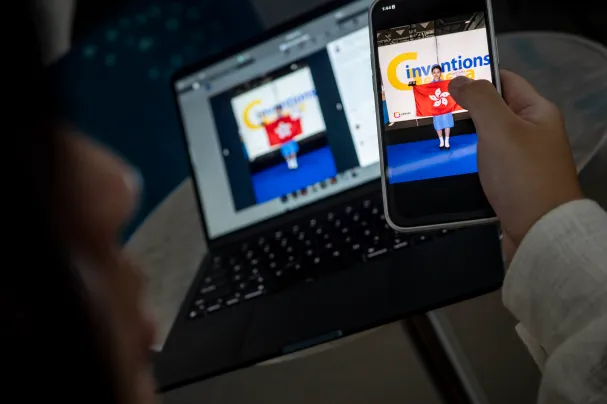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诚然认识到“我们是最后一代”代表着许多刚成为社会中坚阶层的中国人对这个国家和政权的真面目开始有了认识。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或者说并不会真的让这个国家有改变。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阶层的人意识到他们不应该也不能做这个旧时代的“最后一代”,而是要尝试挺身去做开启“新时代”的第一代的话,这个国家也许就会有些希望了吧。
既揣测“即便滿腔怒火,「和這個體制有了私仇」的宣言也不會轉化爲行動”,又认为最后一代是“沉沦”和“犬儒”,作者颇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和傲慢
中國人,體現了天生為奴的習性,跪得太久,忘記如何過站起來了
其实没必要纠正题目中的字眼,臆断作者对中国式反抗的态度与判断。就像文中最后说的那样,无论是”最后一代“、”润“,还是”私仇“,都是历史脉络中特定时期呈现出的特定现象。我觉得作者分析出了社会中民族主义的高潮迭起,青年一代被限制、被挤压的生存状态下无处可退的悲哀,和呈现的各种姿态背后的心理机制,这就挺好的
@maximus 這個不可以量化地比較吧。
輕視他人的感受和經歷,正是小粉紅普遍的舉動
没有行动的行动也是一种行动,就像选择不改变列车轨迹一样。
「生肓一定會繼續」這句似乎很超現實
請問「最後一代」的個體有多絕望悲憤和無路可退,像新疆集中營裡隨時會被槍斃的維吾爾人一樣絕望嗎,像被在元朗地鐵上被白衣人毆打之後還被警察抓捕一樣絕望嗎?
认为“最后一代”是犬儒地向体制反抗并期待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的论断,可谓是冷漠、疏离又共情失败。你真的体会到了绝望而无路可退的个体的悲愤了吗?不要高高在上地说这些愚蠢的废话了!
禍及三代這件事非常變態,這種變態嵌合在瘋狂的中國下又感到突兀的和諧。
个人面对恶政怎么办?社会学角度一般总结出三种办法:表达、变通和退出。但在中国大陆,表达是会被打压的,变通是大多数人选择的方式,但在面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上越来越没有操作空间,退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后一代”更像是逃避,即表达、变通、退出都不可行的时候绝望的选择~
在没有希望的境地,维护自尊的唯一途径,或许只有自我毁灭
当所有的反抗,不能够唤起民众大规模的支持和联动,只能将个人的命运推向悲剧。那最后的抵抗就是,要么逃离,要么苦难到我们这一代为止,奴隶不再繁衍奴隶,则奴隶主们只能再去寻找其他奴隶。
有一類人,一邊覺得反抗無用只識得叫苦,一邊甘願規規矩矩為政權工作續命。旁人譏諷幾句就跳起來,講你怎麼會明白我們的難處。這些人先叫犬儒。只要挖社會主義牆角者,均為吾輩之同志。
非暴力不合作算犬儒?!
不行动也有很多种,比如现在国家要放房地产,这种时候就要捂住钱包,不买房,少消费,存黄金,当然也是有效反抗
这篇文章写的很差。作者对核心概念“行动”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反抗的角度上看 面对不合理政策的“不行动”,“不配合”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建议作者去看一下两本经典著作 James Scott 《弱者的武器:日常抗争》还有Hirschman的exit voice and loyalty。从吐槽八卦到退出都是抵抗 集体行动是需要暗潮涌动铺陈的 不是靠一天或者某一次的愤怒就突然形成的。尤其要知道,CCP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有非常强大的资源崛取和压迫能力 寄希望于单纯某一个事件的反抗和垮台是很幼稚的想法。想要动摇统治的根基就得从资源攫取上去动摇它。这种自下而上的抗争就依赖于日常抗争。而不生就是这么一种大规模的日常抗争形式 绝不仅仅是什么“悲号”(不生本身对资源短缺的贡献是我不认可的,觉得效果有限) 不生看似对政权的直接冲击有限 但是一方面不生的愤怒会帮助引发各种其他形式的日常抗争 提高政权的资源崛起效率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 正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 表达“没有下一代”的那个人才有了抵抗的底气;另一方面也是以不生作为对政策的不配合也是极强的表达愤怒的信号 是一个长时间延续下去的信号 而且可能形成一个share类似grievance的身份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