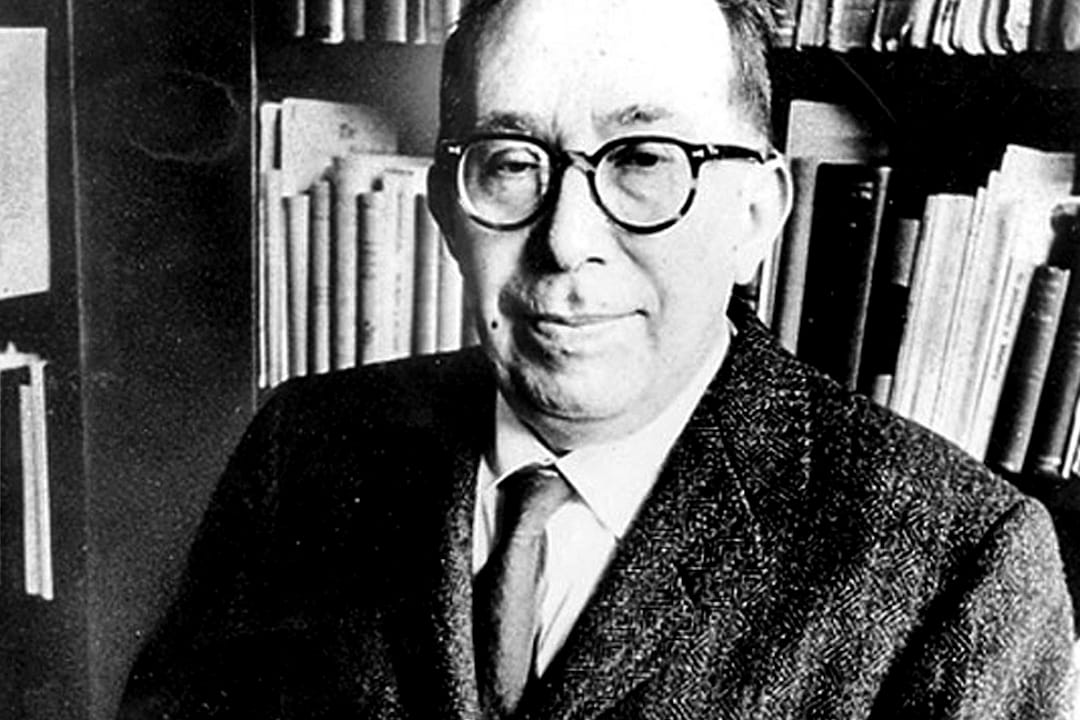2017年12月,我受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思想》季刊之邀,赴台北參加「兩岸三地論壇」。14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周濂老師和來自東京大學的王前老師分別做了題為「施特勞斯與施密特在中國」的報告,我有幸與政治大學的馬愷之老師、高雄中山大學的楊尚儒老師一同擔任第二個報告的評論人。
自2000年以來,劉小楓和甘陽將施密特和施特勞斯引介進中國大陸,此後便形成了一股浩浩蕩蕩的學術潮流。劉小楓利用自己在學術圈和出版界的龐大人脈和資源,組織了對施密特和施特勞斯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翻譯介紹工作。十年下來,二施迅速躋身「被中國大陸翻譯得最多」的外國理論家,如果加上劉小楓主編的「經典與解釋」系列(主要選擇美國施特勞學派的著作或文章,還有以施特勞斯的方法來進行古典學研究的中國學者的文章)、劉小楓自己寫施密特和施特勞斯的著作,以及其友人學生受到施密特和施特勞斯的方法論或問題意識影響而寫成的著作,那說中國大陸存在着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施派」,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如今講到大陸的人文學術界,要繞開這一「中國施派」的影響力,恐怕是自欺欺人。
對這個話題進行與談的四個人,王前老師長期在日本教書,馬愷之老師(Kai Marchal)來自德國,楊尚儒老師在台灣土生土長,而我一直在大陸,雖然說學術無國界,但我們各自的發言,確實都帶有從不同的背景所投射出來的光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