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时,所谓“美国犹太社群游说组织”(例如AIPAC)的影响力向来引发许多争辩以及想像。但晚近半世纪以来,形塑政策、左右大众论述的主要力量其实不是美国犹太社群整体的意向,而是极少数拥有美国犹太社群“代表权”的头人。
这个观点来自史丹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闻学教授和资深媒体人Eric Alterman。身为美国犹太裔的Alterman在2022年底出版《We Are Not One: A History of America’s Fight Over Israel》一书,广泛引用不同组织的档案纪录、不同人物的传记资料,以及新闻报导、民调数据、其他历史学者的研究,分析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犹太社群如何讨论以色列。他的结论是:一群极少数人绑架了整个美国犹太社群,进而绑架整个美国社会谈论以色列的方式。这些极少数的犹太裔菁英与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亦步亦趋,而且近半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社群的组织“彻底不是民主产生:其效忠的对象是保守派金主,而非组织领导人宣称自己所能代表的人群”。
这些少数金主不只有钱,更知道如何运用金钱影响政治,积极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参考对象,同时利用各种方法压制社群内外反对的声音。虽然以色列的犹太人远比美国的犹太人更右翼,但多数时间,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巴勒斯坦、关于美以两国关系的辩论,却反而比在以色列更受到压缩,即使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自由派媒体上,对于巴勒斯坦观点的陈述,甚至还比以色列的自由派大报《国土报》(Haaretz)来得更加单薄。原因正是这些寡头金主的影响力。
在《We Are Not One》里,我们见到的故事是:一小撮人善于利用其他人的沉默,积极抢占论述的空缺,并且打压其他人的声音,让自己能够持续独占发言权。但就是这一群极少数的人,改变了美国犹太社群,甚至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

“替代的上帝”:当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身份
在2013年的一个民调发现,仅有38%的美国犹太人表示相信以色列政府“真心寻求和平”,在年轻世代当中更只有四分之一这么认为,而支持以色列屯垦政策的美国犹太人更仅有13%。当时以“对抗反犹主义歧视”为宗旨的知名组织Anti-Defamation League(简称ADL)领导人Abraham Foxman轻蔑地回应:“听好了,犹太世界组织多得是,这些组织者才是真正付帐单的人”。Foxman 时常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代表”犹太社群抗议各种反犹主义的表现,而且经常指控批评以色列政府的人“反犹”:曾中箭的包括各大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公共电视资深记者﹑甚至卡特总统本人。
Foxman的底气,来自ADL的金主,犹太裔的右翼赌场大亨Sheldon Adelson。在基层犹太裔选民压倒性支持奥巴马的2012年,这位金主在初选期间以超过9,200万美元支持共和党。这也反映了近四十年来美国犹太社群领导人的趋势:即使基层犹太选民高比率支持自由派,但领导人们却频繁和右翼结盟,尤其是最右翼的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他们其实对犹太人充满偏见,但认为支持以色列能“加速上帝的再临”。在Adelson的支持下,ADL财力雄厚,聘请的全职员工就超过三百名,在美国多个州都能建立区域办公室,有助游说选区国会议员。这位金主相当慷慨,甚至让Foxman本人更可以随时调用他的一架私人飞机。
既然有Adelson这样的金主“付帐单”,也难怪在面对对美国广大犹太社群内的不同意见时,Foxman自认有本钱嗤之以鼻。
而像ADL﹑AIPAC这类的组织是怎么变成美国犹太人的“代言人”的?根据Alterman,转捩点出现于1967年:那年埃及等国联军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却在六日之内被以色列彻底击溃,反倒让以色列占领更多土地。这场“六日战争”,直接令美国犹太裔社群的面貌翻天覆地。

在1967年前,多数美国犹太人都没有“以色列情结”:主要犹太组织的刊物的关注重点是美国国内种族平等议题,或是其他社群工作,而以色列议题经常位置靠后、篇幅偏少,甚至只是被放在“海外议题”的大标题下。当时已有几位知名菁英是以色列建国的热切支持者,但一般犹太社群成员、特别是中上阶级犹太人普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有限,《纽约时报》当时的犹太裔老板甚至公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些菁英高度认同美国,不觉得自己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真正的家”,遑论接受“真正的祖国”保护。许多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也更“普世价值”,犹太人所建立的公民组织的关怀,和其他自由派组织其实相差无几。
但六日战争让犹太身份认同变得极其重要。当时美国犹太社群先集体经历以色列可能灭国的恐慌与无力,但在一周之内又迅速感受到大获全胜的骄傲和胜利:在战争之后,犹太社群的报纸里大幅报导各地美国白人的赞叹,犹太人迅速感受到“书呆子”之类的刻板印象被颠覆的自豪:“虽说犹太人很会拿钢笔、提手提箱,但如果有必要,犹太人也很能操作来福枪和坦克车。”那时美国媒体刊登的以色列士兵照片魁梧潇洒,被专研美国文化的权威犹太裔学者Amy Kaplan形容成“兼具军事胜利和阳刚性魅力的图像”。
那时美国犹太组织开始主打为以色列募捐,捐款爆增四倍以上,许多美国犹太人开始以捐款、以支持以色列为展现自己犹太认同的手段。50年代的美国犹太组织其实山头林立,但在1967年的分水岭之后,以“为以色列政府行动”为职志的金主开始取得领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各种社区动员、国会游说、政策智库、媒体论述的组织。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尤其奖励这种大型的组织,既可以在各州、各地区发展,又可以在联邦层级一致统筹,运用金钱和人脉发挥影响力,AIPAC以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通常简称CoP)皆是在此一背景下,逐渐在政坛、在主流视野中跃升为犹太社群的“代言人”。

这些组织与以色列政府密切合作,而由于自1977年之后、亦即在这些组织茁壮的同一时期,右翼的以色列联合党(Likud)多次胜选,连续长期执政十余年,更确保了这群头人又与这些组织头人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让这些组织的议程已经远远不只是“亲以色列”,而是和以色列当中的右翼亦步亦趋。
影响所及,书中提到当工党籍的拉宾(Yitzhak Rabin)于1992年重新当选以色列总理时,其实明确向AIPAC表示希望他们撤手,让工党新政府自己决定协商的进程。他的财政部长也表达,以色列已经足够富裕,并不需要这些美国金主的捐赠。新任外交部副部长更是在会议中直接向CoP成员呼吁:拜托不要再打压美国犹太社群内的不同意见了。但在这个时候,AIPAC根本无心住手,反而与以色列的右翼合流,包含在破坏奥斯陆协议的阶段性成果之后,选择在此时于美国国会运作立法,要求克林顿政府将大使馆迁移至耶路撒冷。
如同书中引述的一位资深记者所说,这揭穿了AIPAC的谎言:他们甚至根本不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政府,而是支持以色列内部的右翼政党。
谁敢批评以色列?
“只要报纸里出现看似对以色列有任何一丝批评的东西,我的编辑从一早就会有接不完的电话。”
这一群右翼鹰派的头人们,挟著巨大的资源,以犹太社群的代表自居,抢占各种政策制定和公众论述的空隙。社群内固然有不同的声音,但他们在一波波斗争中败下阵来:早在1972年、也就是六日战争的五年之后,就有一群自由派的拉比和知识分子组织倡议组织Breira(意指“选择”),呼吁以色列必须“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承认巴勒斯坦人对国家的渴望具有正当性”。其中一位共同创办人解释,他认为进步派犹太人“有责任”另起炉灶,不能把所有捐款都给予传统的犹太社群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才是真正“盲目让以色列自取灭亡”。

一开始,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发表肯定该组织的社论。但组织头人们立刻予以反击,比如在给基层会员的新闻信中污蔑他们是在提倡投降,或者杯葛与任何同时邀请Breira成员的活动;尤其在Breira的几位创办人和一位被认为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的阿拉伯裔作家密会之后,CoP公开谴责这样的会面是巴解组织宣传战的一环(即使他们的会谈原先是秘密),美国犹太社群内的主流刊物更攻讦Breira证明敌人意图消灭以色列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并且特别点名其中特定几位领导人在先前曾参与社会主义团体,将他们“抹红”。很快地,原先加入的成员陆续在压力下退出,捐款人也陆续撤回捐款,Breira在五年内就彻底销声匿迹。
书中提到,在Breira事件之后,犹太裔大导演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历史学家贾德(Tony Judt)等也都曾在社群内被点名批判。时至今日,寒蝉效应依然存在:作者引述一份2013年的犹太教内部调查,显示在认同自己是“鸽派”的拉比当中,有高达四分之三表示害怕表达自己对以色列的看法。作者引述一个代表近两千名自由派拉比的组织领导人的解释:鸽派的拉比们“非常害怕,原因是他们会被右翼的教众攻击,而他们经常控制财源。”
当然,比起在美国犹太社群内部打压异己,这些组织更为人所知的是对“外人”的攻击。书中提及其中一个经典案例:AIPAC自1973年起组织了专门反及媒体中“假讯息”的部门。《洛杉矶时报》负责报导埃及的记者David Lamb回忆,“只要报纸里出现看似对以色列有任何一丝批评的东西,我的编辑从一早就会有接不完的电话”;而以色列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发言人自己也向记者炫耀:“不论是记者、编辑还是政治人物,只要知道他们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接到几千通愤怒的电话,要批评以色列之前也会考虑再三。”获奖无数的《纽约时报》国际记者Thomas Friedman在1982年到以色列、黎巴嫩实地采访,在报导中写下“今日在西贝鲁特全境,以色列战机、炮舰和砲兵无差别(indiscriminate)发射弹药”--这句看似平凡,但编辑仍不顾Friedman反对,强行删去“无差别”字眼,以免读者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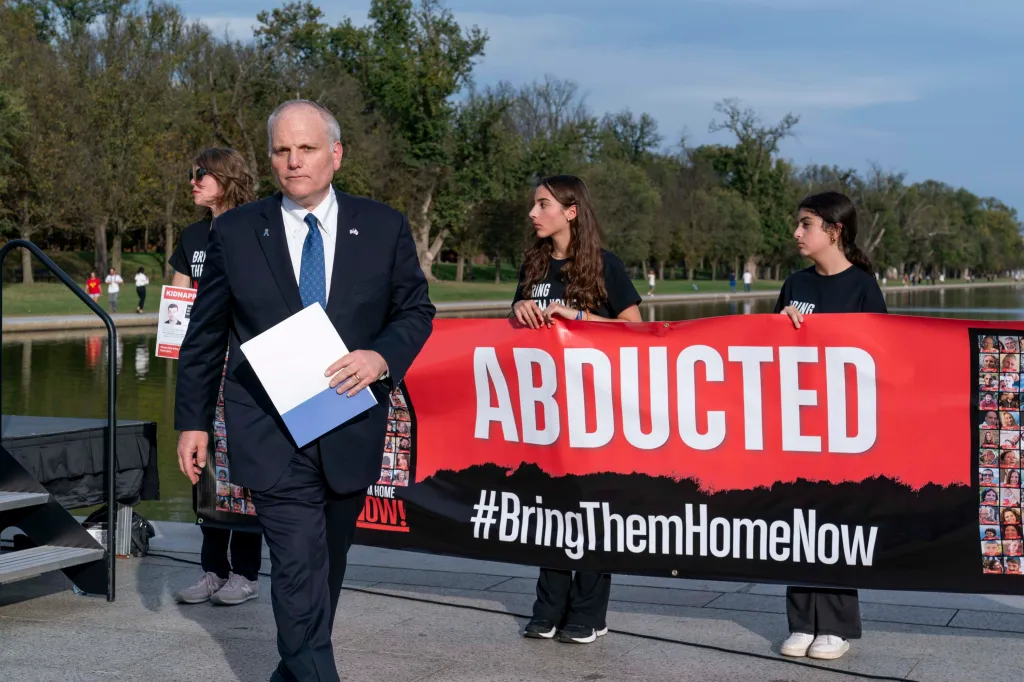
这些组织不只盲目攻击敌人,同时也搭配著积极抢占阵地,让自己的声音更容易成为主流社会的“预设立场”。比如在政坛上,AIPAC等组织的强项在于有庞大的研究与幕僚人力,能够迅速提供政治人物各种法律草案、谈话重点、智库研究报告,并且能以巨额政治捐助吸引政治人物予以采纳。在2016年,美国知名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EMILY’s List的主席Stephanie Schriock分享她过去担任幕僚时的经验:
“在你和犹太社群会面募款之前,你就必须先和你州里的AIPAC领导人会面,此时,他们会清楚要求你必须先提出你关于以色列的书面政见。所以你就开始打电话,去找你那些已经提出书面政见的朋友,用他们的政见当成你的政见,而你朋友的书面政见则是AIPAC设计好的。”
媒体上的道理也相仿:“攻击对手”本身不是目的,让自己的论点成为社会预设的正当论述才是。比如在2000年以巴又一波谈判破裂之后,由于谈判秘密进行,一度存在资讯的真空,人们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的情形。这些少数菁英在媒体上所散播的论述,是强调以色列政府如何做出史无前例的让步,但巴勒斯坦代表依然错失机会、贪得无厌,大幅形塑了美国社会对此波谈判的观点。
其实,《纽约时报》驻耶路萨冷的记者隔年即出版调查报导,克林顿的国安顾问Rob Malley也投书媒体,双双抵触了此一主流叙事。两篇文章都相对持平,提到以、巴、美三方都各有误判,也都各有无法接受的条件。然而,这样的文章不但为时已晚、大众已经有既定印象,而且他们又再度受到头人们针对性的攻击。Rob Malley当时就被CoP的领导人公开指控为“最亲近阿拉伯的国安团队成员”,CoP又重申“事实只有一个,不容争辩:巴勒斯坦人导致大卫营谈判崩解”。名义上专注于对抗反犹主义的ADL的领导人Foxman,亦同样指控Malley是“依照‘某些人’的议程行事”。

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奏效,使得这些寡头菁英在主流论述中的地位屹立不摇。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媒体经常根本不觉得自己能找到代表其他观点的正当发言者。作者提到,知名的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依德(Edward Said)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唯一例外,是少数美国媒体和观众所能接受的发言者;否则在太多时候,代表巴勒斯坦观点的人除了美国人眼中张牙舞爪的“恐怖分子”阿拉法特之外,就只有在大学校园上“捣乱”、满口学院理论术语、终究也说不清楚该怎么改变的大学生。
改变的可能:打破组织头人的垄断
这样牢不可破的垄断,真的能够打破吗?Alterman却认为一切仍大有可为。近年在美国犹太社群内部,如J Street、T’ruah等新组织的出现,虽然游说、选战资源远远无法和AIPAC竞争,但在论述、在政策上有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方案”,协助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更知道可以怎么做,也有了合作的对象。近年来,更多的美国犹太作家、宗教领袖也都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逐渐撑开论述的空间。
而既有组织头人至今仍持续运用相同的斗争策略,半世纪来始终如一。举例而言,ADL执行长在2022年指这些新兴犹太组织“尝试以自己的犹太身分当成盾牌”,窝藏“反犹主义”的敌人。就此而言,建立发言的正当性依然是一条主要的战线。Alterman举例,面对如国际特赦组织等团体提出研究报告,具体指证以色列的种种人权侵害和战争罪行时,与其争论以色列“是否可以跟南非相提并论”、接著深陷“这个指控是否构成反犹主义”的既有泥淖,更好的策略应是努力尝试,促使人们严肃看待报告中对于以色列现状的种种具体批评。
而若要削弱这些头人的影响力,则必须注意这些既有组织头人最大的弱点,其实也正在于他们和基层社群成员脱节。其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现象,莫过于美国犹太人选民依然多半属于自由派,但组织头人却在近四十年来集体右倾,尤其不断与福音教派的代表人物过从甚密。发展至今,AIPAC甚至于2022年宣布成立行动委员会,与MAGA派金主一同资助上百位共和党候选人。除此之外,美国犹太社群的青壮世代根本并未亲身经历六日战争,反而更熟悉各种近期战争惨况的报导,他们所认识的以色列总是由内坦雅胡这样的强硬派所代表,这些矛盾都是挑战头人们垄断地位的重要利基点。

这也扣合了本书的书名:We Are Not One,“我们并非一体”。数十年来,以色列右翼偕同美国犹太社群头人们,不仅独占代表犹太社群的正当性,更让他们的观点成为主流政坛和舆论所预设的唯一正确答案。然而,美国犹太社群和既有组织的寡头金主们不是同一群人,和以色列民众、特别是其中的极右翼更不是同一群人。这样的矛盾是当下困局的历史起因,而在作者Eric Alterman看来,这也应该是冲破既有限制的最佳起点。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