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23年6月13日的凌晨自杀离世。我知道时已是三天后。
按他之前的说辞,当时他在贵州打多份工,给在医院躺了两年的父亲赚钱治病。每隔两天,才能抽出空档“报平安”。这份惯例,让我在6月12日收到他问我借钱的短信后,专心进入了新一轮“等待”。过了三天,意识到不对、辗转联系到他妈妈时,再收到的和他有关的消息,只有他的死亡证明。
“他就这样抛弃了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妈妈喋喋不休、颠来倒去地讲。
我大脑连续空白。几天前,他在我长达三个月的劝说下终于放下心理负担,和我约定,七月就来北京找我,结束长达十年的异地恋。我会帮他一起还债,从此“相依为命”。他怎么会突然就自杀了?
我一遍遍盯著死亡证明里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6月13日。是我们相识整十年这一天。这是只有我们两人才知道的记号。可是他为何不直接告诉我,而是让我猜?
极端悲伤下,一些出于自我保护的猜想自然地衍生:他一定是“假死”,这样就能“人死债消”,换个面貌重生。这个想法有诸多漏洞,但我不得不靠它支撑,让我至少能挨到,找到他的坟墓——过了三天,葬礼早就结束,他留在世上的只有一个坟。
我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拿到他的遗物以及或许存在的遗书。只是我总缺一点勇气。因为,我俩的恋爱有些地下党的性质:我的生理性别,是男性。
他的社交圈和绝大多数在大陆长大的顺直男性一样,提到同性恋,会嗤之以鼻。在他们的语言系统和认知逻辑里,“gay”甚至可以是有侮辱性质的形容词。关于我俩的关系,他从不对周围人多说,他的同学和父母对我的了解,是“女朋友”和“网友”。
而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埋在了哪里。他妈妈不肯说,宣泄完情绪后直接拉黑了我。一直陪著我的朋友此时发现了突破点:
6月13日,他自杀后,他妈妈发过一条“朋友圈”,说“要忍著悲痛于6月14日下午某时某分在某中学几百米处”安葬他。我的朋友在南方地区长大,对丧葬文化中“玄学”的部分很敏感:她确定,他妈妈会如此详细地预知埋葬的地点、时间,是因为找“专人”算过。按照这个方向去找,绝不会出错。
6月16日,我和她商量好,定下了“寻找墓碑之行”。
1.
2013年,我正读高中。政策红利给这里带来远高于其他省份的名校录取率,十公里外的学生还在上晚自习时,我已经回到家,玩著曾在页游时代风靡一时的“你画我猜”了。那年6月12日的晚上,在某个“频道”里:我对著系统词语“彩虹”,写了个“D吧”,期待有人能像金庸小说中师兄弟相认一样对出我的暗号。
“小红书”出世前,“人人网”衰落后,百度贴吧是网络住民的最大站点。人们在这里围出了一个个有趣的小组。D吧人最多,它原名“李毅吧”,为调侃球员李毅的自大发言“我护球像亨利”组建。各色人群的涌入,让它从对个体的吐槽,慢慢转为了对社会现象的针砭,变为建“墙”之初极大的建政根据地。D吧管理员中,最出名的一位叫“彩色哥”。
台下的几个人里,一个顶著漫画头像、英文名称的再普通不过的玩家最早答对,紧接著发了句“吧友别走”。我就是这样认识了他。这之后,我俩一路从游戏聊到了贴吧,又加了QQ,他变为了每天放学后都能和我聊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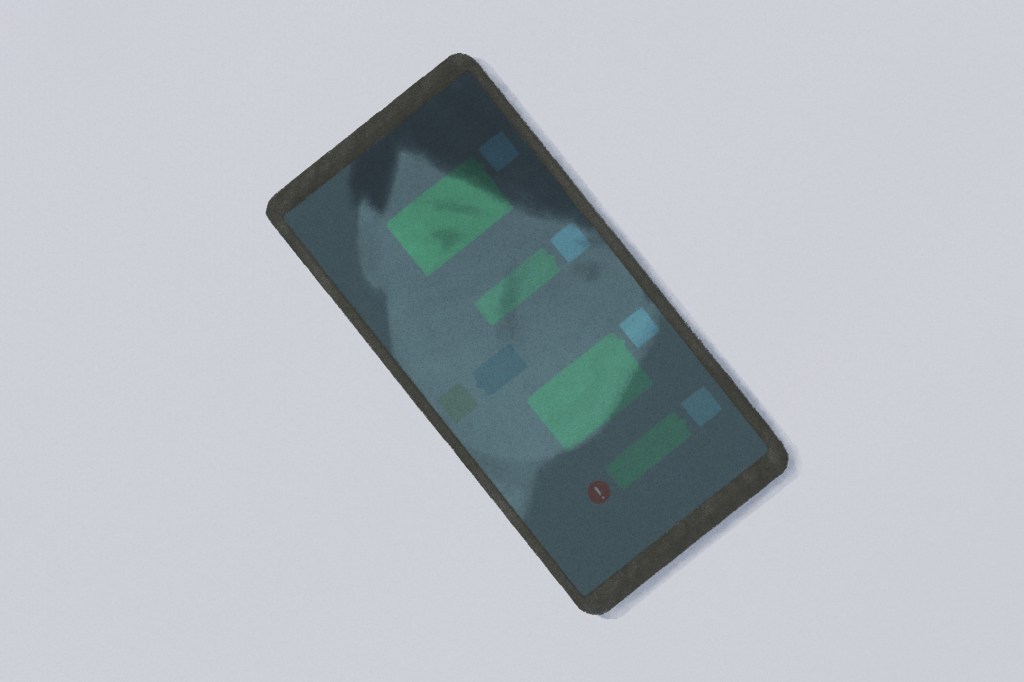
他很有耐心,总让我毫无保留地打开倾诉欲。我讲,我父亲很强势,他则像大哥哥一样安慰我:父亲是希望你学习好些,不像他这样辛苦;我讲了我从小到大的奇思妙想,他总能激励我、赞赏我,接著分享他的。
不久,我对他的感情变了。当我上无聊的政治课时,当我夜晚睡不著时,都有了一个可以去想像的对象。没见过他的样子,我就自己从偶像剧里找原形。
我在他心中好像也慢慢不一样,他会偶尔逾矩,说我“好可爱”,在没回消息时,也会著急地向我道歉。拉扯了一些时间,他突然说,自己有了喜欢的女孩子。酝酿了很久没等到回复后,他又接著补充,是我。
这太意外。他明显是错认了我的性别。在网络上,我的头像是我喜欢的女性漫画人物,暱称则是我喜欢的作家三毛的英文名。我的谈吐也不像传统的男孩子,可这不是我有意为之,我只是想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尽可能自由一些地做自己。
我下意识想纠正他,但怕他知道后会以为是我故意骗他,于是不敢明确答复:他只是说喜欢我,这不是“恋爱邀约”,我可以不作回复。他没追问,只是联系明显变少了。除了舍不得,我心里也卸下了一块石头,当时的我不懂得责任的意义,只本能不想欺骗人。
再次交心是在2015年底。我上了一家好大学,在家长的期望下读了一门不喜欢的语言专业,每天上课,学的都是当地男权至上的人文背景,像在接受酷刑。他也有新的烦恼。两个孤独又合意的人一搭上话,场面就不可收拾。
但长了两岁的我明确知道,辜负一个人的期望是过于不负责的行为。终于,在他问我为何会忽略他的心意时,我像豁出去一样,说明了一切,和他真切道歉。
他沉默许久,接著郑重地说:我们以后去西班牙结婚吧。

我多次说过这个三毛曾去过的国家,在那里同性婚姻能得到法律允许。我惊讶,心砰砰跳。宿舍熄灯后,充电宝的提示灯光持续照亮著我黯淡的心情。他说他从最开始就隐约感受到我是男孩子,也曾多次暗示说哪怕我是男孩子也要娶我。我没当真。没想到这是他的心里话。
他也和我坦白了很多。比如他刚遇到我时,不是高二,是初二,他实际比我小两岁。他以前也网恋过,相信它只能满足一时。我那次没有答应他的告白,只是催化了他离开的计划。
认识三年,我们终于以最真实的面貌和对方相见了。这之后的五年并不都是一路顺利,我们分分合合,每次挨不到要见面就会又分手,可仍走到一起。我坚定相信,我们是天注定的。
2.
但不意外地,该有个转折。
2021年6月某天,他说父亲得病了,要去医院一趟。接著失联,消息不回,电话不接——这和过去他几次以冷暴力的方式分手的场景如出一辙。影响最大的那次,我甚至因此出现严重的抑郁症躯体化反应,最终不得不退学。我条件反射般地变著花样联系他。短信发了几百条,QQ和微信的语音通话打到忙音响起无数遍。
再取得联系,是很多天后,他说父亲病很重,他要担起家里的责任。相处多年,我对他也算有了解,他的确优点很多,但也有一遇到挫折就想放弃的习惯。而我,往往会是他最早放弃的。
我提前打预防针,安慰他,有事可以一起承担,这次千万不要不告而别。但几个月之后,分手的信息还是来了。我还是在他找我聊天后写长文安慰他,希望他好好生活。挨到2022年,在我的鼓励下,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了希望,他又同我复合了。
但他仍偶尔失联。我体谅他的艰难,偶尔问问是否需要帮助,不多烦他,又是很久没收到回复后,我试探地发了个消息,显示我被拉黑了。
红色感叹号冒出的刹那,我心灰意冷,这感觉和以往都不一样。

我懂得人在面对巨大危机时想回避的本能心理,但经过几轮教训,我想通,提分手有很多方式。直接敞开说明,我未必不能接受。每次都选择冷暴力,根本只是因为他害怕面对我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也不想付出安抚的成本。“怕拖累我”实在是伪善的说词。
我依次点开QQ、通讯录、B站、网易云音乐⋯⋯这不单纯是我们的连接,也承载著许多过去。但将他最后一个联系方式也果断拉黑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变得不一样了。我没再哭到睡著,让时间宽慰情绪,而是利落打开电脑,完成我刚刚接下的稿子,也期待我接下来的和他无关的人生。
有些人好像就是有这样奇怪的性格,当你彻底放弃了,他就又想回头。
2023年1月,他的QQ空间里,发了一条:“大家好好生活,我先走一步了。”
我觉察出了不对劲,立刻经过一番折腾联系到了他。他说,为了给父亲治病,办法都用尽了,也看不到希望,只能自杀赎罪。他这段时间在工地上班,疫情缺人,来钱快,不是工友发现,他可能也不会和我有这次的聊天。
他继续说,他给我留了一张银行卡,有十万,密码是我生日,他攒著给我出国留学用。我22年时转发过很多由不合理的防疫政策造成的新闻,也提过想通过留学的方式“润”到国外。他牢牢记在了心里。他还说,他写了很多信,请快递员每年寄给我一封,口吻是他工作后、结婚后、生子后,以此让我彻底死心,迎接我未来的生活。
后来和同伴聊起这件事,她大惊:你采访时会分辨出受访者每一句话的纰漏,挖出他们可能记错的事实,轮到自己,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
总之,我推翻了对未来的全部规划。他如此为我著想,我没理由不和他共渡难关。但疫情后,他很好说话的亲戚都成了穷凶极恶的债主,怕收到追问,他不敢打开社交软件,每天也只睡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两个月后,他回复消息的频率变快,我没高兴多久,他就吞吞吐吐地转移了话题,问能不能借他些钱。我立刻转过去了刚收到的稿费,表忠心一样说要和他一同承担。这像开了一个口子,他找我聊天变得有规律了:每周的周中,每次要借钱时。原因也在更新:父亲清创碰到了身体要进重症;父亲得了肺炎,要抢救。我不是没怀疑过,但每一次,都想起他上次自杀后在电话里的痛哭。
他说他以前不懂事,故意提起别人家都很有钱,他父亲听了嚎啕大哭,换到现在这个辛苦的工作。他父亲已经很久没醒来了,他想亲自和他父亲道歉。
5月,他又一次来借钱了。这次的说法是,他父亲终于等到了手术的时机,只要最后一笔钱,这几年的挣扎就不会白费。我早已山穷水尽,朋友也借了个遍,上次筹钱甚至回收了写稿用的ipad。他沉默无言,语气变得无比颓丧:“我手里现在凑到了几万块,只能⋯⋯只能补偿你这么多了。”接著挂了电话,再也打不通。
我惊地坐起。他的意思足够明显,他要自杀赎罪。没多想,我失智一样,慌张找了网贷,终于凑够了钱。我兴奋地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沉默片刻,声音软下来,有些懊恼地对我道歉,说一定会还,接著就说要去做“蜘蛛人”赶工,回头再联系我。我忽略了因为他而高筑的债台,只因他懂得担当的品行而欣慰。
这次手术后,他回我消息的频率也没那么慢了。我们约定,工期结束,他就来北京,做这边雄安新区的建设项目。我沈浸在迎接未来的喜悦中,家中东西都换了个遍。没想到,等来的是不容抗拒的噩耗。

3.
北京到他老家的路很漫长,一小时地铁、八小时高铁,到湖南后,再转半小时地铁、一小时动车,接著打车半小时。早上五点出发,抵达时天空已经暗了。
封闭的小镇里,消息是藏不住的。学校门口超市的老板给我们指出一个方位,说是他外婆的家。我猜想的“假死躲债”,几乎被宣告了不可能。
小镇老区一条路通往山上,周围有堆满水泥的农田和写著“不得占用耕地”的中国特色宣传画。自建楼一个挨一个,朋友和我一栋栋找。他家在一组低矮楼房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他说他家“很穷”。
我们向他家人说是“他认识多年的网友”,他们听我回忆了许多他的信息才收起戒备,带我们踏上寻找墓碑之行的最后一段路。
路不长,但错综,如果是我们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找到。坟在一个小山坡上,那一堆土被鞭炮碎屑铺著,还不到半人高。碑没立好,或许是太仓促,来不及订做。他家人说,警察不让把尸体拉走,只能当天烧了后把骨灰运到家里埋。
这小小的一堆土,躺的会是他?我找不到半点和他有关的象征,只麻木地行著。回去路上,他家人指著某处被白色塑料覆盖著的灰烬,说“这是给他烧的房子”。那分明是纸做的,和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的“未来要有个大房子”完全不是一种。
就算要保持“网友”的身分,我也快忍不住泪流。但接下来的谈话,却让我猛地冷静下来。
他家人停下,紧张地小声问,我们和他有没有债务往来,我俩相视一看,著急否认,对方点点头,也放下心说起家常。对方说,他的死实在蹊跷,他们在他生前住过的宾馆里找到一部电脑、四个手机,都设了密码。“现在送到华强北了,也解不开。”
听到这里,我愣在原地,重复:“四个手机?”但我心中真实疑问的是“电脑”。他借钱时,我抓住机会和他聊过未来,他很落寞地说,以后不会做程序员了,只能打工还债。我心疼他:为了给他父亲治病,他卖了陪了他多年的电脑。对于酷爱编程的他,无疑是送走了一个伙伴,和希望的倚仗。
他家人接著说,深圳警察查公寓监控,往前推了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异常。深圳?我僵住。他多次和我强调,他一直在贵州工地打工,我想去找他,他还以这里太偏远、不安全为由不肯透露地址。
朋友意识到了我的状况,连忙说我们明天再拜祭,带我回了住的地方。我没精力去在意这些和他的说法有出入的细节。我心里仿佛慢慢拼凑出了一个真相,但我害怕让这真相落实,本能抗拒任何和它有关的事。

后来我们又去往坟堆两次,朋友留在原地,给我们留出空间。泪水终于在它本该落下的场合倾泻而出。我靠在坟堆上,像靠在他怀里,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想像写文章一样有逻辑地指控,为何丢下我,为何不告而别,为何他的话和事实有诸多出入。话却像电视里一样老套。哭到累了,我想起正事,抓起把土,放进袋中,接著靠在坟堆前,拿出手机自拍。
十年了,这竟是我们两个唯一的合照。
4.
我能得知他的死讯,要感谢他的同学L。我曾以“女友”的身分和他们一起玩过游戏。他自杀后,同学L帮我联系到了他的妈妈,也在我去往湖南、回到北京的路上漏夜安慰我。
刚开始,同学L说的都是关于他的好话。但或许是天意使然,同学L不忍看我越来越沉迷,试探著吐露了一些有些残忍的细节。我从前很抗拒得知这些,但被复杂又矛盾的情绪折磨够久,我心里也隐约觉得,我要走出来,就不能不知道这些真相。
在同学L的讲述里,从2021年到2023年,我们竟然没分开。2022年,他拉黑我后,还曾邀请同学L和“我”一起玩游戏,并在12月去贵州找“我”,一直同居到2月才回深圳。同学L说:“我当时就很疑惑,你从来不开卖,这次却全程语音秀恩爱。”他还说“我”现在做幼师,他在贵州找到工作就定居。同学L觉得奇怪:我是在北京读的书,怎 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做幼师。
事实呼之欲出,他竟在拉黑我之前,就已有了“女朋友”,和别人过上了我期待好多年的同居生活。他同学补上最后一刀:“当时警察接到报案,说是女朋友打来的。我还以为是你。”
我想回复消息,找不出能说的词。我知道,我这两个月一直当作寄托的遗书或遗物,根本不可能存在。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想到的不会是我,拥有他一切的是那个女生。
我关闭手机,眼泪夺眶而出。十年来,他和我讲过无数次,藏在他心里的一个有关英雄的梦想。他是长在平民窟的普通少年,有个光荣的任务,打败恶龙,拯救公主。在电话里,在信件中,他说过无数次,我是他心中的公主,他要越过艰险来娶我回家。
他这次甩掉我,会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的不只是具体的人,更是“公主”的设定,而此时刚好身边出现了一个更像公主的人。当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心动,而且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人,就完全可以不带负罪感地把我踢出去。毕竟,人不能一直活在网络世界里,和我“奔现”以后,他面临的世俗难题会更多。
我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外界压力,会不会他内心本身也不接受我的生理性别,只是舍不得一个一直对他好的人,才从最开始就欺骗自己也欺骗我?可是,我们曾很多次隔著屏幕“性爱”过,无论是语音文字还是照片视频,他的一系列生理反应是装不出来的。学界对于同性恋、异性恋的定义是,会不会对同性或异性的人产生性的冲动。他说过,看同性成人影片时不会起反应,但是一想到我,就会。我因此才接受了这个浪漫的说辞:爱的不是某个性别,而是具体的人。

事实已经无法揭晓了。但一旦开了一个口子,对真相的探询就无法止住。从不同人的讲述里,我拼凑出了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真相。
他的父亲生过病,但不严重:曾有人在2023年和他父亲通过电话,对方回答早就能正常工作了,根本不是他口中的“一直没醒来”;
他不仅骗我,也骗身边的人,2022年,合租的同学把三个月的房租转给他,请他交给房东,他转头就自行收用,理由是给父亲治病。欠条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到现在分文未还;
他并不是一个坚定求生但被现实打倒的人,而是经常放弃、得过且过。2020年,他找到工作,经常找理由请假,躲在家里通宵玩游戏。
听的时候,我还是下意识怀疑,本能担心是他们被他骗了钱后讲他坏话,但随著他们的讲述,结合对他的了解,我越来越相信这就是他。很多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次“分手”,他就是截图和小号的聊天,来冒充是他哥哥强迫他;每一次的冷暴力,他也都会找出借口来为自己的懦弱圆谎。
我疑惑,为何他的众多优点会在一刹那消失,擅长倾听、富有同理心、积极向上的少年会突然变得拒绝沟通、不通人情、懒惰消极,难道这些优点不过是他的人设,后面才是现实中的他?
他的朋友说,他其实很上进,也很有计划,想做的事总是列下来贴在桌子前,可一旦有一点点不如人意,就会全盘推翻。通宵了一整个晚上玩的游戏,只因为其中有个属性不符合他的期待,就可以直接注销,重新再玩;闲聊时,他也经常提到,希望能“重开”,到一个富裕的家庭重新开始,好好做人。
他在贴吧有很多帐号,刚认识他时,他是很明显的“逗比”(搞笑)形象,没多久,他就注册了新的帐号,关注了一批艺术、哲学类的贴吧。对于资深网民,帐号就是身分证,但对他来说,每个帐号可能都是新的人生。

不知道他自杀,是不是觉得,人生也可以像帐号一样,一个注销键就能抹掉过去做错的一切,选一个想要的人生继续培养,不满意了又可以从头再来。
但我又想起,2018年,他做过一个决定:读高中,参加高考,读好大学,才“配得上”我。他说,父母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也在这生下他,俩人没赶上任何风口,一直都只是勉强让全家人不挨饿。他小时候日子比我辛苦,唯一的计划是早点赚钱,深圳是高新技术密布的城市,他读中学时,正是互联网公司的红利期,他干脆直接读了职校:三年就能工作,再读大学简直是浪费时间。到了2017年,他快毕业时,才发觉自己想得太简单,职校和211在面试前的门槛差异是难以弥补的。
大陆这些年对高考的管理越来越严苛,他没法在深圳读高中,就让他妈妈托关系把他送进了湖南老家某个高中。可新年来临时,高考学籍筛查终于从城市深入到了小镇,他妈妈四处“找人”,办法用尽,也没办法再读。
没多久,他就说自己未来无望,不能耽误我,单方面提了分手。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努力过,只是环境的容错率太低了,选错了就没法回头。
六
2024年10月,我去了趟深圳。我要去他去过的地方,走他走过的路,像陈奕迅《好久不见》唱的。
最后一站是他的坟。小山坡上,人脚踩出的路又长出了许多植物,一茬盖一茬。我还记得坟堆的样子,就遥遥地停在某个山头上,我能清楚看到他在哪里,但就是过不去。我干脆站在小山脚下,说著积攒了一年多、几经转变的想法。我想,这些执念解决后,我再也不会来了。
网上流传一个说法,人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住一生。但我想知道我真正执念的究竟是什么。
小时家境很窘迫,家人外出打工,用“离散”为代价来换钱。在同龄人的圈子里,我一样孤单,男性同学们会找出各种我“像女生”的证据来排挤我。讲话“娘娘腔”,白嫩得像女孩,衣服和文具也像女孩的一样洁净。我不懂辩驳,只努力学习他们的规则:在操场滚、躺把衣服弄脏,粗著嗓子讲话,试图和他们同频。但他们总能识别出我是装的。在操场排队时,众目睽睽下,粗鲁地把我推进女生队伍里,引起隔壁班大笑。只有班里的女生会释放出最大的善意,接纳我,带我玩,而之后,男生的奚落又会变得更丰富。
他在此时出现,不只是作为能陪伴我、倾听我的人,还是第一个肯真正尊重我的“男性朋友”。但我又觉得不能这样归因,会陷入“把自己的一切遭遇怪罪到原生家庭和不幸童年”的困局。
会不会是因为大陆男同性恋的世界里总是“0多1少”,所以我想抓住他不放,就是怕错过他?但我又否定了这个猜测。我遇到的能扮演“1”这个角色的人并不少,和他分手期间也曾和几个人交往过。
我接著回溯,终于找到一个最可能的理由。
2013年,大陆网络防火墙还没完全建立,大家能相对自由地登陆外网,我当时跟著“文艺青年”的潮流,在ig上关注了很多深圳的同龄人。他们的校服是清新的天蓝,他们的高中生活同样不晦暗。有人在学校组建乐队,和志同道合的人发行的原创专辑; 有人结伴骑行,足迹一步步延伸到了欧洲。
那一身蓝色的校服上衣从此在我心里点燃了一团火,我不只想要见到外面的世界,我也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别人问起我的家乡,也会说这是老牌繁华都市,但我在小镇长大,除了高考,没享受过太多社会福利。
而2013年,他拍给我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穿著蓝白色的深圳校服。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寄托著我跳脱出现有桎梏、追求美好未来的向往。多年的相处里,他的身分逐渐复杂。灵魂伴侣、性爱对象、靠得住的家人,一个一个标签重叠,他也变为了一个最丰富的集合体。
这些年我都是独自奔往我向往的世界。他从一个人,变为一个寄托,一个象征,这些美好的期待渐渐和他混为一体,哪怕我并不真的需要他这个人,也无法让自己将他拔出去。
那么对于他呢?我想我也一样是一个由“寄托”、“需要”等关键词拼凑出的集合体。他才会在有利可图时到来,利散而退。“喜欢”当然也是有的,但对于长时间处在不健康的生活状态中的人来说,它又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东西。
想明白以后,虽然我心里还是被阴影笼罩,怕会被骗,但也不再抗拒新的关系。我慢慢懂得,不要再依靠“恋爱”来解决自身问题,它该更纯粹一点。我陆续认识了一些人,也终于体会到了健康的亲密关系。只是这一次,不再只是通过网络。
我想我从前陷入了一个误区。对于15岁的我来说,周遭即世界,当时的网络的确是一个拓宽社交的渠道,但现在我已经走得够远,完全不用把结识新人的期待全部交付给错综复杂、难辨真伪的网络了。何况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变了,D吧被战狼攻陷,“你画我猜”也因有网友会在画板上写“反动言论”而遭下线。人和人的相处,都不再真诚而互相信任。

两个月前,他的朋友问起我的近况,寒暄两句后,我们终于聊到最后一个未解决的话题。他找我借的钱,都花去哪了?种种线索最终指向了一个可能:网贷。
自从2020年起,他就一直借网贷度日。一旦享受到了来钱的容易,往往会陷入奢靡,“以贷养贷”,直到彻底断供。后来重新联系上我,很可能是网贷还不上了。而他从2022年起找同学借钱时搬出的给父亲治病的理由,其实也不过是维持他人设的遮羞布。
2023年,为了给他凑钱,我不得已借过网贷,之后几个月一直没能痊愈,靠网贷维持著生计。我没把这当回事,心想自己并不奢侈,也有不错的工作。可这天后,我立刻覆盘花销,果然发现了很多笔远在我计划外的支出。我制定了未来的收入计划,避免被卷入其中。如果说,他对我还有何副作用,大概就是,他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他坏得并不彻底,要不然也不会自杀了,他的原生家庭无法拉他一把,他不想接著拖累我。后来想想,自杀可能只是因为在我这里也借不出钱,编造谎言混日子的感觉太累,他不想继续了。至于我的感受,他应该不曾考虑过,毕竟连这些真相,也是我独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勉强拼凑出的。
我偶尔还是会想,他自杀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13日我们认识十周年这一天。难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不是想用这个方式告诉我,放下执念,这十年是个错。还是他觉得在这一天自杀,来世就能变成他期待的,十年前刚认识我时他说的身分?但我不能再想了,我把它当作一个巧合。
我和他交融太久,久到分手后做的每件事也仍有他的踪迹。吃牛肉火锅,我会想,我和他曾一起计划去北海道玩,吃当地的和牛;去ktv唱歌,下意识不去点曾和他一起听过的那些。
这一年半,我做了一个名为“消除与覆盖”的计划。和他期待的事情,我都陆续独自或和朋友结伴做了,再提起类似的话题时,我首先想起的,不再会是他。
回忆是种恫吓。写下纪录时,媒体人的惯性让我时不时担心,这件事会不会被消解成一个个简单粗暴的标签,比如:一个网瘾少年在现实“重开”、被网贷压垮的年轻人,或者被传成是“直男装gay来骗钱”。但我想,只有从头审视,认真书写,才能记住它是怎么发生的,这十年才不算白费,才能让我真正去走向我的“未来”。而对于他,爱意和恨意在这快两年的频繁回望里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我终于能平静而真心地说一句,愿他安息。如果有来生,祝他过上真正想要的人生。





有類似的經驗,謝謝你幫我們寫出來。
心疼作者经历了这样一段欺骗、利用和喜欢交织的感情。很难想象他拼凑出真相时会有多难过。希望他接下来会过得幸福和顺利。
寫的很好,後面有些反轉,真的是現實比小說更精神
就算不是網戀,也會充斥金錢的計算。
哪里还能看到作者其他的文字?
好细腻的笔触,感觉作者是个温柔又坚强的人。捉个小虫,文中倒数第二张打游戏的图片注释有误~
写得真好,角度也与众不同。
看完想给你个拥抱,真是一个内心勇敢强大的人。
很好的文字,认真 平静 温柔
看到一半想说我在端传媒上看天涯论坛…但是看完之后想说很喜欢这篇文章,写得好细腻,好真诚。
好溫柔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