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学名药的发展,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日中国上演的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也在中国把天价药问题再次推上台面,矛头直指医药专利权。美国医学史学者杰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的新书《便宜没好药?》,正是探究了被视为“原厂药”(Brand drug)的替代物、能降低药价的“学名药”(Generic Drug,仿制专利权过期药物的处方药)的历史,谈及二者之间的争议、医药专业的利益冲突、药厂间的利害关系、专利的攻防战等等。虽然葛林的研究地点是美国,但学名药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全球化,因此对东亚读者而言也别具意义。本文为台湾国立阳明大学教授郭文华为该书所作的序言摘要,《端传媒》获作者及左岸文化出版社授权编修节录刊载。
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从药物切入医疗体制的好书。作者杰瑞米.葛林(Jeremy Greene)任教于医学史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长为药物与社会。他也是内科医师,不断从实作中汲取历史书写的线索。相较过往用伟大医师与医疗发现串起的大事记,或者爬梳现代医学起源、解构其客观性的概念分析,或者聚焦临床、探究医病互动中体现的身体论述,这本书提供扣合制药趋势、反省临床操作、直指市场的跨界书写,情节紧凑,高潮迭起。
一直以来,媒体不乏批判高腾的研发费用、问题重重的临床试验,甚至是药价黑洞的内幕报导,这本书有何特出之处?它是产业分析、商业史,还是批判医疗的社会研究?对此,我认为可以先从这本书的主题──“药物”开始。
很少人可以自信地说他从小到大从没用过药。就算没上医院,没看过医师,他们或许去过药房买过成药,上超市买维他命,喝过各种提神饮料,更别说在医食同源的概念下,把传统药物当进补食材天天服用。正如医学人文大师William Osler的睿智观察:人天生渴求药物;历世累代的勇猛剂量早已养大身体对药的胃口。是人类对药物的渴望,将他们从其他动物中区分出来。
可是,在当代,药物是高度管制的商品,层出不穷的药害造就严格的立法,令药品从研发、制造到流通销售都要层层把关。而管制要有让人服气的游戏规则,以美国为例,1962年《食品与药品法修正案》(Kefauver Harris Amendment)确立当代临床试验的架构:药物不但要安全可靠,还要证明“有足够疗效”才能获得核准。换句话说,即便药厂拥有药品专利,如果不能让药品通过审查,就不能上市回本,更不用说赚钱。
另外,复杂的临床试验带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与创新制药产业(以PhRMA为代表)的扩张。前者为广大药物使用者把关,后者则护送产品尽早上市,两者的交手攻防构成制药业的尖端形象。这不但令进入产业的门槛不断提高,造成药厂的寡占特质,跨国药厂更洒下大笔经费在准备临床试验资料与通过审查。
大家渴求好药,但对繁复的法规科学(regulatory science)与制药体制无从认识,信任不足,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是药物与社会的难题,也是目前医疗史亟待突破的领域。
好药还是劣货?学名药的政治经济学
《便宜没好药——一段学名药与当代医疗的纠葛》
作者:Jeremy A. Greene
译者:林士尧
出版日期:2018/07
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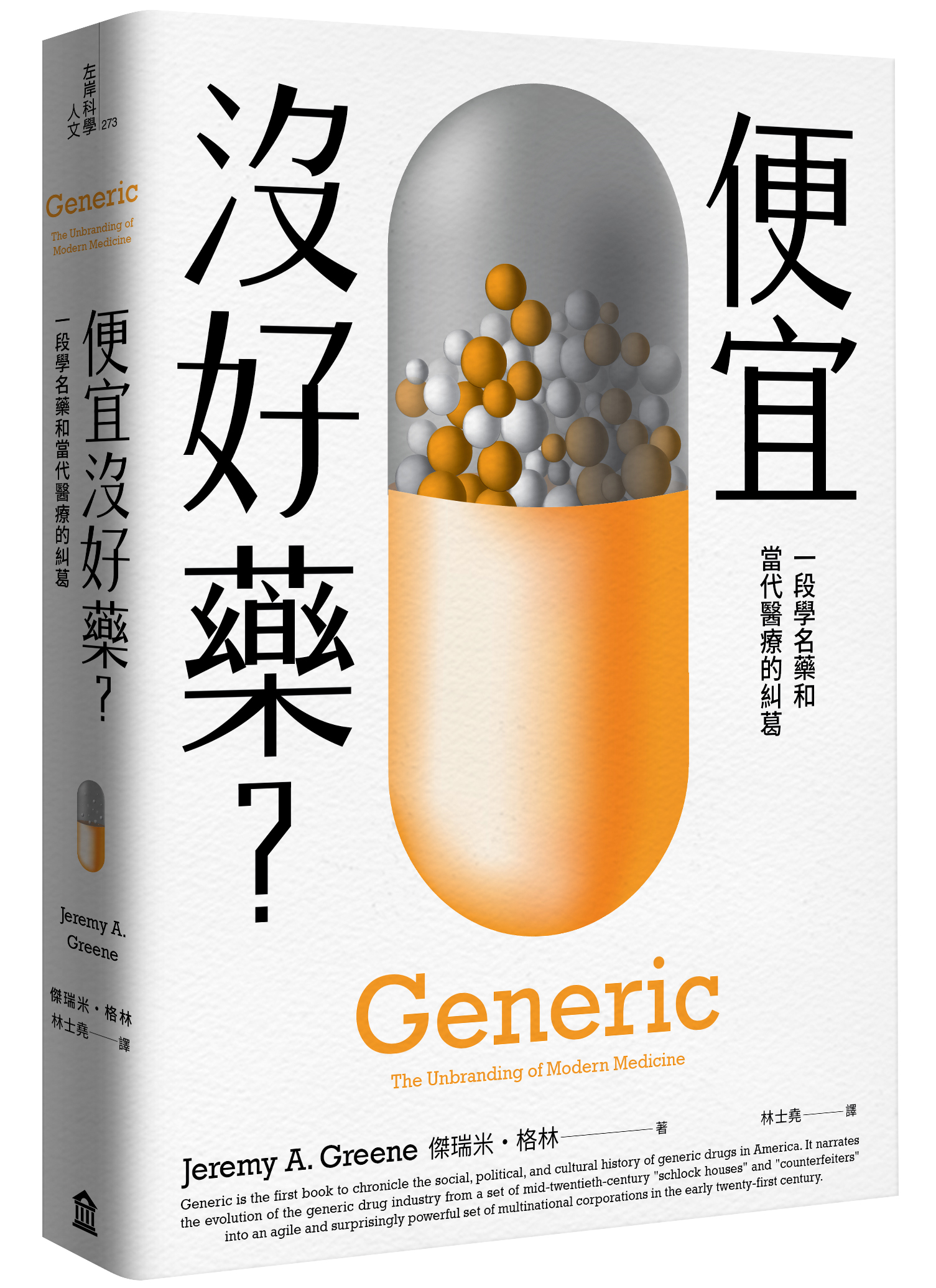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下,“学名药”提供看似不起眼但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对于不熟悉药物研发的读者,一个了解学名药的好例子是普拿疼(Panadol®,港译扑热息痛)。它是四五年级生(编按:台湾指1950—1960年代出生的人)的回忆,也是目前最常使用的退烧止痛药,但“普拿疼”其实只是像“可乐”一样的商品名,最初由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药厂所生产,而它的主成分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才是学名或公定名。
虽然普拿疼大名鼎鼎,但市场上以乙醯胺酚为主成分的药品多达两百种以上,包括此间常见的斯斯或伏冒,还有小儿常用的安佳热等。这些药在现实世界有不同名称,但只要翻翻药典,会发现它们分享同一个学名。
本书作者认为学名药是健康照护体系中少数“便宜有好货”的例子,但这个看法与大家的印象或有落差。学名药在台湾常被认为是“劣货”或次级品。老一辈医师看过太多本地生产、品质参差的“品牌模仿药”,一些医师也承认他们不相信学名药,觉得它们成色不足,药效不稳,不够创新。学名药当然合法有用,要不然卫生机关不会准予上市,但对一些病人来说,使用这些药不但没有捡到便宜的感觉,反而有种无从选择的无奈。
虽然学名药的优劣人言各殊,但如果抽离个人感受,将格局放大到产业与健康照护体系,意义便有所不同,以下用三个事件分析:
在长达一年多的折冲后,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在压力下撤守调降药价的竞选承诺,改以松绑管制来促进市场竞争。在特朗普当选之初,这些拥有专利、标榜创新的药厂曾推演最坏状况,认为政府会大力介入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者大举引进国外学名药产品,但结果并未如此。在节制药价的前提上,特朗普一方面将部分药物纳入议价范畴,同时美国FDA也放宽管制,加速审查,让药物可以迅速引进,相互竞争。
往回推几个月,台湾立法院于2017年12月通过《药事法》修正,引进专利连结制度(patent linkage),让国内学名药审查与其是否侵害跨国原厂药专利挂钩,兴讼时甚至将延缓国内学名药发行上市许可。这个修正是因应《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会议及《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现改名《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规范,引起相关人士批评。他们认为此举将不利本土学名药的竞争,经济部也于2018年4月在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回应,指出台湾的药厂不能局限于学名药与国内市场,而必须以并购、开发与挑战专利权等方式积极扩展。
事实上,这次修法同时纳入学名药独占制度,鼓励本土药厂思考升级战略,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湾FDA)也在几个月前宣示与通过“国际医药品稽查协约组织药品优良制造”(PIC/S GMP)稽查的学名药厂携手合作,挥军东南亚市场。
再往回到2016年。当年2月,C型肝炎原厂口服新药取得台湾上市许可。相较过去的干扰素加雷巴威林(ribavirin)治疗,新药尚未传出副作用,疗程较短,但价格昂贵。因此有代办业者从印度、孟加拉引进学名药,但定价不一,品质不明,造成市场混乱。台湾政府虽然编列预算因应,但缓不济急,被媒体炮轰失职。于是健保署以专款专用方式,在2017年1月将原厂药纳入给付,以病况与治疗策略来决定优先使用对象,总额为8000人。之后名额逐步放宽,到2018年时治疗名额已增加到16440人。
对此次政策演变,媒体加以肯定,并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宣示2030年扑灭肝炎,全球进入“根除竞赛”,呼吁加码全公费治疗方案。但也有药政专家黄文鸿质疑当局购买原厂药的策略,认为台湾应该善用国家高度洽商在本地生产学名药。这样不但确保药物来源,节省支出,更可强化制药产业并推动国际卫生。
在这三个事件中,我们看到学名药催动的国际政治与制药产业折冲。即使是有能力研发新药、主导市场的美国,依然需要学名药来维持群体健康。而原厂药为了在专利到期前穿透海外市场,则不惜督促政府透过贸易谈判,以智慧财产权之名要求贸易对手配合管制。而台湾则在具有“国病”意义的肝炎上受到学名药挑战。它打乱政府将新药纳入健保给付的时程,也让政府默许患者以自费方式进口药物。
这样说,原厂药与学名药看似《纳尼亚传奇》里的现实与魔幻世界,各自生产与流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专利为“魔衣橱”,它们相互连动,相生相克。没有原厂药厂的研发不会有可用的新药,也没有蓄势待发的学名药。没有学名药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原厂药不会精进,以新专利阻挡学名药上市。而原厂的专利布局是学名药的研发焦点,突破后才能以竞争性价格抢夺市场。
如果将医药当作一个以专业与专利框住的领域与市场,学名药是挑逗规则,打破垄断的推动者。学名药一方面挑战制药业“高科技因此高获利”的论述,一方面也在不逊于原厂药物的前提下,给予使用者多元的治疗选择。
去品牌药物的历史起源与演化

本书体现葛林对药物与社会的研究理想,或可说是兼具学术性与社会意义的历史书写。如前所述,现代制药的创新性某种程度上仰赖专利,而专利又需要庞大经费与人力才能转化成可赚钱的商品。然而,本书不附会制药产业的邪恶,也不过誉学名药破解法规的机巧。
相反地,作者回到药物史的原点,指出学名现象之于医药体系的意义,是它的英文书名Generic: The Unbranding of Modern Medicine的主标题。在此,“generic”不是熟悉的形容词用法,而是作为名词的“不特定称呼”。因此本书的中心关怀是:为何药物要“去品牌”(unbrand),成为诉求市场的“剪标品”?抑或是反过来问:如果现在学名药泛指某类不特定称呼的药物,那它们原先的“特定称呼”会是什么?
简单说,为了方便管理合成药产业,避免大众被误导用药,19世纪末开始出现介于诘屈聱牙的化合物称呼与繁复商品名之间的俗名,或者是通用名,并透过像《美国药典》之类的官方典籍进行体系化。药厂持续为自己的商品命名,但在与美国医学会的折冲中磨合出学名的产出机制。对他们来说,如何让学名不“恶紫夺朱”抢了商品光彩,甚至取代自家产品,是1960年代的话题。
交代这段“史前史”之后,作者在书的第二部分处理学名药产业的现身。1962年美国的《食品与药品法修正案》中,政府授权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订出统一学名,原先定位不明的“无名药”也就有了身份,与掺伪假药有所区隔,不至被污名化后一筹莫展。然而一直到1970年代,也就是医药黄金时代“神奇子弹”的专利开始过期后,这些学名药厂才有机会用自家好药打出一片天。
这样说,19世纪以商品垄断的药品市场在20世纪前半叶分化成以专利为界,各有品牌的学名药与原厂药。虽然产品态势看似泾渭分明,但生产端则暧昧不清。原厂药厂以“创新不足”的老梗贬抑学名药厂,但同时仗着坚实的制造基础涉足学名药。一些学名药厂本来就是原厂“代工”,发展自有品牌也是常理。更何况一些学名药还可以趁乱而起,抢在专利到期前就达阵上市。
如何处理开放竞争后的管制乱象,是书的第三部分的主题。前面提到1960年代的修法确立临床试验体制,大举拉高药品上市的审查门槛。因此,如果1984年的《海契─韦克斯曼法案》( Hatch-Waxman Act)让学名药可以跳过不确定的研发过程,便可分食市场,就要有说得过去的法规论述。“学名药相似性”便是在这样的基调下产生的。
虽然药品“相等性”或“可取代性”不是新话题,但随着药物法规的发展,这两个概念于1960年代后重回焦点。原厂药厂试图阻挡,指出同成分药品(即学名药)不见得有一定药效,或者在使用上与原厂药有差异。但既然学名药是既成事实,许多人透过药品的竞争而受惠,这些差异就不宜夸大。于是,一方面美国FDA统一药物生体可用率(bio-availability)的标准,保住学名药的上市之路,另一方面原厂药厂则不买单,坚持学名药是“未受检验”的产品。
虽然学名药与原厂产品的比较莫衷一是,但从群体健康的角度,它确实活络了照护系统,创造绕过原厂把持的替代方案(第四部分)。只是与19世纪把关药(ethical drugs)的想法相反,此时如何说服医事人员从掺伪假药的泥淖中脱困,相信学名产品可以接手原厂品牌,变成政府的难题。但这一回合制药产业已非吴下阿蒙。虽然全国性的统一规定并未出现,以《纽约州安全、有效与可互换药物处方集》(New York Formulary of Safe, Effective, and Interchangeable Drugs)为代表,各州开始立法为学名药厂背书,将医疗还原成健康的公共财。
而像这样牵涉公共利益、专业与法规管理的现象也从药品的消费端看出(第五部分)。一方面学名药厂如同原厂的竞争者,可以向消费者推销产品,提醒他们的健康权益,而原先是原厂药“消费者”的医师们,则受到来自病患需求的挑战。而关注焦点移到药房与卖场等通路,学名药以其制作品质获得上架机会,但同时期消费运动发起的去品牌“通用食品”(generic food)则不被美国FDA认同,显示主管机关面对食品与药品管制的矛盾立场。
就结果而论,学名药站稳了脚步,从1960年代市占率10%增加到2010年的近80%,对长期予取予求的创新制药产业造成压力。这不全是学名药厂的功劳,而是公共卫生、专业自主与市场角力的结果。
因此,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带出三个本世纪的发展。第一是同疗效替代(therapeutic substitution)与“模仿药”(“me-too” drugs)问题。相较于学名药同成分却药效不同的论述,模仿药是成分类似(因此不是学名药),但实际药效差异不大的药物。这些药物固然增加市场选择性,但是否可以学名药施行“替代”,考验着医疗的专业判断。
第二是健康保险机构的兴起与健康科技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过去原厂药与学名药直接在市场厮杀,现在主战场转移到保险的药物处方集,透过给付方式操弄开药行为。同时保险机构也有自己的考量。不管原厂药还是学名药,承保单位会透过科技评估衡量药效与进货成本。
第三是来自海外的学名药挑战。在美国的大药厂关心海外市场,但在智慧财产权谈判上遭遇阻力,不像在国内一样呼风唤雨,让一些学名药厂可以成长坐大。而呼应美国的医药需求,海外的学名药大厂则顺势叩关美国,分食市场大饼。
究竟学名药何去何从?迥异于商品与全球化的抽象批评,葛林回到药物的基本关怀──创新与分享。在制药产业从小分子的合成药往大分子的生物制剂迈进时,学名现象继续存在,但这次的主角是生技药品。生技药品不算学名药,但依循着学名药打出来的研发脉络发展。
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学名药完成“创造竞争,打破垄断”的阶段任务,开立学名药成为各界共识,但跨国药厂的品牌角逐才正开始,对此他不乐观。他指出,这些大药厂挟庞大资本翻弄原厂药与学名药,用品牌将这些产品纳入旗下,回到20世纪初期制药大厂主导品牌与市场的光景,值得有志者关注。
(郭文华,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公共卫生研究所合聘教授)

咦 樓下已經指出來了
四五年級生應該是民國4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人喔
四五年級生(編按:台灣指1940、50年代出生的人)
小編,四五年級生應該指的是1950-60年代生人吧?
第一段應為高潮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