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实味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有人称他为共产党文字狱首位有姓名的牺牲者。《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一书作者自2008年起访谈了十多位同时在延安,与王实味亲历整风的老人,附以口述、档案资料、文本解读、以及新发掘的材料,比较不同声音和视点,了解和纪录未能被成功改造思想的王实味。
《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
出版日期:2016年07月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作者:魏时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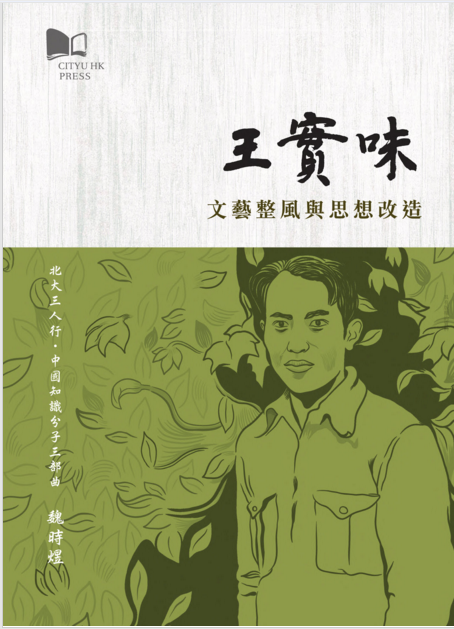
读《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下称《王实味》)如读狂泉之国前史。以前每读肃反整风历史,均觉深陷精神病院,目睹一两个未疯的人被残酷折磨,继而是疯子们互相折磨以为乐。但这本书因为作者魏时煜的纪录片导演背景,尤其形象可感,不只是王实味之冤魂在字里行间形销骨立,也有一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屈辱的阴影在狂舞、在变幻,不得超生。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档案随便打开一个,都是一个时代的录鬼簿。王实味固然更甚,然而他不是鬼,是照妖镜。《王实味》一书的写作方式的大量引用那些历史老人的采访,与王实味的命运相关的众人也像电影《黄金时代》里那些幽灵一样,轮流出来说话。但当中有多少是真实多少虚伪呢?那些“党内开明派”如果不是后来也经历和王实味相似的命运,他们会是迫害者还是同情者呢?就像纳粹纪录片一样,每一个人都强调自己是平庸的恶、附庸的恶,而正是这无数恶力集中起来,使康生的处决命令和那把砍刀顺理成章地砍掉一颗“死不足惜”的头。
实际上在1947年被杀害之前,1942年6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出席自己的斗争大会,就已经被精神处死。那一天的场景在书中通过萧军与温济泽的日记穿插写出,尤其是萧军日记栩栩如生,清晰地告诉我们那天的延安完全是二十年后中国各地批斗大会的预演,甚至样板。一个精神病院沸腾了,那些最早被洗脑的人、那些只认阶级与党派而仇恨“爱”的人,疯狂地污蔑、批斗王实味。而与文革不同的只有:一,有一个侠义的萧军试图捍卫王实味;二,王实味坚持他看到的真相,不肯低头。

闹剧当中最可恶的是丁玲、艾青等作家,王实味的遭遇,理应使他们物伤其类的,而他们选择的不是沉默而是落井下石,那是深知自己也是恶兽的猎物而主动成其为伥了。艾青攻击王实味曰“立场是反动的,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丁玲提出要“打落水狗”说王实味“为人小气、卑劣、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破坏革命的流氓”。亲炙过法国自由气氛的艾青、曾张扬女权的丁玲尚且如此,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王实味本人,从此仅仅能以“疯言疯语”维持他一点作为人的尊严罢了,就像萧军用他不见天日的几十万字日记所为。1949年之前的党内斗争,杀AB团是一个讯号,整王实味是另一个讯号,后者如此昭昭,为何未能叫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警醒?是他们洗脑过甚而不能醒,还是他们醒了,却吓得装睡,害怕成为另一个王实味?但无论如何,他们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都将遭遇王实味的命运。
其后他们就只好乖乖渴望平反,大多数人都像丁玲一样,她在1984年得知自己被平反后幽幽吐出一口气说“我现在可以死了”。但王实味呢?他需要平反吗?他如果活着会像丁玲那样谢主隆恩吗?
平反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另一种侮辱。强调王实味不是托派,强调他并未被正式开除党籍等等,都是对施害者的逻辑的认可。几乎等于是说王实味其实是忠臣,你们冤枉他了一样。王实味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因言获杀的第一人不是偶然的,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杂文里面,表面基调纯然是忠言劝谏,但也不至于像鲁迅曾说的那个指出皇上衣服破了的那个臣子那么可怜,他并没有跪伏在皇帝前面瑟瑟发抖,反而不时抽出锋利的匕首——我相信正是这种有尊严的态度触怒了毛。
1940年代的毛在其新兴王国中,早已习惯面对一群奴隶的唯唯诺诺,何尝想到有一个人站着要和他平等论辩,而且此人是他党内低层,属于他最瞧不起的只能用做宣传工具的文人。更使龙颜大怒的是王实味的语言承接鲁迅的犀利,剑剑刺中要害,就算毛及延安的其他特权阶级脸皮够厚不受影响,王实味的行为本身已经把前者置于鲁迅及左联作家攻击的国民党的位置上了。
王实味越不服输,毛越是要彻底消灭他的精神。流氓不怕流氓,就怕圣徒。王实味摆出了准备殉道的姿态,更显得他人的卑贱,这也是延安大多数知识分子顺势落井下石的其中一个心理原因(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害怕获得同样的命运)。毛不希望王实味死,在得知他死讯之后大发雷霆我相信也是真的,因为他担心王就此成为一个殉道的圣徒,成为可能存在的反对派的精神偶像。
王实味的振振有辞来源自他对共产幻象的超越认识——来自他数百万字的马列经典翻译经验以及对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认识,也来自他身处延安中层对现实的敏锐触觉,但归根到底是基于他的硬骨头。1942年3月,他自己在《硬骨头与软骨头》中写道:“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这简直就是对几个月后他的处境的预言。
王实味是一个异端,相信共产主义是一个可以企及的天国般的存在,不过在人间运行时被魔鬼骑劫而已,他作为真诚的清醒者,有责任以命相抵去纠正这条通往天国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托派的确非常相似。然而使他超越教内异端或者托派的,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相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
因为“北大三人行”(王实味、胡风、王凡西)这个背景设定,在《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常常出来与王实味相呼应的,是他的北大同学、日后成为托派最后精神领袖的王凡西。在书中引用的王凡西回忆中,他俩最早的争论就是日后王实味被其党大力批判的“人性论”。“依他之见,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要同时进行。”王凡西并未苟同。这论点挑战了中共和托派都同样服膺的马列主义阶级社会决定人性的那一套,就凭此,王实味超越教内异端的局限,几乎成为背教的先知的角色。
鲁迅没有机会殉道,他的私淑弟子王实味代为完成了一个刚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必经的劫难。在现实中,王实味因为他相信的人性而惨遭荼毒,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可怜的精神史上,他这种稀罕的人性坚持成为万马齐喑中一点铮鸣,证明无论多严苛的思想禁锢中仍然可以有独立精神的存在,这,难道不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吗?


第一次知道王實味是在捷運上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時,我永遠記得當時自己低垂著頭,不知是為一個剛正素樸的理想主義者所懾,還是為其之後的殞落垂淚。只記得當下腦子盤繞著:「好不甘心」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