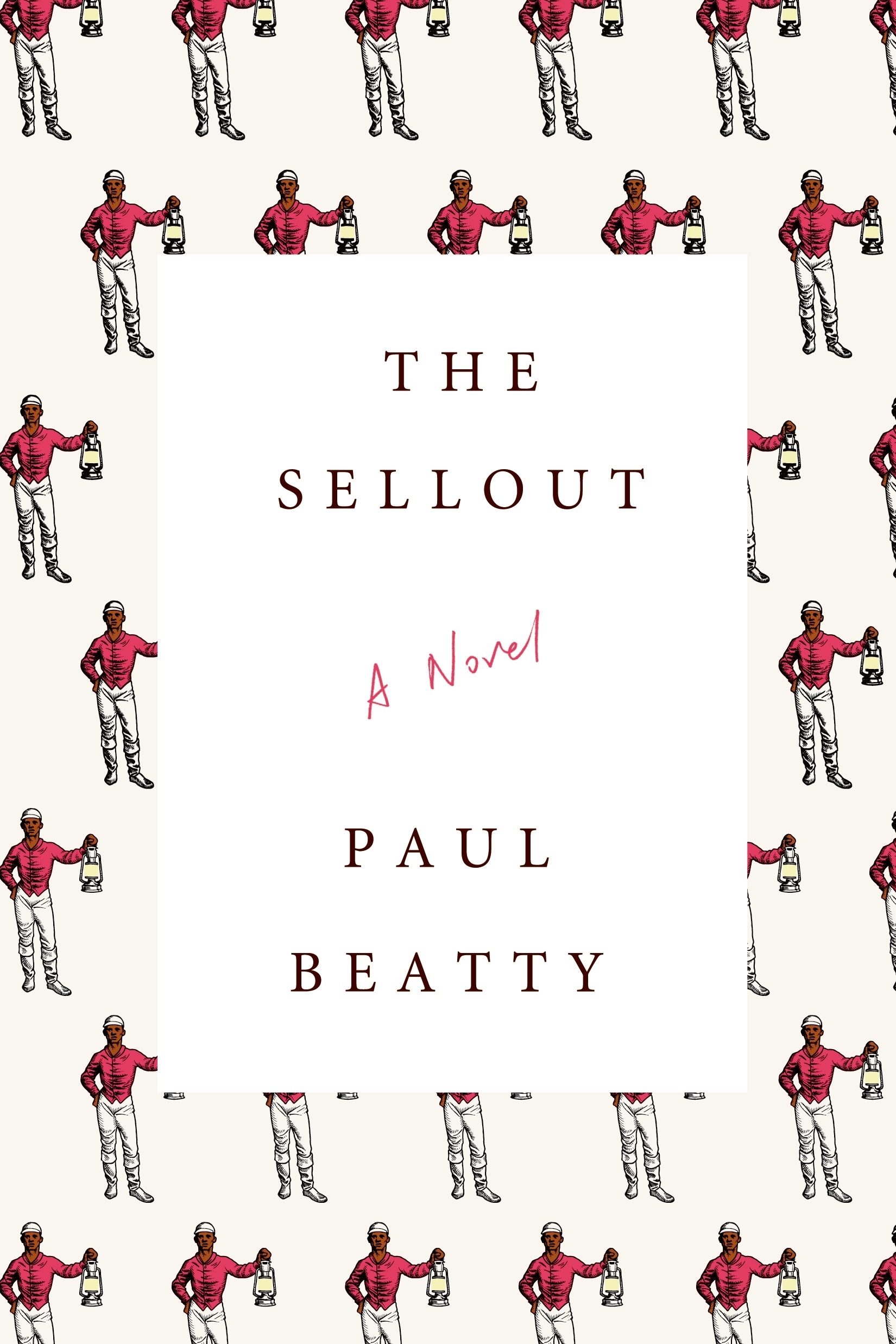
布克奖的初衷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所有英语文学奖项中占据更高的地位。不过此项改制开始以后,也多有批评者认为,这会使得本来已经在英语文化圈(Anglophone culture)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美国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继续增强影响力,而其他英语国家的作家将会被更趋边缘化。可见,在奖项改制争议背后,大家关注的实际上是地缘政治博弈与角力的问题。
保罗・比蒂的得奖或许是布克奖的一个平衡之举,它既把自己甄选的范围扩大到了最大的英语国家——美国,同时选择颁奖给这部对主流美国文化有着极大挑衅的作品,且又体现了颇为独立的意识和眼光。
介入种族议题的布克文学奖?
布克奖向来都有鼓励英语文化圈的少数文化区和移民作家的传统,诸如曾获布克奖的拉什迪(Rushdie)和奈保尔(Naipaul)等作家都为当今英语文学做出了别样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英语文学的面貌,他们甚至使用强烈地方色彩的英语挑战了日常的标准化英语。保罗・比蒂写作所使用的英语同样融入了特别的嘻哈文化的韵律和色彩。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少数文化是当下重要的政治议题,因此布克奖对此的关注可谓击中了当下的痛点。
近来对国际文学奖项似乎陷入过于“政治化”色彩倾向,批评声不绝于耳。而事实上在学院中,从性别、阶级、种族等角度切入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也是日益泛滥。然若辩证地来看这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与社会关系这个老问题,作为对现实进行反叛的艺术,是不是就不能跟现实扯上关系呢?
“讽刺让人难受,并非因为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击,而是因为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
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早在《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中就回答过这个问题:艺术既是自律的,然而又不是自律的,即,它是无比依赖于“他性”的,也就是无比依赖于经验和现实材料。第二,一种从文学外部入手的视角和方法论,将文学文本直接化约(reduce)为政治批评的例证,也同样是走极端的。这会忽略阿多诺所说的艺术的自律性,也就是文本虽然涉及到了性别、阶级、种族等话语,但文学本身的暧昧性可以随时颠覆这些既定的政治话语。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中推崇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小说:“讽刺让人难受,并非因为它在嘲笑,或者它在攻击,而是因为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保罗・比蒂的小说就具有这样一种颠覆一切确定性的特征。保罗・比蒂在访谈中表示自己也不愿意为这部小说做出任何解释。
自从1862年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以来,虽然有制度和言辞上的保证和承诺,然而抗争和批判种族歧视的主题,始终没有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学中稍有减退。在如今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中——一边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和多元主义文化,一边是美国日趋单一化的普世意识形态——非裔文学究竟如何同这样的状况进行对话?由此形成了什么样的面貌?而此次保罗・比蒂的得奖于我们将有何种启示?
“种族”不应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保罗・比蒂在发表小说之前发表过一些诗歌集。他的第一部小说《The White Boy Shuffle》就得到很高的声誉。这部小说讲述一个起先住在加州白人区的黑人小孩Gunnar,他有诗歌和篮球两项才能,觉得自己天生同其他黑人不同。在母亲决定举家迁入黑人区以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其中的怪胎,最终他以自己的诗歌才能成为了当地具有煽动性的政治领袖,一个弥赛亚一般的人物。小说中,Gunnar始终受困于自己模糊不清的身份认同,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这种设定不仅仅颠覆了向来对黑人的模式化想象,而且质疑了非裔是一个同质化的集体,相反解构了非裔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性,也就解构了“种族”这个概念本身。
保罗・比蒂在2008年发表的《Slumberland》,一部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成熟境界的作品。《Slumberland》的主人公Darker是个专做色情音乐的DJ,在他观看了一部配乐的影像以后,决定上路寻找这位作曲家。从美国走到德国,他找到了那位作曲家,并发现他的曲子可以让人沉浸入跨种族、跨物种之间的性交。同样地,这部小说也表明了黑人身份的不确定性,保罗・比蒂还写到了德国的黑人文化,涉及了非裔族群的离散(diaspora)现象,也就是将非裔身份认同的探索不再只局限在美国地区,而是从全球的视角来呈现非裔内部的多元化,解构了种族的概念。
这部小说彻底探索了人类社会中“区隔”现象的本质,讽刺了奴役与被奴役的现象、将他人或自己进行区隔和分类几乎是人们自动的心理需求。
《The Sellout》依然延续了保罗・比蒂对身份认同不确定性的思考。这回,主人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他的名字就只是一个宾词“Me”,主人公不断地重复诉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故事的主线具有超现实感,主人公企图在洛杉矶恢复奴隶制度,并作为一个原告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告上了最高法院的审判席。但主人公意识流的思考、游离、独白和评论完全淹没了整个故事主线。除了可以看到一贯对黑人刻板印象的质疑:“这可能很难令人相信,但作为一个黑人,我从没有被偷过任何东西。”,以及讽刺黑人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本质化和整体化(小说中解构了黑人解放运动史的编撰)。
这部小说彻底探索了人类社会中“区隔”现象的本质,讽刺了奴役与被奴役的现象、将他人或自己进行区隔和分类几乎是人们自动的心理需求。如小说中所言:“无论在古罗马还是现代美国,你要么是公民要么是奴隶,要么有罪要么纯洁……”(Be it ancient Rome or modern America, you’re either citizen or slave, guilty or innocent……) 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对种族议题本身的思考,而深入到对人类命运、历史和时间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不是光靠喊口号便能糊去差异
周蕾(Rey Chow)在《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认为,民族再现与自我再现“是紧密结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操作中的”。种族和其他常见分类一样,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中一种劳动等级制度。这些范畴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可以流动的,假如以后没多少黑人能承担这个等级链条上的被投射任务,“那么他们还会发明一个‘白种黑鬼’来承担”。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际是在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一元普世主义所服务。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下,少数族裔的特殊性被拿出来强调,仅仅是为着佐证其普世理想之荣光和伟大。
正如保罗・比蒂已经在小说中所表达的那样,黑人强调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他对此进行不遗余力地嘲讽。甚至在一些机械化“二元对立”者看来,都误以为他对黑人有敌意,而他不过是在质疑为什么要把黑人的身份进行整体化和标签化。
《The Sellout》不仅嘲讽白人眼中被标签化的黑人,也嘲讽黑人对自己的美好想象。小说开篇以一种颇为荒诞不经的语调叙述了主人公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个疯狂的社会学家,在从事一项“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他崇敬各种解放运动的英雄,希望用科学实验证明,只有黑人才能够用完全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人,肩负了人类解放的希望。他拿自己儿子来做心理实验,他认为“旁观者效应”只会出现在冷漠的白人社区。他在马路上假装抢劫自己的儿子(身上挂满了珠宝),认为有爱心的黑人一定会来帮忙救人。结果一群黑人上来暴揍了主人公一顿。
强调自己种族的特殊性来对抗西方霸权,用尼尔・拉森(Neil Larse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欧洲中心主义”(inverted Eurocentrism)。他们将外界投射到他们身上的身份给内化(internalised)了。实际上,“白人”从来不会将自己身份进行特殊化,反而叫自己“美国人”。相反,那些“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等身份标签,不过都是在确证那条形成等级的链条:“他们是朝向未来的,到了那一天,美国就会彻底实现它的普世理想”,但他们这些“特殊性”的存在则证明了,那个“普世理想”从未实现。可以说,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际是在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一元普世主义所服务。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下,少数族裔的特殊性被拿出来强调,仅仅是为着佐证其普世理想之荣光和伟大。事实上,少数族裔越是建立这样的身份认同,越是陷入了一个逐渐失去自己身份的怪圈。这种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非常保守的。
人们到处制造一些漂亮的、抚慰人心的座右铭和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仿佛“属于黑人的美国”只需要不断喊口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The Sellout》同样也嘲讽了这种普世理想的虚伪性,在序言中作者调侃地对一种“座右铭文化”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讨论,人们到处制造一些漂亮的、抚慰人心的座右铭和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仿佛“属于黑人的美国”只需要不断喊口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这里,作者所嘲讽的口号无疑既是指那些“普世理想”,也是指那些被压迫者在反抗时对普世理想所进行的拙劣模仿。
保罗・比蒂总是擅长把严肃、重大的命题轻巧地化成一个幽默的玩笑。他谈到在学校,到处都是对歧视的指控。他回忆当时的经历说道:“我从来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人们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在评定种族歧视?”那些正义凛然的反抗,那些高举着标语和口号地追求平等,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些可疑且可笑。
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经表示,她想要在没有任何“白人凝视”的情况下写作,那就不会仿佛有人在指挥她应该要如何写、应该要如何感受的压力。保罗・比蒂对此回应道:不,这简直像一部纯黑人的电视剧,里面没有一个白人角色…… 也许保罗・比蒂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那么非“黑”即“白”、截然两分,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张沅汐,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研究兴趣为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者。)
编注:题为编辑所拟,作者原题目为〈保罗・比蒂:我不知道人们用什么标准评定种族歧视〉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