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到田野中去!」這是來自人類學的呼喚。人類學學者們常常要「做田野」:確定一個課題,到那個地方去,學習當地的語言並在那裡生活一段時間,理解當地的文化意義系統,分析與問題相關的權力博弈,或者拆解外界如何與當地關聯。人類學的研究興趣廣泛,為了了解「異文化」,有的人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去一個部落、小島、工廠,有的在城市間撰寫其他族群、人群的遭遇,或在街角、社運基地漫遊。歷經多年,「田野」的空間早已更為多元,但人們對田野的想象依然充滿新奇、樂趣及異域風情,人類學家的生活好像「打怪」,總是充滿挑戰但又總是能有驚無險地化解。
但「田野」真的是這樣嗎?人類學有一本著名的小書《天真的人類學家》,就誠實而風趣地紀錄了人類學家在田野過程中面臨的乏味、挫折,甚至災難、生病與敵意。新鮮事物當然是有的,但畢竟,這是一個做研究的過程,在與研究對象互動的過程中,研究者要調整學術成見,從海量資料中抽取關鍵,也要反思和檢討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地位與盲點。
而相較於海外的田野讀本,華人學者的研究經驗或許更容易引起共鳴與討論,同時也不乏對英語類人類學研究的再反思——這就是兩本新書《田野的技藝》(新版)與《辶反田野》所想要呈現的內容——以較輕鬆的方式。《端傳媒》獲「左岸文化」授權,摘錄兩本書的部分序言及書摘,以比照閱讀的方式,來為讀者介紹這兩本書的樂趣。希望無論你是人類學專業與否,都能抱持開放的心態擁抱及反思自己與這個世界的種種關係。
《田野的技藝》
作者: 林開忠, 張雯勤, 郭佩宜, 王宏仁, 趙綺芳, 莊雅仲, 容邵武, 龔宜君, 顧坤惠, 邱韻芳, 林秀幸...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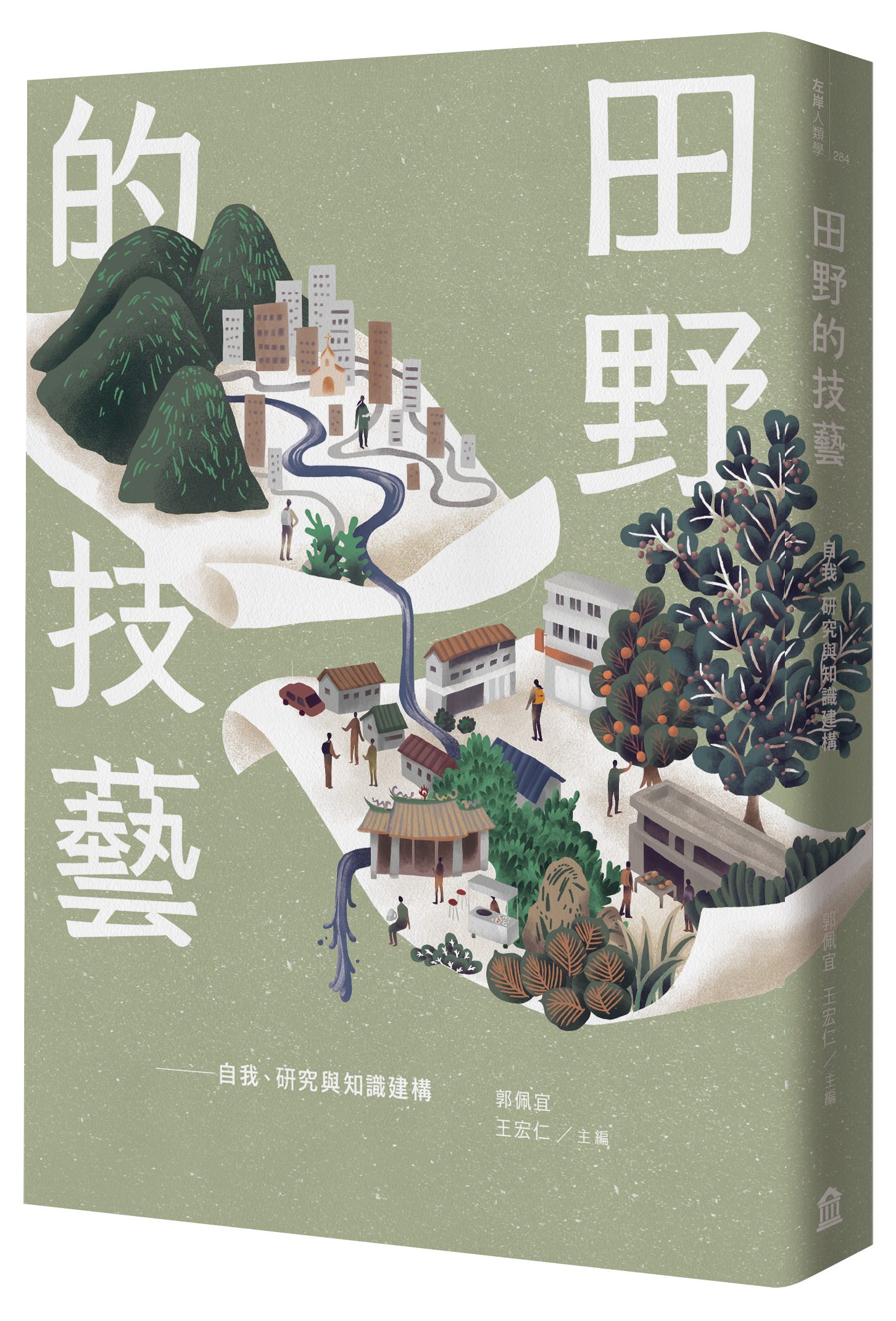
##《田野的技藝》新版序(郭佩宜、王宏仁):
什麼是「田野工作」?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做的田野有什麼不同?十多年前,一群學界菜鳥決定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面對自己,檢視研究的歷程,勇敢地把犯錯、掙扎、焦慮、喜悅與領悟,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書寫出來。我們認為台灣需要這樣的一本書,相較於翻譯國外的田野讀本,台灣學者的經驗以及田野背景更能引起讀者共鳴。
二OO六年二月,《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問世。攤開台灣社會科學的研究入門或研究方法課程大綱,這些年來,《田野的技藝》幾乎是指定閱讀或參考閱讀書目的基本元素了。許多老師反映,書中的田野故事與議題,往往引發課堂上的熱烈討論;這本書也廣泛為橫跨許多學科的博碩士論文以及一般學術論文引用。台大人類系林開世教授指出,這本書「是國內目前對於人類學式田野工作過程中,研究者的經驗與民族誌知識建構之間的關係,提供最全面與最多樣的反省與檢討的作品」。
這本書並不只預設為課堂使用,而是希望能作為社會科學普及來閱讀。我們在導論一開始就說:「如果你不是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生,也不打算跨進這個領域,只要你對了解異文化有興趣,對了解研究者到底在做什麼感到好奇,這本書還是很有趣。」全書從導論到每則故事,都「講白話」。
>田野過程變化多端,我們經常必須走進意外旅程。
田野過程變化多端,我們經常必須走進意外旅程,本書非結構化的寫作風格,也恰恰表現了田野過程的多樣面貌,讓這個技藝呈現複雜多元的可能。
《田野的技藝》中講述的故事,在一齒年後的今日讀來,一點都不過時。我們大致保留原來文字與全書結構,包括兩位主編的幾段賦格曲對話。此外有些作者也添上後記,敘述自己研究的轉變,以及讀者們最想知道的、故事中角色的後續發展。隨著近年台灣社會的劇烈轉變,以及新生代研究者、研究課題的浮現,加上國際學術思潮的影響,田野工作也面臨了不同的挑戰。《田野的技藝》重出江湖之際,我們也策畫了第二輯姊妹作——《辶反田野》,邀請讀者們兩本田野故事對照閱讀,一起琢磨田野的技藝。
##《田野的技藝》書摘:太魯閣或賽德克?
在一九九六年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所舉辦的「正名『太魯閣族』研討會」中,正名的議題首次浮上檯面。在這次會議裡,幾位Truku牧者大力抨擊過去政府與學界錯誤地把Truku人歸類為「泰雅族」,並提出正名為「太魯閣族」的主張。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正名議題並未引來大社會太多關注,反倒是形成了族群菁英內部之間的爭議,進而衍生出「泰雅族」、「太魯閣族」,和「賽德克族」三派不同的主張。其中強烈反對脫離「泰雅」的是著有數種泰雅相關著作的Truku學者廖守臣,認為應以「賽德克」為族名的呼聲則主要來自南投,不過,在花蓮也獲得不少Toda、Tkdaya知識分子,以及部分Truku菁英的支持。一九九九年廖守臣去世之後,主張以「泰雅」為族名的陣營頓失重心,但另兩派之間的爭議仍舊無法獲得解決,正名運動就在這樣的僵局下漸漸地停擺。
二○○一年八月,人數僅有三百多人的邵族被官方承認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族,帶給當初推動正名的Truku菁英相當大的刺激,使得正名的議題再度受到關注。雖然我研究的主題是宗教,但正名運動是長老教會所主導,因此也成為我觀察的項目之一。參與相關活動的過程中不免會被問及對正名的看法,對於這樣敏感的問題,我自然很小心地不去下價值判斷,更不會擺明去支持哪一方,但私底下當然還是有自己的一些觀點。在我看來,Truku和自稱Tayal的「泰雅」之間的族群界線是很明確的。雙方在文化形貌上雖有相當的相似性,但並無同源的認知,即使長期被學界同歸為泰雅族,也並未因此形成一體感。至於花蓮的Truku和南投的「賽德克」則明顯的是同一來源,因此就「邏輯」而言,涵括了Truku、Toda、Tkdaya三個群體的「賽德克」一詞,似乎是比「太魯閣」(Truku的國語音譯)更合理的一個族稱。
隨著正名運動的重新推動,主張「賽德克」與「太魯閣」為族名的兩派陣營間的對抗也日益激烈。在不願放棄「太魯閣」這個名稱,又無法獲得南投方面認同的僵局下,一些花蓮的Truku菁英開始修正「太魯閣族」論述的內涵。他們表示,在老人的口述中,Toda和Tkdaya乃是從Truku人的起源地,亦即南投的Truku-Truwan分支出去的,因此以「太魯閣」來統稱三個群體有其合理性。如果南投方面和花蓮其他兩個語群認同「太魯閣族」並願意加入,他們非常歡迎,若這些群體有自己認定的族名,他們也表示尊重。相對地,各群體也應該尊重花蓮Truku人對自我族稱的堅持。
發展至此,花蓮的太魯閣族正名運動已經從原先的以脫離泰雅族為訴求,轉為強調花蓮經驗與南投經驗的不同,來支持Truku人脫離「賽德克」範疇,另以「太魯閣」作為族稱的合理性。在二○○一年年底所舉辦的「太魯閣事件一○五周年紀念研討會」中,幾位Truku知識分子均以「花蓮的太魯閣事件」來與「南投的霧社事件」做對比,強調前者在戰爭的規模與激烈程度上皆超過後者,卻遠不如霧社事件受到大社會與學術界的重視。我坐在台下聽著這些慷慨激昂的陳述,突然覺得他們有些像這些年來力圖建構自身族群主體性與認同,以凸顯與中國之間差異的台灣人。自此,當再被問及有關Truku正名的看法,「中國vs.台灣」成了我用來分析南投賽德克與花蓮Truku關係時一個常用的類比。我說,就像獨立和統一的主張一樣,族群的認同乃是基於主觀的認知,無關對錯。一方面我們無法否認台灣和大陸的歷史淵源,但另一方面,經過了長時間的分隔,雙方在歷史記憶、生活經驗各方面都產生了相當的歧異。在這種既相似又相異的混沌中,無論獨立或統一都有充分的材料得以發展出支持其主觀認同的一套論述。
>這樣的比喻不曾遭到反駁,我自己也認為相當客觀、合理。可是漸漸地我卻發現,「中國vs.台灣」與「賽德克vs.太魯閣」這個比喻的移入,使得我對正名運動的立場與觀感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
這樣的比喻不曾遭到反駁,我自己也認為相當客觀、合理。可是漸漸地我卻發現,「中國vs.台灣」與「賽德克vs.太魯閣」這個比喻的移入,使得我對正名運動的立場與觀感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原先我是以一個置身事外,理性的他者(etic)角度,去看待「賽德克vs.太魯閣」之間的關聯,認定前者是較「合理」的族稱。然而,在「中國vs.台灣」這個二元框架中,我卻是一個局內人,有對這件事的「土著」觀點,其中負載了我自身的成長經驗與情感。在政治傾向上、情感上,我的認同始終是偏向台灣的,這樣的立場使得我對於太魯閣族正名產生了同理心,以至於不知不覺中卸下了理性,從一個更接近主位(emic)的角度去體會他們之所以堅持以「太魯閣」為族名的心情。我開始注意到,在花蓮,支持「賽德克」為族名的一方往往以學者的研究、客觀的歷史證據來支持其論述,而主張「太魯閣」的這方所訴諸的卻主要是認同、情感與自身的成長經驗;當主張「賽德克」之陣營的一名大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陳述其意見時,前一句國語的「我們賽德克」,在下一句轉換成母語時卻不得不成為「Ita Truku」(Ita:我們),因為在花蓮的用語中,sediq/seejiq/seediq只意指「人」,而不像在南投同時也是Toda、Truku,以及Tkdaya三個群體共同的自我族稱。這些線索引導著我進一步去發掘原先沒有感受到的,正名的意識形態背後所潛藏之更深切的文化、情感與歷史等細緻的面向。
此時另一位人類學研究生的出現,讓我更清楚意識到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對於現象的詮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進入人類學這個領域之前,我和這位研究生都曾從事與原住民相關的工作,在部落裡有過一面之緣。多年後在田野裡相遇,幾次交談後我發現,兩人看待Truku人正名的角度有著相當的差異,而這主要是源於我們各自不同的部落經驗。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因蒐集泰雅族紋面的素材走訪了全省各地的「泰雅」(包含Truku在內)部落,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對「泰雅族」有著深厚的感情,也親身感受到被歸為「泰雅族」的各個群體間,的確存在許多文化的相似性。因此,他在面對太魯閣正名的議題時,始終將其放在整個「泰雅族」的架構下來考量。而我過去工作時所接觸的原住族群中並不包含泰雅,對泰雅的陌生,使得我看待正名時完全是以Truku為中心。
雖然在田野中已經預期到兩人日後在正名這個主題上會有相當不同的呈現,不過,當我看到他的論文時還是頗為震撼。除了對一些相同的材料我們有近乎相反的詮釋,他文中的一個結論也讓我覺得難以釋懷。他認為,那些力主「太魯閣族」正名的Truku菁英一連串同中求異的論點,徹底印證了「工具論」的主張,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目的與脈絡下,人們可以任意裁切、混合族群的傳統與文化,以形塑個人或族群的「新」認同。
我並不否認花蓮Truku人的正名訴求有政治動機在內,正名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的行動,但它絕不僅僅只是為了利益,同時也包含了更多複雜的面向。對整體泰雅族的情感使得前述的那位研究者將目光聚焦在Truku人正名過程中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而我卻因為自身的台灣認同傾向,被正名行動背後所蘊藏的「根本賦予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所吸引。我們都不可避免地在個人經驗的引導下,影響了詮釋時所採取的角度。
《辶反田野》
作者: 趙恩潔, 蔡晏霖, 郭佩宜, 呂欣怡, 容邵武, 方怡潔, 羅素玫, 李宜澤, 邱韻芳, 陳如珍...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

##《辶反田野》序言(蔡晏霖、趙恩潔):
從高科技產銷到創新社會設計,越來越多領域伸臂擁抱「田野」,期待「田野調查」為相關產業帶來更正確的市場評估、更精準的受眾認識、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題。可以說,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不只強調演算法的大數據夯;與大數據精神完全相反,強調「純手工、親體驗」的田野工作,也正夯。
隨著社會遞嬗,今日田野的樣貌變化萬千,田野技藝也隨之轉變。曾有不少人擔心、甚至預言,當所謂的「傳統」消失(姑且不論所謂的「傳統」是否只是一種「現代性」的追求下,被篩選整合起來、甚至「發明」出來的一套東西),人類學將無用武之地。但這個預言失準了,因它小看了田野觸角的延伸力,也錯估了人類學的精神。今日,在更多意想不到的空間,「田野」遍地開花。不論是在紐約華爾街、西方與非西方的科學實驗室、世界各地的電子工廠、醫院診所、爵士酒吧、高空彈跳現場、黑客松、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棲息地、「第二人生」的線上虛擬遊戲,乃至殘酷的戰場邊緣,都可以找到正在做田野的人類學家。
與此同時,「田野工作」也早已不再只是人類學與最靠近人類學的質性社會學研究的專利。雖然很少有其他學科的人會仿效從事「古典田野」的人類學者那樣,長年專一地「只過他人的生活」,而通常是以相對短期、也可能長年延續的參與及訪談為主;但有越來越多的學科,都加強了其對「田野」方法的倚重。舉凡教育學、地理學、政治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歷史學、國際關係、科技與社會、藝術研究、社會工作、環境資源管理,以及其他越來越多學科開設相關課程教授田野工作,也有高中老師指定學生作業必須根據田野材料而寫成。台灣社會似乎在短短幾年間,就有了各式各樣急速增生的「田野」實踐。
這本書,是一群田野工作者對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邀請,與補充。既是錦上添花,也是盛世危言。身為以人類學為職志的田野工作者,我們無意捍衛「田野」不可動搖的最低底線或「正統」。恰恰相反的,我們想延續《田野的技藝》一書的精神,搜羅種種難以寫進田野教科書或工具書的田野歷程,同時更進一步分享,在遇到國家官僚發展計畫與學院管理績效化下重重機關的硬體制時,已經被迫「轉大人」甚至變成「老鳥」的人類學者,該如何選擇田野、也被田野選擇?這些歷程難以被複製、被標準化,或是按表操課,甚至可能是屬於這一輪盛世的特有種經驗,但卻是我們認為「做田野」最迷人、也是最讓我們髮稀齒搖終不悔的理由。
這本書,同時也是一群田野工作者檢視自身田野歷程的直心書寫。說直心,並不是因為我們的田野故事比較激情、勁爆或者十八禁(雖然,那也很值得期待XD),而是因為我們都曾經傻呼呼地土法煉鋼,對田野感到沮喪、挫折,卻仍從田野工作的平凡無奇與日復一日的未知黑暗中,看見了田野之光。藉由此書,我們想為這個田野盛世打開的,是細膩描寫個人經驗,不怕自問,一邊深入直搗田野的種種難題,一邊拒絕被績效控管的另類空間—一個田野異托邦。在這個異托邦,田野狀況無法事先規畫預測、生命體會的成果無法寫入研究報告、最想說的話不會被刊登在期刊、最想做的計畫也不會通過制式的倫理審查。
>我們將本書命名為「辶反田野」,一個同時表達「反田野」與「返田野」的多義雙關詞。
我們將本書命名為「辶反田野」,一個同時表達「反田野」與「返田野」的多義雙關詞。我們特別選取「辶」部首為字,它有「忽走忽停」與「奔走」的流動意涵,以此指出「反」與「返」之間的時間差,並標示「反」與「返」重疊交錯的可能。因而,「反田野」、「返田野」、「辶反田野」是本書的三大主軸。
「反田野」,代表我們對於古典田野工作範式與大眾想像的不斷反思。在什麼條件下,「古典」的田野範式精神依然足以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田野風景,且在被賦予更多工流動的形式與生命之後,與新田野範式們仍有可承接之處?藉由「反田野」,本書的作者們嘗試思索田野範式與時空背景之間的關係。
「返田野」,聚焦的則是我們對田野的一再回返,透過不同田野的對比與反差來探問何謂田野工作。藉由「返田野」,我們努力思考從一個自己愛過或痛過的田野,到下一個新田野之間的斷裂與承接,誠實面對個人生命與學術職涯之間的交織愛恨。
最後,從「反」到「返」的時間差與輪迴性,則提醒我們關注田野的時間質地。慣常的田野想像中,時間是同質與線性的流動:進入田野↓進行田野↓完成田野。然而在成書過程的共同書寫與討論中,最引發眾人共鳴的話題,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更多異質的田野時間想像。
抱著如此對時間的特定關懷,本書因而有別於過去三十多年來英語系人類學界所發展出的各種新田野概念,諸如「反身性民族誌」(書寫者的權威應被挑戰)、「去地域化的空間」(每個「地方」的固有疆界如何被權力關係生產出來)、「全球組裝」(治理術、技術與倫理的再地域化或在地用法,如生物科技在世界不同角落有著不同的運用),乃至「多點田野」(比如研究移民與難民,其生活流動的本質,要求田野工作者無法蹲點在單一地點)等。我們雖然承接以上這些概念的基本精神,但更強調從空間的反思進入時間的反思,最後迎向非生產性導向的另類時間觀。我們認為,人類學田野工作中許多必要的學習、醞釀,與等待,以及在自身與異文化之間的不斷反覆對照,雖然看似缺乏「效率」與浪費「時間」,其實卻正有助於我們捕捉複雜繽紛的動態真實,甚至還拓展了我們對於「真實」的想像。

##《辶反田野》書摘:「發展計畫」中的人類學家
位於桃園復興區的嘎色鬧在行政區域上屬於奎輝村的七至九鄰。奎輝村共有五個部落—枕頭山、下奎輝、中奎輝、上奎輝及嘎色鬧,其中地處最深山的嘎色鬧是唯一經過奎輝村主要道路時看不到的聚落,海拔七百到八百公尺之間,群山環繞、多雲多霧,因位於最角落之處,就連同為復興區的泰雅族人,也未必知道有嘎色鬧這個部落。
在活力部落計畫的人員配置中有兩個最基本的職位,分別是計畫主持人與部落營造員,而後者的角色又比前者更為關鍵。營造員是計畫中唯一領專任薪資的職位,對外必須面對原民會、縣政府,和輔導團隊,處理非常多且繁瑣的文書與行政事務,對內則必須協調不同立場、觀點的族人與各個組織,是非常辛苦且需要耐心與毅力的職務。相對於專職的營造員,計畫主持人的參與程度則相當有彈性,有些甚至只是掛名而已。嘎色鬧的哈告牧師是少見的非常投入的計畫主持人,他和營造員星美是我在活力計畫中所見過互相搭配最好的工作伙伴。
二○一二年八月,我到嘎色鬧做每個月例行的活力部落訪視,星美和牧師談起下一年度所要提的計畫內容:
「老師,明年營造民族環境部分,我們想要以蜻蜓作嘎色鬧的部落意象。」
「蜻蜓?為什麼是蜻蜓?」我的腦海立刻出現許多問號。
「因為我們部落有很多種不同的蜻蜓。」
「就只是這樣?」我繼續追問,「可是,蜻蜓和泰雅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牧師和星美一時也無法解答我的困惑,於是我請他們透過部落會議再和族人討論看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此外,計畫內容中還有一個項目是想請一位近年來知名度頗高的年輕泰雅畫家在部落入口處繪製故事牆。我沉默了一會兒,忍不住又說出心中不同的想法:「我看過那個畫家的畫,挺好的,真的,可是︙︙你們要不要考慮自己動手畫?」
我的擔憂其來有自。前幾年,曾有一個我陪伴輔導的泰雅部落聘請這位年輕畫家繪製故事牆,成品美雖美矣,但我總覺得他的個人風格太強,以致畫出的作品和部落生活有一種距離感,感覺那面故事牆仍舊是屬於畫家本人,而非在此生活的族人。再者,我也擔心會有越來越多的泰雅部落邀請這畫家來「負責」部落民族環境的營造,到時,豈不又是一場看起來都「一樣美」且「一樣泰雅」的惡夢?
一個月過後,牧師和星美告訴我部落會議的討論結果。故事牆的部分採納了我的建議,不假他人之手,由族人組成工班,自己討論、繪製和施作;至於部落意象,還是決定用蜻蜓。這回牧師除了再次對我強調部落裡至少有七、八種以上的蜻蜓外,還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族人認為可以用「蜻蜓點水」來比喻他們的祖先從原居地遷移到嘎色鬧部落的曲折歷程,途中經過幾個地點「產卵」都沒有成功,一直到抵達了有許多獵物足跡的嘎色鬧才定居下來。
雖然我心裡對於蜻蜓是否為合適的「部落意象」還是有些不確定,但部落會議的背書,加上以蜻蜓作為比喻來詮釋部落遷移歷程的說法暫時說服了我。不過,後續的發展充分證明了「蜻蜓」的確是一個可以凝聚嘎色鬧族人的有力象徵。工班和隨機加入的族人們熱列地討論該用什麼材質、形式,然後一起動手施作,最後完成了十來個色彩繽紛的蜻蜓裝置意象,以及三支巨大的體驗管蜻蜓。
蜻蜓意象的製作,意外地成為這個小小部落裡的吸睛事件,也讓一些原本不清楚或是未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族人加入了討論,甚至實際動手參與。此外,因為這些五顏六色的成品太討人喜歡,甚至有上部落的族人抗議,為什麼只有下部落有這些蜻蜓意象,他們也想要。星美解釋由於經費有限,加上需要土地同意書才能施作,因此只能先在進入部落的道路兩旁以及入口區域設置。商量後,上部落的族人決定自己解決經費與土地的相關問題,請工班也為上部落製作蜻蜓意象裝置。
故事牆的部分又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過程。延續了之前製作蜻蜓意象的經驗與熱情,這次工班施作故事展板的步驟更加細膩,從討論主題、繪製草圖,到線雕、上色,最後把展板裝上牆面,雖然不是很專業,甚至最後的成品還留著錯誤塗抹的痕跡,但卻非常樸實動人,且從材質到內容都是獨一無二的嘎色鬧風味。工班總共協力完成了八個故事展板,每個展板都代表了一個他們討論後想要表達的重要主題,再利用羅馬拼音的族語和簡單的圖像來表達。第一幅就是用「蜻蜓」意象描繪族人從原居地一路找尋適合居住的家園,最後來到了獵物豐饒的嘎色鬧定居之「部落遷徙圖」。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主題則是「sbayux」(換工),下方三個子圖繪出了過去族人最主要的換工場景:「kbalay ngsal」(蓋房子)、「muhi pagay」(種稻),以及「mnayang」(燒墾)。
期中評鑑當天,我聽著牧師向評鑑委員一一述說這些不同故事展板所要表達的意涵,以及製作過程中族人的相關討論,深深感受到這些展板不僅僅只是為了要讓外來的訪客藉此了解「嘎色鬧」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是族人合力創造出來的作品,刻畫著他們共同擁有的文化與記憶。
一個月後,我再度到嘎色鬧做例行訪視時,特地多留了一天。當晚和哈告牧師以及他的弟弟達告閒聊時,我才知道,原來蜻蜓除了生態與作為遷徙象徵的意義,更讓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牠是這些和我年齡相仿的中生代嘎色鬧族人共同的兒時記憶。兩兄弟神采飛揚地向我敘述他們小時候如何比賽抓蜻蜓,如何在其尾巴綁一條線「溜」蜻蜓。「蜻蜓是我們的童玩。」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然後,從蜻蜓又聊到他們孩提時的「狩獵」。達告說,嘎色鬧的國小分校對面那塊地過去種水稻,後來休耕長滿了芒草,就成為孩子們的遊樂園,以及抓竹雞、老鼠、伯勞鳥的狩獵場。他們可以在下課十分鐘從教室衝出來放陷阱,再在下一次下課時跑出來檢查有沒有抓到小動物,有些老師還會用便當和孩子們交換獵物。
>我聽得目瞪口呆,望著那塊如今種了火龍果的果園,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們口中的「狩獵場」。我突然理解,原來蜻蜓也不只是蜻蜓,而是與族人記憶中熟悉且難忘的部落環境與身體經驗深深鑲嵌在一起的。
我聽得目瞪口呆,望著那塊如今種了火龍果的果園,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們口中的「狩獵場」。我突然理解,原來蜻蜓也不只是蜻蜓,而是與族人記憶中熟悉且難忘的部落環境與身體經驗深深鑲嵌在一起的。在選擇「部落意象」時,嘎色鬧的族人沒有被一般刻板印象的「族群」文化所綁架,而是找到了「蜻蜓」──這個他們有著共同記憶因此可以投注情感與意義的物──作為代表部落的象徵,並且在將其轉化為具體部落意象的過程中,透過共同的討論與行動,賦予「蜻蜓」這個原本可能日漸從記憶中被淡忘的「物」新的詮釋與意義,使其成為連結嘎色鬧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媒介。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