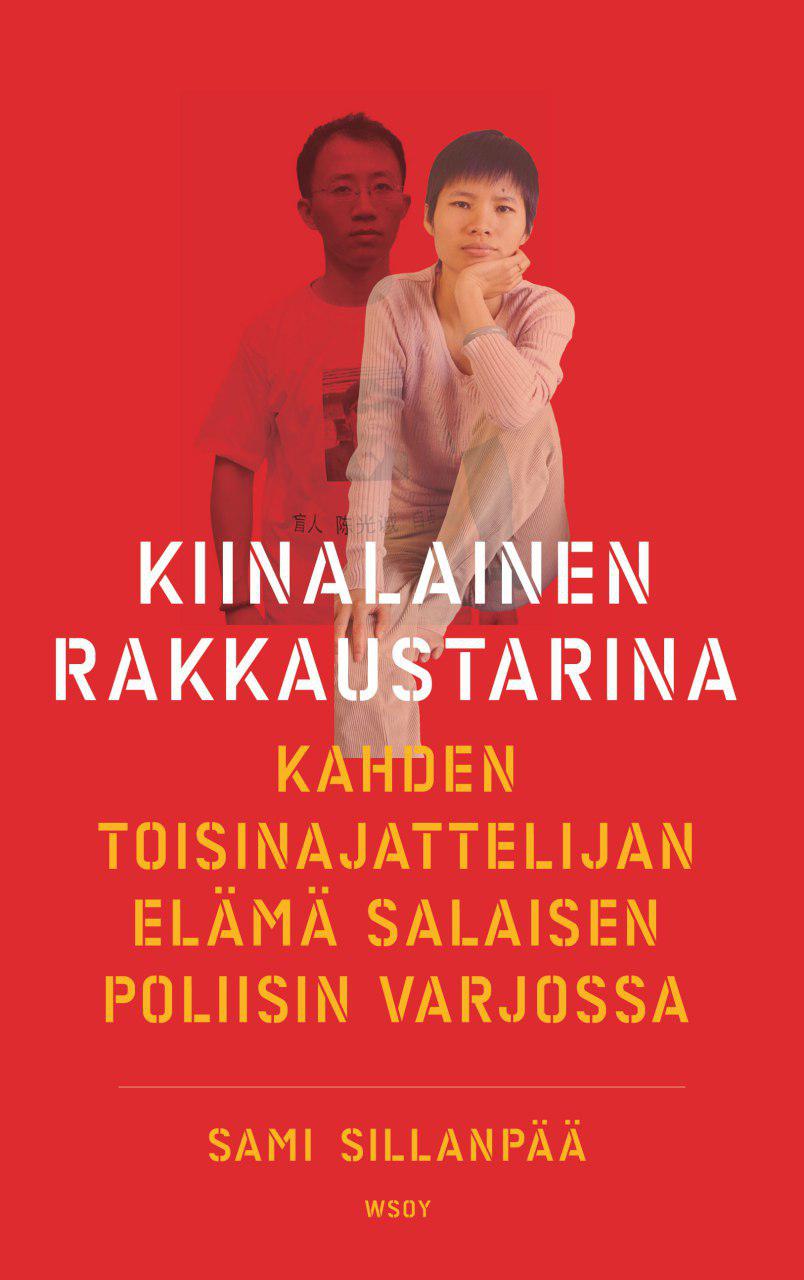
曉波在最後的陳述裏,表達了對妻子劉霞濃濃的愛意:「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曉波多次、長期被監禁的事實,劉霞在曉波勞教中與其成婚的經歷,劉霞和曉波情詩表意並被友人集結成集出版的紀錄,都告訴我們,在冰冷的政治中,在嚴重的不公面前,當公正遲遲未能降臨之際,這種深深理解對方、與對方共同承擔的浪漫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令曉波和劉霞在極度非人性的處境下,還能保持一個「誠實、負責、有尊嚴」的自我,令持續在中國土地上抗爭的人們,扼腕悲嘆、傳唱、進而奮起反抗。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註一: 愛爾蘭藝術家 Trish McAdam 選取了《我沒有敵人》的部分內容作為劇本創作了 No Enemies 的動畫。
註二: 所有未註明出處的引文,都來自《我沒有敵人》。
我們即將推出深度專題付費閱讀計劃,現在就參與群眾集資,立即成為付費會員

看完文章,默默的叹了一口气,有多少人未能知这篇文章,有多少人未知这样的可怕,如今要封锁vpn,更是让人心寒!香港的改变使人感到恐惧!刘晓波的就医限制使人感到可怕!
那天,的士上司機來一句話: 根本,有人類社會歷史以來,幾千年所有人同類間的政治鬥爭、廝殺,沒有新事,莫非都是為資源財富,跟森林爭吃爭地盤的動物完全一樣!
這甚有哲學意味的說話,竟出自一位市井之口。我敬佩劉曉波,他提醒讀者,我們即使在森林中,仍應該做個人,有"人"的特質,沒必要因為"我在森林中"這現實,就變成不是人。聖經有句近似的說話:"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從這眼光看,中共既得利益者外表很風光,大魚大肉,但他們極度可憐,他們在政治的近乎獸性的廝殺自選不做"人",天天恐懼驅動,天天刑罰自己,也漸漸做野獸,與"人"隔離。
習總訪港幾日,舖天蓋地的保安擾民,只使我搖頭嘆息: 這個人的恐懼,竟然到這種程度了? 紅歌抗音器近乎癲狂式地在灣仔鬥市早上炸到晚上,在厚重的大廈玻璃幕牆內,我一邊工作一邊被高音頻的紅歌精神虐待,也感到,香港很陌生……偶爾到玻璃牆邊看看街外一片紅色,我也只有訕笑沒有憤怒: 真可憐!這些沒有思想動物!
劉曉波和曼特拉都很對,你若是個人,對著沒有人的靈魂的野獸,沒必要變成野獸,也沒有必要憤怒了。
最近端的讀者質素有多下降,我是該慶幸端打入了敵人內部嗎?
狗屁文章,只是一群反中国的极端分子在迎合反华势力而已!
不管是所谓支持他的“自由派”或者反对他的“建制派”,都有一句共同的说辞,历史会还他公道的,就目前这段10年左右的历史来看,08年到17年,中东毁了,委内瑞拉完了,英国脱欧了,欧洲被难民搞垮了,然后美国出川普了,中国人均GDP快破1万了,深圳逐步靠近并超越曾经遥不可及的香港了,历史永远不会等人,但或许这段时间中国运气太好吧,就等历史继续进程吧
刘晓波的伟大在于他明白这个国家应该往何处去?应该如何往前走?可是这都不见容于当权者,还要迫害致死,而一般犯人更是没有保障了。敬佩刘晓波,但是已经不对当局抱有任何希望。可怜的是香港建制派成为了匍匐在中共脚下的奴隶,成为了香港民主的阻碍力量。大陆民主没来,香港反而要变成臭港了。
特别赞同里面的这句话:“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有时候反抗一个极端的人也会不知不觉走向另一个极端;两者皆讨人厌,而后者更会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遂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