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1日,夏霖的案子終審宣判。我一夜沒睡,六點起床,洗頭吹頭,還做了一個面膜,又化了粧。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門口見到大家,每個人都出奇地蒼白憔悴,我用手機背面照照自己,青天白日下,看見一個精心塗了口紅的鬼。我們進不去,過了一會兒宣判結束,律師仝宗錦出來,對着一堆精神極差的人說,夏霖的精神倒還可以。
2016年9月案子一審,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夏霖被以「詐騙罪」判監12年。我們繞着法院走了很多圈,最後確定了囚車會出來的門,遭到法警的阻擾,但車緩緩開出的時候,大家都成功地對着車大叫夏霖的名字。後來宗錦去看守所會見,夏霖說,他透過車窗看見了蕭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這次我們又等對了門,但他們找了兩輛囚車,蕭瀚跟着第一輛跑了很遠,我的直覺是夏霖在第二輛車裏,我是對的,這次我們看見了夏霖在車內對大家揮手。蕭瀚沒看到,他走遠處走回來,我們相互抱怨,我抱怨他太笨看不出法院的小把戲,他抱怨我既然有直覺卻不叫住他,大家都剛哭過,讓這不像吵架,倒像一種隱秘的互相安慰。
夏霖最終判了10年,這件沉沉壓在我們身邊每個人心頭的事情,起碼在程序上看起來有了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局。下午大家去了郭玉閃(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夏霖曾為其代理律師)在北邊的院子。初夏,萬物都美得驚心,院子裏有三隻貓。我們唉聲歎氣說一會兒夏霖,又興致勃勃談一會兒生活,最後大家開始熱烈討論,到底怎麼能在夏霖出來之前發財。他的面前是讓人絕望的漫長刑期,我們卻得若無其事照常生活,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勇敢,還是怯懦。
這篇文章也是這樣,它是勇敢和怯懦混雜的產物,兩年了,它一直放在我的電腦裏。始終不發的原因大概是始終有某種僥倖,覺得一切會有變化,但最終只是變得更糟。
消息越來越壞,直到沒有消息
剛出事的時候,我們總是見面。
見面的地點在北京城裏遊動。東四環的一個公寓(暖氣極熱,進屋後要脱掉襪子)。北四環萬聖書園沿着走廊一路往裏的老闆辦公室(桌上厚厚一疊進貨單,我着迷地一翻半個小時,看《小于一》又賣掉多少本)。西直門的卡拉OK(團購送五份炒飯,走廊裏有男人把女人逼到牆角激吻,我佯裝打電話,圍觀了全過程)。
這是2014年的冬天,大部分日子是濃濃灰霾,然而我們都習慣了這樣的北京,不再劇烈咳嗽與過敏,偶爾有那麼幾天,寒風刺痛萬物,天空是一種不應如此的湛藍,我們又重新對這個城市保留幻覺。
見面是想知道更多「消息」和商量「對策」。交換消息時,我們把手機放在老遠的地方,據說這樣就不會被竊聽。商量「對策」時,我們激烈辯論,好像手中真的有可以與之拼命的匕首。消息越來越壞,終於在抵達一個未知的臨界點時讓我們失去了鬥志,即使這種鬥志不過是指向虛無縹緲的敵人。
我們鬆懈下來,又開始討論八卦、美食和漂亮裙子。有一天我們在萬聖(書園)對面吃烤魚,有半頓飯時間大家為偶像劇《何以笙簫默》笑成一團,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值得笑的東西。笑到最後,我覺得自己的靈魂慢慢升起,凝視那一大盤子酸菜烤魚,有一些激烈的情緒在空氣中尋找出口,但房間逼仄,唯一一扇小窗早被鎖死,那股氣在藕片年糕和海帶萵筍中盤旋良久後發現無路可走,我回到了原地。
2015年1月中旬,有「消息」說,郭玉閃會在3月回家,夏霖的案子也可能隨之解決。我們見面的頻率從一週兩三次變為兩三週一次。我們把沉默歸咎於等待,以逃避若無其事照常生活的屈辱。大年三十那一天,大家在我家包餃子,十二點我煮了一鍋湯圓,吃完也就散了。(註:2014年10月,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2015年1月被以「非法經營罪」正式逮捕,9月獲取保候審,當時夏霖為其代理律師。)

想到多年前有一個大年三十,只有我倆和玉閃、阿潘(郭玉閃妻子潘海霞),我們聊到凌晨四點,蕭瀚偷偷在他們枕頭下放了壓歲錢。那時候北京還沒有限制外地車,阿潘開一輛深圳牌照的綠色 QQ,大年初一,他們走上空曠的五環,回到西二旗的家中。現在那輛 QQ 停在北邊郊區一個雜草重生的院子裏,它不被允許再次上路,這個城市無情地拒絕一切,而我們,在沉默中吞下了這些拒絕。
4月到了,北京的春天是沙塵暴、霧霾和白色玉蘭花的混雜物,讓我想不清楚愛憎。我買了許多新衣服,修改完一部關於愛情的長篇小說,但玉閃和夏霖並沒有回家,我們沒有得到更多消息。
有些事我不再一無所知,但跟我全無真正關係
是不是一定存在某個決定性瞬間,讓「我們」成為「我們」?
大學一年級,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紀錄片,《六四真相》。盜版VCD畫質粗糙,我模模糊糊記得王丹是個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個時候就有點發胖的影子,美麗的梁曉燕老師胸前搭着長辮子(後來我第一次見到她,就遺憾地問:曉燕老師,你的辮子呢?)。紀錄片裏的鮮血,和我父親多年來對他夢中情人杜憲的唸叨(杜憲,前央視《新聞聯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時,她身着黑西裝,以宣讀訃告的語氣宣讀中共中央決定,後被停職),再加上家裏的幾本「走向未來叢書」(1984至1988年出版,共約80本,1989年遭禁,編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讓我大致知道了八十年代與它的最後一個夏天。
大四快畢業,我在南京大學破舊悶熱的女生宿舍裏,讀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那是一本來路和去向都不明的盜版書,後來我才知道,這本書就是以這樣的形式先在南大校園內流傳,後來慢慢流向了全國。寫這本書的老師居然就在我們學校,而我,上過幾次他的選修課。雖然課堂上大部分時間忙於在最後一排給男朋友發短信,我還是莫名驕傲,去水房衝完冷水澡依然渾身滾燙,一股讓我陌生的快感和痛意在皮膚下流動,也許是因為那本書裏的毒太陽灼灼傷人,也許是因為南京已經接近四十度。
除了在知識層面上給我某種虛榮感,這些激動人心的瞬間並沒有真的帶來什麼。大學畢業,我去了廣州,在一家號稱全國最好的黨報裏做時政記者。工作忙碌,有時候下班已經十點,我和同事們去五羊新城的茶餐廳吃九塊八一隻的特價乳鴿,熱烈討論那些頭版上出現的名字和不知真假的官場秘辛,自以為那就是充實和體面。一個小姑娘,已經時不時進出省委開會,名字被鄭重其事印在與會人員名單上,去高級餐廳吃巨大的龍蝦刺身,飯後一個官員打電話叫另一個官員來買單,後者帶着厚厚幾疊現金,我眼睜睜看着他數了一百多張。這些場景多經歷幾次,我有時候覺得荒謬,有時候卻又滿足於虛妄。
我迅速適應了單位的話語體系,並且憑藉自己對文字的一丁點天賦熟練使用它。我為省委組織部寫的典型人物報導在報社內頗得好評,傳說中有一篇得到省委書記的批示,領導讓我為忘記什麼特刊寫幾篇讚美共產黨而且必須「文字優美」的散文,我就寫了,篇篇優美,在評報會上獲得加分,好像多拿了三百塊稿費。和某個部門的副主任在電梯裏遇到,她特意拍拍我的肩,說:「小姑娘,幹得不錯。」我很高興,以為自己真的幹得不錯,以為這就是我的前程。那個時候我絲毫沒有意識到,文字自有其靈魂與尊嚴,高華老師寫下的文字,和我所寫下的,會同樣白紙黑字留在歷史裏,只是他的流向大海,我的滋潤爛泥。
我還是喜歡讀書,買了新出的《米沃什詞典》,書裏說「我敬慕過許多人,我一向自認為是一棵彎曲的樹,所以尊敬那些筆直的樹……」。這句話寫得真好,我用紅筆在下面打上着重號。我還讀米沃什(Czeslaw Milosz,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詩,「你最好學會喜歡你的羞恥因為它會跟你在一起。不會走掉即使你改換了國家和姓名。可悲地恥於失敗。恥於供宰割的心。恥於獻媚的熱忱。恥於機巧的偽裝。恥於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當柴燒的樹木.…… 你時刻受到恥辱。」然而一轉頭,我又打開電腦,把省委給的通稿改成一篇消息,我所熱愛的文字和我所寫的分屬兩個平行世界,至於我自己,不覺羞恥,熱忱獻媚。

後來到了北京,工作單位變成在一家市場化都市報。我還是一個極為文藝的文藝青年,花680塊去看黃磊和袁泉那版《暗戀桃花源》,雲之凡美得不得了,即使在最無情的時候,她也是最美麗的山茶花。我人生最大的惆悵不過是並沒有人對我唱《追尋》,「你是晴空的流雲,你是午夜的流星」,雲之凡說「你看,到處充滿着希望,就像我們兩個一樣,你說,對不對?」我一路滴淚,坐地鐵回通州的家。
在這些纏綿悱惻的情緒之外,另外一個我一點點甦醒過來,也許是因為又讀了《墓碑》和《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引用富蘭克林,「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也許是一旦抽離那個一切理應如此的場,常識和自尊心總能在強光中掙扎着睜開雙眼。我在寫稿和談話中謹慎地不再使用「建國後」、「三年自然災害」和「毛主席」這些詞語,工作的榮譽感從稿件被省委書記批示,迅猛轉到了能不能在最高法院新聞發布會上逼問發言人對聶樹斌案表態。但一個人總會本能地為自己的生活辯護,有時候想到往事,我急切地說服自己:那又怎麼樣,那只是工作。
我連續幾年去報導全國「兩會」,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唇邊長泡,額頭有痘,披頭散髮滿臉浮腫的照片不知道怎麼被髮到網上,入選「兩會美女記者」,以前追過我的男同學看到了,給我發短信:「你都胖成這樣了啊。」我氣急敗壞回他:「我只有82斤!」為了採訪某個副部長,我在他的房間外一坐兩個小時,採訪的內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又採訪到一個高官,好像他的頭銜真能增加我的質量。我一點都不喜歡記者的工作,但敬業也是一種本能,我還不懂得站在工作背後的,是不可逃避的倫理與價值。
很多年以後,還是從米沃什的書中我知道「敬業」自有其複雜曲折,1949年他作為波蘭駐美國外交官回到華沙,參加一個聚會,他們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點才出門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着犯人的吉普車。在場的士兵和守衞穿着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兇」。
有一年我參加了總理發布會,精心打扮,穿正紅色羊毛大衣,戴一對從拉薩買回來的水晶耳環,虛榮地希望鏡頭掃過我,讓父母和追求男看到我體面標緻的樣子。發布會上最後一個問題,忘記是法新社還是路透社的記者問到(註:應為路透社記者),有一個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審判,他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一個月之後胡佳被判刑三年零六個月,我在上外媒網站看影評時無意中看到他妻子曾金燕在法庭外的照片,短髮,抱一個小嬰兒,神情憔悴。

真可憐,我想,出來時孩子都快四歲了。
這就是我當時的所有情緒,出於一種距離遙遠的人道主義憐憫。就是這樣,我輕快地越過六四真相、高華、米沃什、楊繼繩,越過和我一樣住在通州的胡佳、金燕,越過那些含混不清的反省與刺痛,自以為只是文學烏托邦的公民,有些事情我不再一無所知,但跟我全無真正關係。
又過了一年多,我遇到自己的關鍵性瞬間。我和蕭瀚在相識後迅速戀愛,迅速結婚,新世界轟然而來,它是幸福、恐懼與前路茫茫的混雜物,讓我想不清楚愛憎,一如北京的春天。
猶太人不會參加在奧斯維辛的春晚,我也不
最開始,我們只聊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沈從文,毛姆。我給他買李洱的《花腔》和諾曼•馬內阿的《論小丑》,他讓我去看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我閲讀政治意味濃厚的文學作品,卻很少將其與窗外的青天白日建立聯繫,我和一個在課堂上講六四的大學教師談戀愛,卻沒有意識到這背後可能隱藏的深淵。我們在盛夏的傍晚去後海喝酒,看見光照在水上,卻已迅速敗退,有那麼一段時間,光明和黑暗相安無事,在中間隔離出曖昧不明的陰影,我們就住在那裏。
不可控制地,話題半徑慢慢擴大,文學不再能滿滿填充愛情,因為生活就是如此。他提到劉曉波,我去查了一下,哦,是個詩人,但詩寫得一般。他提到王軍濤,我又去查了一下,哦,辯護律師是張思之,我知道張思之。他提到許志永和滕彪,呀,我知道他們,我是記者,記者總該知道孫志剛案。他重點提到郭玉閃,我就重點查了一下,哦,學經濟學的,參加了兩個 NGO,一個叫傳知行,一個叫公盟,是個胖子。
2009年7月的某一天,我們去吃米斯特披薩,在通州家樂福一樓,對着一家佐丹奴專賣店,我喜歡帶他來吃這家店,因為他們有三十二塊一位的自助沙拉吧。天氣苦熱,商場內空調開得極低,我們懶洋洋吃了一盤子又一盤子水果,把披薩里的芝士拉出長長白絲,熱戀時的話癆綜合症漸漸消退,我們開始享受在一起而不用說一句話的時間,看玻璃門外撐傘經過的姑娘,陽光在每一條裸露的小腿上照出斑駁光影。
他接了個電話,幾分鐘後掛掉後跟我說:許志永被帶走了。
那個時候我不像現在,對「被帶走」這件事已經有一套完整的應答程序:被誰帶走?國保還是派出所警察?有沒有給手續?手續是什麼?傳喚還是拘留?行政拘留還是刑事拘留?罪名是什麼?這個罪最高是判幾年?有沒有提前簽好委託書請好律師?
那個時候我只是呆呆地說:啊……那怎麼辦?
就像後來每一次有朋友「被帶走」,大家開始商量怎麼辦。但其實永遠不會真正找出「怎麼辦」,他們有監獄,我們,(按照我方人員的標準官方答案),只有信念、道義,和愛。這些詞語就像被寫進了手機備忘錄,時不時發出叮鈴巨響,提醒我們不要恐懼,不要被監獄佔據心靈。然而監獄就是監獄,得在眾目睽睽之下上廁所,一週只能洗一次頭,改善伙食才有大白菜熬肥肉,讀不到一本書,不能聽 Leonard Cohen 的 In My Secret Life(滕彪說過,在2011年「被帶走」的兩個多月中,他狂熱愛上對方用來墊盒飯的《新京報》,每天要求警察給自己放愛國宣傳片,因為這樣就可以聽到背景音樂)。
想到這些,我恐懼得要命。
我在庫切的《內心活動》裏看到本雅明的故事。1924年本雅明在意大利遇到拉齊斯,事後他說:「真正的愛情使我變得像我所愛的女人。」拉齊斯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本雅明則是猶太人,拉齊斯說:「愛思考的進步人士,如果他們是明智的,他們的道路將通往莫斯科而不是巴勒斯坦。」本雅明因此沒有移民去巴勒斯坦。
後來本雅明自殺了,我卻不想死。我恐懼蕭瀚甚至自己有一天都會進監獄,但又無計可施。我27歲,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相愛的男人,總不能為了一種讓人恐懼的可能性就放棄當下愛情。然而我又是個軟弱的人,平生經受的最大肉體痛苦不過是拔智齒,切菜切到手也要落幾滴淚,從來沒有想過,談一場戀愛需要做好這樣奮不顧身的準備。
忘記了後來到底是「怎麼辦」。好像蕭瀚包了一個黑車四處奔波找人在公開信上簽名。好像郭玉閃半夜打來電話,兩個男人羅裏囉嗦聊了五個小時,中途我幾次醒過來,看見窗簾外的黑夜漸漸不那麼黑,又轉頭昏睡過去。再後來,許志永出來了。

他來家裏吃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見面沒多久我就知道,我們有不同氣場,他不像郭玉閃,不會和我們成為親密朋友。但坐在一起嗑瓜子的時候,我還是感覺魔幻:眼前這個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連任海淀區人大代表,大學教師,上過《時尚先生》和《南方人物週刊》封面,在上訪村住了整整兩個月(這段經歷大概有利於他在監獄中熬下來)。有一次我去最高法院採訪,遇上他帶着訪民站在門口,那是隆冬時分的北京,我用羊絨圍巾遮住整張臉,急匆匆走向温暖的室內。等我參加完一個體面莊重的發布會出來,他還站在那裏,裹一件灰色棉襖,乍眼看過去,也就是訪民的樣子。這樣的人簡直應該入選「感動中國」,卻因為辦了公盟,一個做法律援助的 NGO,莫名其妙進了監獄,再莫名其妙又獲自由。
我做了幾個簡單的菜。我頗能做一些好菜,但我內心默默為朋友劃出等級,郭玉閃和夏霖來家裏,我花上五個小時做剁椒蒸肉,提前一天醃好雞翅,一大早去八里橋市場挑新鮮魚蝦。許志永來家裏,我用一個小時胡亂做出四五個菜,保證他能吃飽。他吃得挺投入,興高采烈給我們講他的「新公民運動」。2013年,他因為這件事再次進入監獄,這一次他被判了四年。但在當時,我對這個「運動」沒有一點好奇心,我只是忍不住在許志永走後和蕭瀚八卦:他現在女朋友是誰啊?他是不是要為反革命事業獻身,不打算結婚啦?
幾年之後,我們參加了許志永的婚禮,在北邊一個美麗的院子裏。烈日炎炎,我和阿潘在滿池荷花邊拍照,幾個小朋友擠擠挨挨抱住我倆的腿,奮力地希望鏡頭拍到他們的小臉蛋。我們沉浸於夏天、蓮葉和自助餐,渾然不知有一桌人不請自來,穿黑色衣服縮在牆角,冷冷觀察這個被陽光照得滾燙的大廳。新人以巴哈伊教教義宣誓的時候,我們在底下竊竊私語開玩笑:許志永運氣挺好,老婆看起來很靠譜,能跟着他吃苦。
誰知道後來她吃的苦一路吃到給他送牢飯,許志永被抓,崔箏剛懷孕,孩子生出來之後,她有一張抱着孩子等候會見的照片在朋友群裏流傳。我在一個深夜裏看到那張照片,孩子養得很好,像他爸爸一樣圓圓腦袋,崔箏則瘦了不少,她茫然望着地板。那個穿短裙的夏日在眼前跳動,荷葉上滾動露珠,新娘塗鮮紅脣膏,我在黑暗中落下淚來。
再回到2009年,10月1日那天我被報社分配去天安門廣場報導晚會。出發前我和小區裏的黑車師傅拿着北京市地圖看了很久,終於在種種限行的重圍中殺出了一條極其複雜的進城路線,在一度甚至上了京沈高速之後,我成功地來到了北京市區——我是說,長安街以外的北京市區,因為整條長安街幾乎都被限行。這個時候的北京完全是一個陌生之地:天藍得可怕,城市安靜地可怕,道路順暢得可怕。我們從南四環開到南二環,路上遇到的車不超過十輛,大部分的店鋪都關着門,路口沒有戴着紅袖章的老大媽,這個城市在舉行慶典的時候,連鴿子和風箏都不允許起飛。
我在下午三點到達金水橋接替同事,他在前一個晚上凌晨三點安檢結束後,坐着小板凳痴痴地等了七個小時。在後面的五個小時裏,我和幾米之外拿着紅綢子黃綢子的大中小學生們面面相覷,我煩躁不安,撐一把遮陽傘,看見前方有人等得太累,躺在長安街上睡起覺來,我羨慕那些睡着的人,他們好像把這個世界隔離在外。晚會結束後,我從天安門走到故宮,因為打不到車又重新穿過天安門走回前門去坐班車,自從去西藏爬了海拔4700米的雪山,我就沒有走過這麼長的路,但讓我挫敗的不是疲憊,而是荒謬和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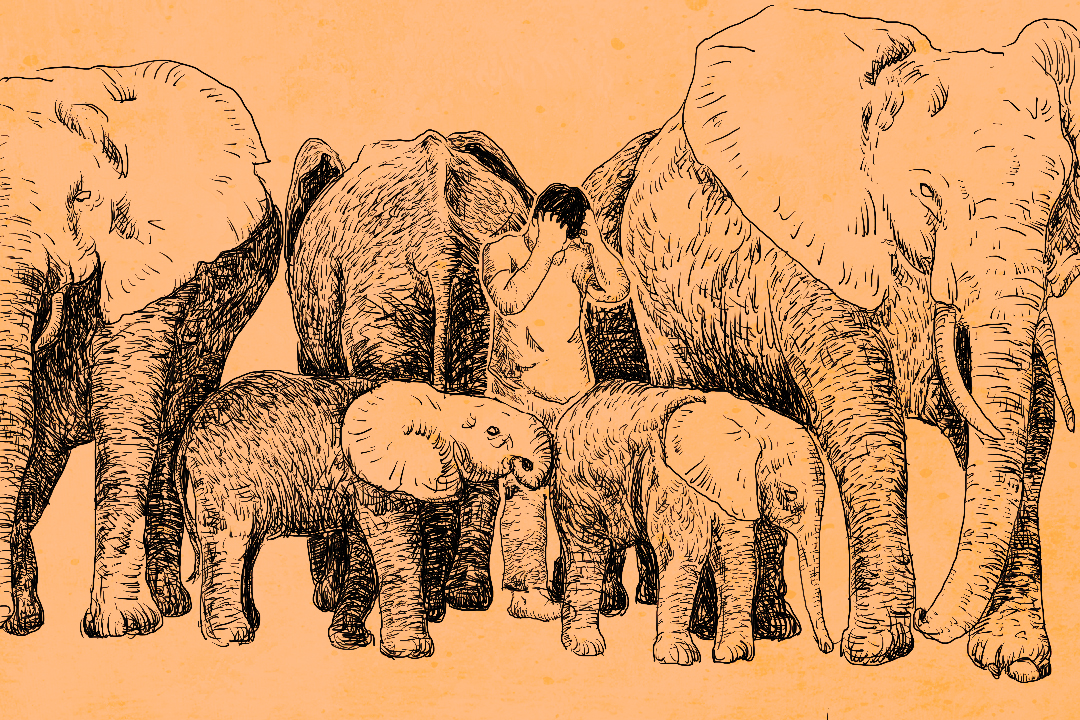
那個晚上讓我想到馬內阿在《論小丑》中描述齊奧賽斯庫的生日:「每年,為了慶祝他的生日這個國家都會組織盛大的活動。那種盛況既莊嚴又庸俗。就連那些組成千米長『人鏈』維持秩序,以防快樂人群擁擠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竊笑。」我回想那些舞動的彩色綢緞,廣場上巨大的花環,不敢相信自己身處其中,害怕某一張照片會拍下我,拍下我坐在一個曾經流血的廣場上,參加了他們的節日。猶太人不會參加在奧斯維辛舉辦春節聯歡晚會,我也不能如此。
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刻開始,我決心不再加入他們。我不要加入一個囚禁我的朋友、又轉頭若無其事燃放焰火的慶典。有張老照片裏,當所有人伸出右手向希特勒致敬時,有個男人冷冷注視這一切,收起了自己的右手。我決心收起自己的右手,我有點害怕,但也不那麼害怕,因為那個男人是孤身一人,我卻有愛人和朋友。

喜欢阿花的文字,那感觉就像自己一样,一个知道了真相的普通人,在生活和思想里摇摆,没有一种哲学告诉我信仰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敌人是体制还是某个谁,无从摆脱的谎言在大街小巷传颂。在公交车上广播。在宴会上堂而皇之的光鲜着。我没勇气站起来,大声喝骂,拆穿他,也没有抵抗的决心。因为任何事件的背后都是血泪,任何决定都会把一部分人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这泱泱大国里的少数人。我说了,也许会伤及无辜,妇人之仁如我,也只能默默站在这个少数的队列里,努力跟上真相,努力不被愚弄,努力摆正自己的信仰。我的爱也许和你不同,但不比你的真切少半分啊。
写的没头没脑
文中的通州家樂福也是我們日常生活無數次光顧的地方⋯世界這麼小⋯
雪崩发生前没有任何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可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哪怕不是最后一根,能够其中一根就可以堪称荣幸了。
阿花是算得上社会良心的传媒人,希望大家都不违背自己也都不违背良知。
谢谢阿花,谢谢端。
说句题外话,作者还没有摆脱做文章最忌惮的矫揉造作的习惯。很多地方无意义的卖弄文采,就拿标题来说,主题既与《鼠疫》无关,也与《局外人》无关,和加缪也牵连不大。文中的一些引用,比如米什沃,也欲言又止。这不是一个对文字有掌控力的人应该犯的错误。
这就是中国,我曾经如此近的住在文章里所叙述的通州,文章里所叙述的场景还如同昨日,现在我只能选择逃离,我没有选择也无从选择,国家机器的强大,我只能做一根稻草,传播这个党国的丑恶,期望有一天可以压垮它。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看完这篇,真的只能无奈的一声叹息,我们既无法与黑势力抗争,也无法逃出围墙,难道只能屈辱的苟活一辈子吗……
感谢端能登出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