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想法深刻影響著至今的政治學,奠基了政治學主要的國家理論——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在「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下人們處於無政府狀態,過著原始生活,無法處理各種瑣碎衝突,由是變成紛爭,因此人們需要相互結盟以保存己身,是之戰事撕殺不斷,文明無法產生,浪費各種資源。國家的作用即為最終仲裁者,解決人際間的種種衝突,定下發展方向,社會趨向良善。這種說法,烙有對「原始人」的定見與歧視,也因此證成了國家的權力與其對自然的侵佔,美其名為善用資源。今天種種對社會組成國家權力的政治理解,依舊以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論作為基礎,在國際關係層面尤甚。
與之相對對原住民的夢幻刻板形象則是「高貴野蠻人」——未受現代社會沾染,過著簡單生活的純真住民。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自然狀態的另外理解中窺探到這種對原始人的美好想像——原始人本性溫柔,對同類有愛,日常靠收集野果及狩獵維生,我們無法從群獸中分別獨特的個體原始人,他們沒有紛爭;一切的自私自利、爾虞我詐只是文明進化的不幸,是原始人以至我們現代人的不幸。
然而不管是「高貴」還是「沒有文明」,這兩種意像都試圖消除原住民的能動性(Agency),即是說,他們並沒有自主的行為,而是被動接受任何天災或人禍的次等人種。《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希望透過書寫這本書,來消除我們對原住民的定見,以至嘗試理解學習另一種生活形態的智慧。
查爾斯.曼恩以其接近報導文學的方式,穿插學術與歷史爭論,在這本超過600頁的中譯本裏娓娓道出1491年,在哥倫布「大發現」以前,印第安人的歷史。他指出,在十六世紀以前,印第安人口一度高達數千萬,而且大部份人住在城市裏,科技進步,他們會定期燒林開田,製造豐富肥沃的「印第安黑土」,卻深諸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與之取得平衡。事實上,今天我們所見廣大無邊的亞馬遜森林,當日不是現代人想像中的荒野森林,而是印第安人進行各種狩獵、採集、祭儀和人群活動的地域,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相互構成,對印第安人來說,無「墾植」與「野生」地貌之分,他們只是「單純依照生長於其中的物種而將地貌分為數十種類別」。
然而殖民者來到之前,美洲卻出現大旱災,以及由歐洲傳入的天花病,令到整個美洲的「基石物種」兼土地管理者——印第安人——大規模死亡,土地失去了穩定、靈活的照料,生態出現劇變,森林於是愈來愈濃密,成為後來殖民者所見到的「宏偉荒野」,換句話說,這種「荒野」乃是「人造荒野」。而且,如果把土地描成從無住民管理之空蕩大陸,也就意味著土地可以任由殖民者競奪,合理化他們「更好地」運用資源。「無主之地」這種說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文明社會」對各地原住民的踐踏,「壯麗的荒野」,實際上是建立於原住民的墳墓之上。
在以現代之名排斥毀滅各種生命形態的今天,「原住民」也許意味著更多。以為我們已經了解社會一切,可以操弄自然的觀念,不過是近百多年的事。我們讀到的歷史,也很大部分不過是能夠書寫文字留有奢華古物者的歷史。被消失的歷史,總是有意為之,當中總有國家所懼怕的顛覆潛能。我們也許該對各種被指示為落後、不合時宜的耕耘,持有學習的心態,有著更多敬意。
端傳媒一連數天摘載《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部份內容,這是第二篇,獲「衛城出版」授權刊出。
《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
出版時間:2016年12月
出版社: 衛城出版
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
譯者:陳信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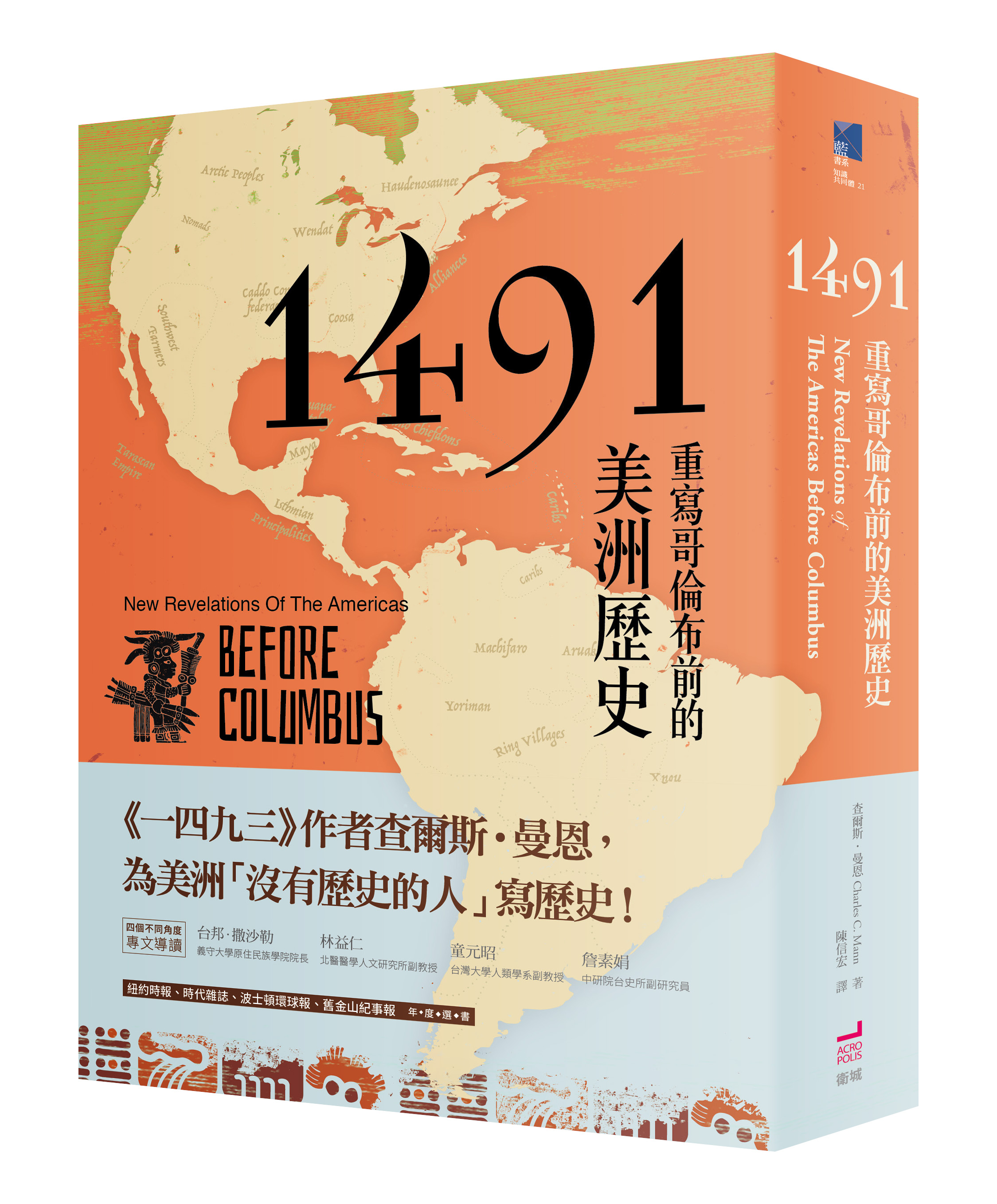
亞馬遜地區——奧雷亞納看見了什麼
要重建前哥倫布時期的歷史,最大的困難在於我們欠缺來自那段歷史的聲音。中部美洲的民族留下了若干文獻,現在那些文獻已逐漸揭露了他們的祕密;但在缺乏書寫文字的其他地區,則是留下一大片的寂靜。當然,過往事件的蛛絲馬跡可以在美洲原住民的口述傳統當中找到,但這些傳統比較著重在詮釋永恆真理,而非詳細的事實報導與歷史記載。聖經記述了許多過去的事情,但大學教授教導古代中東歷史的時候,還是必須審慎辨別其中的內容,並補充其他文獻資料。同樣的,流傳至今的印第安傳說間接呈現出過往的繽紛,但我們如果要瞭解古代印第安人的生活,就不能迴避最早見到他們的識字人士所留下的記載:包括歐洲的冒險家、尋寶客及傳教士。
從歷史文獻的角度來看,殖民時代的記述有許多不足之處。那些作者經常都與他們的書寫對象印第安人處於敵對狀態,也通常不懂得必要的語言,而且幾乎總是懷有其他目的,而不會單純秉持同理心描寫原住民的風俗習慣。有些人撰寫這些記述是為了促進自己的事業,有些人則是為了政治上的利益。但儘管如此,也不能因為這些原因就完全不理會這些記述。只要謹慎使用,這些記述還是能夠發揮佐證甚至闡釋的效果。
以卡瓦哈爾(Gaspar de Carvajal)為例,他撰寫了第一份亞馬遜河的書面描寫,卻幾乎自從一發表就因為其中偏離事實與充滿私心的描述而備受唾罵。卡瓦哈爾在一五○○年左右出生於埃斯特雷馬杜拉(Extremadura)這座西班牙城鎮,長大後加入道明會,前往南美洲向印加人傳教。他在一五三六年抵達,即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被殺的四年後。這時,擔任祕魯總督的皮薩羅已經學到,如果要避免無謂的暴力衝突,他就必須讓自己的部下隨時保持忙碌。其中一個最令人頭痛的麻煩製造者就是他自己的半血緣弟弟貢薩洛(Gonzalo Pizarro)。在那個時候,西班牙征服者的圈子裡熱烈流傳著黃金王(El Dorado)的傳說,據說這位美洲原住民國王擁有為數極多的黃金,會在一年一度的儀式上用金粉塗滿全身,然後再到一座特殊的湖泊洗掉這層閃亮的塗料。這種洗浴儀式施行了數百年後,那些金粉因此鋪滿湖底。一座黃金湖泊!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聽來,這個傳說實在荒誕不經,但聽在貢薩洛耳中卻不是如此,因為他已幫忙征服了一個坐擁大量珠寶與貴金屬的帝國。他決定去尋找黃金王所統治的黃金城,皮薩羅也鼓勵他這麼做,甚至可說是把貢薩洛推出了門外。一五四一年,貢薩洛率領著一支探險隊從安地斯山脈上的高海拔城市基多(Quito)出發,隊伍中包括二百至二百八十名西班牙士兵(各方記述互有出入)、二千頭豬及四千名高地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雖然沒有奴隸之名,實際上卻是奴隸)。這支探險隊的隨同教士就是卡瓦哈爾。
貢薩洛的尋寶之旅很快就從異想天開淪為一場災難。他根本不曉得該到哪裡去找黃金城,便在安地斯山脈東側的山麓丘陵盲目亂走了幾個月。那個地方在當時也和今天一樣是一片濃密的森林。由於山丘擋住從亞馬遜盆地吹來的風,吸收了其中的所有溼氣,所以那裡的地勢不僅陡峭,也相當潮溼,還富含生命力:到處都是昆蟲,空氣炎熱潮溼有如魔鬼的氣息,又在藤本植物與樹枝的交織之下遮蔽得暗無天日。才過幾個星期,大多數的馬匹就陸續死亡,馬蹄也因為浸泡於泥沼中而腐爛。大多數的印第安奴僕也未能倖免,他們被役使到精疲力盡,紛紛命斷在這片炎熱、潮溼,又和他們位於高山上的涼爽家鄉落差一萬二千英尺的地區。在失去馱獸與僕役的情況下,西班牙征服者只好奮力拼湊出一艘粗陋的船隻,載運著他們的槍枝與沉重器材從納波河(Napo River)這條亞馬遜河上游的支流順流而下。至於那些士兵,則只能在河岸上跋涉行進,雖然路線相同,卻艱苦得多。
森林愈來愈濃密,鄉間居民也愈來愈少。不久之後,他們就成為荒野中唯一的一群人。「沒有犬吠聲攪擾水面,」普雷斯科特在《祕魯征服史》中寫道:「除了荒野中的野生物種、笨重的巨蟒和在溪畔曬太陽的醜惡鱷魚,眼前不見任何其他生命跡象。」由於沒有印第安村落可供劫掠,探險隊很快就陷入糧食不足的窘境。他們身邊的森林雖然充滿食物,但西班牙人不曉得哪些植物可以食用。於是,他們先把倖存的豬隻全部吃光,接著吃狗,然後再用矛叉捕蜥蜴來吃。愈來愈多人病倒。貢薩洛的副手兼表親奧雷亞納(Francisco de Orellana)先前曾聽聞一些傳說,隱約提到納波河下游有一個富裕的村落,便提議由他帶領一部分的探險隊成員前去尋求補給品。貢薩洛同意了,於是奧雷亞納在一五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搭著探險隊最重要的船隻出發。他帶了五十九人,包括卡瓦哈爾在內。
九天之後,在納波河下游六百英里處,奧雷亞納發現了有糧食的村莊:他把這個社會稱為奧馬瓜(Omagua)。他和部下大吃一頓之後,開始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沿著原路逆流而上,把補給品帶給貢薩洛和其他人,這麼做的前景實在不吸引人。畢竟,逆流划船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而且他們也很清楚沿途根本沒有東西可以吃。結果,奧雷亞納決定拋下挨餓的貢薩洛,駕船前往河口,因為他相信這條河會注入大西洋,而他也猜對了(但他以為這條河不會太長,卻是猜錯了)。
卡瓦哈爾知道貢薩洛如果意外生還,必定會認為奧雷亞納背叛了他,因此自告奮勇偽造了一份為他們的行為賦予正當性的文件:撰寫一份記述,「證明」他們拋下貢薩洛是不得已的決定。為了滿足西班牙的法律要求,奧雷亞納假裝自己因為不願拋下貢薩洛而辭去他的暫代領導職務。卡瓦哈爾宣稱眾人「對神發誓……對著十字架,也對著四福音書發誓」,表示他們希望奧雷亞納繼續領導他們。在龐大的壓力下,奧雷亞納只好順應眾意,於是他們建造了另一艘船隻,朝著下游出發。
他們對貢薩洛的反應感到憂慮確實是有先見之明。奧雷亞納離開之後過了半年,那支探險隊的生還者衣衫襤褸地拖著腳步走進了基多。貢薩洛也是其中一人。他隨即要求逮捕及處決奧雷亞納。他指出,奧雷亞納從他那支饑餓不已的部隊手上帶走了船隻、大多數的獨木舟和部分武器,「任何背信棄義之人都比不上他那麼殘忍」。
另一方面,奧雷亞納和他的部下則是在亞馬遜河上漂流了五個月,卡瓦哈爾記錄下途中的每一個時刻。他們看見的環境不可能不引起他們的驚奇讚嘆。亞馬遜河遠比歐洲或亞洲的任何一條河流都還要大,含有地表淡水的五分之一。亞馬遜河上有和國家規模相當的島嶼,也有像島嶼一樣大的漂浮植物團塊。亞馬遜河的支流中,有五、六條足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成為舉世聞名的大河。從大西洋上溯一千英里,亞馬遜河的河道仍是寬得驚人,在高水位期眺望對岸,只能在地平線上隱約看見一條深色線條。渡船必須航行半個小時才能橫越河面,遠洋船隻更是能夠一路航行至祕魯的伊基托斯(Iquitos),距離河口二千三百英里,是全世界位置最內陸的深海港。
在滿心擔憂可能遭受叛亂審判的情況下,卡瓦哈爾對他周遭的獨特環境寫得相對較少,而是致力於為奧雷亞納從事這趟旅程的價值與必要性編造一套辯護理由。從今日的觀點來看,他其實沒有什麼努力的空間。他的論據主要有三:(一)奧雷亞納是被迫的(如上述);(二)那群部屬對於聖母的虔誠信奉;(三)他們一路上遭遇的苦難。實際上,最後一點不像是假造的。根據卡瓦哈爾的記述,他們除了挨餓之外,也飽受各種痛苦與疾病的折磨。「我們吃下座椅與馬鞍前穹上的皮革,」就是一段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回憶:「更別提鞋底乃至整隻鞋子,唯一的搭配醬料只有饑餓本身。」

遭遇河畔居民的情況非常頻繁,也經常充滿敵意。經過河流沿岸的原住民領域,就像是經過一排憤怒的蜂巢一樣。印第安人在鼓聲與信使的預警下得知有外人前來,就搭乘獨木舟躲在樹木後面等待他們,射出一陣毒箭之後便撤退。再航行幾英里,又會遇到另一群印第安人發動另一波攻擊。除非必須索取糧食,他們一行人都盡可能遠離每一座村莊。儘管如此,還是有三名西班牙人死於交戰過程中。一枝箭射中了奧雷亞納的臉,導致他一眼失明。
卡瓦哈爾對於那些處心積慮想要殺他的民族並未留下多少記載,但在他寫下的少數內容裡,描繪出一片人口眾多的繁榮樂土。他提到,在接近今日祕魯與巴西邊,「我們愈往前,人口不但愈來愈多,土地的狀況也愈來愈好。」有一段一百八十英里的河段「全部住滿了人,每座村莊之間的距離不到一箭之遙」。他們看見的下一群印第安人擁有「非常多且非常大的聚落,還有非常漂亮的鄉間與非常肥沃的土地」。在那些聚落後方,則是緊密相連的村莊:「我們有一天經過了二十座以上。」在另外一個地方,卡瓦哈爾看見一個聚落「延伸了五里格遠(按:一里格約五公里),房屋與房屋之間完全沒有空隙」。
在距海約四百英里的塔帕若斯河口,奧雷亞納的殘破隊伍遇見了他們當時所見最大的印第安聚落:其住宅與菜園沿著河岸綿延超過一百英里。「在河岸上約一、二里格的內陸……可以看見一些非常大的城市。」由四千多名印第安人組成的水上迎接隊(二百艘戰鬥獨木舟,每艘搭乘二十至三十人)出來會見這群西班牙人。另外還有成千上百人站在南側的陡岸上,動作一致地揮舞著棕櫚葉,形成有如足球波浪舞的景象,這在卡瓦哈爾眼中顯然很古怪,也令他緊張。他深受這幅景象吸引,而總算注意到了一些細節。那些搭乘著大型獨木舟前來的印第安士兵都穿著由鮮豔羽毛製成的披風。在獨木舟艦隊後方還有一個水上樂團,由號角、笛子,以及有如三弦魯特琴的雷貝克琴組成。樂團一開始演奏音樂,印第安人隨即展開攻擊。西班牙人是靠著火器所引發的驚嚇,才得以趁機逃跑。
奧雷亞納於一五四六年第二度前往亞馬遜河的航程中逝世,而這次航行也沒有成功。卡瓦哈爾後來在利馬成為一位小有名氣的教士,八十歲時壽終正寢。奧雷亞納的航程與卡瓦哈爾的記述都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實際上,卡瓦哈爾的記述直到一八九四年才正式出版。他們的歷險之所以沒有引起注意,部分原因是奧雷亞納沒有征服任何地方,只是活著回來而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沒幾個人相信卡瓦哈爾對亞馬遜河的描寫。
他的記述之所以引人懷疑,是源於其中一段聲名狼藉的內容,宣稱他們在航行途中遭到一群上身赤裸的高大女子攻擊。那些女子打起仗來冷酷無情,而且她們的社會裡沒有男人。根據卡瓦哈爾的說明,這些「亞馬遜女戰士」一旦想要繁殖後代,就出外抓取男人。那些女子的「興致獲得滿足」之後,就會把精疲力盡的俘虜送回家鄉。卡瓦哈爾嚴正警告,如果有人認為滿足那些女子的興致是一件誘人的事情,因此想要親自造訪她們,他將會「去時青春洋溢,回來時衰老疲敝」。一般都認為這段荒謬的故事證明卡瓦哈爾的記述不可信,也證明奧雷亞納的背信棄義。「滿紙謊言,」史學家高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卡瓦哈爾完成他的手稿之後不久嘲諷道。
自然科學家尤其不肯接受他對亞馬遜河的描述。在生態學家眼中,南美洲這座巨大熱帶森林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荒野地區,原始而古老,是一片有如伊甸園的區域,幾乎鮮少受到人類的干擾。這些科學家指出,由於亞馬遜盆地氣候嚴酷、土壤貧瘠,又缺乏蛋白質,所以從來不曾存在過大規模的社會(那裡永遠不可能有大規模社會的存在)。因此,亞馬遜地區絕不可能像卡瓦哈爾描寫的那樣居住著眾多人口。
由於人類學家比較知道實地考察工作的變數繁多,所以他們會以比較友善的眼光看待卡瓦哈爾。「他對於亞馬遜女戰士的描寫也許不是完全捏造出來的結果,」杜蘭大學人類學家巴雷對我說:「他有可能看到了女性戰士,又或者他認為他看到的戰士是女性。如果他向印第安人詢問過那些女性戰士,有可能會誤解對方的回答。又或者他可能正確理解了對方的回答,只是沒有意識到對方耍了他。我們現在已認識到人種學研究非常複雜,很容易出錯。」
更重要的是,開始對北美洲與中美洲的原住民文化造成的環境衝擊進行重新評估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地理學家與歷史學家,都不免將注意力轉向那片熱帶森林。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都認為亞馬遜盆地同樣也留下了原始住民的印記。這些科學家指出,今日的亞馬遜叢林根本不是像月曆圖片上呈現出來的那樣,宛如一片百萬年來亙古不變的原始荒野,而是人類與環境長期互動之下的產物:而且曾與這片環境互動的人類中,就包括卡瓦哈爾筆下的那些人口眾多且歷史悠久的印第安社會。
這類主張激怒了許多保育人士與生態學家。環保運動者警告,亞馬遜地區正迅速朝著災難的深淵滑落,所以拯救這片森林必須成為世人眼中的當務之急。他們認為,在推土機蓄勢待發要摧毀地球上最後一片巨大荒野的情況下,宣稱曾有大量人口在亞馬遜盆地居住過數千年,是極度不負責任且幾近不道德的行為:這個說法等同給了土地開發商許可證。
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則反駁,亞馬遜盆地不是荒野。何況,聲稱亞馬遜盆地是荒野,只會因為無知而導致環保人士希望補救的那些生態問題更加惡化。亞馬遜盆地的印第安社會跟美洲其他地區的原住民一樣,對於如何管理及改善他們的環境已建構出一套驚人的知識。這些研究者指出,環保人士若是否認這類活動存在的可能性,恐怕不但阻擋不了森林的滅亡,還會加快這種結果的發生。

光是相關文明古蹟,看起來就需要龐大的農業帶才有可能支撐非農業建築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