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歲月滄桑》簡體版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研究三部曲,終於完成最終章,而這遲來的第二部,也是錢老最為看重和傾注了最多心血的一部。
現年77歲的錢理群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最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在出版界,他與錢鍾書並列為最具有市場生命力的當代中國學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錢理群說,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錢理群就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的設想。他那時預計寫7本書,從「五四運動」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他計劃要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為線索寫出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變遷史,也以此了結他的「共和國情結」。後來,他將7部縮減為3部。
錢理群自述,前後跨時近20年的三部曲有「起承轉合」的關係:1996年完成的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象與選擇,是其「起」;2016年出版的第三部《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九死一生的命運,是一個「承轉」;2007年完成的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作「合」,以自己為主角,「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合』,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
在這三部曲中,《歲月滄桑》是錢老晚年最重要的作品。2015年,他帶着妻子搬進了養老院,平均每天寫2000字,一年裏完成了70多萬字的寫作。這本「寶貝」完稿後,錢理群如釋重負。
《歲月滄桑》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作者:錢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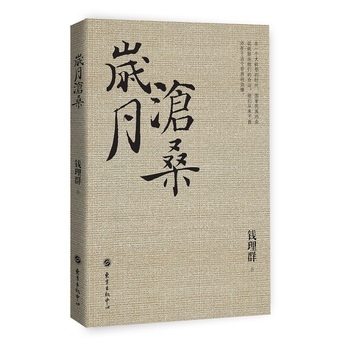
用錢老自己的話來說,《歲月滄桑》的一對關鍵詞是「改造」和「堅守」──在中國,脱胎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現代知識分子仍深受士大夫傳統影響。經晚清和民國鉅變後,他們改造家國的努力在上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碎成了每個個體的悲劇性命運中的顛倒夢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前者成了奢望,後者成了底線。
《歲月滄桑》以上世紀50年代後的沈從文、廢名、梁漱溟、趙樹理、郭小川、王瑤、邵燕祥等知識人為個案,通過將知識人放置到歷史語境,將文本細讀(主要是檢討書、歷史交代、書信、日記等私人性的材料)與心態分析縝密地結合了起來,基本上勾勒出了知識分子在動盪大時代的心靈史與歷史命運,深深切入知識人群體隱秘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們對國家和時代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堅守,看到知識分子個人命運在時代中的幽隱和精神上的波瀾。
以《歲月滄桑》為契機和對象,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對話錢理群,當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底線上如何掙扎;這條底線延續至今,在其上重立獨立人格與思考甚至是語言的如何可能。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知識分子,真正超然、想避世的是極少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通過不同方式來參與政治。知識分子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
唐小兵:你在書中反覆重申一個經典性的主題:上世紀50年代以後,像沈從文、梁漱溟、王瑤、趙樹理,廢名、胡風等知識人,無論是偏自由主義還是傾向左翼的,或是儒家知識分子,都在尋找跟新中國的契合點。你認為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自覺的追求。但回頭看,即使他們這樣地努力,最後還是難以避免悲劇性的歷史命運。
錢理群: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如此選擇,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他們都是愛國主義者,追求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富強,這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的共識。還有一個前提,那個時候,無論哪一派,他們確實都對國民黨政權完全失望了。沈從文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個案。他對新時代的特徵很有預見:「思考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信從與信仰的時代已經開始」。
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可貴的,他們對國家的責任感發自肺腑,像沈從文就說,「這樣一個新中國,怎麼能沒有我!」在歷史的轉折點,一個時代結束了,大多數知識分子承認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新的時代究竟應該怎麼走,很多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想法,每個人又對新中國有不同的預期與想象。
唐小兵:以前讀廢名的那些散文,感覺他是很超然世外的知識人,從沒有想到原來他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乃至政治藍圖。
錢理群:這正是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這些知識人對國家怎麼走有一些很強烈的主張,而以前的歷史對這個群體的描述是不符合實際的。
比如我們對沈從文有很深的誤解,認定他是一個田園詩人,但其實他有一整套政治看法;老舍也有一套治國的方略。這是知識分子士大夫傳統的表現。不管是什麼類型的知識分子,真正超然、想避世的是極少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通過不同方式來參與政治。知識分子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都肯定中國革命,也肯定共產黨領導新中國的成績,認同民族國家統一的實現。這就是為什麼抗美援朝能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強烈共鳴。
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一段歷史,包括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心靈史,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歲月滄桑》中貫穿兩個核心主題,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堅守。上世紀50年代後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若以全世界的視野來看,也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獨一無二。這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比如知識分子的改造其實是自覺或者半自覺的,還有一個問題是知識分子的內疚感。
那一代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是一套制度化、精密化和技術化的改造知識分子的系統。思想改造中無所不在的監督,製造了一種恐懼的技藝,並形成定制。
唐小兵:回頭看上世紀50年代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左翼也好,自由主義也好,鄉村建設派也好,都有一種愧疚感甚至負罪感。這樣一種集體氛圍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原罪。一方面,地主家庭或者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決定了這種原罪,另一方面,沒有拿過槍、上過戰場、流過血,甚至對革命有過懷疑或抵觸,卻分享了革命的果實,這也是有原罪的。但知識分子生活在新中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單位,從政府那裏拿工資。無功不受祿的傳統心理進一步強化了知識分子的負罪感,在心理上每個人都好像被降格了,也就是被降服了。這個心態史的分析特別到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風骨也好,氣節也好,都蕩然無存。中國站起來了,知識分子卻站不起來,在人格上立不住了。
5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處理的另一個具體問題,是你在《歲月滄桑》中反覆談到的知識分子與群眾的關係。像沈從文的「新人民觀」,認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個『讓老百姓翻身』的歷史變革;共產黨及其領袖『代表的是萬萬勞苦人民共同的願望、共同的心聲』」。像趙樹理的小說,總要寫關於真正的農民的生活,要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來說話。在這種主流價值敘述中,「民眾」、「人民」、「農民」這些大詞被無限崇高化、神聖化。這就像對所有的知識分子施了一個魔咒,每個人都屈服在這個大詞前面。
錢理群:這涉及中國的一個傳統。總體來說,傳統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大夫被兩個東西給罩住了,一個就是所謂的「道」或者說「道統」,一個是對帝王的依附性。個體性的、獨立的知識分子傳統比較微弱,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總要從更抽象的「天命」、「天理」或者人格化的「皇帝」那裏尋找。當然,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很大的一個優勢,體現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意識。這是一把雙刃劍,很容易讓人放棄個人的獨立,把更高的價值給丟掉了,包括知識分子本該具有的個人的獨立、對真理的追求。
當然,那一代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是一套制度化、精密化和技術化的改造知識分子的系統。它高度自覺地利用了人性和知識分子的弱點。邵燕祥的個案顯示知識分子隨時都有可能被利用。邵燕祥身上明顯表現出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他被打成右派以後他怎麼稱呼自己,就是革命理想主義最後被感化成一個接受改造的邏輯。
我的書稿中抽掉了對束星北檔案的分析。當時思想改造的制度化非常厲害,不接受改造不給飯吃,導致知識分子為了生存必須接受改造。束星北是個性很強的人,最後不僅個人飢寒交迫,家人也連帶受罪。另外,思想改造中無所不在的監督,製造了一種恐懼的技藝,並形成定制。
建立一個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理論,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本質。
唐小兵:你在《我的精神自傳》裏面也談到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它也是現代中國的啟蒙問題。在新的革命政治裏面,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啟蒙者的社會角色完全被顛倒過來了,變成了被啟蒙者和被教育者。教育知識分子的除了黨,還有此前在文化和社會經濟地位上都處於底層的工農大眾。在自上而下的改造和角色顛倒之中,那些堅守基本價值理念和人文立場的知識人,究竟是依靠什麼思想資源在支撐?
錢理群:在那樣一個天地玄黃的大時代,真正能堅守下來的知識分子是極少的。沈從文的《古代服飾研究》並非橫空出世,而是有很深的文化與心理淵源。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的認同,守住了既有韌性又有智慧的人格。他還堅持自己的語言和話語方式,但這是有代價的。沈從文後來退出文壇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台上就必須要使用一種新的語言。沈從文選擇了退出來,以寫家書這種不公開的方式表達其思考,避免面向公共的寫作,如此來保留自己一個獨立的天地。這其實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智慧。
還有一個就是趙樹理。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對農民問題進行獨立思考的就他一個人。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對社會主義農村怎麼搞,包括怎麼建設社會主義農村,怎麼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理解,也堅持和努力保持農村、農民的統一立場。他說:「我是農民的聖人,知識分子的傻瓜」,這句話太妙了。首先他本身是現代知識分子,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魯迅的影響,但他跟其他知識分子不一樣,他沒有屈服過。另外,他不是簡單的農民代表,他有社會主義理想。他有幾個標準,如生產要發展、農民要獲得實際利益、法律的倫理化,在今天看來都非常珍貴。
他還提出一個隱憂: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之中,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要消失,而年輕人接受現代教育後都離開農村,一去不復返。所以他到晚年就大寫體力勞動者的頌歌,強調既要保證你的腦力勞動,也要從事體力勞動。這在今天看來非常深刻。可見趙樹理不僅在堅守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且他還留下了一些思想資源。實際上,堅守住的就是這麼幾個人。
唐小兵:這引出了另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你反覆用精神迷誤來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中的處境與心靈,一方面中國文化有一種強勁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強調責任感,要參與社會和國家建設,要勇敢地發聲;但另外一方面,知識分子可能並不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甚至像馬克斯·韋伯所講的,缺乏一種責任倫理或者對政治的實際進程充分的了解政治能力和心智成熟。這就陷入兩難困境的悖論之中。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究竟應該保持一種怎樣的狀態才是比較合理和正常的?
錢理群:可以肯定地說,實際生活脱離不了政治。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有不同方式,一種方式就是直接參與,或是政治運動,或是參與國家的具體政治實踐;一種是社會運動,包括抗議運動、維權運動等。一個是體制內的政治,一個是體制外的政治。
我一直認為胡適和魯迅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兩個典範。胡適終其一生對政治都有興趣,甚至有直接參與,但每次到最後要求入閣了或競選副總統的最後關節,胡適就止步。胡適提供了一個參政還保持獨立、在進退之間把握了分寸的典範。但有一個條件,蔣介石能接納他和包容他。魯迅也是一個典型,就是「精神界的戰士」:不直接參與實際政治運動,但在思想、文化領域方面做批判知識分子,面向公眾和知識界發言發表獨立性的、批判性的言論。
還有一種類型是我自己最推崇的,就是間接的政治參與,比如說在教育和文化領域倡導改革、發表意見。你不一定對當下政治直接發表意見,卻可用文化實踐產生影響,因為目前能做的反而是這些領域。當下在這些領域發出獨立的聲音來,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參與。
知識分子還有一種道路是思想啟蒙家,比如康德式的啟蒙。理論和實踐看起來是保持距離的,實際上是對一個時代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和新的價值觀念。建立一個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理論,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本質。我認為這是要比前面的幾種類型知識分子更重要的。
我對這種隔岸觀火、居高臨下的所謂知識分子極其反感。那些居高臨下的要求,帶有很強的道德專制的意味,不僅做不到而且不合情理。
唐小兵:澄清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迷霧,包括語言上的、思維上乃至心靈深處的,是一件急迫而需要長久努力的工作,但很少有人願意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線去從事這種思想啟蒙工作。這或許也是很多知識分子推崇王小波式寫作重要性的緣由,因為王小波讓我們從一種僵化、空洞卻鏗鏘的語言中解放出來了,這樣一種新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的確立是很重要的。
錢理群:實際上中國現在最缺乏新價值觀念的確立。它不完全是純理論的,而是必須跟學術研究聯繫起來。學術研究其實有兩種類型,一種完全基於個人興趣,但它背後有極大的人文關懷,這種研究的前提是要與政治保持距離。第二條路更困難,走政府導向的類似智庫研究的「偽學術」道路。原則上我不反對這種研究類型,問題是你進去會不會保持獨立,而保持獨立非常難。前者比如像一些教授,他也沒有太大的社會關懷,但老老實實做學問,這種學問有相當大的普世價值,就值得尊敬。事實上,大部分人走的是這樣的道路。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說「憑興趣做學問,憑良知做人」,做人的底線很重要。
唐小兵:前段時間爭議很大的錢鍾書、楊絳夫婦在50年代後的處境與選擇,也涉及「守住底線」或者說「消極自由」的問題。
錢理群:我認為錢鍾書其實是看得最透的人。他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所謂潔身自好,但又不摻和到醬缸裏面去,對現實政治甚至社會相對來說比較疏遠,甚至自覺疏遠。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按理說,改革開放以後按他的智商和學習準備基礎,應該有許多新的理論創造甚至總結性著作出來,但事實上沒有。錢鍾書只是守住原來的知識體系,整理原來的知識積累。我的導師王瑤先生也是如此。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都是太聰明的人。看透了,心涼了,不願再寫,並進行自我保護。
唐小兵:有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聰明地保持沉默的「犬儒知識分子」,面對不義之惡,缺乏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氣。
錢理群:我對這種隔岸觀火、居高臨下的所謂知識分子極其反感。他們不知道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多惡劣。最好是能夠完全堅守住良知與底線,有時候守不住了,甚至出現了精神迷誤做錯了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分清是非之後應該寬容。但不能因為寬容,就沒有是非觀念,要有一個對人性弱點、對知識分子弱點的理解。那些居高臨下的要求,帶有很強的道德專制的意味,不僅做不到而且不合情理。
知道真理並不等於你代表真理,我追求真理也並不等於我代表真理。真正的完全平等是彼岸的存在。
唐小兵:你在書中還談到了一個核心問題:左翼知識分子。這些人一方面受到五四運動啟蒙觀念的影響,這種啟蒙思想和價值觀念又是伴隨着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一起闖入,從一個遙遠的異邦移植過來;另一方面,左翼的知識分子又有追求民族現代化,甚至追求民主自身獨特性的自覺追求。所以,這中間有糾結、有矛盾。
據你的研究,民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既是反權力的,又是反資本的,但好像這個左翼的傳統後來就很微弱了。就中國知識分子主義的左翼傳統而言,你覺得哪些成分還可以繼承,哪些地方應該更深刻地反思?
錢理群:這和我自己的思想經歷有關,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左翼傳統培養出來的,當五四運動發生分化時,我們屬於左翼傳統。我現在身上左翼的傳統都淡化了,某些具體的觀點、言論、做法都淡化了,只留下一些帶有本質性的東西。
首先是為真理而鬥爭,有追求真理的自覺──具體是什麼真理跳過去,真理絕對化後就變成一個問題,但是他追求真理本身並沒有錯;其次是對現實強烈的批判意識,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批判性;再次是對社會平等的追求,對弱者和社會底層的關心,並對此有韌性的堅持,不輕易地放棄。左翼傳統明顯表現出的批判性、對社會平等的要求、對底層的關懷,跟自由主義式的精英意識是大不一樣的。其實,我們中國真正嚴格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很少,他們也會有左翼的一些特點。
唐小兵:你在《歲月滄桑》做了兩個左翼的劃分:政黨領導下的左翼與魯迅為核心的左翼的區分,前一個強調命令和服從的關係,內含着等級制。
錢理群:後一個是獨立於政黨的,我很明確說過自己是魯迅派的,總體上其實是偏左翼的。真正的批判性除了反思和批評之外,還取決於自我批判。是否真正的左翼,有一個標準就是是否批評自己。自以為有一個左翼的立場掌握了真理,就要把異端全部打倒,從不自我反思,或革命政黨所要求的「自我詆譭、自我污名化」,都不是真正的左翼,也不叫自我批判。
知道真理並不等於你代表真理,我追求真理也並不等於我代表真理。真正的完全平等是彼岸的存在。我的信仰就是左翼信仰,核心就是反對一切人壓迫人的制度和現象。
唐小兵:這種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是超越民族和超越國家的。
錢理群:革命政治和革命理論認為在此岸可以完全實現烏托邦,我認為自由、平等等最基本的價值只能在彼岸才可以完全實現。而且我認為,人壓迫人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一切社會形態裏都可能產生奴役和壓迫。社會的任何進步同時也可能產生新的奴役,比如說科技日益進步,網絡是最明顯的,會產生新的奴役。我不但反對老師對學生的霸權,我也反對學生對老師的霸權,那也是一種奴役,不能因為年輕就覺得具有天然的話語權。我對一切奴役現象極度敏感,這也是左翼傳統的一種表現。
原文發表於《新京報書評週刊》,端傳媒獲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上)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9e33c7b-abbf-49da-91bd-d05710439da6
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很多大頭目都是共產國際的統戰對象或間諜,所以當時會有妄圖與中共組成聯合政府共治中國的想法,其他老右派後來慢慢被中共馴服,千方百計的想批上黨旗,也是夠堂堂正正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批判性;再次是對社會平等的追求,對弱者和社會底層的關心,並對此有韌性的堅持,不輕易地放棄。」
如此看來,在中國被污名化的公知比小粉紅更貼近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有為了體驗領袖快感的假公知,但總的來說,公知更有社會責任感,而小粉紅或五毛從來不可能自我批判。他們對社會底層的關心就是在微博上轉發一些山區學生的圖片,或在發生災難時發個祈禱的表情。社會問題很多的情況下,如果政府不做,那麼民間做行嗎?不行!看看中國的NGO生存現狀吧。最恨這種佔著茅坑不拉屎的行為(對不起我把天朝變成茅坑了),偏要向你們證明世上有反對派,偏要做公知和迷信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