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通過投資活動「殖民」非洲乃至世界的說法,常見於各類媒體和學術文章。進入2018年,中美貿易戰牽引出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馬來西亞大選後系統檢討「一帶一路」、斯里蘭卡和越南民眾抗議中資建設等事件,讓許多觀察者認為,一個擴張中的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受到阻擊。
中國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雄心壯志為什麼會導致各種在地抵抗?回答這個問題,除了關注吸引眼球的衝突事件,更需要對中國的投資活動如何「落地」進行細緻的社會學觀察和政治經濟分析。以央企為主的「中國資本」,在被政策短時間內引到他國的過程中,未見得對彼邦的情況有準確的把握。而抵抗的觸發,也與當地政治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理解「全球中國」經投資活動為中介的「在地相遇」,我們需要追問:
真的有一種資本,可以被統稱為「中國資本」嗎?頂著國字招牌的中資企業帶到非洲和世界各地的資本,在看似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還能被中央控制嗎?它們會帶來什麼新的勞工問題?是否像人們所想像、恐懼的那樣,全知全能的中國政府,正在掌握一切?中國只是在重複全球資本主義的做法,還是像官方表述的那樣,建立新的跨國連帶時,也能提供新的發展道路?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李靜君(Ching Kwan Lee)教授,在新書《全球中國的幽靈:政治、勞工、外資在非洲》(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註1)中,試圖回應上述廣受關注的問題。她通過分析中國央企在贊比亞不同產業的投資情況,比較了「中國國家資本」(Chinese state capital)和「全球私有資本」(global private capital)的異同。基於長期田野調查,她試圖傳遞一種更為審慎的思考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方法。
李靜君認為,與其談論「中國是否殖民非洲」這樣在她看來過於籠統的問題,不如先走進由普通勞動者、政客、外派員工等不同角色組成的世界,看看帶著國家任務來到非洲的央企到底在做什麼,能否實現它的目的,又給當地人民帶來哪些影響。在她看來,中國政府的「無所不能」雖有現實的權力基礎,但也是一種迷思。
當下,中國的國家行為被廣泛注意,但也在不同場域受到挑戰。「全球中國」這個幽靈,也因此有被進一步祛魅的可能。李靜君的新書問世後,相繼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及國際亞洲研究會頒發的六項最佳專書獎。近日,端傳媒在香港對李靜君進行了專訪。
是否像人們所想像、恐懼的那樣,全知全能的中國政府,正在掌握一切?當下,中國的國家行為被廣泛注意,但也在不同場域受到挑戰。「全球中國」這個幽靈,也因此有被進一步祛魅的可能。

端=端傳媒
李=李靜君
通過田野拆解「中國殖民非洲」
端:你的新書是最早一批針對中國在非洲投資活動的實證研究,也是第一本基於長期田野調查寫成的專著。出於哪些契機,你開始把目光投向非洲?
李:通過工人階級的視角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直是我的研究範疇。在1980年代末,我念研究生院的年代,中國已經走向改革。最初,我關注的是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第一本書《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性別與南中國奇蹟,註2)關注南中國如何變成全球的製造業中心。通過研究第一代移民工和第一代外資在中國的相遇,我分析了是什麼力量保證了生產過程的「平穩」。寫第二本書《Against the Law》(對抗法律,註3)的時候,工人階級開始出現很多集體抗爭的問題;同時我也關注,在國內,資本主義深入到東北取代社會主義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過程:在這個宏觀體制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工人的集體經驗與抗爭的形態又是什麼。
這兩本書都是關於中國內部的問題,而隨著中國資本的全球化,新的勞工問題也一定會隨之而來。所以,我當時很自然地覺得,「中資在非洲」是延續我理論思考的場域,需要跟進它的發展。2007年,我剛寫完第二本書,在想下一步做什麼研究,那時候國際傳媒不斷報導中國在非洲引起的爭議,重點就是勞工的問題。一些非洲當地的批評也說,中國老闆「特別」剝削工人。我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研究院,我的同僚也都在談這個事情,引起了我的興趣:資本家從來就是剝削工人的,為什麼人們會說中國投資者「特別」剝削工人?究竟中國去的投資者有什麼特殊性?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作者:李靜君
出版日期:2018/01
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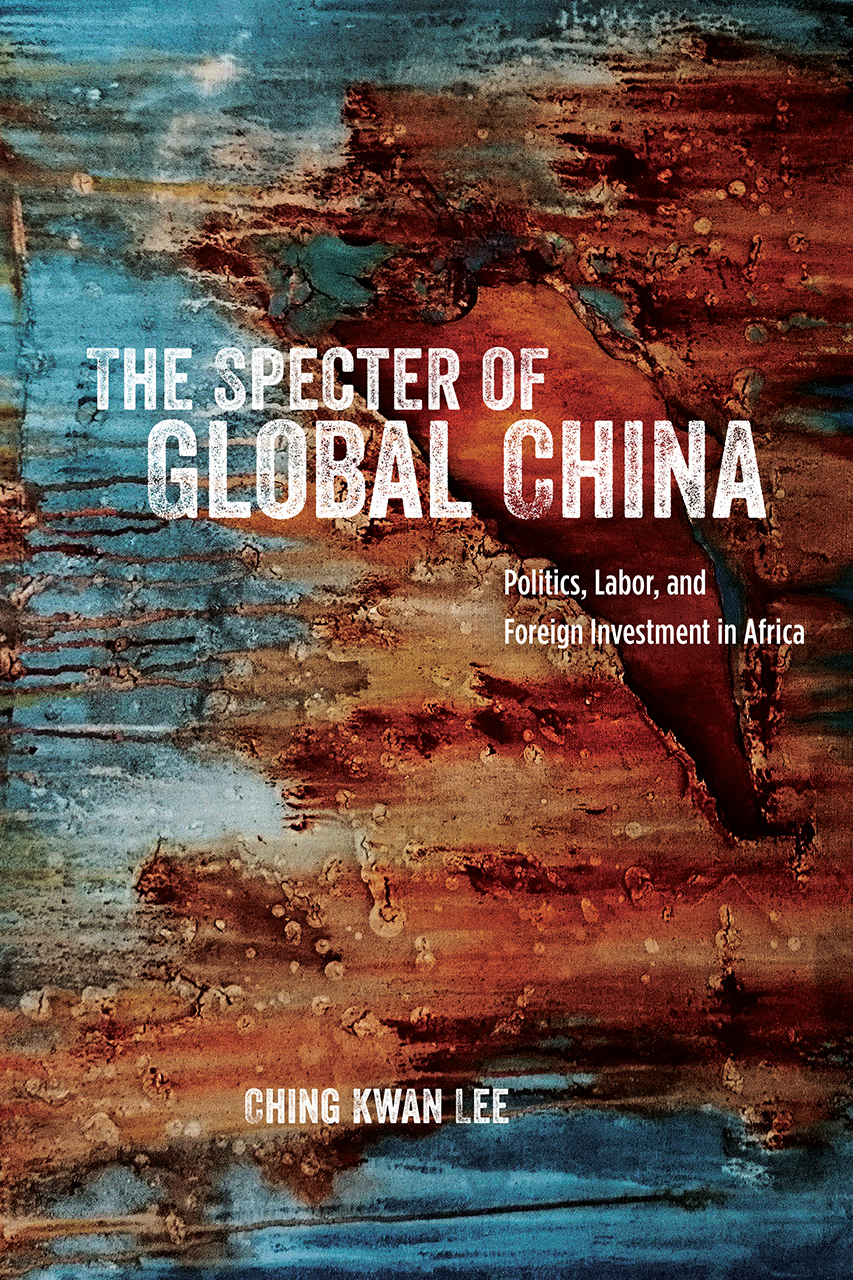
端:「中國殖民非洲」的說法,在學界和媒體中廣泛傳播。你嘗試在本書中拆解這樣的描述,尤其是「殖民主義」這個概念的用法。你具體是怎麼做的?
李:你要看到是誰在用「殖民主義」。在我的研究初期,這樣說的有兩批人。一批是政客,包括一些西方領袖、在自由世界比較有影響的人。他們害怕中國擴張和來自中國的競爭,同時需要擺明政治觀點。這種情況下,「殖民主義」是一種方便的批評。另一批人要賣書(註4),他們用「殖民主義」這個在西方語境下好像很容易理解的詞彙,看中的是它可以直接觸發恐懼。但是對於學者來說,這種批評太簡化了。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殖民」到底指的是什麼?假如以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為標準, 就現在的情況來說,也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說中國對非洲已經造成了「帝國主義式」的影響。中國沒有軍事佔領,不經營特許公司,也不存在宗教輸出或制度移植。
假如以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為標準, 就現在的情況來說,也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說中國對非洲已經造成了「帝國主義式」的影響。中國沒有軍事佔領,不經營特許公司,也不存在宗教輸出或制度移植。
假如我們從事實出發,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斷通過國家主導的投資進行海外擴張。在我看來,這種「全球中國」現象,核心動力是中國想通過政治和地理空間的手段,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並藉此過程增強其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但是,中國有全球野心不等於中國已能實現其全球野心。同時,在現在的國際條件下,中國也無法直接複製歷史上被稱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做法。況且,中國對非洲等地的大量外向投資只是近十幾年的事,而歷史上的殖民或帝國,往往是上百年的政經權力的生成。所以,我認為用殖民主義的視角去分析全球中國,學理上是很牽強的。
所以,這本書有意避免直接和數量眾多的殖民研究對話,而是把「全球中國」視為一種事件性時刻(eventful moment)。意思是,中國作為資方大肆進入非洲,雖然可以視作資本在中國過度積累之後的結構性轉移——這符合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軌跡——但中國的做法有沒有特殊性,是不能用既定理論推演的;它帶來的後果,也不只有一種可能。「全球中國」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可能但不保證帶來結構性變化的事件,而不是已有結果的歷史過程,因此需要用實證研究去理解。
端:你通過長期田野調查的方法寫成此書,這在諸多對中國投資、「中國因素」的研究中並不常見。這樣做讓你有哪些不同於一般論述的發現?
李:我在書裡面提到,不能否認「中國因素」的客觀存在:大量的資本投了、勞工去了、礦也買了,這都是事實。但是,很多人聽到「中國因素」這樣的詞,就不再思考,覺得中國就是重複以前西方做的事情,進而做簡單的責難。
通過長期田野調查,我的主要貢獻有兩點。第一,我不止於研究政策文件和統計數字,看有多少錢到非洲,而是看它們到了中國國家資本和當地政治精英及民眾怎樣周旋。在理解這種互動的過程中,我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國家資本」是否與「全球私有資本」有根本差異?換句話說,問題核心不是有多少企業和工人從中國去了非洲,而是來自中國的國家投資與一直佔據主導的全球私有資本相比,有什麼不同?
第二,我具體分析了為什麼在不同的產業中,「中國國家資本」與在地政治的互動有不一樣的機制、產生不同的影響。我對比了基建和銅礦兩個產業,解釋了它們在政治經濟環境、勞工的動員能力、在地政府策略,以及政治領袖發展產業的意圖等方面的差異。把這些條件和中國資本結合在一起看,才能理解中國國家資本為何在銅礦行業帶來發展效應,而在建築行業卻相反。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光口號式地把所有中國海外投資說成殖民主義。

「中國國家資本」的邏輯
端:我們逐條來談。首先,在分析來自中國的投資時,你沒有簡單地使用「中國資本」或者「中資」,而是提出了「中國國家資本」(Chinese State Capital)的概念。你如何定義它?為什麼要做這種辨析?
李:在日常的話語裡,「中資」是個地域性、種族化的概念——指從中國去、中國人的資本。但事實是,資本本身沒有國籍、種族,不問所以然就把它們與國籍、種族掛鈎,是歧視性的做法 (就如當年歐洲看待所謂「Jewish capital」),分析上也是錯誤的,因為從中國來的資本有很多種,他們的行為、目標、邏輯都不一致, 不可混而一談。從中國來的小企業、家庭小店、私人企業、省級國有企業,其實跟別國的私企沒什麼差別;但真正有中國特殊性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即央企。
這些所謂的「中資」在做的事情不一樣,所以,我把央企對非洲投資時用到的資本界定為「中國國家資本」,是為了在各種類型的「中國資本」中說明它的特殊性。我們不要止步於看資本從哪裏來,而要看某種具體類型的資本在追求什麼利益,它怎樣實現這樣特定的利益,又受到哪些阻力。「國家資本」不單指某個國家擁有或使用的資本,而是說這種資本的利益是由國家來確定:在「國家」的視野下,「利益」涵蓋的範圍要大得多,不是賺錢那麼簡單。
「國家資本」不單指某個國家擁有或使用的資本,而是說這種資本的利益是由國家來確定:在「國家」的視野下,「利益」涵蓋的範圍要大得多,不是賺錢那麼簡單。
端:這就觸及到你研究的核心問題了,我們可以繼續展開。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與佔主流的「全球私有資本」之間的異同,具體是怎麼分析的?
李:自馬克思以來,我們很少對資本的類型進行理論性思考,而傾向於假設了資本是私有的、其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潤極大化。理解中國央企在贊比亞的投資活動時,這種思路捉襟見肘。在以往的討論中,學者們提出「國家資本主義」 來分析中國國內的制度,比如國家怎麼控制經濟、共產黨如何管治企業、企業家等;但當央企「走出去」,投資的場域已經超出共產黨及中國政府的管轄範疇,所以「國家資本主義」不足以分析全球中國的現像。
我的研究比較了中國國家資本與全球私有資本(意指那些在國際股票市場上交易,由股東擁有的跨國公司)。我想比較的是這兩種資本的不同利益,以及實現這些利益的手法。我的發現是,「全球私有資本」的核心訴求,確如馬克思所言,是利潤極大化,但使用「中國國家資本」的央企,則試圖實現一種囊括性的積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經濟盈利並不是央企投資時被國家賦予的唯一使命。除了經濟收益,它還被賦予作積累中國的政治資本和外交影響力、獲取戰略性資源等使命——這些都是國家定義的「利益」。我們要了解的是國家資本要實現這些目標,它在非洲要如何在地運作,如何與非洲政府及當地民眾交往。
以銅礦業為例,上市的跨國企業往往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而中國央企因為「受命」保持銅礦這一戰略性資源的供給,就要維持平穩生產。這兩種不同的利益目標,導致兩者對待本地勞工方面的明顯差異。全球資本為保證股東利潤,在回應市場波動時,往往大量裁員及改用非正規勞工,讓工人的集體談判力大降。反過來,中國央企為保證戰略資源(如銅)的穩定生產及增加其政治合法性、政治資本,傾向用正規工人,不會任意裁員而導致生產中斷,傷害它的國家形象。工人的抗爭也因為是正規工人而力量較大,逼使國家資本作出多於全球資本的讓步。
另一方面,這兩種不同的資本在非洲要實現它們不同的利益訴求,也非常依賴各自的外派員工。為此我對比了駐贊比亞央企在管理理念(manegerial ethos)和工作文化上,與私有跨國資本的企業的主要不同。比如說,央企會安排各種層級的員工同吃同住,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營造一種強調中國人一起「吃苦」的集體苦行主義(collective asceticism), 總部的黨委也有派團到贊比亞來視察,做思想工作,落實中央的方針政策。相反,跨國企業的駐贊員工,有個人生活的空間,工作和生活分得很開,外派對於他們來說是更個人主義意義上的職業發展訴求。我在書裡介紹了,在這種與外界相對隔絕的工作環境裏,央企如何通過提高員工的工作紀律性來保持穩定生產,尤其是需要為中國提供戰略物資的銅礦業。
「全球私有資本」的核心訴求,確如馬克思所言,是利潤極大化,但使用「中國國家資本」的央企,則試圖實現一種囊括性的積累。

全球中國的在地互動
端:央企為了維持生產穩定而不會輕易裁員,聽上去有一絲妥協意味?當地經常傳來中國企業與當地勞工之間的勞資糾紛,在一般印象中,這說明資方是「邪惡」的。事實是如何?中國企業比其他國家的企業更邪惡嗎?中國企業之間存在行業差異嗎?
李:中國國家資本恰恰因為要追求多元的政治、經濟、資源目的,而非單單追求利潤極大化,所以才更有必要與贊比亞政府進行協商,向勞工的集體訴求妥協, 不然的話,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礦權的延續都不利。這在銅礦業很明顯——贊比亞政府和社會,在銅礦價格上升、資源和民族主義捆綁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政治協同,向中國國家資本討價還價。而央企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穩定的戰略資源供應、建立政治影響力及認受性),而作出比全球資本更多的妥協。例如,中國在贊方要求下,建立了經濟特區,讓贊有機會發展銅產品工業, 而不停留在採礦;而其他跨國資本都以「不賺錢」為由,對贊比亞說不。
但這種對國家發展的「政治協同」, 不一定存在於每個國家、每個行業。例如,中國國家資本在建築行業 (主要體現為優惠貸款),就比全球資本更有掠奪性,主要因為贊比亞政府缺乏對建築業和基礎建設方面的國家政策,加上建築工人的集體力量比銅礦業薄弱得多,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家資本的多元目的 (利潤、政治影響)就使得它比全球資本更有殺傷力。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利用對非洲的優惠貸款,建立對非的庇護關係;但相比於發展國家經濟,非洲政客多用這些基建貸款來爭取選票,因此往往令非洲國家債台高築。
端:中國企業所要應對的當地政治,和一般人想像的有什麼不同?換句話說,直接處理、面對這些當地政治的,就是中方管理層員工,他們在中國成長、受訓,面臨贊比亞的勞資關係時,他們需要處理哪些新問題?
李:他們當然有很多既定的辦法和思路,但都用不上。因為他們去了沒多久就發現,非洲勞工非常窮,可是他們有工會、勞動法,政府有很多時候為了選票,會幫助工人維權。中國管理者去了之後,不管他們腦子裡的觀念是什麼,現實是人家的工會和你談判,平起平坐地和你在一起,中方管理者一開始當然是不愉快的。他們覺得,你是我的員工,你為什麼和我可以平等地在一張桌子上討價還價?可是後來還不是乖乖地一起談。
他們去了沒多久就發現,非洲勞工非常窮,可是他們有工會、勞動法,政府有很多時候為了選票,會幫助工人維權。
端:這很有意思。對於中方管理者來說,一方面天高皇帝遠,自主處理事務的權力更大了。另一方面,承擔的問題也多了許多,不能靠既定辦法處理。
李:對。這對他們來說是新的挑戰,可是他們很快就學習改變。你不談,工人罷工,政府把你牌照拿走,你怎麼辦?在真刀真槍的政治面前,他們必須改變觀念。我在書裡也寫到,他們剛開始的確會有文化障礙。他們去非洲之後,除了吃飯睡覺,也不用去照顧家庭、不太娛樂,工作之外還是工作。他們自己這樣也就罷了,但如果要求本地工人都那麼勤快,人家肯定不願意。中方可能出於慣性要求人勤快、要求人聽話,但要在非洲的地盤上實現這些要求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端:在中國國內,中國工人也是常常受到資方剝削的。那麼在遙遠的非洲,中方普通員工在當地的勞動權益,又能否得到國家的保障呢?
李:我研究的主要是中方管理人員,和工廠工人不一樣,他們地位較高,工作相對穩定。這些企業員工,按照中國的制度走,領五險一金,工作時間按照中國企業的要求。不過,這種「中式安排」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來這邊,不受任何法律保護。我和贊比亞的勞工部長討論過很多次。他一方面承認,這是政府要處理的問題——只要到贊比亞工作的人,應該受到當地勞工法保護;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這個問題在贊比亞沒有人會關心——你是外來工,我為什麼要保護你?中國企業和老闆更不會保護你,你拿的是他們的工資啊。
所以,即使在海外,中國工人也受到中國資本的極大剝削,這種剝削因為當地法律保障的薄弱而加劇。中國的勞工不會去找贊比亞的法律幫自己。他們對制度不熟悉,有語言障礙,而且也不相信贊比亞低效率的官僚可以幫助到他們。另外還有一些非法入境的中國工人。他們被帶過去,許諾更好的工資,但最後被騙了,又沒有簽證,處境悲慘。中資跨國流動中帶出的法律、維權問題,是後續的研究可以跟進的。
即使在海外,中國工人也受到中國資本的極大剝削,這種剝削因為當地法律保障的薄弱而加劇。
端:近來,「一帶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國家開始檢討中國國家投資的情況。你在贊比亞的研究說明,中國國家資本的作為,會因當地的政治社會生態而變化。它既不一定是天生的魔鬼,也不是天生的天使。
李:在討論「一帶一路」、「中國在非洲」 或 「全球中國」時,人們往往只看重中國的意圖,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能量。貧困國家其實也有複雜的政治,有選舉與選民的壓力。最近,我們看到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巴基斯坦、馬爾代夫等國家的政客與民眾反對中國國家資本,其實都驗證了我書裡的分析。
在討論「一帶一路」、「中國在非洲」 或 「全球中國」時,人們往往只看重中國的意圖,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能量。貧困國家其實也有複雜的政治,有選舉與選民的壓力。

端:近來,「一帶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國家開始檢討中國國家投資的情況。你在贊比亞的研究說明,這種在地的角力的出現是日常的一部分,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李:是的。外界很多人以為,是北京單方面想在贊比亞建立一個工業園區。但實際上這不是中央的計劃,是下面的人和贊比亞官員一起提出的,比如非洲看起來有很多中國人管的園區,但有的是省政府一級的園區,也有私人投資的園區,單在資本來源這一點上,就已經很不同;所以不能看到一個中國園區,就以為是中國逼著建設的,也不能忽略歷史過程,以為只是中國單方面想去找機會。
事實上,「尋找機會」這個過程很多時候是反過來的,贊比亞老早就在想,如何提高銅礦的附加值,在中國還沒去買它們的礦的時候,就已經做好各種準備,包括法律制定、請馬來西亞及日本專家設計建設藍圖等等。所以,考察中國在非洲,就一定要分析非洲政府與人民的能動性,不要假設他們只會逆來順受。
考察中國在非洲,就一定要分析非洲政府與人民的能動性,不要假設他們只會逆來順受。
尤其當地精英,在和國際發展的長期互動中,他們其實也知道怎麼玩與外資討價還價的遊戲。中國人一下子去了,也不可能順風順水。在贊比亞的時候,不管哪個行業的中國人,沒聊幾句就會告訴我,在這裡做生意是多難的一件事!這是從心裡面說出來的話。
全知全能國家的迷思與現實
端:中國觀察者常假設中國有一個全知全能的理性國家機器在運作、控制一切事情。在中國國內,中央對資本的控制或許相對容易,那麼「走出來」之後呢?中央-地方的關係,會有怎樣的變化,又如何影響國家資本的利益實現呢?
李:即使在國內,中央對經濟的控制從來也不是那麼全面,比一般觀察者想得要複雜。在「走出去」以後,很多影響投資的因素中央更難控制。比如別國的工會、選舉政治,北京再有力量也管不到。銅礦工人罷工時,我問那些中方企業的管理者,你的決定是你自己做的,還是要打電話給北京總部?他們就笑我,居然問這樣的問題,說那肯定是我們決定啊。他們報告上去的,是已經發生過了的事。北京根本不可能理解當地的勞工訴求、生活狀況,也沒有處理這些在地問題的機制。外面的報導以為你有錢就可以擺平一切,但其實哪裏那麼簡單。權力的運作,在很多時候是不能化約為錢的。反過來說,即使投資本身不賺錢,也未見得意味著「國家利益」沒有達成。
即使在國內,中央對經濟的控制從來也不是那麼全面,比一般觀察者想得要複雜。在「走出去」以後,很多影響投資的因素中央更難控制。比如別國的工會、選舉政治,北京再有力量也管不到。
端:中國政府不擔心這些在外央企失去控制嗎?怎麼監管它們的投資失敗?
李:央企和中央政府之間也有博弈。若是央企拿到了「國家任務」,那即使賠錢也要完成任務。但它們也有主動性,比如看到某個業務好做、外面市場挺好,就會自己出去,所以你會看到每個央企都要搞建築,建築好做呀。同時,央企也會 「以下犯上」,它們想把賺到的利潤留在企業,有時候就要「走出去」才能避開中央的管治。
端:民企以及私有資本和政策鼓勵的國家資本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他們會因為政策的東風得到好處嗎?
李:這個問題值得展開說一下。「走出去」是中央提出的口號,民企和私有資本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各種補貼、優惠都需要競爭性地申請,主要是由央企、國企拿到。所以從政策中受惠的,主要是已經有規模的企業。這和國內的玩法是一樣的,像各種工程項目的招投標那樣,有資質參與競爭的是少數。
不過要知道,民企和私有資本「走出去」的時間更早,從80年代就隨著中國對非洲的援建過程開始了。當時,北京把對不同的非洲國家的援助分發給不同省份,省級國企先走出去。到了90年代,參與這個過程的國企工程師在去了幾次以後也嗅到了商機,他們也感覺到,國有企業鐵飯碗快要被改革,所以這批人就去非洲「下海」了。帶頭出去的是建築行業,它們比其他行業更早發現非洲市場。
民企和私有資本「走出去」的時間更早,從80年代就隨著中國對非洲的援建過程開始了。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也是世界銀行和貨幣組織要求發展中國家加速新自由主義化的時刻,許多當地的政策對外資門戶大開。在這樣一個雙重節點上,中國工程師成了第一批移民創業者(migrant entrepreneurs)。這些都發生在央企、國企大批出去買礦、做基建之前。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贊比亞客戶,變成私有資本。這些中國私有企業,反倒成為後來才出去的央企、國企的競爭者。

端:你想這進一步說明,與中國有關的資本不可以一概而論。贊比亞官員會看到這種複雜性嗎?還是認為它們都是「中國資本」?
李:非洲的官員因為對中國體制不了解,會認為共產黨能控制住所有來自中國的企業、投資者和工人,即使是當地的政治精英,也搞不清楚中國的複雜性。他們覺得反正你是中國人,就是中資。以為資本可以用國族來分類,但這種想法帶來很多盲點。對於非洲的勞工組織和政府來說,若想更有效地利用中國國家資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他們需要更準確地理解「中國國家資本」的獨特性,以此為協商的基礎。
中國政府很喜歡把自己塑造成有統一口徑、統一行為、統一利益的實體來理解。「統一」試圖體現的是一種很大的能力和權威,我們作分析和經驗研究的人,要分清楚這只是意識型態,而不是事實,而要看國家政策和在地實踐之間的異同。 許多傳媒和學者喜歡聳人聽聞,沒任何經驗考證就套用「殖民主義」的論述,這樣他們一方面既製造了「全球中國」這個幽靈,同時也迴避了更重要的問題——中國對外擴張是否有自己的手法而不是重複西方的作為?
「統一」試圖體現的是一種很大的能力和權威,我們作分析和經驗研究的人,要分清楚這只是意識型態,而不是事實,而要看國家政策和在地實踐之間的異同。
端:最後一個問題,縱觀全書,整體上你強調了一個觀點:中國有全球野心,不等於能實現全球控制。但也有人提問說,有全球的野心難道不就是有殖民/擴張的野心嗎?中國的國家利益中不也包含對資源的「戰略性」攫取這種積累方式嗎?只是不「原始」了而已。我想這終究要回到對「殖民」是什麼的理解上去。對於這種說法,你有何回應?
李:上面我已經指出,中國至今沒有重複西方殖民主義的核心作為——軍事佔領、經營特許公司、弘揚宗教、制度移植。所以,當你堅持用「殖民主義」去看中國,我會反問你對「殖民」的定義是什麼。不管人們用什麼詞,我們要關注的是:中國要實踐它的全球野心,要通過什麼手段、機制、過程,產生什麼刻意的、非刻意的後果。只看中國的意圖,忽視它身處的客觀世界對它的回應與反抗,是唯心論,無助於了解「全球中國」這現象。
(撰稿人:黃山,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1: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7
註2: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註3: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註4:例如 Howard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Vintage,
2014

"Empirically, imperialism pertains to the expansion of a polity’s influence or dominion through usually militaristic but also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eans."
Shilliam, Robbie (2021-02-17T22:58:59.000). Decolonizing Politics . Pol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说“洗白”那位朋友能别这么情绪化吗?我觉得这文章真的相当客观了。长了很多见识,接受了很多新思考视角。说实话不止西方有中国是“殖民者”的错觉,在大陆很多人也有。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官媒各种夸大其词的宣传。
特别不喜欢「洗白」之类的说法
殖民是有特定语境和基本定义的,如果你说今天不是这个定义,那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进入讨论和研究的层面,势必要分清定义。
這一篇還是不可以截圖 可以請小編check一下嘛
怎麼我看下來,感覺只是:李教授在用一種很高級的方式再為中國/中國政府洗白?1. 現在民間或學界說中國“殖民”非洲,指的肯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百年帝國殖民,而是在說一種新型殖民吧,利用國家資本在國家策略下的統一擴張,在非洲、一帶一路地區換取核心資源和政治、文化上的影響力;2. 李教授一邊說不能簡單說中國殖民,但她舉的例子,實際上不能消除殖民的陰影,例如她也承認,中國的國家資本追求的並不僅僅是錢方面的利益,它要的是另一個國家的礦產資源和政治、文化,甚至高層政治上的影響力;3. 李教授也說,私有資本和國家資本本質不同,如果只是中國老百姓自己去非洲、去一帶一路國家做生意謀生,那不過是人口和資本的自然流動,他國不會擔憂和反感,中國也不會被人家說成是殖民。
好文
注2中书名漏字,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感謝您的指正,已修改!
“全知全能国家的迷思与现实”这个部分中,第一次对话,受访者回答中, 跟本=>根本
感謝您指出,已修正!
“我的研究比较了。。。。。。我们要了解的是国家资本它在非州要如何在地运作,如何与非洲政府及当地民众交往。”这一段中,“非州”应为“非洲”。
感謝您指出,已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