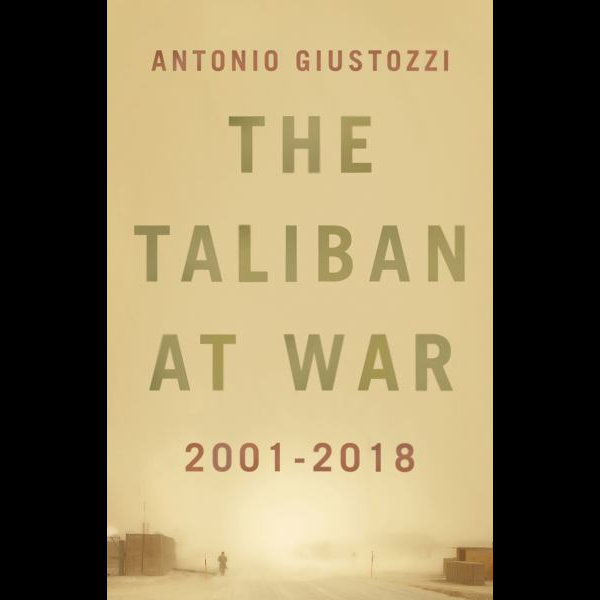
Giustozzi提出一個問題:為何塔利班成員要重新拿起武器?一方面,阿富汗政府軍和聯軍對塔利班成員和疑似成員的糟糕待遇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曝出各種各樣的虐囚行為,政府軍對村裏人也常常以「塔利班」為由濫加逮捕,把很多人推向了塔利班。比如,加茲尼地區的一名塔利班武裝人員告訴研究者:「在Dayak地區有一個村子,人們有共產主義背景,從俄國人入侵開始就沒有支持過我們。但是警方襲擊了村子,在一間清真寺毆打了那裏的老人,逮捕了他們,說他們是塔利班。他們花了重金賄賂才被放出來。這件事之後村子給我們捎了信,對以前錯誤對待我們表示懺悔。」
更重要的一點是,聯軍和新的喀布爾政府在一開始完全不與塔利班成員和解。未來將會成為塔利班領袖的曼蘇爾(Akhtar Mohammad Mansur)就在2002年的時候躲去了鄉村,他一度想要隱姓埋名生活下去。但是聯軍不斷搜查、抓捕塔利班成員。曼蘇爾不可能成功躲避,於是又出來組織聖戰。
在2005年到2010年之間,流亡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高層重新組織起指揮系統,並且和地方上的指揮官們建立聯繫。一方面,高層將海外的援助對接到阿富汗境內的軍事武裝組織,另一方面,他們也嘗試讓自發形成的阿富汗境內塔利班武裝更加服從集中的領導。這一時期,海外的援助開始恢復,據Giustozzi的研究,塔利班的外援在2005年之前幾乎停滯。2005年之後,巴基斯坦重新認為支持塔利班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巴軍的三軍情報局(ISI)開始幫助塔利班獲得資助。另一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衞隊和某些海灣國家的政府,都開始撥款給塔利班。塔利班甚至在2005年專門成立了財政委員會處理籌款和儲蓄。
另一邊,在前線作戰中,塔利班逐漸開始了「軍事專業化」過程。儘管2009年到2014年之間塔利班在聯軍的大規模攻勢下遭遇了很大損失,但是其軍事力量和戰鬥方式也變化巨大。相比開始時堅持正面攻擊,塔利班在2010年之後接納了游擊隊模式,利用路邊炸彈等方式避免正面和軍警衝突,減小損失。他們改進了自殺式炸彈的用法,更多作為軍事武器而非恐怖襲擊,搭配更好的訓練和支援小隊,在缺少炮火的條件下把人體炸彈作為火力掩護和攻堅力量。他們甚至還改善了物流,成立了醫院和機動醫療隊,設置了機動部隊和預備隊系統。
隨着塔利班開展游擊戰並納入更多戰術,其傷亡和戰鬥素質都有明顯改善。2015年時,塔利班就已經可以宣稱自己控制了阿富汗一半的國土(儘管事實上未必達到了這個數量)。
不過,塔利班的戰爭改革並非沒有遭遇抵觸。Giustozzi提到,不少老塔利班都不喜歡游擊隊模式,他們覺得聖戰士「應該像男人一樣戰鬥」,並隨時準備犧牲。有些被研究團隊訪談到的聖戰士認為2010年代之後的戰鬥變得不純粹了。在他們眼中,2001年之後幾年的艱苦歲月是最值得懷念的——因為那時候的戰鬥是「純粹」和浪漫主義的。那時候他們自帶乾糧和軍餉,倒貼錢參加「聖戰」。相比之下,他們認為近年來很多年輕人加入塔利班甚至是為了每個月定期拿工錢——塔利班的工資在2015年之後和政府軍警的工資接近,只是傷亡率要高出不少。

集權或分權:如何理解塔利班的組織?
《戰爭中的塔利班》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在意識形態上,塔利班強烈反對列寧主義式的嚴密組織——戰爭有沒有在這點上改變他們,把他們推向更組織化和集權化的模式?
答案是,有也沒有。Giustozzi將塔利班二十年來的組織和人事變化稱為「一場反中心運動的不可能的中心化」傾向。這是說,在二十年的戰事中,塔利班擁有了更多集中權力和調配協調資源的能力,但是因為各種原因,他們並沒有真正實現集權化的統一指揮。其權力結構和決策機制仍然是多中心的。
在近二十年中,塔利班的兩名領導人曾經試圖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他們是巴拉達爾(Abdul Ghani Baradar)以及曼蘇爾(Akhtar Mohammad Mansur)。巴拉達爾如今是駐卡塔爾的塔利班政治代表——就是之前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談,到天津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面的那位。而曼蘇爾已經在美軍2015年的一次襲擊中死亡。
時間回到2000年代早期,因為塔利班的重整來源於地方上武裝人員的自發集結,因而在巴基斯坦重新整理好腳跟的塔利班高層們遇到了這樣一個情況:如何去聯繫、指揮那些前線的「將軍」們?
答案是成立「連接網絡的網絡」。那些地方武裝是一個個小網絡,在其之上,塔利班用更大規模的網絡將他們連接起來,併入一個指揮、資金和政治網絡中。這其中包括如今在喀布爾和卡爾扎伊等人談判的「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這個網絡以家族統治、殘酷無情,戰鬥力強而聞名。
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核心團隊組建了一個領導委員會(Rahbari Shura),外界稱之為「奎達舒拉」(Quetta Shura)。舒拉是會議或委員會的意思。奎達舒拉開始逐漸派出省長節制各地的塔利班武裝。試圖令大家認可其繼承了之前的塔利班喀布爾政權的正式法統。
但奎達舒拉只能有限管理前線指揮官。比如,哈卡尼的網絡2007年才正式加入奎達舒拉,雖說在此之後,哈卡尼網絡的任何行動都要經過奎達舒拉批准,但他們還是擁有很大的,相對於奎達舒拉的自由。
既然是靠打仗起家,那麼各地的指揮官也就都有各自的忠誠隊伍,比如坎大哈的達魯拉赫( Mullah Dadullah)就在塔利班基層武裝中名聲很好。他大膽,敢打而殘酷。奎達舒拉的領導層向這些有很強個人號召力的戰地指揮官們做了妥協。比如任命Dadullah為總指揮。並且允許指揮官們以陣線(mahaz)的形式組建武裝。到了2006年,大部分的奎達舒拉的兵力都歸入四個「大陣線」(loy mahaz)裏。 分別由達魯拉赫、巴拉達爾、法魯克(Mullah Faruq)和易卜拉欣(Mullah Ibrahim)管理。四個大陣線有自己的籌款權力和人事權力,就連外在支援也不同,法魯克和海灣國家親近,和巴基斯坦冷淡;易卜拉欣則和巴基斯坦親近。

大陣線的問題很快暴露——它們完全忠誠於個人;在戰場上,各個大陣線之間無法協同作戰;人們會為了更好的條件而改投其他陣線——導致陣線之間惡性競爭;同時,陣線們都太依賴領袖,比如達魯拉赫一死,他的陣線的整個帶有攻擊性的風格都改變得更中間派了,隨之而來是很多他的人退出陣線甚至退出塔利班。
巴拉達爾不斷嘗試「削藩」,試圖把所有其他的陣線都吸納進自己的麾下。比如,巴拉達爾和達魯拉赫非常不和,後者死後,他的大陣線一半人被併入了巴拉達爾的陣線。另一個陣線的領導人易卜拉欣死後,巴拉達爾不讓他的人繼承陣線,並掉了他的陣線。過程中動用了很多政治手腕,比如給易卜拉欣的人豐厚的職位,然後遊說巴基斯坦斷掉對這個陣線的援助,等等。有一個塔利班內部流傳的陰謀論認為,達魯拉赫的死是因為巴拉達爾派人當奸細報告給了美國人。是領導權鬥爭的結果。
巴拉達爾利用較為集中的權力,試圖聯繫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開啟和平進程,但很可能是因為這一點令他惹怒了巴基斯坦,他於2010年被巴基斯坦政府逮捕,直到多年後才獲釋參與和美國的談判。他的集權化嘗試因為他的被捕而失敗了。
與此大約同時,塔利班分出了「白沙瓦舒拉」。這是一個由阿富汗東部不受奎達舒拉節制的塔利班分子混合了阿富汗老軍閥希克馬蒂亞爾(Hekmatyar)的舊部組成的「第二中心」。他們一方面反對奎達舒拉強烈的南方普什圖人氛圍,另一方面爭搶巴基斯坦的支持。Giustozzi認為白沙瓦舒拉很快得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全力支持,因而得到了大量的資金援助,得以和奎達舒拉全面競爭。在2012年的時奎達舒拉已經位於下風。
雖然白沙瓦舒拉在2015年之後因為金援轉移而弱化,但今天回頭看,如今塔利班的很多制度和方向都和白沙瓦舒拉有所關聯。比如,白沙瓦舒拉重視阿富汗東北地區的多民族狀況。他們大量招募包括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在內的非普什圖人,也更願意提拔基層指揮官。他們在行政架構裏設置了專門處理NGO和公司事務的部門,用來吸引NGO和私人公司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比如向塔利班控制的村落提供飲水和基礎設施。更值得一提的是,Giustozzi指出,白沙瓦舒拉設立了類似憲兵的軍事行動部門(nizami massul)。這一部門的塔利班成員要求是受過教育,會識字,會撰寫報告的。他們要通過政治審查,成功入職後先調動到基層撰寫報告向上傳遞,之後慢慢成為白沙瓦舒拉在前線的傳令者,根據白沙瓦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策劃接受和貫徹指令。
白沙瓦舒拉和奎達舒拉的權力爭鬥在2014年之後慢慢減弱下去,奎達舒拉重新得勢。不過,這個過程中塔利班也經歷了巨大的內耗。白沙瓦舒拉試圖藉助奎達舒拉的軍事領導人扎克爾(Mullah Abdul Qayum Zakir)奪取奎達舒拉的權力。這助長了巴拉達爾被捕後,奎達舒拉內部扎克爾和曼蘇爾的兩個派系之間的爭鬥。雙方的競爭之激烈,甚至在2012年到2014年之間到了互相暗殺對方中層領導人的地步。鬥爭最終以曼蘇爾勝利告終。但曼蘇爾試圖成為塔利班最高領導人的過程也讓他得罪了包括前任領導人奧馬爾之子雅庫布(Mullah Yaqoob)和前領導人巴拉達爾在內的許多人。2015年的最高領導人選舉中,曼蘇爾被指責妄用死去的最高領導人奧馬爾的名義加強他個人的集權。最終曼蘇爾仍然上位成功,但也導致了不少人退出塔利班,不接受曼蘇爾的管轄。
通過《戰爭中的塔利班》的描述,我們會發現,把塔利班的組織截然分成「前線」和「後方」兩層,並且預設矛盾發生在「前線」和「後方」之間,可能是不太準確的。在塔利班的組織中,無論是後方還是前線,都有好多層平行交錯的關係和組織。其中的經濟援助和指揮關係都是多中心,彼此交疊的。
2016年5月,曼蘇爾死於美軍無人機空襲。他死後,沒人再嘗試徹底集權化塔利班,但是塔利班的很多軍事行動,確實也設置了協調和統一安排。Giustozzi認為,塔利班介於集權化和多中心化之間,儘管無法實現單一中心的組織架構,但也逐漸找到了適應多中心狀態的節奏。

塔利班將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
塔利班的上一次執政從1996年到2001年,以被美軍推翻告終。那時候的塔利班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沒有一個合格的政府,並且完全反對現代化。如今,20年過去,塔利班可能會如何在阿富汗執政?Giustozzi的研究令我們可以有機會從以下幾個角度觀察塔利班的動態。
首先,儘管《戰爭中的塔利班》中的數據來源和具體計算未必準確,但如今的塔利班嚴重依賴各方的援助,應該是站得住腳的一個推論。這意味着,今天的塔利班比當年的塔利班要更依賴「境外勢力」。《戰爭中的塔利班》認為塔利班的收入中,外國政府援助可以佔到50%以上,私人捐贈佔約10%,恐怖主義網絡提供了16%,而他們自己的税收約有10%。可以想像,在開始統治國家之後,收入困境依舊會困擾塔利班的選擇。況且腐敗也一定會發生。Giustozzi列舉了一些帶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比如,Badghis的前省長Mullah Lal Mohammad因挪用塔利班作戰人員的工資被解職;Faryab的省長Salahuddin從境外NGO那裏收取賄賂以允許他們在塔利班控制區做塔利班會不允許的項目,也因此被解職。
尤其是,重建後的阿富汗國家本身就高度依賴國際援助。那麼,塔利班的新政治是否也仍然是一種「援助政治」?是否意味着政策上要向外國資助者/援助者做妥協?比如,接受了伊朗的援助後,塔利班是否會對阿富汗國內的什葉派穆斯林更加温和?又比,如海灣國家如今推行一種混合伊斯蘭、資本主義和威權政治的社會統治模式,塔利班是否會在資助方的遊說下向這種模式「取經」?這句話的反面是,一旦外界資助變少,塔利班是否會轉向一種跟之前一樣封閉、一樣保守和殘酷的統治方式?
其次,塔利班如今並非一個集權的政治組織。這意味着內部有很多權力並非穩固。這幾天來,我們看到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Hamid Karzai)與和解委員會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既要去卡塔爾會見巴拉達爾,也要在阿富汗國內見哈卡尼。這兩次會見的人之間,在塔利班的架構下會有多少張力?此外,在接管政權的過程中顯然會出現更多的利益和職位糾紛,面對這些,塔利班是否會開始轉入內部鬥爭。一旦內部鬥爭再次開啟,外在的政策,如婦女地位,教育問題,國際關係,是否會面對極大的不確定性?之前的承諾是否隨時會被鬥爭撕碎?也許,掌握政權的時刻,才是塔利班真正開始自身「組織建設」探索的時刻。
更關鍵的是,塔利班並沒有在奪取政權的戰鬥過程中培養出新的經濟組織模式和社會管理模式。他們的整個社會基層基礎仍然和從前是一樣的:傳統社會,灰色貿易,境外資助。如果這些不改變,那麼塔利班的人事制度再有變化,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因為儘管城市顯示出了很不一樣的面貌,但塔利班仍然要面對那個傳統的阿富汗。
甚至,他們也一樣要遭遇阿富汗政府面對的問題——需要從境外要經濟援助,需要改善農村的糟糕處境,需要阻止官員的腐敗和社會的貧富差距,需要警惕農業減產和饑荒。




又介紹了一本好書!把塔利班剝開,看裡面的實際架構。為觀察阿富汗局勢提供了一個新角度。
把很少有人细读的学术书梳理的很细致,感谢分享。
相當優質的書籍推介,為阿富汗的政局帶來更多的視角,而塔利班也不再是現在輿論場里的人格化形象。